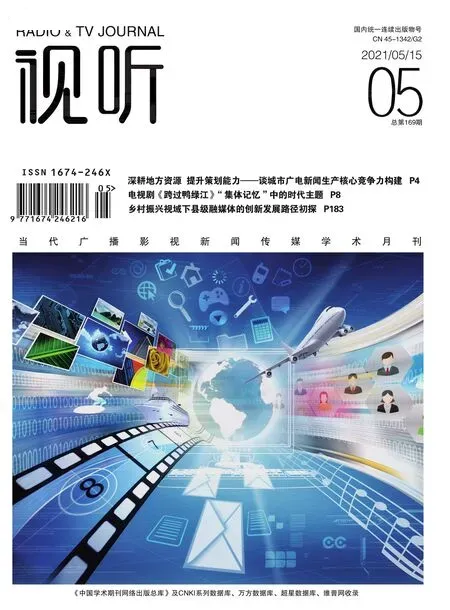建設性新聞何以興起——一種基于新聞本身的探討
□ 任陽
建設性新聞的概念來自西方,它不再執著于“壞事情才是好新聞”的負面和沖突的新聞報道框架,而是將報道框架集中于對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以積極且具有建設性的方式來建構新聞,從而激發受眾的積極情緒。
一、建設性新聞何以登上歷史舞臺
(一)心理—情緒視角
建設性新聞的理念原點在于它將受眾接受新聞的心理和情緒以及新聞本身對受眾的行為影響納入了學術視野,反思了新聞生產不應只把受眾看作是分散和原子化的個人,而應該充分考慮到受眾的心理和情緒以及受眾對于新聞的期待和需求。
新聞業的基本矛盾是有限的新聞對無限的世界進行呈現的矛盾,新聞對世界的反映本身不全面,而平淡無奇的事實變動往往缺乏新聞價值,所以“好新聞”青睞負面事件,但傳統的新聞報道框架對負面、沖突新聞過于關注的偏向日益受到詬病。對“童年的消逝”其實可以有另一層理解:兒童無憂無慮的原因之一是兒童尚未養成持續關注新聞的習慣,成年人痛苦則在于成年人不間斷地通過新聞觀察這個世界,天災人禍盡在眼前,加速了心理感知的不平衡與不安感。當一個人受洗于新聞的宗教中,他的童年期也就結束了,他轉變為一個和外界充分接觸的成年人。長期關注新聞或許會讓人的幸福感降低,更有可能讓讀者產生一種新聞鈍感,麻木于紛紜變化、晝夜不歇的新聞事實中。因此,當我們將受眾接受新聞的心理和情緒納入到研究視野中會發現傳統的新聞報道框架確實存在著天然的缺陷,建設性新聞的興起就是試圖彌合這種缺陷,將報道框架集中于對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以積極且具有建設性的方式來建構新聞,從而激發受眾接受新聞的積極情緒。
(二)新聞的結構與受眾的認知基模視角
建設性新聞所隱含的邏輯即新聞可以且需要“有所為”,而非僅僅滿足于客觀、真實的報道。工業社會發展起來的新聞業規范適應了當時的需要,但傳播生態的急劇變遷讓我們發現,基于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和標準而出產的新聞產品遠不完美,也并未做到讓“歷史終結”。從現代新聞業迄今為止的實踐來看,社會結構和現實情況愈發復雜,僅僅堅持客觀、真實、平衡等傳統原則的新聞報道并不足以完成為人類構建理性社會的任務,我們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業界亟需轉換新聞生產的理念與范式。
以污染—環保類新聞為例,我們對這類新聞的報道模式并不陌生,也看到過大量關于“居民長期舉報污染——記者前去采訪并致電環保部門——相關負責人推諉不作為——當地污染問題等待后續進展”的新聞,甚至這樣的新聞已然形成了某種定式。倘若找一百篇污染類的新聞并對其進行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我們可能會發現這些新聞基本上大同小異,不過是污染環境的地點和主角換了一下而已,整個新聞文本的敘述結構非常接近。盡管這種情況也有其他社會原因,不全是新聞框架的問題,但新聞界仍需對此反思,因為基于這種現象來看,新聞業大量的新聞實踐實質上是一種重復建設,讓受眾感到厭倦和抵觸。在筆者對他人有限的交流中發現,很多讀者表示自己常常會無視污染類新聞,對此類文本不再有閱讀的興趣,其原因集中在兩方面:“1.不看也知道這種新聞大概說什么,不愿助長消極情緒;2.這樣的新聞看了又能怎么樣?徒增內心無力感。”從這個角度看,在某些新聞框架下新聞的議程設置功能是無效和被消解的,大量議題的呈現只是默默存在,并未與社會和受眾產生共振并形成有效共鳴。因此,日夜轟鳴、從未間斷的新聞生產需要重新定位自身的社會功能與角色,以積極的方式報道負面事件才更有可能促進個人和社會的健康發展。
此外,“認知不協調”理論告訴我們,人會有意無意地給自己接觸到的各種外部信息提供一套讓自我滿意的解釋來達到一種暫時的平衡。如果新聞不改進報道理念和框架,那么無論是留守兒童話題還是報復社會的惡性事件,相同主題和敘事結構的新聞重復一千次可能受眾仍然會按照舊的基模去看待。建設性新聞就是期待打破這種情況,通過積極解決問題的導向,讓新聞產生新的信息增量,從而讓受眾形成新一輪的認知不平衡的沖突并再次嘗試協調以恢復平衡。而這個過程的實現也伴隨著受眾采取行動的可能,從而促進問題的解決并追求美好生活的到來。
套用社會學范式中存在著的“結構—行動”的二元視角,建設性新聞不再滿足于忠實地反映社會結構和外部環境的事實變化,而應該積極介入行動,反作用于社會結構。類似污染類新聞,建設性新聞要求媒體不再只反映“監管和違法之間的沖突”這種單一的基于沖突框架的模式,而應該賦權促進民眾參與,尋求問題解決。例如污染類新聞經常變成有頭無尾的斷尾式新聞,媒體就不能局限于對“此時、此地”污染的報道,而應該追求新聞敘事的時空更加寬廣,既報道當下,還要追溯過去、交待背景,還需探尋未來發展趨勢,保持對新聞事件持續和長期的追蹤。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報道可以變得更加有知識存量,向受眾提供豐富的價值信息,比如面對蠻橫的污染,如何合法、有效地舉報并保護自己不受傷害,如何求助于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公民自己具體可以做什么小事情來避免污染環境,讓受眾看到更豐富、更多元的事實與信息。
二、建設性新聞與民主和公共生活
新聞學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對“規范性”的研究,對實然的考察和對應然的想象是常常交織進行的兩條路徑,不僅探尋新聞是什么,還考察新聞的理想狀態與優化可能。建設性新聞就是對新聞業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的一次探索。我們今天提倡建設性新聞,原因之一是希冀建設性新聞為促進公共生活和理性提供一條新路徑,更好地培育我們對于民主生活的理解。新聞之所以可以勾連公共生活,是因為人們的世界觀建構在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和了解的基礎上,新聞的品質顯然對社會是否趨向良性發展有重要影響。作為現代信息形態的典型,新聞業在今天的使命和責任更為凸顯。畢竟,新聞背后的權力與控制,對受眾形成一種隱性的召喚,無形中讓每一位讀者都被“馴化”,我們被收編到新聞的邏輯和價值中。新聞如此強大的魔力必然要求我們不得不重視并持續探索新聞的理想形態。
我們參與其中的公共生活離不開新聞承擔一定的角色,而作為一種積極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的新聞實踐,建設性新聞是基于一種共情文明(Empathy)和同理心的新聞追求,這是其內在蘊含的精神脈絡。具體而言,建設性新聞強調共情的能力,意味著新聞媒體不再僅僅冷靜、漠然地反映每天上演的災難、沖突、矛盾,受眾也不再疏離于新聞里的人、事、物,而是以一種積極心理追求美好價值的實現。建設性新聞強調受眾的參與和對受眾的賦權,喚起讀者對周遭世界的關注和同情,讓讀者認為自己積極可為,而不是和新聞事件及其反映的問題平行永不交集或存在著有心無力的實踐鴻溝。在以往的新聞理念和新聞實踐下,受眾作為分散的個人即使看到反映社會負面問題的新聞可能也并不知道自己該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建設性新聞則提供方向,讓他們變得組織化和行動化。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導向而進行新聞報道的建設性新聞,既揭露問題,又關注解決方案,帶動讀者和社會各界采取行動。即便是負面新聞的報道也要讓受眾感受到可以依循和遵從的方向和典范,從而達到引領公共生活的作用。這種參與和賦權的過程,恰恰可以培育和磨練公民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建設性新聞對民主生活的促進具有廣闊的實踐前景。
三、結語
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在新聞業危機話語甚囂塵上的當下,建設性新聞的確為疏解新聞業的困境做出了可貴的努力和嘗試,連接了當下的實踐與未來的可能性,重塑了一種優化的新聞范式,為理解新聞學和新聞業提供了新的價值共識,讓我們對未來新聞業多了一些想象和展望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