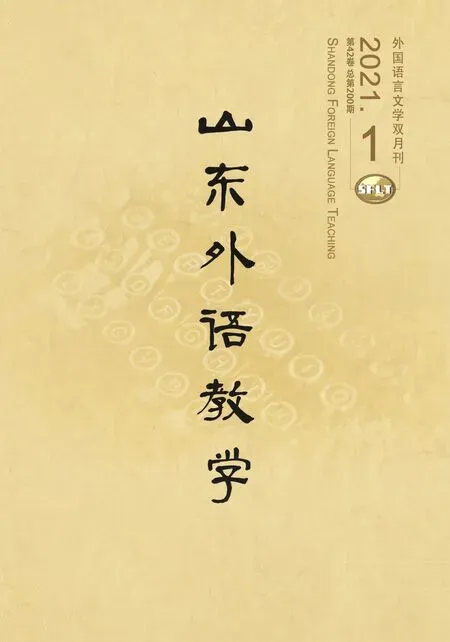論《強盜新郎》中的國家空間生產
劉智歡
(福建農林大學 國際學院, 福建 福州 350002;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3)
1.0 引言
在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1909-2001)的第一本小說《強盜新郎》(TheRobberBridegroom,1942)中,她將目光投向18世紀末位于美國西南邊疆的納奇茲(Natchez),別出心裁地將格林童話、希臘神話、圣經故事、南方民間傳說以及真實歷史人物等雜糅在一起,講述了白人種植園主、剪徑大盜以及印第安原住民之間的糾葛、沖突和對抗。不少評論家認為,韋爾蒂在這本小說中“模糊了歷史事實和虛構小說的界線”(Wilson,1993:64),表達了對美國民族神話的質疑,“嘲諷國家對自由主體性(free agency)的應許以及驅動西部擴張的資本主義欲望”(Trefzer,2007:24)。這些論述揭示出《強盜新郎》對國家歷史的批判式重寫,卻往往忽略了小說創作的時代語境。雖然《強盜新郎》寫于1940年,但其創作靈感來源于1936年韋爾蒂在新政機構工程進度管理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工作經歷。在此期間,她曾前往納奇茲采風,翻閱了許多與之相關的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創作出這部作品。在經濟大蕭條席卷美國、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肆虐的歷史背景下,韋爾蒂為何轉而書寫美國南方早期的拓殖歷史?她的民族神話“反敘事”隱含著怎樣的現實關切?本文從空間生產的視角出發,結合文本創作時期的歷史語境,解讀《強盜新郎》中納奇茲從荒野到城市的發展歷程,探究韋爾蒂對美國疆域變遷及其內蘊的政治張力的獨特書寫。
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認為“(社會)空間是(社會的)產物”(1991:26)。社會空間在人類社會實踐和生產過程中形成,反過來又影響、指導甚至重組生產實踐和社會關系。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空間(the space of the nation-state)的生產取決于具有“層級結構”的全國市場和“控制及利用市場資源或生產力的增長以維持和加強統治的政治力量”(Lefebvre,1991:112)。也就是說,國家空間是由統一的經濟結構和政治權力主宰的抽象空間。美國獨特的大陸擴張史,加之資本主義在地理上的不平衡發展屬性意味著美國的國家空間生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沖突的漫長過程。國家空間的生產與民族身份的形塑密不可分。如果說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安德森,2016:6),那么正是在生產方式和權力結構以商業活動、地圖測繪、社會制度、法律政令以及文化觀念等形式將特定的領土疆域不斷組織整合為同質化空間的過程中,共同的民族意識和身份認同才得以確立。在《強盜新郎》中,韋爾蒂以文學想象還原了美國早期領域性空間的生產過程,消解了國家敘事中“南方/美國”的二元對立,揭示出南方實際上是美國的一面鏡子,折射出美國擴張主義領土實踐中的種族沖突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排外性民族身份認同。
2.0 種植園南方與美國資本主義發展
在美國的國家建構工程中,南方一直扮演著“內部他者”(internal other)的角色(Greeson,2010:1)。早在殖民地時期,南方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種植園農業經濟就使之走上了不同于新英格蘭的發展道路。從18世紀開始,奴隸制、種族主義、貧窮、暴力、偏狹以及仇外等成為南方地域文化的標簽,將這一地區與標榜自由、民主、平等、富裕的美國區分開來。用詹妮弗·格雷森(Jennifer Greeson)的話來說,南方“將國家理念和國家現實之間的差距空間化”,“這樣我們就可以把美國生活中的道德缺陷描繪成地理問題”(Greeson,2010:4)。到了20世紀30年代,南方的貧困落后、種族隔離以及政治保守主義日益被視為對國家理念和價值體系的威脅。羅斯福總統在1938年的國情咨文中稱南方為“全國第一號經濟問題”(Duck,2006:74)。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開始注意到南方白人至上的社會政治秩序與法西斯政權特別是納粹德國的相似之處。對美國其他地區而言,除去內戰前的幾年,南方從未顯得如此“格格不入、極具威脅以及充滿危險”(Brinkmeyer, 2009: 4)。主流敘事將南方描述為“具有顯著文化他異性(alterity)的場所”,一方面以“落后的南方”意象反襯出美國的民主傳統,另一方面則繼續“將種族等級制度編碼為地域特征”進而不加干涉(Duck,2006:14)。韋爾蒂的空間書寫破除了國家敘事中南方作為“內部他者”的迷思,探究了種植園南方與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復雜關聯,呈現出南方“地理空間的政治屬性”(Jarvis,1998:52)。
在《強盜新郎》中,18世紀末的納奇茲正處于從混亂無序的異質性荒涼邊疆轉變成為同質性美國領土空間的過程之中,具有明顯的閾限性①。雖然納奇茲即將被納入美國版圖,但“國家政府的規章制度、民族文化、法律政令等并不能隨即自動彌漫至國家新增領土,邊疆空間的‘領域性’(territoriality)需要通過多維度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實踐得以確立”(郭巍,2017:84)。當早期的拓荒者來到此地開疆辟土時,他們就將新的經濟政治結構引入舊有的地理空間,促進了邊疆的“領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小說中種植園主克萊門特的發家史即是一部微觀的國家空間生產史。他拖家帶口從弗吉尼亞長途跋涉、一路南下來到納奇茲,卻不幸成為印第安人的俘虜。劫后余生的克萊門特攜女兒羅莎蒙德與同樣家破人亡的莎洛姆重新組建家庭,造屋葺舍,將荒蠻之地改造為宜居之所。他們一開始在森林中搭建小木屋聊以安身,但很快就“新增了精美的臥室,墻上掛著一面鏡子,臥室后面有獨立的儲藏室,房子后面是帶有大爐子的廚房,廚房后面是小豬圈,里面有一頭新買的小豬。它后面的樹上栓著一頭新買的牛”(Welty,1998:14)。然而,篳路藍縷開拓荒野的并非克萊門特一家,而是他們購買的黑人奴隸。羅莎蒙德在抱怨繼母莎洛姆的刁難時,透露出家里的奴隸承擔了主要的勞作,“奴隸天天都擠牛奶,為什么不讓他們去做”(Welty,1998:31)。可見,作為早期的拓荒者,克萊門特帶到邊疆的除了積累土地和財富的欲望,還有基于奴隸制的生產模式。
克萊門特在納奇茲發展奴隸制種植園,離不開新興的美利堅共和國對奴隸制擴張的支持。建國初期的美國尚未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加上缺乏強大的聯邦政府,新增的領土往往成為潛在的分裂因素。其他國家的虎視眈眈、印第安人的拒絕遷徙以及西部殖民者的謀求獨立都威脅著國家的統一。為了團結南北的政治家,建立起全國性政治聯盟,聯邦政府違背了《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國準則,支持奴隸制在西南邊疆的擴張(Baptist,2014:35)。雖然克萊門特閉口不談他來納奇茲的動機,但驅使他南下拓荒的少不了國家政策對奴隸制的扶持。小說伊始,克萊門特剛從新奧爾良歸來,把種植的煙草“以不錯的價格賣給了國王的人”(Welty,1998:3)②。他的交易能夠順利進行也許要得益于美國與西班牙簽訂的協議,允許農場主把經濟作物和其他商品通過新奧爾良港口運往世界市場(Baptist,2014:40)。克萊門特先后種植過煙草和靛青,但棉花是他發家致富的關鍵。用他的話來說,有一年莎洛姆“讓我試著種棉花,然后我就發財了”(Welty,1998:15)。美國南方擁有棉花種植所需要的自然環境,包括肥沃的土壤和適宜的溫度及降水。1793年軋棉機的發明大大提升了棉花加工效率,植棉業發展迅速。為了賺取盡可能多的利潤,種植園主開始擴大奴隸貿易。雖然1783年到1888年間禁止國際奴隸貿易,大約有17萬名黑人奴隸仍然被運輸至美國(貝克特,2019:102)。盡管我們對克萊門特如何購買、壓榨奴隸不得而知,僅僅知道他“派新來的奴隸帶著斧頭去砍伐更多的樹木”(Welty,1998:14),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一望無際的田地和不斷擴建的種植園大宅都是強制奴隸勞役而生產的空間。可以說,南方的奴隸制種植園是在美國初創時期的拓殖領土實踐中興起的。
反過來,奴隸制種植園經濟也加快了國家邊界向西推進和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由于棉花種植容易耗盡地力,種植園主不斷向西和向南擴張,形成了包括南卡羅來納、佐治亞、阿拉巴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肯色以及德克薩斯部分地區在內的棉花種植帶,建立起南方的“棉花帝國”(Dattel,2009:42)。到了19世紀中葉,納奇茲已從荒涼的邊疆發展成為全國最為重要的城市之一。全美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百萬富翁居住在此,興建的種植園大宅超過四十多棟(Bethea,2001:36)。美國日漸成為全球棉花市場的主要供應商。在19世紀初,南方的種植園主主宰了英國市場,到了19世紀30年代,他們還占領了新興的歐洲大陸和北美市場(貝克特,2019:109-110)。雖然美國歷史敘事把奴隸制視為南方特有的罪惡,但奴隸制種植園經濟為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積累了原始資本,推動了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使之在19世紀能與歐洲分庭抗禮,成為國際制造和貿易的中心(Romine & Greeson,2016:36)。正如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所言,“美國經濟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礎上,也是建立在奴隸制的脊背上的”(貝克特,2019:110)。
韋爾蒂運用“時代誤植”(anachronism)的寫作手法來彰顯奴隸制種植園經濟在美利堅帝國崛起中的重要作用。克萊門特的妻子莎洛姆和他一樣貪婪無度,是“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化身”(Trefzer,2007:139)。除了野心勃勃地計劃把靛藍、棉花和煙草的種植面積都翻一番,她還打算建造恢弘氣派的種植園大宅,“起碼五層樓高,頂部有觀河的瞭望臺,還有二十二根科林斯柱子承托著屋檐”③。莎洛姆夢想中的豪宅實際上是竣工于1861年的溫莎宅邸(Windsor Mansion)。作為密西西比州占地面積最大(約1052公頃)的種植園大宅,溫莎宅邸是南方種植園制度全盛時期的空間表征。韋爾蒂把象征著奴隸制經濟社會制度的種植園大宅設置為早期拓荒者為之奮斗的目標,暗示了奴隸制并非南方特有的原罪,而是國家擴張性的領土實踐和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作用于南方自然環境的結果。她也借由時代錯置影射了歷史和現實的交疊之處:如果說建國初期的領土擴張和經濟發展是以犧牲黑人的基本權利為代價,那么30年代的新政在重新整合國家空間,把南方納入美國的經濟政治軌道時,再次忽視了非裔美國人對平等公民權利的訴求。為了實現經濟復興的目標,聯邦政府容忍了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以換取南方種族主義統治者對改革舉措的支持(卡茨尼爾森,2018:19)。其結果就是,新政沒有改變黑人的二等公民境遇:到1938年,非裔美國人獲得選舉權的比例不足4%(卡茨尼爾森,2018:16)。韋爾蒂在新政機構工作期間走訪了密西西比州的各個鄉鎮,對深陷貧窮和種族歧視的底層黑人民眾抱有深切的同情,并且以攝影的方式記錄了他們的尊嚴和抗爭。《強盜新郎》中雖然沒有對奴隸生活的細致描摹,但韋爾蒂通過對歷史的巧妙拼接批判了美國社會對黑人長期的系統性歧視和迫害。
3.0 邊疆空間的馴化與民族身份建構
除了建立統一的經濟政治結構,國家空間的生產也是在劃定的領土邊界內形塑共同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認同的過程。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特納(Frederick Turner)的邊疆學說就點出了國家空間生產與民族品性鍛造之間的關系,“那片自由的土地滋養著個人主義、經濟平等及自由民主的上升空間”(1920:259)。從1776年建國以來,美國一直處于向外擴張的狀態。因此,美利堅民族身份的建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方面要求共同體成員產生同一性的想象,另一方面也需要對進入國家空間的異族分子進行監管、馴服或清除、驅逐。阿巴拉契亞山脈和密西西比河之間的大部分土地原本是印第安部落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園(何順果,1992:82)。18世紀末,為了將這片土地收歸國有進行有效的統治,美國國會頒布法令,取消印第安人對部落領地的自然權利,將之作為“自由土地”供移民定居開發,強迫原住民搬到政府劃定的保留地去。為了把驅逐印第安人的行為合理化,主流話語不僅將他們的部落領地描述為荒無人煙的處女地,而且把印第安人妖魔化為野蠻暴戾的種族,鼓吹他們的滅絕就像季節更迭一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克萊門特在回憶自己被俘的經歷時,就重復了囚擄敘事中認為印第安人“代表了人性墮落全部特點的野蠻人和魔鬼”的論調(金莉,2018:92)。他表示“印第安人知道自己大限已至……這讓他們變得無限放蕩兇殘”(Welty,1998:12)。正是在這樣的話語邏輯支配下,像克萊門特一樣的早期殖民者打著馴化邊疆空間的旗號大肆侵占原住民的土地,把他們放逐至國家空間的邊緣地帶。
韋爾蒂把小說設置在以印第安納奇茲部落命名的地方,這一選擇本身就駁斥了原住民在美利堅國家空間生產中毫無貢獻的成見。不僅如此,她也再次以錯置歷史的方式譴責了國家版圖拓展背后的種族清除。早在1729年,納奇茲部落就遭到法國殖民者的屠戮而幾近滅族,為數不多的幸存者或被當作奴隸販賣,或加入其它印第安部落而漸被同化(Trefzer,2007:125)。韋爾蒂復活了納奇茲印第安人,又讓他們再次湮沒在邊疆開發的過程中,旨在揭露帝國主義殖民擴張中一以貫之的種族暴力,戳穿美國例外論的歷史敘事中諸如“新世界”“大西部”“追求幸福”等謊言(Thorton,2003:55)。《強盜新郎》中最血腥的場景莫過于以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土匪威利·哈普(Wiley Harpe)為原型的強盜小哈普對一位印第安少女施加暴行。無惡不作的小哈普意欲取代小說同名主人公吉米·洛克哈特的頭目地位,趁他外出之際來到強盜們的巢穴發動叛亂。他企圖侵犯吉米的新娘來彰顯自己的權力,卻誤將被劫掠來的印第安少女當作羅莎蒙德,當眾剁掉她的無名指并凌辱了她。和同名的格林童話相比,韋爾蒂不僅把施暴者從強盜新郎替換成美國南方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也把受害者改為印第安少女④。正如韋爾蒂在《納奇茲小徑的童話故事》(“Fairy Tale of the Natchez Trace”)一文中所言,她的改寫凸顯出“歷史講述的事情比童話更為可怕”(1990:309)。就像小哈普借由殺害印第安少女獲得在強盜團伙中的主導地位,白人殖民者通過驅逐原住民掌握了國家空間的統治權,進而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的社會等級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30年代見證了美國對印第安文化的重新發掘。新政時期,聯邦政府資助的考古活動對南方的印第安遺跡進行了大規模的挖掘開采,出土了墳堆、洞穴、村落以及大量的人工制品等(Trefzer,2007:1)。1938年,政府撥款修建了納奇茲小徑公路(Natchez Trace Parkway)。國家公園管理局在公路邊豎立的告示牌上寫道,“在你背后的公路是舊納奇茲小徑的一部分——這條荒野之路最初是西南地區的印第安部落使用的一系列小路。納奇茲小徑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軍事方面對美國早期的發展都極為重要。”⑤納奇茲小徑作為印第安遺址被納入美國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成為國家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但這并不意味著印第安人被接納為“美國”這一想象共同體的成員。考古更多體現的是“帝國懷舊”(imperialist nostalgia)的心態,即“殖民者對被他們摧毀或改變的生活方式的向往”(hooks,1992:189),以展現帝國文明的包容和進步。但印第安人在現代美國社會依然是被邊緣化的群體。當時的好萊塢電影往往用怪異的語言和奇特的身體姿勢來表征印第安人,強化他們“在語言上甚至智力上都是有缺陷的,充其量就是不合時宜的群體,注定會不復存在”的種族主義成見(Kilpatrick, 1999: 38)。美國的國家建構工程一方面利用印第安文明重構美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將美國歷史往前推進了幾個世紀,另一方面則以“消失的種族”話語割斷現存印第安人和古印第安文明之間的紐帶,淡化他們在美國空間生產中的作用。
在《強盜新郎》中,韋爾蒂不僅嘲諷了主流敘事中的印第安人刻板印象,也通過書寫人物身份的轉變揭秘了民族身份建構對印第安人的利用。她以局部代替整體的提喻(synecdoche)修辭手法來刻畫白人殖民者眼中的印第安人:當克萊門特被俘時,“一只紅皮膚的手拽著他站了起來,他直視那雙世故的圓眼”(Welty,1998:69);復仇的印第安人在林中發現小哈普時,透過樹木看著他的臉“是紅皮膚的,裹著羽毛,眉頭緊皺”(Welty,1998:70)。這些更像是出現在迪士尼動畫片中的形象而非真實的歷史人物(Kreyling,1998:5)。小說對印第安人的夸張表征與印第安少女的悲慘遭遇形成了鮮明對比,讓讀者得以窺見被種族刻板印象所遮蔽的原住民血淚史。此外,小說中的白人人物在將印第安人他者化的過程中確認自己的美利堅共和國公民身份。與邊疆空間的閾限性相對應的是身份的不確定性。《強盜新郎》的人物大多具有雙重身份(double identity),比如克萊門特和莎洛姆既是不畏艱苦、開疆辟土的拓荒者,也是貪得無厭、追逐利益的種植園主。而最具戲劇張力的雙重身份當屬吉米·洛克哈特:他既是行俠仗義、拯救克萊門特性命的紳士,也是為非作歹、奪走羅莎蒙德貞潔的強盜。外出打劫時,吉米用漿果汁把臉涂黑,而需要以紳士面目示人時,則把偽裝卸掉,“像太陽一樣發出光芒,整潔、年輕、睿智、樂觀”(Welty,1998:34)。有論者指出,吉米的偽裝“呈現出早期殖民者刻板印象中美洲原住民顯著的暴戾特征”(Merricks,2005:7)。換言之,吉米借由“扮黑臉”來操演所謂的“印第安性”,把肆無忌憚的燒殺劫掠行為加以種族化。他的行徑不禁讓人聯想到興起于19世紀美國南方的“黑面表演”(blackface minstrelsy),即白人裝扮成黑人,模仿他們的口音和舉止進行音樂或舞蹈表演。這種表演是“白人憑借當時的種族政治和文化優勢對黑人文化的肆意挪用,其目的就是消遣、貶低美國黑人,以達到‘他者化’黑人族群的初衷”(王卓,2016:13)。同樣地,吉米也是通過操演程式化的特征來強化種族成見,為屠殺印第安人尋找正當的借口。他帶回家的戰利品中就有“克里克人的頭皮”(Welty,1998:43)。吉米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后,他就徹底放棄了強盜的營生,搖身一變成為受人尊敬的紳士。他是通過把原住民塑造為嗜血成性的民族他者來完成身份變化的。
和吉米相比,羅莎蒙德獲得美國人這一身份的過程更為曲折。在美國建國初期,女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極為低下。她們沒有選舉權,也沒有擁有土地及繼承財產的權利,只能以“女兒”“妻子”等附屬性的身份確立自己的社會角色(王恩銘,2002:4)。羅莎蒙德和受害的印第安少女一樣都是種族主義父權制社會的他者。因此,當繼母莎洛姆責罵她時,羅莎蒙德只能“帶著印第安野蠻人的安靜神色接受毆打和虐待”(Welty,1998:33)。在目睹小哈普施暴時,藏在房間角落的羅莎蒙德甚至短暫地和那位不幸的印第安少女產生了強烈的共情,“幾乎要以為她是在強盜們的注視下站在屋子中間而不是躲在桶背后”(Welty,1998:63)。然而,在意識到自己也可能面臨類似的命運后,羅莎蒙德選擇了與種族主義父權制結成同謀。她揭開吉米的偽裝,推動了他的身份轉變,并最終和他在新奧爾良成家立業;他們坐擁的湖畔豪宅是其成功實現美國夢的標志。韋爾蒂改寫了格林童話,給《強盜新郎》安排了一個看似光明的結局。克萊門特一家從荒野到城市、從種植園主到商人的生活軌跡對應著美利堅共和國的發展路徑。然而,細察之下,這一幸福美滿的結局卻有著“令人驚訝的黑暗輪廓”(Pollack,1990:22)。畢竟,無論是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轉變還是國家的迅速崛起都離不開對民族他者的塑造、踐踏及驅逐。
4.0 結語
在《納奇茲小徑的童話故事》一文中,韋爾蒂寫道,“歷史和童話故事的界線并不總是清晰的,正如《強盜新郎》一直指出的那樣”(1990:309)。她通過文體雜糅再現了美國初創時期風云激蕩、充滿張力的國家空間生產過程,修正了國家歷史敘述,解構了“南方/美國”的二元對立。韋爾蒂的用意并非在于替南方免除種族主義的指責,而是借古喻今,提醒讀者注意美國社會中持續并廣泛存在的種族問題和民族身份形構中的排外傾向。作為初出茅廬的南方作家,她沒有被當時的愛國主義思潮所裹挾一味贊美美國的榮光或哀嘆南方的怪誕,而是以獨立之姿反思了“現代世界中民族主義的性質及意義”(Ladd,2001:156)。此外,她也以文學想象的方式肯定了種族他者的空間實踐對北美大陸的發展起到的重要作用,確認了他們作為美利堅民族成員的身份。在這個意義上,韋爾蒂在這個看似輕松愉快的故事中書寫了另類的美國歷史。
注釋:
① 在18世紀末,密西西比仍在西班牙的管轄之下。1798年3月30日,美國和西班牙簽訂的《圣洛倫佐約》(TheTreatyofSanLorenzo)生效,密西西比州成為美國的領地。1817年密西西比州正式成立。
② 此處“國王的人”(the King’s men)指的是西班牙在納奇茲的殖民勢力。
③ 科林斯式圓柱(Corinthian column)源于古希臘,是古典建筑的一種柱式。柱頭用莨苕作裝飾,形似盛滿花草的花籃。科林斯柱式是希臘復興式建筑(Greek Revival Architecture)的特征之一,而希臘復興式建筑是19世紀美國南方流行的種植園大宅建筑樣式(Bonner & Pennington,2013:6)。
④ 在格林童話的《強盜新郎》中,磨坊主的女兒和她的追求者訂了婚。有一天她漫步至未婚夫在林中的屋子,卻驚恐地發現他的真正身份是強盜。磨坊主的女兒躲在屋子角落的木桶背后,目睹了強盜們殘忍地將一位劫來的姑娘折磨致死。她被剁下來的手指連同上面的戒指一起飛到了磨坊主女兒的懷中。在婚禮上,磨坊主的女兒當眾出示了這枚戒指,揭露了新郎的暴行,成功地將他繩之以法(Pollack,1990:15)。
⑤ 關于納奇茲小徑公園的介紹,參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chez_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