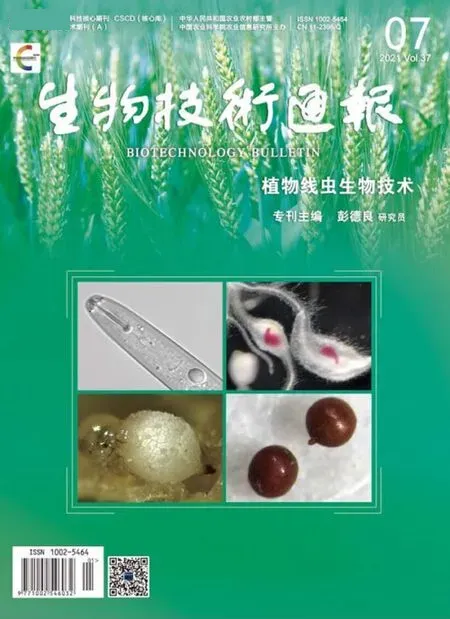腐爛莖線蟲(Ditylenchus destructor Thorne,1945)生物學(xué)研究進(jìn)展
趙洪海 梁晨 張?jiān)?段方猛 宋雯雯 史倩倩 黃文坤 彭德良
(1. 青島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植物醫(yī)學(xué)學(xué)院 山東省植物病蟲害綜合防控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青島 266109;2. 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植物保護(hù)研究所 植物病蟲害生物學(xué)國(guó)家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北京 100193)
腐爛莖線蟲(Ditylenchus destructorThorne,1945),英文通用名譯為馬鈴薯腐爛線蟲、塊莖腐爛線蟲或馬鈴薯塊莖線蟲[1-4],在我國(guó)又被稱作馬鈴薯腐爛莖線蟲、甘薯腐爛線蟲、馬鈴薯莖線蟲等[5-8],在動(dòng)物界的分類地位是:線蟲門(Nematoda)、色矛綱(Chromadorea)、色矛亞綱(Chromadoria)、小桿目(Rhabditida)、墊刃亞目(Tylenchina)、墊刃下目(Tylenchomorpha)、宮外翻總科(Sphaerularioidea)、粒科(Anguinidae)、莖線蟲屬(Ditylenchus)[9-10]。莖線蟲屬由Filipjev(1936)建立,是植物線蟲中最復(fù)雜且種類鑒定最困難的屬之一[2,11-13],雖有近200個(gè)名義種已被描述,但約半數(shù)被后來的學(xué)者視為無效種,目前有效種約有90種,具體數(shù)量尚難確定[11-14]。該屬多數(shù)種類是食真菌性的,部分為高等植物的寄生物,其中腐爛莖線蟲、起絨草莖線蟲[D. dipsaci(Kuhn,1857)Filipjev,1936]、水稻莖線蟲[D. angustus(Butler,1913)Filipjev,1936]和非洲莖線蟲(D. africanusWendt et al.,1995)等為農(nóng)業(yè)上的重要有害生物[2-3]。
腐爛莖線蟲與起絨草莖線蟲和非洲莖線蟲均存在派生關(guān)系[1,15]。起絨草莖線蟲最早由Kuhn(1957)在德國(guó)起絨草(Dipsacus fullonum)上發(fā)現(xiàn),是莖線蟲屬的模式種和一個(gè)極其復(fù)雜的復(fù)合種[2,4,16-17];與腐爛莖線蟲相關(guān)的最早記載,可以追溯到1888年Kuhn在德國(guó)對(duì)馬鈴薯塊莖腐爛病(“Wurmfaule”)的描述,該病病原在1945年之前一直被認(rèn)為是起絨草莖線蟲[1,18-20];但1945年Thorne[1]對(duì)發(fā)生在美國(guó)愛達(dá)荷州侵染馬鈴薯的莖線蟲群體進(jìn)行形態(tài)比較之后,將其鑒定為不同于起絨草莖線蟲的一個(gè)新種,即腐爛莖線蟲。1988年,Jones 和 De Waele[21]在南非發(fā)現(xiàn)“腐爛莖線蟲”侵染花生果莢和種子,之后幾年中,南非花生上“腐爛莖線蟲”群體的侵染特點(diǎn)、寄主范圍和發(fā)育溫度等得到廣泛研究[22-27];但1995年Wendt等[15]基于形態(tài)學(xué)和rDNA的RFLPs特征,將侵染南非花生的莖線蟲鑒定為不同于腐爛莖線蟲的一個(gè)新種,即非洲莖線蟲。因此,早期記載的侵染馬鈴薯的起絨草莖線蟲可能是腐爛莖線蟲,而南非花生上“腐爛莖線蟲”的生物學(xué)不適用于腐爛莖線蟲。
腐爛莖線蟲在世界范圍內(nèi)主要為害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甘薯(Ipomoea batatas)、大蒜(Allium sativum)等作物[3-4]。二十世紀(jì)50到70年 代,腐爛莖線蟲是歐洲和美國(guó)馬鈴薯上的重要有害生物,之后約30年中除對(duì)中國(guó)甘薯和日本大蒜的危害之外鮮有報(bào)道,但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后在愛沙尼亞等地又重新成為大問題[3,28-30],在我國(guó)也開始出現(xiàn)為害馬鈴薯的情況[7,31-33]。腐爛莖線蟲是我國(guó)甘薯上最具毀滅性有害生物之一,造成毀種絕收時(shí)有發(fā)生,被列為全國(guó)農(nóng)業(yè)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34-37]。腐爛莖線蟲一直是日本大蒜上的重要病害[38-40],在我國(guó)大蒜上也存在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33]。腐爛莖線蟲在馬鈴薯田持續(xù)存活性問題不甚明確[19,29,41-44],它對(duì)不同作物的侵染危害表現(xiàn)也存在差異。據(jù)此,本文對(duì)腐爛莖線蟲的地理分布、寄主范圍、生殖發(fā)育、侵染循環(huán)、環(huán)境適應(yīng)和存活致病相關(guān)機(jī)制等進(jìn)行綜述,旨在為腐爛莖線蟲的研究及其監(jiān)測(cè)預(yù)警和有效防控提供見解思路和有用參考。
1 腐爛莖線蟲的地理分布
腐爛莖線蟲在世界上主要分布在溫帶地區(qū),目前發(fā)生在5大洲的42個(gè)國(guó)家,包括歐洲的德國(guó)、愛沙尼亞、白俄羅斯等27個(gè)國(guó)家,北美洲的美國(guó)、加拿大和墨西哥,亞洲的中國(guó)、日本、韓國(guó)、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大洋洲的新西蘭和非洲的南非[3,45-46]。在歐洲和北美洲主要為害馬鈴薯,在中國(guó)主要為害甘薯,在日本主要為害大蒜,在南非有侵染觀賞植物蛇鞭菊(Liatris spicata)的記 載[3-4]。腐爛莖線蟲被53個(gè)國(guó)家列為限定性有害生物[47],在澳大利亞被評(píng)估為5種最高生物安全風(fēng)險(xiǎn)植物線蟲之一[48],目前被20多個(gè)國(guó)家和植物保護(hù)組織(如APPPC、EU、PPPO)列為檢疫性有害生物[45]。腐爛莖線蟲被我國(guó)列為進(jìn)境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和全國(guó)農(nóng)業(yè)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8,49]。根據(jù)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的數(shù)據(jù),腐爛莖線蟲在我國(guó)的分布行政區(qū)為北京、河北、內(nèi)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安徽、山東、河南、陜西等10個(gè)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73個(gè)縣(市、區(qū))[50],在江蘇、甘肅、山西等省也有發(fā)生的記載[36,51-53]。腐爛莖線蟲在我國(guó)的河南、山東、河北、安徽等省發(fā)生危害面積較大,主要為害甘薯,其次是馬鈴薯和當(dāng)歸(Angelica sinensis)[37,52,54]。
2 腐爛莖線蟲的寄主范圍
腐爛莖線蟲是高等植物的專性寄生物,除侵染植物外,還能取食真菌菌絲體,擁有植物和真菌兩類寄主。
2.1 植物寄主
腐爛莖線蟲可以侵染的作物和雜草種類遠(yuǎn)遠(yuǎn)超過100種,在農(nóng)林生產(chǎn)上受侵害較重的主要是塊莖、鱗莖/球莖、塊根和肉質(zhì)直根類作物[3,29],包括馬鈴薯、甘薯、大蒜、當(dāng)歸、胡蘿卜(Daucus carota)、甜 菜(Beta vulgaris)、啤酒花(Humulus lupulus)、西洋參(Panax quinquefolium)、鱗莖鳶尾(Irisspp.)、大麗花(Dahliaspp.)等[4,55-56]。比較重要或報(bào)道較多的雜草寄主有田野薄荷(Mentha arvensis)、苣荬菜(Sonchus arvensis)、沼生水蘇(Stachys palustris)、大車前(Plantago major)、酸模(Rumexspp.)等,其中田野薄荷尤其重要[41,56]。遺憾的是,除馬鈴薯、甘薯、大蒜、鱗莖鳶尾、當(dāng)歸、甜菜、田野薄荷等10余種植物因支持腐爛莖線蟲大量繁殖而被普遍認(rèn)為是適合寄主外,其他“寄主植物”被記載為寄主,大多是基于腐爛莖線蟲在其體內(nèi)發(fā)生的定性觀察,缺乏鑒定寄主適合性的線蟲繁殖系數(shù)等數(shù)據(jù)信息[57-58],也存在已記載寄主(如苣荬菜)不被侵染的報(bào)道[57]。因此,腐爛莖線蟲的植物寄主范圍是不完全的,而一些已記載寄主的適合性尚需進(jìn)一步明確[19,29,44]。我國(guó)幅員遼闊,農(nóng)田雜草種類繁多,但有關(guān)腐爛莖線蟲雜草寄主的調(diào)查研究鮮有報(bào)道。
2.2 真菌寄主
腐爛莖線蟲可以在70多種真菌上生長(zhǎng)繁殖,主要的真菌寄主有尖孢鐮刀菌(Fusarium oxysporum)、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青霉菌(Penicilliumspp.)、立枯絲核菌(Rhizoctonia solani)、印度毛殼(Chaetomium indicum)、綠色木霉(Trichoderma viride)、毛霉(Mucorspp.)等[2,4,19,59],它可以取食香菇的菌絲體而引起香菇病害[60]。腐爛莖線蟲在有真菌共存時(shí)群體常常增殖迅速,而在貯藏期它對(duì)馬鈴薯、大蒜等危害的加重,與真菌的二次侵染密切相關(guān)[61-63]。某些真菌菌劑對(duì)腐爛莖線蟲的生物防治出現(xiàn)失敗,可能與該線蟲的食真菌習(xí)性有關(guān)[64]。
3 腐爛莖線蟲的生殖發(fā)育
腐爛莖線蟲為雌雄異體,兩性生殖,具有一套2n為44-48的染色體[16],蟲態(tài)分為卵、1-4齡幼蟲和成蟲(雌蟲和雄蟲)。雌蟲繁殖力強(qiáng),每頭產(chǎn)卵多達(dá)250個(gè)[65]。最后一次蛻皮之后,雌蟲的性接受期約為1周,而雄蟲保持交配能力至少3周。每24 h年輕雌蟲通常產(chǎn)6個(gè)未分裂卵,最多12個(gè),而較老雌蟲僅產(chǎn)1-2個(gè),其體內(nèi)偶爾存在已經(jīng)發(fā)生卵裂和胚胎發(fā)育的卵。從第一次卵裂到1齡幼蟲發(fā)育完成約需48 h,2齡幼蟲從形成到破殼孵出約需3 d,在3齡幼蟲期即可辨別其性別[66-67]。4齡幼蟲蛻皮初期,新口針起源于位于原口針基桿處以3個(gè)角質(zhì)化環(huán)為標(biāo)志的原基區(qū),而不是墊刃線蟲中通常的起源部位—口腔壁[67]。
在已報(bào)道的雜交試驗(yàn)中,腐爛莖線蟲不同寄主和地理來源的群體間雜交產(chǎn)生可育的后代,但與起絨草莖線蟲或食真菌莖線蟲(D. myceliophagus)存在生殖隔離[16,68-70]。
4 腐爛莖線蟲的侵染循環(huán)
腐爛莖線蟲是植物遷移性內(nèi)寄生線蟲,其侵染循環(huán)涉及線蟲的存活、侵入擴(kuò)展、傳播擴(kuò)散等環(huán)節(jié)。
4.1 存活和初侵染源
腐爛莖線蟲需要存活(包括越冬、越夏)來渡過田間沒有作物寄主的時(shí)期,為新的侵染保存和提供接種體。腐爛莖線蟲可以通過成蟲、幼蟲或卵在土壤、糞肥中或多年生雜草地下組織內(nèi)越冬,通過取食雜草寄主或可能的土壤真菌而以寄生方式存活[71-72]; 受侵染的馬鈴薯塊莖、甘薯塊根、大蒜和鳶尾鱗莖等,是極其重要的存活越冬場(chǎng)所[29,36,39,73]。 盡管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土壤棲息真菌對(duì)腐爛莖線蟲的存活和消長(zhǎng)有影響,但是缺乏該線蟲在土壤中取食利用真菌的直接證據(jù)[29,64]。
腐爛莖線蟲主要依賴寄主植物在土壤中生長(zhǎng)繁殖,因其不能像起絨草莖線蟲那樣形成“線蟲絨”而進(jìn)入自我保護(hù)的低濕隱生狀態(tài),在田間缺少寄主植物的情況下,它在土壤中能否長(zhǎng)期持續(xù)存活是個(gè)倍受關(guān)注的問題,但已有研究的結(jié)果不太一致,原因不夠明確[28-29,41-44]。田間沒有寄主植物的情況下,有研究認(rèn)為土壤中腐爛莖線蟲可持續(xù)生存3年[29],MacGuidwin等[44]報(bào)道線蟲可存活至少6周。受植物寄主和可能存在的真菌寄主的可利用性、土壤條件、拮抗生物、氣候條件等多因素影響,腐爛莖線蟲的存活期限無法準(zhǔn)確判定,但它可能在農(nóng)田土壤中以低群體密度水平長(zhǎng)期存在,而低密度群體通常造不成可察覺的作物損害[29]。馬鈴薯連續(xù)數(shù)年種植和正常收獲模式下,存在腐爛莖線蟲逐年消減而不能在田間持續(xù)存在的現(xiàn)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塊莖的每次收獲導(dǎo)致作為塊莖寄生物的線蟲大部分被從田間移除,而田間的殘留塊莖和雜草寄主(如田野薄荷)有助于線蟲持續(xù)存在期的延長(zhǎng)[29,42-43,71]。從感染腐爛莖線蟲的馬鈴薯田塊土壤中很難分離收集到該線蟲,可能歸因于線蟲在土壤中的非常規(guī)分布(位置深或高度密集)[44],而另一個(gè)可能原因是線蟲主要在塊莖內(nèi)寄生而很少進(jìn)入土壤。本研究團(tuán)隊(duì)自2016年以來的田間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一些腐爛莖線蟲嚴(yán)重發(fā)生的馬鈴薯田,接茬或重茬種植的馬鈴薯上該線蟲只是輕微發(fā)生;而一些常年種植小麥、玉米的田塊,第一年種植馬鈴薯健康種薯卻出現(xiàn)腐爛莖線蟲嚴(yán)重發(fā)生的情況,其初侵染源來自何方令人費(fèi)解。甘薯和大蒜連續(xù)種植和正常收獲模式下,未見腐爛莖線蟲逐年明顯消減的報(bào)道,病田土壤是重要的初侵染源,從中不難分離得到線蟲[34,40],究其原因,可能是甘薯和大蒜收獲時(shí)線蟲隨病組織被留滯在土壤中的數(shù)量較多。
4.2 侵入與擴(kuò)展
腐爛莖線蟲主要為害寄主植物的地下部分,如塊莖、鱗(球)莖、塊根、根狀莖和肉質(zhì)直根等,在不同作物上,其具體侵染部位、侵入途徑和損害表現(xiàn)有差異。在馬鈴薯上,該線蟲主要侵害塊莖,偶爾侵染匍匐莖和地下莖,極少侵入根系,通常從皮 孔和芽眼侵入發(fā)育中的塊莖(直徑約2-4 cm)[19,73], 盡管與匍匐莖相連的塊莖基部侵染點(diǎn)較多[2,73],但經(jīng)匍匐莖侵入塊莖的說法應(yīng)該不常見;侵入后,線蟲在塊莖皮下方的4-5個(gè)周皮細(xì)胞間穿行取食,導(dǎo)致細(xì)胞崩解,形成 “白堊狀”或“蜂窩狀”的空腔,腔內(nèi)有細(xì)胞壁殘余和少量淀粉顆粒;群體增加后線蟲可擴(kuò)散進(jìn)入相鄰組織,產(chǎn)生另外的空腔,直到形成隧道和空腔構(gòu)成的網(wǎng)格系統(tǒng);空腔外的塊莖皮則出現(xiàn)青褐色病斑,稍微凹陷,常開裂;病部可被真菌、細(xì)菌、螨類等二次侵染,真菌定殖后線蟲能夠大量發(fā)生,而細(xì)菌和螨類入侵后,線蟲很少存在[19,61]。微生物的二次侵染,是受線蟲侵染的馬鈴薯塊莖在貯藏期發(fā)生腐爛的主要原因。
在甘薯上,源自病塊根或植株的秧苗可攜帶腐爛莖線蟲,移栽后常直接引發(fā)嚴(yán)重發(fā)病[34-36]。土壤中的腐爛莖線蟲,主要從秧苗的下部末端傷口侵入,侵入后線蟲可向上擴(kuò)展至地下莖、地上莖(最遠(yuǎn)可達(dá)地面以上9 cm)和不定根,中后期擴(kuò)展進(jìn)入塊根,偶爾侵染葉柄,未見侵染須根的報(bào)道[74-77]。人工表皮接種后腐爛莖線蟲可侵染塊根,但僅在表皮層積累為害,引起糠皮癥狀[78-79]。受害后,主蔓莖基部?jī)?nèi)部變褐糠心、外部出現(xiàn)褐色龜裂斑塊;塊根整個(gè)內(nèi)部組織崩潰離析,呈褐白相間的干腐糠心狀;糠皮癥狀以塊根表面的龜裂褐斑為特征,與馬鈴薯受害狀類似[34-36]。線蟲侵入前,可能受到甘薯地下不同部位所含或所分泌物質(zhì)的吸引或排斥[74,80]。在大蒜上,腐爛莖線蟲侵染蒜根、基盤和蒜皮,并從外皮經(jīng)由內(nèi)皮擴(kuò)展到蒜瓣,大蒜鱗莖中的甲基蒜氨酸(methiin)對(duì)線蟲有很強(qiáng)的吸引作用[40,81]。在鱗莖鳶尾上,線蟲從基盤發(fā)根處侵入,擴(kuò)展進(jìn)入鱗莖和根系,并侵染子鱗莖,土壤中的線蟲偶爾直接侵染根系[82]。在甜菜上,線蟲主要從根頸及其鄰近部位侵入[83]。由此可見,與馬鈴薯相比,甘薯和大蒜受侵染的部位較多,收獲時(shí)線蟲更易隨病組織留滯在土壤中,有助于田間線蟲群體的保持,而腐爛莖線蟲隨病殘組織或種植材料在土壤中的遺留或投放,對(duì)于該線蟲在田間的持續(xù)存在和嚴(yán)重危害將是至關(guān)重要的[43]。
4.3 傳播與擴(kuò)散
腐爛莖線蟲主要通過受侵染的塊莖、鱗(球)莖、塊根、根狀莖、肉質(zhì)直根、秧苗等進(jìn)行遠(yuǎn)距離傳 播[3,8,29,46],故而許多國(guó)家實(shí)施植物檢疫措施對(duì)其進(jìn)行管控。盡管首要的防控措施是生產(chǎn)和種植健康的馬鈴薯種薯、甘薯秧苗和大蒜種蒜等無性繁殖材料,但貌似健康的種植材料可能已被線蟲侵染,而有的種植者有自留種習(xí)慣,這些均增加了檢疫監(jiān)管的難度[28-30]。
田間定殖后,腐爛莖線蟲主要通過導(dǎo)致土壤移動(dòng)的農(nóng)事操作進(jìn)行被動(dòng)擴(kuò)散。盡管線蟲在土壤中能夠借助蠕動(dòng)而主動(dòng)擴(kuò)散,但距離有限,一般不超過1 m[29]。雖然尚無直接證據(jù),但腐爛莖線蟲隨糞肥進(jìn)行短距離擴(kuò)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別是混有受侵染植物殘?bào)w的土雜肥。
4.4 世代歷期
腐爛莖線蟲生活史短,記載的最短世代歷期為15 d[65]。在適宜條件下完成一代通常需要18-26 d,在前蘇聯(lián)(現(xiàn)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地區(qū)的一個(gè)馬鈴薯生長(zhǎng)季可發(fā)生6-9代[2-3,84]。在我國(guó)馬鈴薯、甘薯和日本大蒜上,未見世代歷期和發(fā)生代數(shù)的報(bào)道。
5 腐爛莖線蟲的環(huán)境適應(yīng)性
土壤溫度和濕度對(duì)腐爛莖線蟲的存活、發(fā)育、侵染和繁殖影響最大。Decker從大多來自前蘇聯(lián)(USSR)的數(shù)據(jù)概括出,腐爛莖線蟲在5-34℃下均可發(fā)育和繁殖,最適溫度為20-27℃[2,84]。Ladygina等報(bào)道,馬鈴薯上該線蟲完成1代在27-28℃下需 要18 d,20-24℃下26 d,6-10℃下68 d[2,84]。 Mutua[84]采用氣候室盆栽試驗(yàn)測(cè)定較低溫度(夜間13℃和白天16℃)、中等溫度(夜間17℃和白天20℃)和較高溫度(夜間16℃和白天26℃)對(duì)馬鈴薯上腐爛莖線蟲發(fā)生和危害的影響發(fā)現(xiàn),中等溫度處理下腐爛莖線蟲繁殖最好、對(duì)馬鈴薯?yè)p害最大;較低和較高溫度處理下線蟲也能造成明顯的塊莖損害;較高溫度下線蟲群體密度較低,且幼蟲為優(yōu)勢(shì)蟲態(tài)。該線蟲在15-20℃和相對(duì)濕度90%-100%條件下,對(duì)馬鈴薯的損害最重,脫離寄主組織的線蟲在低于40%的相對(duì)濕度下不能存活[2,29]。在烏克蘭,腐爛莖線蟲對(duì)馬鈴薯的危害在早晨17-20℃和白天20-24℃狀況下最重,并隨土壤濕度由40%到80%的上升而逐漸加重[85]。Ryss試驗(yàn)發(fā)現(xiàn)40%、60%和80%土壤相對(duì)濕度下,馬鈴薯塊莖的受害率分別為11%、63%和93%[2-3]。在農(nóng)田土壤經(jīng)常出現(xiàn)15-20℃和相對(duì)濕度超過90%的地區(qū),腐爛莖線蟲將成為馬鈴薯的重要有害生物[46]。
在腐爛莖線蟲耐干燥(脫水)和低溫能力方面存在不一致的觀點(diǎn)[2]。Ladygina發(fā)現(xiàn)該莖線蟲在-28℃下能夠存活;Makarevskaya觀察到植物組織內(nèi)的腐爛莖線蟲在-2℃下能存活,在-4.5℃下則被殺死[2]。Svilponis等[86]研究發(fā)現(xiàn),處于水、沙礫、馬鈴薯塊莖和M9緩沖液中的腐爛莖線蟲,-5℃處理24 h后,死亡率分別為97%、94%、32%和31%;馬鈴薯塊莖中的腐爛莖線蟲處理24 h后,-15℃下成蟲全部死亡,-30℃下仍有少數(shù)2齡幼蟲存活,成蟲、J4和低齡幼蟲死亡率為90%的預(yù)測(cè)致死溫度(LT90)分別是-7.4℃、-9.4℃和-14.5℃,成蟲和4齡幼蟲的耐冷性明顯不如低齡幼蟲。王宏寶等[87]發(fā)現(xiàn),不同地理來源甘薯塊根內(nèi)的腐爛莖線蟲,在-20℃和-70℃下處理180 d,存活率分別為11%-49%和5%-19%,而甘油和細(xì)沙介質(zhì)中的線蟲經(jīng)低溫處理后均未見存活。Ustinov等曾提到腐爛莖線蟲的卵可進(jìn)入低濕休眠狀態(tài)[86]。來自山東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當(dāng)甘薯塊根含水量降至12.8%時(shí),大部分線蟲仍可存活[34]。盡管如此,多數(shù)信息指向腐爛莖線蟲不耐干燥[20,39,72,82],這可能也是與干燥有協(xié)同效應(yīng)的高溫不利于該線蟲發(fā)生和存活的原因。鳶尾病鱗莖在43.6℃溫水中浸泡3 h,腐爛莖線蟲可被有效控制[46]。直徑9 cm的甘薯塊根在42℃溫箱放置24 h,內(nèi)部線蟲全部死亡[34]。大蒜鱗莖在34-36℃下干燥處理12-17 d,內(nèi)部線蟲數(shù)量明顯下降[39]。由此看來,腐爛莖線蟲喜涼怕熱、喜濕怕干;與游離在土壤中的相比,薯塊等植物組織中的腐爛莖線蟲表現(xiàn)出較強(qiáng)的耐低溫和抗干燥能力。
土壤理化性質(zhì)對(duì)腐爛莖線蟲影響的相關(guān)報(bào)道不多[29]。甘薯腐爛莖線蟲病在質(zhì)地疏松、透氣性好的沙質(zhì)土上發(fā)病重,在黏質(zhì)土上發(fā)病輕[34,36]。
6 腐爛莖線蟲的存活和寄生機(jī)制
作為植物寄生線蟲世系最底層的種類,腐爛莖線蟲盡管不能產(chǎn)生諸如“線蟲絨”(起絨草莖線蟲)、孢囊(孢囊線蟲)、卵塊(根結(jié)線蟲)等自我保護(hù)性存活狀態(tài)或結(jié)構(gòu),卻能延續(xù)至今并屢屢給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制造麻煩[4,37,56]。腐爛莖線蟲的進(jìn)化、存活和寄生適應(yīng)性、侵染致病等應(yīng)該有其獨(dú)特的策略和分子機(jī)制,但這些方面的研究不多。
黃文坤等[88]利用簡(jiǎn)單重復(fù)序列區(qū)間(ISSR)分子標(biāo)記對(duì)來自我國(guó)不同省的5個(gè)腐爛莖線蟲群體進(jìn)行研究發(fā)現(xiàn),遺傳距離與地理距離成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該線蟲對(duì)低溫具有較強(qiáng)的適應(yīng)性。Ma等[89]通過轉(zhuǎn)錄組分析,比較了腐爛莖線蟲響應(yīng)寒冷和干燥脅迫的基因表達(dá)譜,驗(yàn)證了抗寒相關(guān)基因的功能。Peng等[90]對(duì)源于腐爛莖線蟲cDNA文庫(kù)的ESTs(表達(dá)序列標(biāo)簽)測(cè)序發(fā)現(xiàn),22個(gè)ESTs與已報(bào)道的線蟲效應(yīng)子有相似性,大多涉及寄主細(xì)胞壁降解或修飾。Peng等[91]還發(fā)現(xiàn)腐爛莖線蟲的2個(gè)纖維素酶基因產(chǎn)物具有纖維素酶活性,對(duì)線蟲寄生性起重要作用。Chen等[92]驗(yàn)證了腐爛莖線蟲3個(gè)α-淀粉酶基因的功能,認(rèn)為多拷貝的α-淀粉酶基因在線蟲寄生甘薯中起關(guān)鍵作用。Zheng等[93]對(duì)腐爛莖線蟲基因組研究發(fā)現(xiàn),盡管大多數(shù)信號(hào)轉(zhuǎn)導(dǎo)通路被保持,但核心發(fā)育控制過程出現(xiàn)大幅消減,推測(cè)莖線蟲可能處于從取食真菌的自由生活線蟲向?qū)P灾参锛纳€蟲進(jìn)化的中間階段。腐爛莖線蟲的基因組、轉(zhuǎn)錄組和ESTs研究,對(duì)于解析其存活寄生機(jī)制和優(yōu)化治理策略具有重要意義[94]。
不同寄主植物和地理來源的腐爛莖線蟲群體在寄主和環(huán)境適應(yīng)性上可能不同[19,29,87],對(duì)馬鈴薯、甘薯等不同品種的寄生致病性也存在差異[95-98]。盡管不同群體存在寄主范圍、致病性乃至某些形態(tài)特征的差異,但腐爛莖線蟲種內(nèi)迄今尚無生理小種被命 名 和 鑒 定[2,99]。Subbotin等[99]根 據(jù)rDNA-ITS1的二級(jí)結(jié)構(gòu)差異,將腐爛莖線蟲的78個(gè)群體劃分成A-G型共7個(gè)基因型(單倍型)。我國(guó)迄今報(bào)道的腐爛莖線蟲基因型以A型和B型為主,也有C型和F型以及A-G型以外類型(L型和S型)的報(bào)道[100-104]。遺憾的是,腐爛莖線蟲不同基因型與其生存、寄生等生物學(xué)特性有無關(guān)聯(lián)尚需明確;而在世界上如此多樣的腐爛莖線蟲群體中,發(fā)現(xiàn)生理小種乃至新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7 小結(jié)
基本明確的是,腐爛莖線蟲喜涼怕熱、喜濕怕干,在溫帶地區(qū)更具經(jīng)濟(jì)重要性;主要為害馬鈴薯、甘薯、大蒜等農(nóng)作物,受侵染的種薯、種苗、種鱗莖等無性繁殖材料既是其主要的遠(yuǎn)距離傳播途徑,又是其定殖區(qū)主要的初侵染源,對(duì)群體持續(xù)和危害加重至關(guān)重要;主要從傷口或自然孔口侵入寄主植物,缺乏穿透寄主表皮直接侵入的能力。然而,腐爛莖線蟲又具有明顯的復(fù)雜性和不確定性,主要表現(xiàn)在:它兼具取食植物和真菌習(xí)性,寄主植物范圍信息不完整,土壤棲息真菌和一些已記載寄主植物對(duì)其田間持續(xù)存活的作用不夠明確;它在馬鈴薯田定殖后,在田間土壤中的存活持續(xù)性問題尚需解析;它對(duì)馬鈴薯、甘薯和大蒜的侵害特點(diǎn)明顯不同,特別是在甘薯上引起的“糠心型”癥狀和地上部侵染在馬鈴薯和大蒜上罕見,在大蒜和甘薯上引起的根系侵染在馬鈴薯上未見發(fā)生;它群體多樣性豐富,存在諸多不同的基因型。腐爛莖線蟲處于真菌食性向植物專性寄生性進(jìn)化的中間階段,在系統(tǒng)發(fā)育關(guān)系上,它與專性寄生植物為主的起絨草莖線蟲關(guān)系較遠(yuǎn),而與寄生昆蟲和取食真菌的隧蜂莖線蟲(D. halictus)關(guān)系更近[93,105-106],這也許能為理解其復(fù)雜性提供一些方向或線索。
腐爛莖線蟲對(duì)多種作物為害嚴(yán)重或潛在威脅巨大,但人們對(duì)其生物學(xué)和生態(tài)學(xué)的認(rèn)識(shí)不夠全面,對(duì)其在一些作物上的發(fā)生發(fā)展難以預(yù)測(cè),致使某些地區(qū)的馬鈴薯種植者飽受困擾。因此,有必要對(duì)腐爛莖線蟲進(jìn)行深入調(diào)查研究,重點(diǎn)應(yīng)在以下兩個(gè)方面:一是盡可能獲得決定或影響線蟲在土壤中持續(xù)存在的相關(guān)因子信息,諸如作物、雜草亦或真菌寄主的種類及其適合性、土壤溫濕度臨界條件等。二是比較不同寄主作物上線蟲的侵染和為害特點(diǎn),就明確而穩(wěn)定的差異進(jìn)行分子生物學(xué)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