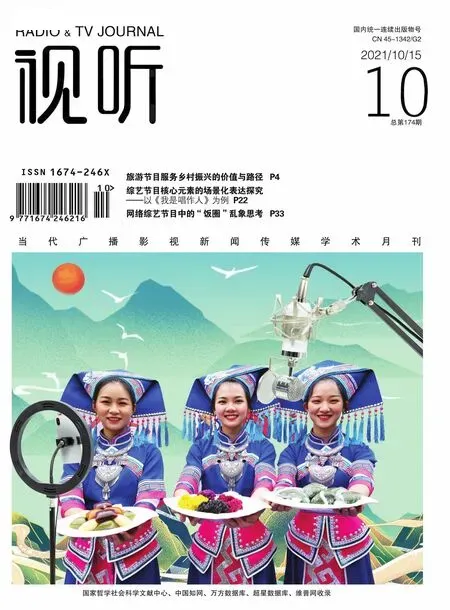神性的清潔與藝術的清潔
——民族審美心理觀照下的《清水里的刀子》
何競祺
《清水里的刀子》是青年導演王學博的長片處女作,獲得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浪潮獎。不同于以往民族元素流于外化視聽符號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該片采用了極簡主義的藝術手法,契合回族審美中對清潔的向往與追求,成功創作了一部形神兼備的回族題材電影。
一、民族心理學觀照下回族的“清潔”審美
“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來說,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作用”①。民族共同體共享著民族文化,并從這種民族文化中孕育沉淀出“共同心理素質”。民族文化與民族的心理品性具有相對獨立性,構成民族的重要內在特征。民族的審美心理正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品行的一種具體體現。各民族在其日常生活、民俗儀禮乃至藝術創作中會體現出個性化的審美標準,民族審美心理是民族審美觀乃至價值觀的根源。在民族發展歷史中,同一民族的人民共享著同一種語言、文化、歷史、神話、儀式、宗教信仰,進而形成了相似的心理模式。這種心理模式在教育、遺傳、環境等因素作用下固化于民族群體,由該心理模式主導的民族審美也一同凝結于民族內部,成為聯結民族共同體的諸多介質之一。即使某一民族的人民走出共同地域,脫離共同經濟生活,只要他們還共享著相似的文化和心理模式,依然可以維持著某一民族共同體的存在。在民族發展的趨同和融合階段,民族存在的根本基礎不再是地域與社會,而是文化。由此觀之,民族是一個超地域、超社會單位的共同體,其中民族心理在維系民族存續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在人類學意義上,潔凈(purity)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是一種后天的建構,它可能源于巫術、宗教或某些象征,與污穢形成了二元對立的關系。英國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在其專著《潔凈與危險》中研究了不同文化中被視為褻瀆而加以禁止的行為、食物。她指出動物的骯臟與否在于其是否符合某一文化的分類系統,而不在于它本身是否干凈。當一種動物為某文化的分類系統排斥,那么這種動物就是不潔的、危險的。換言之,這里的“清潔”概念并非是科學話語中的未被污染的狀態,更是一種文化的建構,具有豐富的文化意涵。
有學者梳理了回族“清潔”概念的重要內涵,包括:以正當手段獲得錢財并拒絕迷信活動;在宗教功修中保持身心的清潔;做到平等愛人,維持家庭生活和睦;保持個人儀表清潔;遵從宗教教規,約束自身日常行為;堅持飲食禁忌以及進餐規范;通過約束自我行為追求高尚的節操②。回族文化中“潔凈”不僅是簡單的衛生概念,更是一套關乎身體與精神、世俗生活與宗教信仰的價值觀念。有學者總結道,回族的清潔觀念是“外清內潔”,即“凈身之污垢,凈心之邪念”③。
在以“清潔”為核心的回族審美系統中,“水”是極為重要的意象。如回族學者張承志在《綠風土》中所言:“在這里,水和人的關系是一種內心的精神關系”。在回民看來,“水”是最潔凈的物質。在回族文化中,“水”不僅是日常生活中為人所使用的、維系人的基本生命的一種物質,更是一種可以滌蕩生命與靈魂的超越性存在。
“禮拜”是回族民眾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功課,在每次禮拜前需以水做“大小凈”,清潔身體,只有在身體凈、衣物凈、環境凈的時候,拜功才能成立。在回族民眾看來,水不僅清潔了物質層面的灰塵污垢,也凈化了精神層面的不潔。以流水清潔身體,是脫離世俗生活進入信仰領域的前提條件,未經清潔的身體無法擺脫現實的泥淖,亦不會得到庇護。“因此,‘水’成為世俗與神圣……之間的橋梁,成為二元世界的閾限”④。通過制度化、規范化的清潔儀禮,回民對清潔的追求,內化于民族文化的系統,并依靠儀禮的具體要求得以實現并維系。
由此,觀念的“清潔”與具象化的“水”,以及一系列以水濯洗的儀禮相互映照,滲透、沉淀于回族民眾的審美心性與文化核心中,指導著回族民眾對現實生活與神圣時刻的理解,并進一步成為族群文化的重要代表與化身。
二、以藝術的清潔照應神性的清潔——極簡主義接合民族審美
《清水里的刀子》改編自回族作家石舒清同名作品,小說原作情節簡單,只用一句話就能描述:“老伴去世了,在四十祭日那天要宰頭牛來搭救亡人,而在宰牛的前三天,牛就不吃不喝,為了以一個清潔的內里來結束自己的生命”⑤。導演王學博表示,聽聞這個故事,首先的震撼與疑問在于“牛為什么要清潔內里”,這樣準確的問題意識或許就是影片得以形神兼備的原因之一。
從第一部回族題材電影《太陽照亮了紅石溝》開始,回族電影已經走過了68年的歷程。然而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并沒有讓回族題材電影積蓄旺盛的活力,反而隨著商業影視興起、政教電影退位,逐步進入“失語”的境地。細數十三部回族題材長片,它們大多無緣院線未曾示人。少數影片,如《回民支隊》,曾引起一定反響,但終究是特定時期政治掛帥的產物,假如保留故事梗概,將片中主人公設定為任何民族,也未見得有絲毫違和。
此外,僵化刻板的民族元素表達,也是包括回族電影在內的眾多少數民族影視難逃的窠臼。如同蒙古族題材電影中永不止息奔馳的駿馬,維吾爾族題材電影中從不倦怠的歌舞,藏族題材電影中不經意露出的布達拉宮,而回族電影總是避不開“白帽”與“頭巾”。誠然,“白帽”與“頭巾”是回族特有的服飾特征,出現在回族題材電影中自有其合理性,但是站在他者立場將回族和回族的文化縮略為一縷白色,營造出扁平化的刻板印象,是一種“東方化”式的貶損。這樣的民族題材影視往往忽略了一個群體的生命活力,抹殺了一個民族具體而鮮活的歷史與文化。
《清水里的刀子》則是難得地嘗試著對扁平化的民族題材影視進行創新突圍。片中關于死亡的思考引發點是民族的、穆斯林的,但是影片的思考對象,乃至由思考促成的認識卻是指向全人類的。沒有哪個民族能夠逃脫生死的詰問,在此意義上,與其說該片講述了穆斯林的生死觀念,毋寧說該片展現了人類面對死亡的一種態度和行動方式。民族題材的影片不能在民族題材的小天地里盤旋,重要的是建立全人類的通感。無論哪個民族,都是人類共同體之一,民族的影視可以討論人類的問題,人類的問題也會有民族的解答,而民族的解答正是人類解答的一種。
在導演訪談錄《生與死,簡與繁》中,王學博表示:“我能提煉出來的第一個東西是‘極簡主義’,……這部影片里的置景,不像‘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的那些寫實風格影片,而是把片中的元素在寫實的基礎上進行簡化,變成一種感受性的傳達”⑥。結合導演后續的說法:“這應該不是我的美學,我自己寫的東西其實挺好看的,我比較追求觀賞性、節奏感。這部緩慢的風格我是覺得它適合于這個題材”⑦。可見導演用極簡主義的風格制作《清水里的刀子》,并非是出于創作慣性,而是有意為之的選擇。所謂“它適合于這個題材”,參透內里,即極簡主義的風格表達切近了回族的清潔審美,能夠貼合回族的風格與審美品性,也適用于對生死觀念的追問。
三、《清水里的刀子》的極簡主義表達
對于《清水里的刀子》的極簡主義風格,可以從形式風格和敘事風格兩個方面剖析。在形式方面,其極簡主義風格體現在對顏色的表意化使用、理想化的簡單布景、低存在感的鏡頭語言、4∶3的畫幅、簡練甚至無應答的臺詞,以及被完全舍棄的非劇情聲音。在敘事方面,也許命題已足夠厚重,導演摒棄了所有非必要的敘事線索,一元主題、無需交代背景的人物,乃至線性的不疾不徐的時間鏈條,讓所有力道都灌注于對生死無常的體悟,簡練而深刻。
(一)形式風格
影片的極簡主義風格首先體現在色彩方面。色調之單純,是《清水里的刀子》的代表性特征。影片中的色彩不只是對現實的再現,更具有了表意功能。黑、白、黃基本構成了全片的色彩,出現次數有限的其他色彩也往往明度很低,帶有一種霧化的效果。如畫家瓦西里·康丁斯基所言,“黑色的基調是毫無希望的沉寂”,黑色“否定白光,否定鮮艷,否定生命”⑧。白色則是回族崇尚的潔凈顏色,白色的禮拜帽、頭巾、羊群與肅穆而沉靜的黑色相映襯。暗淡的黃土色(Ochre)則給人以“恬靜而懷念”的感覺,而這也是西海固地區大面積的沙土的色澤。貫穿全片的黑、白、黃三色,對應著生死詰問、宗教寄托與吾鄉吾土。大面積的色塊,克制而理想化的色彩選擇,結合強烈的光影對比,讓全片的每一幀畫面都呈現出油畫般的質感。
其次,影片的置景也是被簡化的、理想化的。在影片23分處,老人“洗大凈”片段中,可以發現布景的極簡主義色彩。這一片段中,全部布景只有一個用于“沖頭”吊罐,背景是一面土黃色的墻,老者就在這一罐水下、一堵墻前完成了整套的“大凈”儀式。老人在沐浴前先念“太斯米”,然后扯開吊罐的秫秸,按照回族傳統“先上后下”“先右后左”“先前后背”以流水沖洗周身。這一片段的處理,布景極其簡單,鏡頭固定,只有老人的念詞和沖洗聲,導演的參與度很低,觀者的注意力全然被老人俘獲。同時,導演給這部分留下了一分鐘有余的時長,長鏡頭配合著簡潔的畫面,讓人能夠體驗時間的重量以及過程感。
此外,畫幅如畫布,不同畫幅會給觀眾帶來不同的視覺感受。影片一反常態,用4∶3的畫面比例取代了16∶9畫幅,甚至在院線上映時讓觀眾以為出現了技術故障。訪談中,王學博表示,如此取舍的目標是為了與繪畫更接近,并且更貼近人物,“這種畫幅更能走到人物心里去”⑨。4∶3 的畫幅視覺重點更突出,16∶9 的畫幅則更擅長變化場面與環境。對于該片簡單的故事情節,16∶9的優勢無從展現,還會讓多余的視覺元素稀釋主體的存在感。從內容與形式相配合的角度,導演選用了4∶3的畫面比例。與之相配合,影片的視角也始終跟隨馬子善老人的視角,無關的背景畫面被盡數省略,觀眾的視覺中心自然會落在馬子善老人身上。這種冷靜克制的運鏡手法體現出導演鮮明的極簡主義美學風格。
最后,聲音同樣是影片表達的重要部分,在聽覺與視覺的“感官合成”中,可以影響觀者對影像的詮釋,引導觀者對特定影像的注意力。《清水里的刀子》全片未用一處背景音樂,但聲音元素并不寡淡。鳥類長鳴、牛羊叫聲、贊頌辭、邦克、風雨聲、牛的飲水與反芻聲,鐘表走時聲、燒水聲乃至磨刀聲,填充了全片的聲音空間。這些“劇情內聲音”極具代入感,又避免了過于繁復的煽情表達。作者意欲以自然之聲音——牲畜的聲音、勞動的聲音、雨聲等構成一種不失真的節奏與韻律。與此同時,在影片的臺詞設計上惜字如金。僅有的寥寥幾處對白中,就有兩次以沉默終結。其中一次是,老人兄弟因家中女人生產而來老人家借米。當老人兄弟說出不情之請后,老人并沒有回應他,而是在沉默了一會,處理完手中事務后喚起兒媳為兄弟盛取了不少的糧食。影片對語言的吝嗇,讓情緒更為飽滿且耐人尋味。在片中,聲音是簡練的、純粹的、天然的、未經雕飾的,是極簡主義的,亦是“潔凈”的。
(二)敘事風格
首先,影片的敘事異常專注,一切與主題無關的支線都被舍棄,只留下核心的故事被平鋪直敘地呈現。用導演王學博的話說,這個片子是“一句話”就能講完的故事。一個老婦“無常”,老伴和兒子思考如何在“四十”搭救亡人,決定以大牲老牛作為“乜貼”,并在之后的時間里悉心照顧老牛,按照回族的觀念老牛在“四十”前三日不再進食飲水清潔內里坦然迎接死亡,引發了老人關于人類面對死亡的思考。其間穿插生活場景、老人馬子善替亡人換錢、借糧食給親戚的片段以及新生兒的出生,也都是徑直鋪陳下去。這些場景或是對生活實景的填充,或是意向式的表達,但絕非敘事系統中的機關與暗道。按照商業片創作邏輯的慣性,如上的故事顯然不足以填充一部時長90分鐘的電影,但是導演通過沉穩的運鏡、固定長鏡頭、對時間過程感的強化,讓簡單的劇情顯示出一種簡練的風格,并拱衛著全片的終極主題。只講一件事,講好一件事的一元策略,讓影片在傳情達意與藝術審美方面都頗為成功。
此外,片中人物不多,人物關系也并不復雜,每個人的身份都是模糊含混的,他們各自有怎樣的故事和背景顯得無足輕重。這樣的人物處理對于重情節講故事的影片是不可取的,但是對于該片這種著力于形而上話題探討的影片,則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人物形象過于豐滿,人物性格過于鮮明,會讓觀眾以一種不自覺的旁觀視角觀看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故事,而該片人物被弱化處理,避免了劇中人和觀眾的異質帶來的離間。劇中人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有關人類普遍境遇的思考,這樣的思考并不依附劇中人的身份而存在,弱化了身份與背景更能讓觀眾產生普遍共鳴。
最后,《清水里的刀子》整部影片只有一條完整的線性時間鏈條,平鋪直敘無一次使用閃回,亦沒有插敘的片段。沒有任何敘事技巧的加入,也就避免了形式語言和無關輕重的情節分散觀影者的注意力。如此一來,觀眾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故事本身,無需額外對情節進行想象與重組,所有待想象的都是導演有意言明的問題:關于潔凈、關于生死、關于孤獨、關于坦然。
四、結語
《清水里的刀子》是一部東北漢族導演拍攝的西北回族題材的影片,雙重的他者身份沒有影響影片對民族素材的精確傳達。它沒有流于表面的描繪,沒有局限于民族間“異”的表達,而是走入一個民族的內心世界做傳神的表達,找到了人類似異實同的悲喜交加。它以極簡主義這樣一種舶來的藝術風格,擊中了回族群眾的審美靶心,并最終觀照了人類的普遍命運與局限。它的民族性是無意張揚的,又是切中要害的,民族不是為它利用的工具性符號,而是它的角度、它的途徑,最終抵達的則是人類命運的交匯處。
用導演王學博的話說,《清水里的刀子》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作者電影”,沒有任何商業與政治的考量。這也是影片可喜可貴的一個方面,放棄藝術表達之外的企圖心,才能讓一部影片如此簡單、如此純粹、如此真誠,又具有如此普遍的人類共鳴。
注釋:
①楊須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語境考辨——兼論“民族”概念的漢譯及中國化[J].民族研究,2017(05):1-16+123.
②陶染春.回漢兩族 “潔凈”概念結構的對比分析——兼談瑪麗·道格拉斯“分類秩序”理論[J].民族藝林,2015(04):34-40.
③李華英.伊斯蘭教清潔衛生觀概論[J].中國穆斯林,1996(01):22-30.
④何粉霞.“水”與回族的禁忌和社會秩序[J].民族藝林,2014(3):37-41.
⑤⑥⑦⑨王學博,葉航,周天一.生與死,簡與繁——訪《清水里的刀子》導演王學博[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7(03):93-99.
⑧梁明,李力.電影色彩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