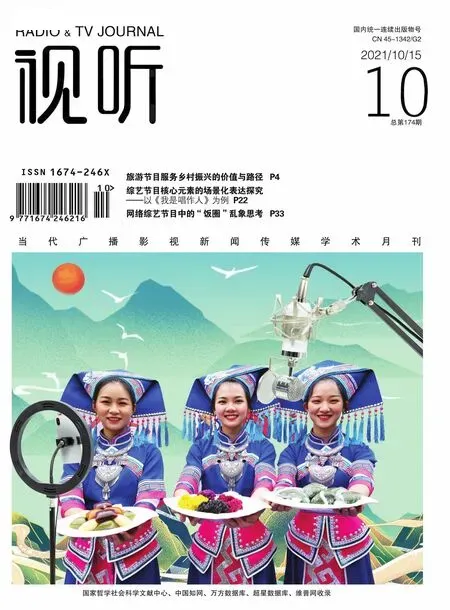豆瓣小組的互動儀式研究
羅一菡
早在1970年,馬歇爾·麥克盧漢就曾預言:“在日新月異的電子媒介影響之下,人類社會將被重新劃分為若干集合,并再次走向‘部落化’。”毋庸置疑,在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下,他的預言正在一步步變成現實。借助互聯網,尤其是社會化網絡技術的全新升級,網絡社群以迅猛之勢發展擴大,各種各樣的網絡社群充斥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中。他們不僅改變了個體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也對社會信息的傳播制式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在浩如煙海的網絡社群中,豆瓣小組以其多元化和包容性,成為國內互聯網平臺中獨具特色的信息社區。“瘋狂攢錢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社會性死亡小組”等豆瓣小組相繼出圈,成為眾多網絡熱議事件的發源地。時至今日,豆瓣小組已經從最初的文藝青年的“精神角落”發展成為擁有60多萬個包羅萬象的話題小組的社交平臺。豆瓣小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內容平臺,用戶從文化消費者轉變為內容生產者,其中的眾多內容真實反映了當下的社會思潮。
一、理論框架:互動儀式鏈
美國社會學家柯林斯在其著作《互動儀式鏈》中提出了互動儀式鏈理論并完善了理論框架。柯林斯認為,社會中的大部分現象都是在人們的交流互動中通過各種互動儀式形成和維持的。人們通過高度的相互關注和情感連帶形成了互動儀式,并且通過這種互動儀式獲取了情感能量,這種情感能量的獲取反過來又成為開展下一次互動儀式的驅動力,由此形成了一個互動儀式的循環。互動儀式鏈是社會結構的基礎,整個社會都可以看作是一個長的互動儀式鏈,由無數個小的互動儀式鏈構成。
二、豆瓣小組中互動儀式的形成
(一)虛擬共在:網絡傳播奠定互動基礎
在柯林斯的觀點里,儀式本質上是一個身體經歷的過程。人們的身體聚集在一起,儀式過程就開始了。沒有親身在場的儀式開展,人與人之間不能進行身體接觸,不能即時接收對方的反應并作出回應,由此便不能產生持續性的相互關注和情感連帶,情感能量的獲取會受到威脅,或者說,產生的情感能量遠不如親身在場開展儀式所產生的情感能量。就好比在現場觀看一場足球比賽遠比在電視機前觀看更激動人心,在現場聽一場音樂會遠比在家聽收音機更能使人沉浸。哪怕媒介技術發展到了今天,親身體驗足球賽、音樂會這種大規模的儀式活動所產生的情感體驗依舊不能被線上參與所取代。但是對于因共同志趣或價值觀而集結起來的網絡社群來說,就不能一概而論了。在如今的互聯網上,存在著大量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網絡社群,他們沒有形成物理上的身體同在,但仍然有高度的相互關注和情感連帶,也形成了群體團結和道德感等結果。
現場聚集的成本是昂貴的,且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網絡群體中的成員雖然不能隨時同處在一定的物理空間內,但是隨著移動終端設備的普及和網絡技術的發展,人們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實現實時在線交流互動。豆瓣小組將擁有共同興趣和價值觀的人們聚集起來,形成一個圈子。在這個圈子里,成員之間可以隨時就某一感興趣的話題進行交流互動,并且這種交流互動是不會隨著一場足球賽或是音樂會的結束而結束的,個體可以實現“永遠在線”。儀式的開展由“現實在場”轉向“虛擬在場”,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二)對局外人設限:互動儀式的準入機制
對局外人設限,是互動儀式得以形成的另外一個前提條件。社群中的話題分組可以對群體之外的人設限,將群體與外部區分開來。在豆瓣小組中,有30個小組分類,包含了60多萬個不同主題的小組,從游戲、生活、情感到同城、租房等,各種類型的小組包羅萬象。人們根據自己的志趣選擇進入不同的小組,不同的興趣圈層之間就有了區隔的屏障。
同時,很多豆瓣小組都有一定的準入機制。進入小組要輸入申請理由,申請理由通常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藏在組規中的“暗號”,需要申請人仔細閱讀組規,從中找到“暗號”;第二部分便是對相關小組主題的理解和自己的入組理由,入組申請理由發送后,待組長同意,才能進入小組。“武林外傳十級學者”小組需要申請人填寫準確的小組暗號和入組理由才可入組,“笑死我了這彈幕”小組需要申請人填寫小組暗號,或是全面總結組規。這些豆瓣小組的準入門檻直接對局外人設限,只有認同本小組的價值取向的人才能進組,同時也能更好地維護小組的秩序,從而進一步強化小組成員的身份認同。
(三)共同關注的焦點:引發互動行為
儀式中有一個共同關注的焦點,并且參與者知道其他人也在關注這個焦點是互動儀式得以順利開展的重要因素。這一焦點可以是一個帖子,一條評論,甚至一個點贊,等等。只要這個信息能夠抓住參與者的眼球并且在這個群體之間能夠引起情感共鳴,圍繞這一焦點就可以開展互動儀式。豆瓣小組中信息的交互性很好地滿足了這個條件。在豆瓣小組中,最基本的互動行為就是圍繞帖子進行互動,每個成員都可以發布帖子,并且這個帖子在小組內是開放的,每個人都可以對帖子進行評論、點贊。在評論下又可以進行評論,并且不會被折疊。所有的互動行為都是針對共同的關注焦點——小組成員發布的帖子進行的。
(四)共享情感:產生情感連帶
社交媒體的本質就在于互動,這種互動不僅是成員間分享信息,也包括情感的交流。互動儀式鏈得以完整呈現的最后一環就是人們分享共同的情緒或情感體驗。在豆瓣小組中,很多成員發帖的目的是分享情感、尋求共鳴。在這些帖子下,小組成員又基于這一共同關注的焦點進行即時性的互動、分享彼此的情感體驗,形成一種感情聚集,使成員間的關系更加牢固。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組中,搞笑的帖子下充斥著小組成員“哈哈哈哈哈哈……”的回帖,小組成員之間保持高度一致,產生了高度的情感連帶和集體興奮。
隨著工業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之間的社交成本越來越高。而資本化的進程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所擠壓,加劇了孤獨感的產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人們渴望在群體里找到寄托,獲得高層次的精神滿足。在“社會性死亡”小組中,小組成員通過發布自己的“社死”經歷與其他小組成員之間進行情感共享,或是得到心理慰藉,或是獲得情感共鳴。
三、豆瓣小組互動儀式的結果
(一)激發個體情感能量
基于卡茨提出的“使用與滿足”理論,每個人都是出于一定的目的來使用媒介的。而柯林斯認為,人的所有的互動行為都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獲取情感能量。柯林斯將社會學中的概念情感能量引入互動儀式鏈理論中,并將其作為理論中的一個核心要素。這里的情感能量與我們平時所提到的情感有所不同,它不是一種短暫的情感刺激,而是一種長期的、穩定的,并且不易被察覺的情感狀態。
柯林斯認為,群體成員圍繞共同關注的焦點參與共享情感的互動。在儀式開始之前,參與者獲得的是一種短暫的不穩定的情緒體驗,但隨著互動儀式的開展和不斷循環,這種短暫的不穩定的情緒體驗就會轉換成一種長期的穩定的情感能量。而且這種情感能量的獲取是有高低之分的。當情感能量“高漲”時,參與者會獲得一種積極自信的感覺,促使其參與下一次的互動儀式。而當情感能量“低落”時,參與者在群體中獲得的是消極的體驗,這種體驗會讓參與者對群體失望,甚至會脫離群體。在豆瓣小組中,小組成員通過發帖獲得回帖的行為獲得了關注、贊同和情感共鳴,這些短暫的情感體驗通過互動儀式的不斷累積轉換成自我認同感、群體歸屬感等,這種“高漲”的情感能量的獲取又會成為小組成員參與下一次互動儀式的動力。反之,如果小組成員在發帖的過程中得不到回應或是得到一些負面的反饋,又或是不能在其他小組成員的發帖中感覺到情感共鳴,獲得的情感能量就是“低落”的,久而久之,就不會繼續參與小組內的分享和互動,甚至會產生退組行為。
(二)創建群體符號
群體符號實際上是群體成員互動儀式中的情感投射,經過互動的不斷累積,每個小組都會形成特定的群體符號,這種群體符號具有排外性,群體之外的成員往往不理解其真實的內涵。而小組成員之間繼續使用這種符號進行交往互動,又進一步加深了成員的身份認同和對群體的歸屬感。在“土味穿搭踐行者”小組中,成員之間自稱“土家人”,有小組成員發布的帖子符合小組的統一認識(即“土”),其他成員就會跟帖評論“歡迎回家”“到家了”等內容。這種群體符號的形成,是互動儀式開展的一個重要結果,不僅在群體內部能夠增強認同感,有時也會出圈,形成這一群體的一個標志特征,可以幫助社群成員辨別誰是其中一員,從而擴大社群的規模。這些群體符號不管是在群體內部使用還是在群體外部流通,都是群體凝聚團結的結果。
(三)強化身份認同,形成群體團結
身份認同和群體團結是互動儀式的一個很顯著的結果,互動儀式的不斷累積最后會強化整個群體的凝聚力,產生統一的道德標準,形成群體團結。在豆瓣小組中,不符合群體價值觀或是違反組規的行為會受到來自其他小組成員的批判,嚴重者甚至會被踢出小組。在“土味穿搭踐行者”小組中,分享“土味”穿搭就是統一的行為規范,如果有小組成員發布相對時尚的穿搭,就會被其他組員評論為“凡”“凡爾賽”,受到嘲諷。在這個小組中,“土”就是統一的價值規范和道德標準,經過互動儀式的不斷循環,組員的身份認同和群體認同感被強化,會自覺維護組內的價值規范。
四、結語
柯林斯提出的互動儀式鏈理論為我們理解人類行為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也給互動儀式帶來了新的變化,移動終端的普及和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互動儀式的形成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虛擬共在、對局外人設限、共同關注的焦點和共享情感是豆瓣小組互動儀式的形成條件,與此同時,互動儀式的不斷循環也激發了小組成員的個體情感能量,創建了小組的群體符號,并形成了群體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