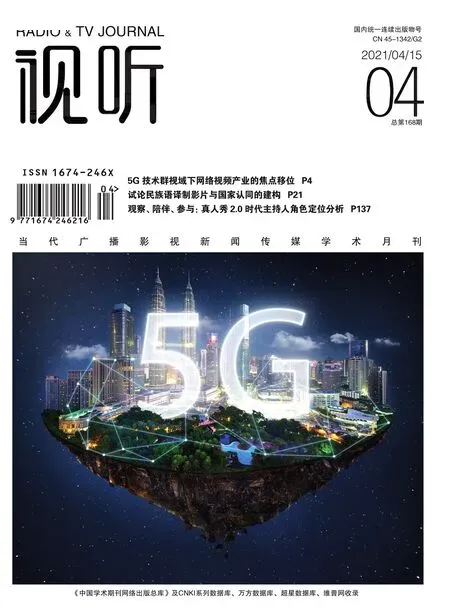淺析鄉村紀錄片的外在形式與內在價值
——以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為例
□ 吳世真
鄉村題材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自問世以來,共獲得了華表獎、白玉蘭獎等20項大獎。總導演焦波在《我拍<鄉村里的中國>》一文中說道:“紀錄片的導演不能導演生活,只能靠自己的觀察、判斷,在每天發生的紛繁的事情中抓取需要的東西。”《鄉村里的中國》以導演焦波的家鄉——山東沂蒙山沂源縣中莊鎮杓峪村為拍攝地點,采用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為時間點,對該村自2012年立春至2013年春節進行了為期373天的跟蹤拍攝。在這部不足100分鐘的紀錄片里,記錄下了這個普通村莊和村內村民一年內的變化,以節氣的變化展現鄉村的變化,真實描繪了中國農村的發展現狀,反映了中國農民的生活現狀。
一、外在形式
(一)視聽語言——原生記錄,真實感強
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會有其自身的傳播語言系統,紀錄片的傳播符號則是畫面和聲音,因此,紀錄片也被稱為聲畫藝術,而畫面語言是紀錄片傳播的基礎。畫面和聲音是影片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幫助受眾在視覺和聽覺兩個方面互相貫通,形成通感,強化受眾身臨其境的感覺,引起受眾共鳴。
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首先映入受眾眼簾的是潺潺的流水、水中的野鴨、初融的冰雪等展現村莊自然環境的畫面,通過杜深忠和妻子開欄放羊、按照當地風俗在羊頭上染上象征好運的紅色顏料、在房外磚墻上寫上大大的“春”字以及老人坐在屋前縫虎頭帽等人物活動,展現當地的鄉村風俗及村民日常生活狀態。該片全部采用原生態的拍攝手法,借助人物之間的對話、互動以及場景和時間的變換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沒有一句解說詞和旁白,同時,片中全部使用同期聲和現場錄制的音樂音響,完全沒有后期配樂。例如孩子們圍在篝火旁“咬春”時的銅鑼聲、廣播里播放的歌曲、通知婦女體檢的大喇叭、杜深忠拉二胡和彈琵琶的聲音以及吊唁張自軍的吊喪聲等,這些對現場聲音的真實記錄有利于還原影片內容的真實性與客觀性。
(二)敘事方式——多線交叉,突出主題
《鄉村里的中國》以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講述農民故事,采用三條主線交叉的敘事手法,圍繞三個具有典型代表的農村家庭,講述了三個家庭的故事。一是以村民杜深忠為代表的農村文化人,在物質條件匱乏的現狀下依然追求精神世界的滿足,反映出我國農民的精神需求難以得到保障;二是以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張自忠為代表的農村基層干部,在村里修建廣場砍樹等看似雞毛蒜皮卻又關乎村民切身利益的問題上,不惜為了集體利益與村民起沖突、鬧矛盾,在解決村民矛盾問題上他兩邊奔波,從中調解,反映出農村人際關系的復雜性和基層干部面臨的集體利益與村民個人利益的取舍問題;三是以杜濱才為代表的農村年輕人,父親患有精神病,母親因此改嫁,他自幼刻苦學習最終考入大學,向觀眾展現了農村年輕人為擺脫傳統的農村生活而不斷掙扎的現狀。三條主線,三家人的故事,在一年二十四節氣的順序中交錯出現,每條故事線都是一個獨立的脈絡,將其匯聚組織在一起不僅僅簡單再現了農村的景象,也更加深刻地突出了該片的主題內涵。
(三)人物塑造——深刻挖掘,樸實生動
藝術作品之所以感人,就在于作品中流露的真情實感,倘若創作者未把自身情感融入到所創作的作品中,那么他的作品是無法打動觀眾的。《鄉村里的中國》在追求真實的藝術風格的同時,也注重在作品中抒發導演自己的情感,表達自己的態度,由此塑造了一個個樸實而又生動的鄉村人物。
當“陽春白雪”遇到“下里巴人”。杜深忠的故事是該片的第一條主線,60歲的杜深忠是全片的“靈魂人物”,他與村里其他村民一樣,靠種田地栽果樹為生。但他又與其他村民不一樣,他愛好書法,熱愛音樂、讀書、寫作,他雖身型消瘦卻有著無比豐富的精神世界。他用毛筆蘸水在地上練書法,在欠債的情況下依然破費六百多元買了心心念念的琵琶,對于妻子粗俗的責備,他反駁道:“說彈琵琶是因為精神也需要補養”。作為一個農民,他對文化知識的興趣大于耕種,比起瑣碎的農活和家長里短,他更加關注的是自己的精神世界。杜深忠的這些喜好和追求與村里其他村民相比顯得格格不入,但在筆者看來他卻活得通透、活得明白。
當“集體利益”遇到村民“個體利益”。第二個故事是圍繞農村基層干部黨支部書記、村主任張自恩為中心展開的,張自恩要處理村里大大小小的各種事務,為村里綠化建設想方案,為農民銷售蘋果拉投資找渠道陪笑臉,解決鄉里鄉親之間吵架斗毆等雞毛蒜皮的小事,甚至被有些村民誤會,向上級舉報村里賬目問題,雖心生委屈,卻依然堅持為全村人民辦好事、辦實事。年底拿到1900元薪水的他,用自己的話說:“賺了一肚子的酒和一把辛酸淚。”
當“命運多舛”遇到“自強不息”。第三個故事圍繞著以杜濱才為代表的農村青年展開,杜濱才兩歲時父親杜洪法患精神病,母親因此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改嫁他鄉。杜濱才從小缺少父母的關愛,由伯父一家帶大,從小的經歷和家庭環境讓他的性格變得內向,但是他自小刻苦學習最終考上大學。在多次內心的掙扎后,與19年未見的親生母親見面,在母親的勸解下杜濱才慢慢理解父親,主動消除父子間的隔閡,并在村里2013年的春節活動上演唱了一首《父親》,送給自己的爸爸。
二、內在價值
(一)社會價值——根植鄉土,關注鄉村
紀錄片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它的客觀真實性,《鄉村里的中國》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體現了該片的社會價值。從宏觀層面來看,《鄉村里的中國》通過對杓峪村這個沒有經過任何修飾的依山而居的小村落生活原生態的記錄,呈現了中國農村的發展現狀。鏡頭聚焦于發生在這個小村莊的故事,基層干部工作難、薪水低等也是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問題。從微觀層面來看,《鄉村里的中國》真實記錄了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態,導演焦波通過多主線交叉敘事的手法,采用從局部到整體的記錄方式,向廣大受眾展現了社會發展進程中農民的生存現狀。片中杜深忠的人物形象打破了大眾對傳統農民形象的既定認識,他不操心瑣碎的農活和家長里短,卻對文化有著很高的自我追求,就像他說的:“人需要吃飯,精神也需要哺養,需要高雅的因素去填補,這才叫品位,這才叫素質”。通過杜深忠,我們不難看出我國飛速發展的社會經濟與農民精神文化需求之間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而影片中青年一代杜濱才刻苦學習、努力奮斗的故事則反映了新一代農村青年為擺脫傳統農村生活而不懈拼搏的精神。
(二)傳播價值——聚焦鄉村,引人深思
“早期的中國大型紀錄片在切入點上一般以民族自豪感、國家意志、歷史記憶和集體儀式為主,敘述者作為一種權威話語的代表處于傳播過程的核心地位”,類似于《鄉村里的中國》關注生活在農村、社會底層或者社會邊緣小人物群體的紀錄片是不多見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鄉村振興策略,把“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擺在國家建設的重要位置。鄉村題材紀錄片因此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格里爾遜曾闡述,紀錄片創作的首要原則是在現實中挖掘素材,并從熟悉素材的過程中自然形成故事,通過生活細節的并列,創造出對生活的闡釋。比起關注農民日常瑣碎的生活,鄉村紀錄片更側重于記錄農村時代的發展變遷,既要做好中國鄉村的“傳聲筒”,也要做好中國鄉村政策的“擴音器”。《鄉村里的中國》整片雖然沒有炫麗的場景畫面,沒有宏大的敘事手法,沒有精彩的解說與旁白,但卻以真實樸素的手法和客觀平視的角度向受眾展示了這樣一群返璞歸真的人物群像,帶給觀眾一種史詩般的震撼,引起受眾共情,在傳播過程中給受眾帶來正確的引導,并在其傳播過程中引發受眾深思,具有較高的傳播價值。
(三)藝術價值——質樸無華,返璞歸真
有學者認為,真正的紀錄片是“創作者根據自己對生活與自然所特有的認識和理解,以記錄真實為前提基礎,以現場拍攝為主要手段,對社會和自然中實際存在著的人、事、物及其思想文化內涵進行盡可能客觀、自然的記錄和真切、藝術的再現的影視片”。既然是藝術地再現,就要求紀錄片不能只是膚淺地流于記錄的形式,而應當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在“今天的紀錄片創作中,紀實主義的美學原則因為消耗性的使用而流于模式化,這背后是理性的缺席和責任感的逃避,只剩下故事化和所謂藝術化追求了,使紀錄片往往落入煽情、悲情或獵奇的窠臼,而日益淪為無關痛癢、閑適的茶余飯后談資”。紀錄片是映照生活的一面鏡子,通過《鄉村里的中國》,我們可以聞見泥土的芬芳,品嘗蘋果的甘甜,感受人性的樸實。在這個小鄉村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活法,不論是誰,他們的生活方式都是值得贊美的,這是鄉村生活中獨有的詩性美。
三、結語
中國作為擁有幾千年耕種文明的國家,對農村問題的關注是不容忽視的,無論是經濟拮據但仍追求精神世界的杜深忠,還是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的基層干部張自恩,抑或是從小遭遇不幸的杜濱才,無不反映出中國農民雖然窮、難、苦,但內心卻依然堅守信念,有著自己獨特的執著和信仰。《鄉村里的中國》秉持著以人為本的創作理念,以鄉村為題材,講述了鄉村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展現了鄉土氣息濃厚且原生態的鄉村生活面貌,具有很高的社會傳播價值。它在記錄農村發展變遷的過程中引發受眾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和反思,呼吁人們關注農村,關注鄉村發展,關注農民個體的發展與內心情感,體現出鄉村題材紀錄片的內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