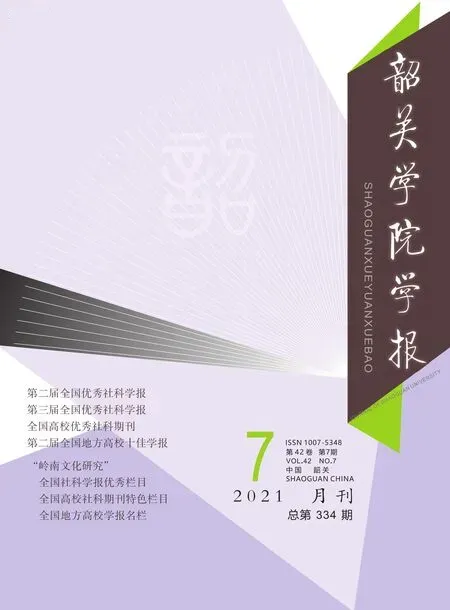我國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改革方向
汪夢龍
(阜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2020年12月26日,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在爭議中迎來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條件地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降低為12周歲。這一修改普遍被視為是對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惡性暴力案件頻發,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回應。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公布以來,關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聚訟焦點從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否要下調轉為新制度施行后的未來改革方向。主要觀點有彈性論、維持論和上調論。
一、彈性論觀點及主要理由
彈性論認為,我國刑事責任年齡不應在現有體制下繼續下調,應該借鑒類似英美法系“惡意補足年齡”原則的彈性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以彈性制度配合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再次下調[1]。
理由如下:
(一)修改后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仍未改正刑事責任年齡“一刀切”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失和
刑法第5條明確規定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即刑罰的輕重與社會的危害性程度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而刑事責任能力指的是行為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這兩種能力和年齡不是正比關系,只是不嚴格的正相關關系。這種正相關的不嚴格性,其程度之高,以至于我們不應當在衡量刑事責任能力的時候簡單地對這種偏差予以忽視,因此單獨以年齡這個因素替代刑事責任能力來決定免除行為人的罪刑是有失公允的[2]。不同地區、不同個體的青少年辨認和控制能力的發展程度差異很大,這個因素也不能被忽略,在現有體制下繼續下調刑事責任年齡并沒有改正“一刀切”的錯誤,沒有尊重不同個體的發展狀況,反而帶來了重刑主義傾向的危險。而破除現有的“一刀切”體制,以彈性配合刑事責任年齡的再次下調,既可以實現個案平衡,又可以有效降低下調刑事責任年齡帶來的重刑主義風險。
(二)應當重視社會年齡對刑事責任能力的影響
具體到確定刑事責任的年齡段劃分問題上,人的社會年齡比人的自然年齡更加具有參考價值。社會成熟年齡趨于低齡化,信息獲取途徑日益發達,知識日益豐富,未成年人能夠認識和控制自己行為的時機越來越早,青少年犯罪低齡化就是證據。彈性化可以在堅持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更好地兼顧行為人的社會年齡。
(三)更符合主客觀相一致的要求
無視未成年人的社會年齡,而簡單地以自然年齡作為衡量刑事責任年齡的標準,對其作出主觀惡性小的推斷,進一步認為他們作為犯罪主體不適格,不追究刑事責任,這體現了單純主觀出罪的傾向。“衡量犯罪的標準就是它的社會危害”[3],雖然貝卡利亞此言有單純客觀歸罪之嫌,但足以說明客觀危害在判斷刑事責任的過程中的關鍵性。只有尊重主客觀相一致的要求,重視未成年人犯罪對社會的嚴重危害,才能更好地實現社會公正。
二、維持論觀點及主要理由
維持論是目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這一部分學者認為,修改后的刑事責任年齡不需要改變。
理由如下:
(一)修改后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已經較好地實現了預防懲治犯罪和保護未成年人的統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并不是直接下調了刑事責任年齡,首先,只有犯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且情節惡劣的情形下,才能對12至14周歲的未成年人追訴。其次,追訴權必須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方得行使,這從實體和程序兩方面對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附加了強大的限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濫訴的風險。另外,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調了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對12到14周歲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威懾作用是已經具備的,“達摩克斯利之劍”已經祭起[4]。
(二)12歲是較為合理的刑事責任起點年齡,事實上已經體現了“惡意補足年齡”原則
就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水平而言,12歲未成年人有能力對嚴重社會危害性行為進行辨認,也基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為,將刑事責任年齡下調至12周歲具有合理性。而刑法修正案(十一)規定的“情節惡劣”的實體要求和“最高檢核準”的程序要求,事實上已經明確了由最高檢對行為人的“惡意”進行判斷的要求,已經可以看作是“惡意補足年齡”原則同我國實際的結合[5]。
(三)刑法應該有足夠的穩定性
維持論者認為,14歲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是社會轉型期內一時的社會現象,為了回應這種現象引起的社會關切,我們對已經擬制并且成熟運用的法律進行了觸及原則性的修改,可以說已經是現階段綜合各方面因素的“最不壞的方案”[6],不宜再輕易上調或者下調刑事責任年齡。法律應當以穩定為原則,以修改為例外,特別是刑法,作為社會規范的最終底線,其修改應當要堅持謙抑性原則,能用其他手段的,輕易不應動用刑法。單純追求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繼續降低,不但不能從根源上解決青少年犯罪的問題,還會引發人們對罪刑法定原則受到挑戰的擔憂。
三、上調論觀點及主要理由
持有上調論觀點的學者比較少,其主要理論依據是刑法謙抑性原則和國際國內的輕刑化刑法改革趨勢。還有學者認為,在輕刑化的大背景下,此次刑事責任年齡的下調本身就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權宜之計,終究是應該回調的。這一觀點支持者甚少,主要是因為理論根基過于薄弱,僅以刑法謙抑性原則和輕刑化趨勢作為理由,缺乏更為具體切實的理論構建,且有朝令夕改之嫌,終究難以服眾。
四、對彈性論和維持論的辯證
彈性論和維持論各有各的道理,筆者認為,現行規則遠非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改革的完全體,更像是一個過渡的階段。然而領先時代一步的是天才,領先時代十步的是瘋子。維持論者之所以能夠占據主流,并不是因為大部分學者看不到現行制度仍有不足,而是因為法律終究是經世致用之學,只有放在社會的土壤之上才會有生命力,以我國當前的司法力量,如果強行適用“惡意補足年齡”原則,難免陷入重刑主義。兩害相權,寧肯背負抱殘守缺的嫌疑,也不可再輕易改動。但這種審慎的態度是符合法治要求的,應當被贊揚的。
筆者整體上贊同彈性論,現行制度在一定時期內稱得上較為完善,但是這不應限制我們對未來的設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進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另一方面,我們要正確看待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它并不是洪水猛獸,而是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內在要求。事實上,“惡意”屬于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方面,而現實中每個案件的判決都需要法官依據客觀方面的外在表現來對行為人的主觀方面進行高度蓋然性推斷,刑法分則中也有許多罪名附加有“情節惡劣”的條件,因此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對行為人的“惡意”進行判斷一直有跡可循,從根本上來說這并非是對現有體系的突破。當然,真正要實現“彈性論”,仍然需要結合司法體制改革、社會矯治、親權管教法制化、學校和社會的人格品德教育等問題的解決,從社會綜合治理的視角,以科學和耐心逐步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