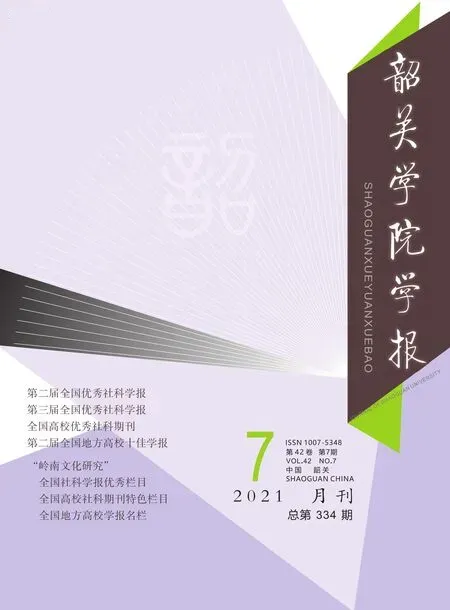具身認知研究評述
王禮申,謝麗芳
(韶關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也稱為“涉身認知”“居身認知”,該理論強調了身體在認知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它重新定義了身體、認知和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啟發人們從身體和環境的角度看待認知,為認知科學的研究帶來了全新的視角,因此成為第二代認知心理學的研究熱潮。在國外研究熱潮的推動下,我國學者也開始關注并加入具身認知的研究行列。因此,整理具身認知現有的實證研究,梳理具身認知的理論發展,評析具身認知的發展現狀,提出具身認知的未來路向,對后續研究者全面地認識具身認知具有重要意義。
一、具身認知的理論源起
具身認知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雖起步較晚,卻有著深厚的思想淵源。西方哲學中具身思想最早出現于胡塞爾提出的“意向性”“生活世界”“身體”“軀體”等概念的區分;身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哲學基礎源于海德格爾的“此在”“在世之在”等觀念的提出。具身認知的直接思想來源是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1]。身體現象學認為,人們借助身體感知世界,因此身體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基礎,而身體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人們的行為,認知、身體和世界是相互統一的[2]。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墨家、法家、儒家和道家等學派均對身心關系做了一定的闡述,如墨家“君子力事日強,愿欲日逾,設壯日盛”和法家“其上世之士,衣不眗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均體現出具身認知思想。明代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更是具身認知的集中體現[3]。
具身認知的思想雖早已萌芽,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導人們思維方式的是柏拉圖和笛卡爾論證的身心二元論。主張身體與靈魂相互分離的身心二元論,成為人們探索身心關系的思想桎梏。20世紀50年代,計算機革命推動了認知心理學的興起。認知心理學研究人的高級心理過程,主要是認知過程。隨著認知心理學的興起及其各領域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身心二元論的局限性。認知具有主動性、情境性,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身體角度看待認知過程,從而推動了具身認知的興起。隨后,鏡像神經元的發現為具身認知奠定了生物學依據,神經生物學家里佐拉蒂(G. Rizzolatti)以猴子為研究對象,發現了可以將外界動作投射到自身實施行為的鏡像神經元[4]。鏡像神經元在動作執行和動作知覺兩個階段被激活的實驗佐證了大腦功能整體說和認知的具身特性[5]。
具身認知興起后,瓦雷拉(F. J. Varela)、湯普森(E. Thompson)等西方學者紛紛開始投身于具身認知的研究。在國外研究熱潮的推動下,我國學者李其維、葉浩生等也逐漸關注并加入了具身認知的研究隊伍,肯定了認知對身體的依賴和身體在認知過程中的根源性,強調了身體的認知功能和認知的物理屬性[6]。具身認知在哲學思辨、概念隱喻、具身教育觀、新認知觀等方面的研究得到極大的豐富和完善。
二、具身認知的理論特征
雖然不同學派和領域在反對傳統認知心理學的身心二元論上達成共識,但是對具身認知的定義和理解仍缺乏統一明確的觀點。目前學界認可度較高的定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具身認知主張身體的生理結構、活動方式、感覺和運動體驗均會影響人們的認知過程[7]。此觀點強調身體及感覺在認知過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廣義具身認知主張認知來源于身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8],該觀點不僅強調了身體在認知活動中所起的作用,還強調身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根據國內外現有具身認知理論,可將其理論特點概括為認知的具身性、認知的情境性和認知的動態性[9]。如今,無身性的觀點導致了傳統認知主義逐漸走向瓶頸,“身體參與認知”成為學術共識,從而引發了由傳統認知主義到具身認知的轉向,無論是心理學的發展還是哲學的發展,“身體”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起承轉合作用。
(一)認知的具身性
認知的具身性是指身體的生理結構和各種感官體驗會影響認知的形成。最有力的佐證就是概念形成和隱喻。如“高”這一方位詞位于身體的上方,需要仰視才能看到,需要跳躍才能夠著,所以“高”被賦予向上的積極隱喻,體現出人們對身份或品行的追求,如“高貴”“高雅”。與之相對的是被賦予消極隱喻的“低”,如“低賤”“低俗”。Valenzuela和Raghubir發現,消費者對貨架上的商品進行估價時,傾向于把高層貨架上的商品判斷為高價奢侈品,把底層貨架上的商品判斷為低價商品[10]。
(二)認知的情境性
認知的情境性指認知來源于身體在特定情境下的體驗,受情境的影響。認知具有情境性這一特征早已體現在建構主義學習理念中,建構主義強調學習者的知識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幫助(如協作、交流),利用必要的信息,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獲得的。Schnall等人在實驗中讓被試在惡臭的垃圾桶旁填寫問卷,結果表明惡臭的環境會使被試的道德判斷更為嚴厲[11]。具身認知重視教學情境的創設,重視學生的身心體驗,關注學生的自我構建,可以糾正目前情境教學中存在的誤區,對情境創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12]。
(三)認知的動態性
認知的動態性指時間、身體和環境的交融會影響和促進認知的調整與發展。很多駕駛新手最初感知范圍往往局限于身體直接體驗到的駕駛室內,難以把控車身與外界物體的距離,容易發生碰撞和摩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與車似乎形成了一個整體,車身也慢慢成為司機的感覺外延,司機也可以清晰地感知車速和距離[13]。瞿春紅在教學研究中發現,當亂丟垃圾的學生置身于臟亂的環境中,體驗過自身行為帶來的不適感受后更能激發其糾正亂丟垃圾等不良行為的意識。若教師加以引導和督促,一段時間后,可以幫助學生樹立愛護環境的意識,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14]。鄭旭東、王美倩在具身認知語境啟發下,把學習環境的構建視為一個自組織的整體重建與動態生成過程,并確立了相應的生成教學觀,從而推動著學習環境的基本觀念從機械的靜態預設走向有機的動態生成[15]。
二、具身認知的研究范式
具身認知理論的多樣性啟發并促進了學者在不同領域的思考,包容并接納不同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實驗范式,并不斷豐富和完善。目前具身認知的實證研究主要有情境操縱法、內隱聯想測驗、心境誘發法等實驗范式。
情境操縱法是指研究者通過指導語或操縱實驗中的變量,激活被試的特定身體感覺,進而影響被試的心理感受或行為傾向。高建偉在研究甜味體驗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實驗中,采用實驗室情境操縱法,將被試隨機分為兩組,實驗組被試喝下甜溶液,對照組喝下白開水,隨后讓被試填寫親社會行為問卷。結果顯示甜味組的被試比非甜味組的被試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16]。
內隱聯想測驗是指研究者在實驗中為被試提供兩組材料:概念詞和屬性詞,要求被試對概念詞和屬性詞的匹配程度作出相容或不相容的任務判斷,根據被試的反應時長,判斷概念詞和屬性詞的聯系程度。閆謹在探究空間位置對權利概念的影響實驗中,要求被試對詞語和空間位置(詞語共52個,其中強權詞和弱權詞各26個;空間位置為上和下)進行相容和不相容的任務判斷,發現權力詞語出現在屏幕頂端(上)時被試對強權詞的反應要快于弱權詞,權力詞匯出現在屏幕底部(下)時被試對弱權詞的反應要快于強權詞[17]。
心境誘發法是指讓被試想像或回憶某一情境,從而誘發被試特定的心境或情緒狀態的實驗方法。劉靜等人在探究保守秘密對自身體重主觀判斷的影響中,采用心境誘發法,將被試隨機分為三組,分別回憶專注秘密、非專注秘密和非秘密事件,隨后完成自身主觀體重的知覺判斷任務。實驗結果顯示,專注秘密組被試報告的身體重量顯著高于非專注秘密組和沒有回憶秘密事件組[18]。
雖然實驗方法不盡相同,卻證實了認知、身體和環境之間的緊密聯系,三者密不可分,相互影響。標新立異的研究思路和不拘一格的實驗方法給具身認知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與生機。具身認知的實驗結果也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和理解具身認知,將其運用于不同的領域。
三、具身認知的實踐應用
(一)教育領域
在具身認知理論的指導下,學者們針對教育培訓提出了具身學習的概念,為教育培訓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指導。具身認知不僅被應用于學校學科教育(包含音體美和心理健康教育),還有特殊人群、農民、教師等非學生群體的培訓教育。具身認知理論啟發教育者在教育教學中樹立學生為主體的教育觀,營造情境性的教學環境,創設多感官參與的教學活動,增強學生的體驗性。耿敬北、韓青認為基于具身認知的小學英語教學模式應該包括制定具身性的教學目標,創設參與性強的情境性教學環境,分析學習內容和學習者的具身特點,設計調動多感官參與的課堂話語,鼓勵學生在學習中自我模擬,建構多元化教學評價方式[19]。
劉海萍基于具身認知理論,從身體的角度總結出學校管理的改進策略,在教學管理中理解學生的身體自由,克服反身性;弱化對身體的規訓,強化身體的參與;重視學生在管理情境中的理解[20]。
國際學習科學領域著名學者亞伯拉罕森教授指出:具身認知理論受到認知發展心理學和社會文化理論的影響,不僅是一種重新看待教與學的方法論,還是一種能夠發展獨特學習理論的認知論[21]。他在學習科學領域中引入具身設計,為特定教學情境設計人工制品,為具身認知理論應用到教學設計中提供了設計框架,并將其分為基于感知的設計和基于動作的設計兩種類型。
(二)產品設計
人是產品的使用主體,人的需求和主觀感受是產品設計和改進的動力。因此在產品設計時,考慮身體的特點和感受,可以提升用戶體驗。具身認知理論引導產品設計者在產品研發和設計時,結合使用者的身心發展規律和特點,豐富身體感官的參與性,優化身體的體驗性,適當引入新技術。Ventre-Dominey等人在實驗中發現增強機器人與人類身體感官互動方式的相似度,如追蹤和模擬人類頭部運動以獲取3D視覺情景,可以提高人們對機器人的接納度[22]。
(三)心身治療領域
具身認知思潮的興起也為人們提供了新的視角看待和理解心理疾病,為人們治療心理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具身認知理論啟發治療者在看待和理解心理疾病時,應該關注身體,提高身體在治療中的參與性,發揮身體的認知作用,提高治療的療效。Harbourne和Berger對20名發育遲緩或腦性癱瘓的兒童分別進行身體運動和輔助運動兩種干預,結果顯示,身體運動干預可有效提高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23]。
(四)道德判斷領域
傳統的道德認知與判斷強調理性的作用,隨著具身認知思潮的興起,身體的體驗與感覺在道德的概念形成和判斷中所起的作用也逐漸被人們所認可。具身認知理論從客觀存在的身體和情境來探討主觀的道德概念形成和判斷規律,幫助人們在作出道德判斷時可以規避客觀因素的影響,在司法決策中公正地作出判斷。Zarkadi和Schnall在研究中發現黑白條紋的背景相比灰色和藍黃線條的背景更能誘發人們“非黑即白”的道德隱喻,從而作出極端化的道德判斷[24]。
四、具身認知的評析與反思
具身認知目前已經成為國內外的研究焦點。隨著對具身認知研究的不斷深入,具身認知的發展也出現了困境,主要表現在理論、實證和方法論三個層面[25]。
相關研究推動了具身認知的發展,也豐富了具身認知的理論內涵。但由于對具身認知的理解各異,理論背景、研究取向、實驗方法等各不相同,使得具身認知的理論難以統一,呈現出散漫雜亂的現象。這影響了人們對具身認知領域所取得的成果作出合理的評價,甚至成為其理論效力和實際影響力擴展的阻礙。具身認知的興起與發展,離不開相關實驗的佐證,如“耳機舒適度測試”等經典實驗曾有力證明了身體參與在認知過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為具身認知吸引了大量研究者與擁護者。近年來,學者們提出了新的研究視角和方式,也開始回顧具身認知的經典實驗。“面部反饋”實驗結論證明面部表情可以影響人們的情緒,這符合具身認知的理論假設。當研究者重新審視“面部反饋”實驗時,有17個實驗室分別獨立重復了該實驗,但結果均與原實驗結論相悖。同時,實驗中難以避免的主試期待效應也被提出,具身認知實驗陷入了難以重復驗證、難以擺脫期待效應的困境。由于對具身認知的理解和觀點不一致,在其發展中出現了還原主義和物理主義傾向。部分學者過分擴大身體在認知過程中的作用,貶低大腦內部的認知加工過程,使具身認知回歸了行為主義觀點。同時,缺乏實踐支撐的具身認知也面臨著二元論、形式主義或生物主義等方面的質疑。因此,在方法論層面,具身認知具有物理主義和還原主義困境。
五、結論
具身認識推動了第二代認知革命的發展,帶來了全新的研究視角,豐富了心理學的理論,促進了不同領域的發展。面臨發展困境,具身認知應在理論層面加強理論統一性和兼容性,借助確切的實驗或數據加強重復性和驗證性充實其實證證據,并運用正確的方法論指導,在實踐中客觀總結,才能發揮其應有的理論效力和實際影響力,以期獲得更廣泛認可及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