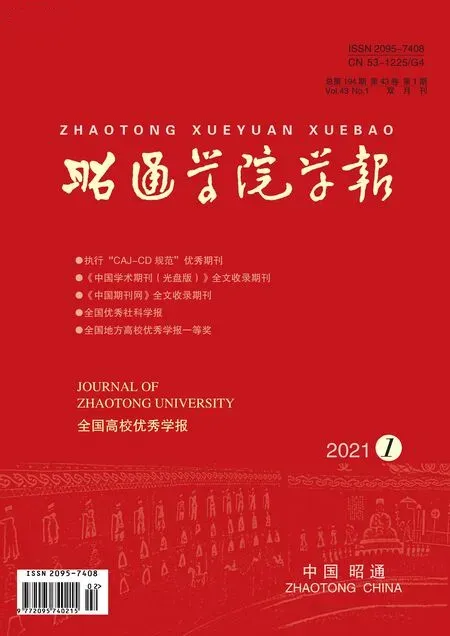從《筱園詩話》與《詩法萃編》看云南近代主流詩學觀念
王 萌,李金澤
(山東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清詩是足以與唐詩、宋詩比肩的又一座高峰,其表現不僅在于水平與范式的成熟,更在于詩人與詩歌數量之多,詩教遍布之廣。云南受到漢文化影響的時間雖然比較晚,但到了清朝,也已經形成了非常成熟的詩歌寫作群體,這從清朝編纂的幾部云南詩歌總集中就可以看出。云南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嘉慶、道光年間保山袁文揆、袁文典兄弟匯集同人編纂的《滇南詩略》,包括《明滇南詩略》《國朝滇南詩略》《續刻滇南詩略》,收錄清嘉慶、道光以前及明代滇南詩人詩作。繼之者為五華書院掌院黃琮,輯《滇詩嗣音集》,收錄嘉慶、道光年間詩人詩作,之后又有許印芳輯《滇詩重光集》,收錄道光至光緒年間百余家詩作,惜僅刻錄至十八卷許印芳便撒手人寰,幸有袁嘉谷、趙藩等人繼刻剩余的一百多部詩稿于《云南叢書》《滇詩叢錄》。至此,云南古代漢詩文幾乎被網羅殆盡,詩人以千記,詩作以萬計。除了興盛的詩歌創作,總結詩歌創作理論的詩文論著也在清代的云南詩壇出現了。據云南大學古典文獻叢書《云南古代漢文學文獻》統計,現已知的云南古代詩話有二十多部,見存者十余部。現存最早的云南古代詩文論著是康乾時期師范所作的《蔭春書屋詩話》。主要活躍在同治、光緒年間的朱庭珍、許印芳的詩學論著《筱園詩話》與《詩法萃編》為云南古代詩文論著中篇幅最長、影響最大的兩部。許、朱二人是近代云南詩壇執牛耳者,門生弟子眾多,培養出了諸如袁嘉谷、李坤、孫文達等云南近代詩壇著名詩人,研究對比《筱園詩話》與《詩法萃編》,可以幫助我們在詩歌理念上對近代云南詩壇有一個整體的把握。
一、《筱園詩話》與《詩法萃編》之成書
朱庭珍(1842-1903),字筱園,石屏人。光緒戊子(1888年)科舉人,除《筱園詩話》外,還著有《穆清堂詩鈔》《穆清堂詩鈔續集》等。石屏朱家人才輩出,有一門三進士的佳話。筱園工詩能文,盡得家傳,自幼以詩名。朱庭珍曾為五華書院監院,又閱卷經正書院,詩學追隨者眾多。袁嘉谷《臥雪詩話》有言:“當時朱筱園先生主持文衡,作者多模朱派,故詩句大體類似,然各能生造,可謂一時之盛。”[1]309在同治三年(1864)仲冬月朔所書自序中,朱庭珍自述《筱園詩話》的寫作源于郡中同人登門請教詩法,此后十余年歷經三次修改始定,他對于詩道延續的自覺承擔,盡都包含在這十數年的深思熟慮之中。《筱園詩話》說理詳細透徹,又融眾家之長,蔣寅在《請詩話考》中評價其:“所述雖無甚創見,然有綜合古今之長,深化傳統命題,集前人詩論大成之氣象,于清詩話亦不多見。”[2]596
許印芳(1832-1901),字茚山,一字麟篆,號五塘,有《詩法萃編》《詩譜詳說》《律髓輯要》《五塘詩草》等,纂《滇詩重光集》。許印芳一生的精力大都傾注在了與詩歌有關的活動中,曾受聘于經正書院主講席,擁皋比六年,門生弟子人才輩出,晚年掌管石屏玉屏書院,大力倡詩,對當時云南詩壇影響之大不難想見。《詩法萃編》是許氏詩歌思想的總結,自序作于光緒十九年(1893),書當成于此年。不同于一般的詩文論著,許氏在此書中收羅了自漢至清的論詩文章及著作幾十種,并為其題寫了大量的按語和跋語,以此來表達自己的詩論觀。生于末世,又親身經歷兵禍,許印芳逐漸形成了通達求變以合于時用的經世思想,這也對他的詩學觀念產生影響。袁嘉谷在為許印芳《律髓摘要》所作序言中評價許氏論詩導源三百,兼采眾長,不囿一格,[3]315可謂得是。
二、《筱園詩話》與《詩法萃編》基本詩歌理念
許、朱二人的詩論有許多相似之處,在傳統詩教觀的指引下,兩人對于學詩者有著同樣的尚實求變、重學重識的要求,此外,他們能夠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古代詩歌史,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學詩應轉益多師,靈活運用詩法的觀點。
(一)詩教觀
許印芳維護傳統詩教溫柔敦厚,委婉含蓄的詩歌風格以及其感物、美刺的作用。在《附錄宋人雜說跋》中,許印芳有感于宋人寫詩得禍,將行使美刺作用的詩歌分為六等,上三等分別是“婉諷:委屈譬喻,無一直致語”[4]206;“譎諫:比興依違,言在此而意在彼”[4]206;“實錄:摭實鋪陳,不著議論,使人讀之,其失自見”[4]206。下三等分別是:“啁謔:形容人短,以資笑談”[4]206;“丑詆:緣飾罪狀,惡言排訾”[4]206;“絞訐:攻發陰私,壞人名節”[4]206。他認為刺惡之詩不是不可以寫,但要注意方法,如上三等詩皆溫柔敦厚,不至于為詩人招來禍患;而下三等詩卻猶如蜇人的蜜蜂,既發怨毒,也為自己招來禍患。朱庭珍也認為溫柔敦厚是詩教之本。他舉出袁枚與趙翼的例子,說他們互相標榜又互相諷刺,雖是游戲之筆,而筆端刻毒,有違詩道。
基于對溫柔敦厚的傳統詩教的維護,在賦比興的傳統詩法中,許印芳和朱庭珍都更偏愛比興。朱庭珍認為比興能言不敢直言,不便明言,不忍斥言之意,使詩品溫柔敦厚,詩情纏綿悱惻,如果一味用賦,直陳其事,則太過直露。[4]268許印芳也在《<文心雕龍·比興>跋》中說:“比興為詩家奧境。詩之賦篇,每不及比興之善。”[4]283可見二人主張傳統詩教的溫柔敦厚,婉諷譬喻。
(二)尚實求變
許、朱論詩皆不喜空疏之作,強調真實,試以二人論“神韻”說證之。許印芳在《<帶經堂詩話>跋》中批評王漁洋以嚴滄浪的妙悟空靈之說解釋詩歌中的興會現象不夠精切。許印芳認為興會是依附于實情實境的,所有的興會之情都是由日常生活中的真實事物生發而來的。如果以妙悟空靈之說解釋興會,就是把詩中之實境變為虛境,也就落入了空腔滑調的窠臼。[4]172許氏還批評王漁洋詩好修飾字句,顯得外重內輕,形貌盛而神骨衰。從這些批評中可以看出許印芳并不反對興會、妙悟之理論,但強調詩歌必須本自實境,言之有物。朱庭珍也批評了這種只求形似,色澤濃艷,詞意偕俗的“假”神韻詩。他認為詩歌之神韻應該是在秉持真我的內核下,追求“興像玲瓏、意趣活潑,寄托深遠,風韻泠然”[4]271,而不是故作不切題意之語,別生枝節,在外則辭藻濃艷,欲說還休,在內則空虛沒有實質。
尚實之外,二人論詩皆重變化,是否在學習前人的基礎上做出適合自己的變化是他們評價詩歌的重要標準。許印芳論及王漁洋 “我朝王文簡公……所為詩,亦拘守唐格,不知通變,為后世所譏。”[4]181朱庭珍與許印芳看法相同,他將歷朝詩人分為大家、名大家、名家、小家等,王漁洋執掌吟壇數十年,以神韻為正宗,朱庭珍評價其詩歌取徑正途,落落大方,但仍舊詬病其只知奉法,未能窺見變化,富于取材而不知獨造,所以“未足副大家之實,為后人取法也”。[4]283“變化”的觀念其實來源于二人論詩法的部分,許印芳在《詩法萃編》序言中提出,為詩文不可泥法,要得法外意,“善用法而不為法所困”[4]149。朱庭珍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可總結為“活法說”,這在后文還會有論述,此處不再展開。
(三)重學與識
許、朱論詩還都強調詩人的自身修養,對“學”與“識”尤為重視。滄浪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5]23-24后人對滄浪此語多有誤讀,廢書而空談妙悟,許印芳和朱庭珍專門糾正了這種誤讀。許印芳說:“此正從妙悟指示學者,非教人廢學。故又云:‘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學人胸中書理既多,因疑而悟,愈疑愈悟,妙緒旋抽,別材別趣,緣此而有。淺人誤會其旨,竟欲廢書,以悻弋獲,謬矣妄矣。”[4]178在《詩法萃編》序言中,許氏也曾告誡初學,只有先“邇孝遠忠,厚培詩本;枕經胙史,深養詩源”,再取《詩法萃編》,習之察之,熟之復之,漸進頓悟,融會貫通,靈活運用,才可能把詩寫好。[4]150朱庭珍也在《筱園詩話》里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強調詩人之第一要義在于“培根柢”,即通過讀經、史“積理養氣”:[4]261讀經要明義理,辨典章名物;讀史要對歷朝之賢奸盛衰、制度建置及兵形地勢等進行深入的思考,以此明白成敗盛衰因革之理……同時,在生活中也應隨時留心,洞悉人情世故、物理事變,與所讀之書交契會悟,豁然貫通。只有這樣,才能“積蓄融化,洋溢胸中,作詩之際觸類引申,滔滔泳赴,本湛深之名理,結奇異之精思,發為高論,鑄成偉詞,自然迥不猶人矣”。[4]262
值得注意的是朱庭珍對“學”的兩個錯誤方向還有進一步的引申解讀,首先是對“廢學者”的批評,集中體現在對袁枚及其《隨園詩話》的批評上。他批評性靈派作詩無根柢,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疏而易于模仿,自袁枚之后“流毒天下,至今為梗”。[4]290其實袁枚未必有筱園所批評的那么不堪,只是當時詩壇確有一股淺薄無根柢的空疏浮泛之詩風,年輕人多效仿者,筱園關心則亂,態度過于激烈也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是對如翁方綱所提倡之肌理派的“學人之詩”的批評,他認為這類以學為主的詩人,往往貪多務博,在詩里堆砌書卷,不知道學問之道貴在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4]259因此,他也反對詩中入“經書板正古奧語”、“子史僻澀語”、“道學理語”,這些都在他所務去的陳言之列。
對于才、學、識三者間的關系,許印芳和朱庭珍的看法也基本一致。針對嚴羽所說“學詩以識為主”,許印芳評曰“語尤中的”。[4]178許、朱二人都認為作詩如作史,才、學、識要三者兼長,但最重要的是識,識見未真而才學兩廢。[4]267至于如何增長識量,許印芳并沒有單獨說明,朱庭珍則強調識量的培養只能依靠詩家真傳,學詩光看詩話是不行的,還必須要虛心請教于名師巨手。[4]178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文章可以記錄詩人的觀點,但詩人的精神、氣度卻是文章難以表達盡的,只有親自與之交談、跟隨其學習,才能夠受其氣度之潛移默化,漸漸培養成自己之識量。此外,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語言大多是感受式的,有些論點不僅難以理解,而且容易產生誤讀,這也是筱園堅持學詩必須請教名師巨手的原因之一。
(四)轉益多師
在對歷朝詩歌的評價以及學詩取徑上,許、朱二人也極為相似。在許印芳建構的詩歌體系中,《詩經》與《楚辭》為后世提供了四言與雜言,是源頭一樣的存在,后世詩歌的變化均可追溯至此,它們既是“詩源”,也是萬世所習之“詩法”。許印芳認為學詩必須有法,但不可泥于法,貴在得法之意,善用法而不為法所困。[4]178以歷代詩歌而言,詩三百和楚騷,一為四言,一為雜言。漢樂府眾體具備而雜言益夥,詩法出奇無窮。魏、晉、宋時期,人們好尚五七言,四言和雜言開始衰落。齊梁人偏講聲病,陳隋變本加厲,詩法愈加狹隘且卑下。唐人沿用五七言,又別齊梁體為律詩,還參用四言和雜言,真正做到了匯聚眾妙,所以許印芳評價 “唐詩有復古之盛,卓然為百代楷模。”[4]149對宋詩以及明人的詩歌復古運動,許印芳評價不高,他說宋詩盛極難繼,“盡翻窠臼、變態百出”, “古意浸微”。[4]149明七子提倡復古,距漢規唐,字摹句仿,只學成了偽體,沒有得到其中真意,“古意浸亡”。[4]149在《附錄明人詩話跋》中,他又對前面的評價做出了補充,提到唐宋人詩皆各有所長,“宋詩足匹唐人”[4]229所以他告誡后學“學詩以多讀書多窮理為根柢,而取法最后,二人都能夠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古代詩歌史,進而主張轉益多師,靈活運用詩法,這基本可以代表近代云南詩壇主流的詩學思想。
三、結語
許印芳與朱庭珍生于道光,長于咸豐,活躍于同治、光緒年間,同時期的詩壇上有許多活躍的詩派與詩人。湖湘有漢魏六朝詩派,代表詩家王闿運只比許印芳小一歲。雖然同光體的代表詩人陳三立比許印芳小二十一歲,鄭孝胥更是比許印芳小了二十八歲,但宋詩運動早在曾國藩寫出:“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同光體是繼續這個運動的產物。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以黃遵憲為代表的詩界革命派,以樊增祥、易順鼎為代表的中晚唐詩派。然而許、朱所代表的云南近代主流詩學思想不同于以上任何一家,顯得中正平和,頗有總結中國古代詩歌思想之氣象。
云南近代詩學思想所表現出的獨特性,大概與云南僻處天南,交通不便,與中原詩壇交流不夠通暢有很大關系。因為交流不暢,所以不容易受到不同詩歌主張的影響,更傾向于在自己的一番天地中體悟與反思歷朝詩歌得失,心態也趨近于中正平和。同時,太平天國運動剛剛平復,云南又發生了歷時十余年的杜文秀起義,許、朱二人都是親歷者,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容易形成通達求變以合于用的經世致用思想,在此影響之下,詩學思想也容易呈現出“通變”的面貌。此外,無論是國家之危局還是地方之危局,作用到詩歌,都會產生一股清洗浮膩詩風的潮流。漢魏六朝詩派在湖南肅清了學習袁枚性靈派的風氣,宋詩派對濃膩浮華的乾嘉詩風有逆轉作用,同時期的朱庭珍和許印芳也在詩論著作中批評神韻說與性靈派,力矯空疏滑膩的詩風,說明當時不同地區的詩人都感受到了時代的變化,詩道由空轉實,這是中國古代詩歌面對危難的時局所作出的共同應對,正如朱庭珍所說:“天不能歷久而不變,詩道亦然。”[4]259漢唐,更當上溯風雅以養其源,下攬宋金元明以參其變。”[4]181
朱庭珍對歷朝詩歌的評價也很通達。他認為一代詩歌,有盛必有衰,最初總是由真正的學問之士開創局面,逐漸發展至于鼎盛,后學者才能不足,囿于門戶之見,衰敗伏于其中,此時又會有才學之士力矯時弊,開創新的局面。這種詩道循環進化的觀念正與同時代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闡述的時代思潮變化規律相似。在此基礎上,朱庭珍從兩漢談起,歷數各朝各代獨領一時風騷的詩歌風潮,論其長短,各有所取。對于宋詩,朱庭珍也肯定了幾位大家,惟對江西詩派意見頗多,認為此派“推崇山谷,而槎丫晦澀,百病叢生,既入偏峰,復墮惡趣。”[4]260又批評江湖詩派“鄙俚不堪入目”[4]260。對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朱庭珍也嘲諷為“優孟衣冠”。基于此,朱庭珍教導后學應該縱觀古今詩歌,取長棄短,融貫、變化,別鑄真我,集詩之大成。如何變化?朱庭珍提出了與許印芳類似的活法說:“詩也者,無定法而有定法也。”[4]258所謂有定法是自古以來一直為詩人所運用的基本技巧,如起伏承接、轉折呼應、開合頓挫、擒縱抑揚、正反烘托、伸縮斷續等;無定法就是詩人對這些基本技巧的靈活運用,即相同的方法技巧,有時錯綜運用,有時變化運用,有時明用,有時暗用,有時正用,有時反用……作詩者應當以我運法,不為法用,開始以法為法,后續則以無法為法,“無法之法,是為活法妙法”。[4]258
綜上所述,作為近代云南兩位詩壇導師,朱筱園和許印芳在基本的詩學觀念上達成了共識,即:維護溫柔敦厚的傳統詩風,并不否定詩歌的美刺功能,但強調婉諷;論詩尚實,許印芳不喜神韻說的空疏,卻也不反對興會、妙悟,主張源于實情、實境的興會、妙悟,朱庭珍也對神韻說導向空疏的陷阱進行了解說與提醒;論詩求變,從對王漁洋詩的相同評價可以看出他們對學詩之路上別鑄真我,求新求變的要求;重視學識與識量的培養,厚養經史,讀書窮理,請教名師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