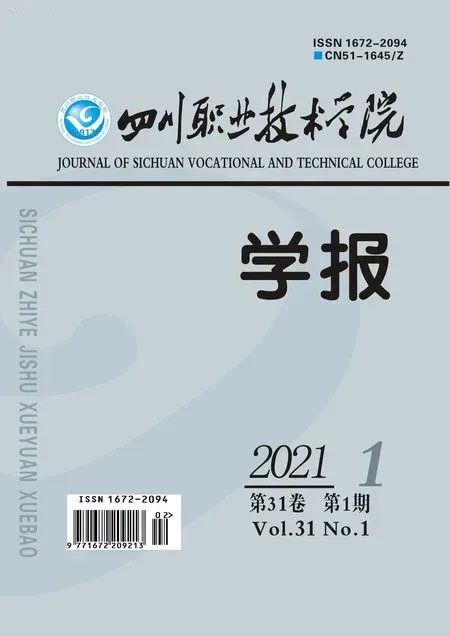安大簡《詩經》與《毛詩》的章次差異初探
鄭婧
(西南大學 漢語言文獻研究所,重慶 400715)
2019年9月21日,《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簡稱“安大簡”)第1輯[1]正式發布。作為戰國早中期的抄本,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詩經》版本。簡本《詩經》58篇中有14篇與現存《毛詩》章次排列不同。
關于安大簡《詩經》與《毛詩》的章次差異,學界多有討論。黃德寬指出:“簡本與《毛詩》的章次也造成一部分異文,這些差異是否體現詩意的差別,尚待深入研究。”[2]呂珍玉認為,安大簡進一步證明了《詩經》的重章疊唱,只要合乎押韻,章的安排在當時可具有隨意性。[3]王化平師注意到安大簡《詩經》章序與《毛詩》不同之處在于,一般是以章為單位發生變化,且很多時候是二、三章之間的變化。他表示:“這與詩歌的音樂性相關,也有可能與抄寫格式相關。”[3]網友“汗天山”指出:“安大簡本《詩經》章序多有與《毛詩》不同者,很多詩篇的章與章之間是并列關系,次序顛倒對詩旨并無任何影響。”[4]趙海麗《安大簡本〈螽斯〉章次探賾》指出,安大簡《螽斯》與《毛詩》相較,二、三章相互錯置,根據詩旨梳理及章次順序的考察分析,認為安大簡是一首用于祝禱子孫眾多的樂歌頌詩;從音韻方面,安大簡以陽聲收尾,較《毛詩》以入聲收尾,在情感表達上更音調暢陽;綜合而言,她認為簡本《螽斯》章次較《毛詩》合理[5]。寧登國、王作順《安大簡〈詩經?江有汜〉異文的解題價值》表示,《江有汜》簡本二、三章與《毛詩》互換后更符合嫡妻感情變化過程,可證《江有汜》為單純的“美媵”詩無疑[6]。
鮑則岳在研究早期詩歌文本問題時,曾提出“構建模塊”(buil ding bl ocks)這一概念,指的是相對較小的文本單元,它們可被靈活地編入不同的文本語境[7]。《詩經》中的章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視為“構建模塊”,即相對于一首完整的詩而言,它只是其中較小的組成單位,可以被靈活地排列在同一詩篇的不同位置。《詩經》作為合樂的歌詞,多重章疊唱,全篇各章的結構和語言往往非常接近,只有部分詞匯發生變化。因此章的安排在當時可具有隨意性,順序變換后大多對詩意無影響。
安大簡《詩經》與《毛詩》不同章次情況如下:
《卷耳》: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簡本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二章。
《螽斯》: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簡本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二章。
《羔羊》: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簡本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二章。
《殷其雷》:簡本第一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簡本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一章。
《江有汜》: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簡本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二章。
《車鄰》: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簡本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二章。
《駟驖》: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簡本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二章。
《小戎》: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簡本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二章。
《黃鳥》:簡本第一章對應《毛詩》第二章,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一章。
《碩鼠》:簡本第一章對應《毛詩》第二章,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一章。
《墻有茨》:簡本第一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一章。
《蟋蟀》:簡本第一章對應《毛詩》第二章,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一章。
《綢繆》: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二章。
《鴇羽》:簡本第二章對應《毛詩》第三章,第三章對應《毛詩》第二章。
以上14首詩中,絕大部分章次變換后在詩旨表達、詩意理解等方面無任何影響,《毛詩》與簡本的順序均可。當然也有例外,如《駟驖》、《綢繆》就存在一定的爭議。兩詩中發生變化的兩章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并列關系,順序顛倒后會對詩意的表達和理解產生一定影響。
一、《駟驖》
《駟驖》三章,章四句。簡本與《毛詩》二、三章順序顛倒。
《毛詩》作: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安大簡作:
《毛詩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孔疏曰:“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于園于囿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于囿中,上二章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蕃曰園,有墻曰囿。園囿大同,蕃墻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于郊……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游于北園,蓋近在國北……”[8]481在“游于北園,四馬既閑”一句后,鄭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游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孔穎達解箋曰:“此則倒本末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游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游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于囿中,多所獲得也。”[8]483-484鄭、孔均認為此篇出現了兩個場所,即園與囿,全詩采用倒敘手法,先說公在囿中“舍拔則獲”,最后解釋原因,即之前公在園中早已調習過車馬與獵犬,所以能夠做到田則克獲。
然陳奐認為二人之說有誤,陳曰:“《有杕之杜》傳:‘游,觀也。’《書?無逸》篇云:‘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渾言之,游亦田也。古者田在園囿中,北園當即所田之地。首章言狩,此章言北園,與《車攻》篇上言狩言苗,而下言于敖,文義正相同也……《箋》以《序》‘田狩園囿’分屬二事,遂謂公游北園為田獲以前,并讀‘閑’為‘邦國六閑’,‘四馬’為‘四種之馬’,恐非《詩傳》之恉。”[9]327-328是以陳奐認為全詩采用了順序手法,但其說或有不足之處。首先,陳奐質疑倒敘說,是從“游”有“田”義出發的。他舉出的《尚書?無逸》篇句子,實際斷句當為:“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10]《漢書?轂永傳》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偽孔傳:“所以無敢過于觀游逸豫田獵者”,“觀”“游”并列,即觀賞游玩,與“田獵”異義。孔穎達正義:“則其無得過于觀望,過于逸豫,過于游戲,過于田獵”[11]513-514。如是,則“游”釋為“游戲”,與“田獵”并不同。此外,《尚書?無逸》篇還有一句將“游”“田”二字并舉:“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傳、疏分別釋作“游逸田獵”“游戲畋獵”[11]512。“游”“田”當分屬兩種不同的行為,即“游玩、游戲”“田獵”。因此,陳奐認為渾言之“游”亦“田”的說法不可從,且遍檢古文獻,無“游”義同“田”的例證。陳奐或是將田獵看作是一種游玩方式了,但很明顯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
至于《駟驖》一詩是否分述兩事,還得看《毛詩》末章中“閑”“載”二字之義。歷來學者對“閑”的理解不盡相同,占主流的說法有兩種:一是“練習、熟練”,經學家多從此義。毛亨、鄭玄均釋“閑,習也”,陳奐云:“《書大傳》:‘戰斗不可不習,故于搜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9]328又《爾雅?釋詁》有言:“閑、狎、串、貫,習也。《釋曰》:‘閑,便習也。’莊二十二年《左傳》曰:‘赦其不閑于教訓。’”[12]今人高亨[13]、袁梅[14]釋“閑”為“熟練”義,乃取“閑”通“嫻”。若“閑”為“練習、熟練”,則《駟驖》分屬二事,在前兩章狩獵完畢后,言之所以能“田則克獲”,是因為之前在北園中已有練習車馬或車馬已熟悉狩獵。二是“休息、閑暇”義,即“閑”通“閒”。《詩毛氏傳疏》:“閑,古字皆當做‘閒’。”[9]327《說文》:“閒,隙也。引申,閒者,稍睱也,故曰閒暇。今人分別其音為戶閒切,或以閑代之。”[15]589此義展現出了狩獵完畢后從容休息之態,若取此義,則全詩采用順序:前兩章敘述激烈的狩獵場景,后一章則言狩獵后于北園休息、整頓車馬與獵犬。
再看“載”字之義。張平子《西京賦》“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張銑注:“獫、猲、獢皆狗也。載之以車也。”朱熹《詩集傳》曰“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16]朱熹訓“載”為“乘”,并由韓愈《畫記》中所記“以騎馬者懷抱一犬”來證明“載犬于車”的合理性。后世從之者眾多,如陳喬樅、牟庭、胡一桂、汪語鳳、日本學者山本章夫等。但反對者亦有,如胡承珙《毛詩后箋》就曾指出:“《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為據,后世事恐難以證古。”[17]561胡說是也。此外,若如朱熹所說,把“載”釋為“以車載犬”也與全篇詩旨及主題不符。從前兩章內容可見,《駟驖》詩重在展示秦狩獵的強健、英勇體魄,若后一章陡轉直下言獵后車馬休息、獵犬乘車,或有諷刺之感,不若鄭玄、孔穎達所釋佳。
鄭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孔疏:“《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8]484馬瑞辰認為,“載”古訓“始”……“始之”即“調習之”[18]369-370。此三人解釋大同小異。胡承珙則進一步指出:“《西京賦》‘載獫猲獢’,語本在將獵之前,正與《詩箋》謂北園調習說合。后儒謂田事已畢,游于北園,以車載犬,休其足力。夫田畢而游,事所恒有,但不必更載田犬以從耳。或疑先言田獵,后言調習,文義不順。李氏《集解》曰此‘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17]561此說可謂一語破的,解決了《駟驖》詩敘事手法的問題。
要之,從“游”無“田獵”之義,“閑”釋為“練習、熟練”、“載”訓“始,始成之也”可知,《駟驖》分屬二事,前兩章描述在囿中的狩獵場景,末章倒敘狩獵前于園中調習車馬、獵犬之事。
簡本將《駟驖》二、三章順序顛倒后,全詩既可看作采用插敘手法,也可看作采用順序手法。插敘是說簡本將《毛詩》一、二章發生在囿中之事割裂開來,先說狩獵的裝備和人物,中間插入之前發生在園中的調習車馬一事,最后敘述狩獵結果——公于囿中“舍拔則獲”。順序是以“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一句為全詩的敘事中心句,如此,無論是狩獵前的裝備、隨從人物,還是狩獵前于北園練習車馬獵犬,都可看作正式狩獵前的準備,只是時間遠近的不同。
從詩旨的表達與詩意的理解出發,無論是《毛詩》的倒敘還是簡本的插敘或順序,似乎都能說得通。但是從詩的連貫性來看,當屬《毛詩》章次順序更佳。一方面,《毛詩》連貫了同一地點發生之事;另一方面,《毛詩》連貫了狩獵的行為與結果,即“狩”與“獲”。
二、《綢繆》
《綢繆》三章,章六句。簡本與《毛詩》二、三章順序顛倒。
《毛詩》作: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安大簡作:
早在1984年,王文君《從民俗學看〈詩經?唐風?綢繆〉》一文就曾提出《綢繆》章次錯簡,二、三章位置應互換,否則,既不符合上古樂歌演唱的定制,又違反了上古婚禮的一般習俗[19]。
安大簡《綢繆》正好與《毛詩》二、三章順序顛倒,但就此說《毛詩》二、三章錯簡還為時過早。《綢繆》章次可有三種情況:或從《毛詩》,或從安大簡,亦或將各章都視為“構建模塊”,章次順序可有不同。具體屬于哪種情況,將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一)《綢繆》詩旨問題
《綢繆》詩旨,從古至今,說法頗多,主流的說法有三種:
刺晉亂說。《毛詩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也。”[8]454-456在詩序基礎上,毛亨與鄭玄的解釋又有所不同。毛亨:“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正義曰:“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取之時也。今我束薪于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正義曰:“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8]454-455
相得而喜說。朱熹《詩序辨說》:“此但為婚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亂也。”[20]
賀新婚說。《詩經原始》:“《綢繆》,賀新昏也。”[21]《詩經譯注》:“這是一首祝賀新婚的詩。它和一般賀婚詩有些不同,帶有戲謔、開玩笑的味道,大約是民間閨閣新房的口頭歌唱。”[22]進入現代詩歌研究階段后,此說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認可。姚奠中《釋〈綢繆〉》中明確提出,“此詩應是歌詠新婚之詩。”[23]邵炳軍、郝建杰《〈詩·唐風·綢繆〉詩旨補證》[24]、王文君《從民俗學看〈詩經?唐風?綢繆〉》[19]均贊同此說。
仔細梳理以上三種說法后可發現,“刺晉亂說”是宋以前的普遍看法,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相得而喜說”是在宋代理學興起的背景下提出的,更注重從文本角度解讀此詩;“賀新婚說”是在清代“經世致用”思想影響下產生并流行起來的,得到了大部分現代學者的支持,并促使他們從民俗學、人類學的新角度去詮釋《綢繆》一詩。
《綢繆》詩旨問題,難有定論,三說各有自己的立足點。考慮到《風》詩多為勞動人民生活的寫實,而《詩序》的“美刺”二元論多為政治服務,脫離了原始的詩旨,因此,從文本本身出發,圍繞《詩序》闡釋得出的“刺晉亂說”不如“相得而喜說”“賀新婚說”有說服力。
(二)“良人、邂逅、粲者”所指
詩中先后出現了“良人、邂逅、粲者”三詞,具體所指,歷來有爭議。
毛傳從第三章的“粲者”訓為“三女”出發,認為“良人”也應指向女性,釋作“美室”[8]455。陳奐[9]284、胡承珙[17]527從之。鄭箋則根據文獻中“良人”多為古代婦女對丈夫的稱呼,認為此處“良人”也不應例外,當指男性[8]455。日本學者竹添光鴻[25]從之。朱熹《詩集傳》、陳子展《詩經直解》在鄭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良人”指新婚之夫。“良人”一詞在傳世文獻中即可稱女性,也可稱男性。“良”最早釋為“善”,胡承珙《毛詩后箋》:“‘良’既訓‘善’,則‘良人’男女皆可通稱。”[17]527此說可從。《戰國策》:“賣仆妾售乎閭巷者,良仆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26]此“婦人”稱“良”之證。“良人”一詞還見于《詩經》其他詩篇,《秦風?黃鳥》:“彼蒼者天,殲我良人。”[27]169“良人”為詩中從殉三位男子的代稱;《秦風?小戎》:“厭厭良人,秩秩德音。”[27]166是婦人對自己丈夫的稱呼語。
《毛詩》“邂逅”,韓詩作“邂遘”,敦煌伯二五二九作“解覯”,安大簡作“矦”。韓詩及敦煌本在形音方面與《毛詩》可構成通假關系,《釋文》:“邂,本亦作解。覯,本又作逅。邂覯,解說也。”[28《]淮南子?俶真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凡君臣朋友男女之會合,皆可言之。”[29]毛傳釋“邂逅”,“志相得”也,新婚夫婦情投意合。“邂逅”一詞還見于《鄭風?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適我愿兮”“邂逅相遇,與子皆臧”。毛傳云:“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愿。”[8]375詩經研究者大多將《綢繆》“邂逅”譯為“不期而遇(的人)”或“喜愛(的人),作名詞,一方面符合“見”后接名詞的語法,另一方面也可以與一、三章的“良人”“粲者”相呼應。新出安大簡“邂逅”作“矦”,[1]145劉剛認為當從簡本,他表示:“簡本反映了詩之原貌,勝于毛、韓二家。因為‘邢侯’作為名詞,與‘良人’‘粲者’詞性一致,可以充當動詞‘見’的賓語,無需像‘邂逅’那樣隨文訓釋……‘良人’指一般民眾,‘邢侯’為小國諸侯,‘粲者’當指代大夫。三者身份層層遞進,所以簡本把‘邢侯’章的次序放在最后。”[30]網友“汗天山”對此持不同看法,他指出,“邢侯”仍當讀作“邂逅”,因“邢侯”指具體的某個人或某類人,使得主角在同一詩篇中出現了不止一位,似嫌重復[31]。此說可從。《綢繆》作為一首婚嫁詩,驀然出現一類具體的人,即劉說之“小國諸侯”,顯然于詩不類。“邢”匣紐耕部,“邂”匣紐支部,音近可通;“侯”匣紐侯部,“逅”匣紐侯部,音同可通。因此,簡本“邢侯”就目前來說,釋作“邂逅”是最佳的。
至于《毛詩》第三章的“粲者”,《廣韻》、《玉篇》均釋“粲”為“美好貌”,“粲”古字作“ ”。《說文》:“三女為 , ,美也。”[15]622可知,此字多形容女性之美。“粲者”于《綢繆》詩中指女性,即新婚之婦,歷來無爭議。但劉剛為了使安大簡“邢侯”為“小國諸侯”的解釋說得通,從毛傳釋“粲者”為“大夫一妻二妾”出發,指出本詞的重心在“大夫”,而不是“一妻二妾”,從而認為“粲者”指代大夫[30]。這一解釋未免過于牽強。
要之,《綢繆》一詩中,“粲者”指代新婦,“邂逅”指向新婚夫婦二人,若將“良人”一詞釋為“美室”,繼續指新婦,則與“粲者”重復,全詩缺少重要的主人公新郎。且毛亨將“良人”釋為“美室”,是從后句“三女為粲”這一解釋出發的,目的是將全詩敘事主人公統一為新郎,以表達不能在良時娶妻的無可奈何,從而附和《詩序》的“刺晉亂說”。但從“良人”一詞在《詩經》中的常見解釋和保持全詩協調性出發,將其看作對新郎的稱呼似乎更加允洽。據此,也可進一步看出“刺晉亂說”的不合理性。
(三)“子兮子兮,如此……何”句式之義
“子兮子兮”句中,“子”分別對應“良人”“邂逅”“粲者”,馬瑞辰:“此詩設為旁觀見人嫁娶之辭,‘見此良人’,見其夫也;‘見此粲者’,見其女也;‘見此邂逅’,見其夫婦相會合也。”[18]346因從古無自稱“子”者,所以第一章的敘述者或為妻或為旁人;第二章的敘述者只能是旁人;第三章的敘述者或為夫或為旁人。考慮到全詩的統一性,敘述者為旁人的可能性更大。這就不免聯系到“賀新婚說”,“旁人”即來參加婚禮的客人。“如何”在《詩經》中多釋為“奈何”,但《綢繆》一詩的“奈何”不是表達無可奈何之感,而是旁人對新婚夫婦的戲謔之詞,“你呀你呀,看你拿這個夫君/美妻怎么辦?”“你們呀你們呀,看你們這對恩愛夫妻怎么辦?”
王文君認為,按照賀婚習俗,客人們應該是先提及夫或妻,最后才會提到夫妻二人的,再從《詩經》音樂中的“亂”章出發,也可證二、三章錯簡[19]。《詩經》作為合樂的歌詞,詩、樂、舞本為一體,孔穎達云:“詩為樂章,詩樂是一。”[32]《詩經》樂曲有“亂”,可證之古代文獻,如《論語?泰伯》:“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33]何謂“亂”,主要有五說[34],其中陰法魯從藝術創作的心理層面剖析,認為“亂”位于一首詩的卒章,從文字上來說,是歌詞的主題部分;從演奏上來說,是音樂和舞蹈的高潮部分,往往采用合奏的方法。他指出:“把‘亂’安排在作品的末尾,一方面企圖使人們當時得到藝術欣賞的最大滿足;一方面企圖給人們留下一個深刻的鮮明的最后印象,長期繚繞在記憶里,影響他們的思想感情。”[35]陰法魯對《詩經》“亂”的解釋,得到了學界普遍認同。《綢繆》詩中,眾人對新婚夫婦情投意合的贊美和戲謔一章,即《毛詩》第二章,相較于其他兩章,是全詩的高潮,用來表達眾人對新人喜結良緣的美好祝福,可以看作是“亂”章。但也不排除全詩無“亂”章,因三章同屬祝福之語,章序變化后只是祝福對象出場順序不同了而已,對詩旨與詩意影響不大。
要之,若從婚俗和《詩經》音樂的“亂”章來看,簡本章次順序確實更加嚴密,較《毛詩》略優。但因詩、樂早已分離,我們目前無法獲知《綢繆》篇的音樂,自然也不能輕易否定《毛詩》章次順序存在的合理性。
三、小結
安大簡與《毛詩》除章次方面有不同外,在詞句、用字方面也存在大量異文。黃德寬曾指出,安大簡《詩經》異文為戰國時期《詩經》的流傳和語言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對漢語史、文字發展史和《詩經》學等多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2]。安大簡的出現,無疑為我們研究《詩經》提供了更多新角度、新材料。相信通過簡本與《毛詩》的對比研究,《詩經》史上一些長期的疑難問題也將得到進一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