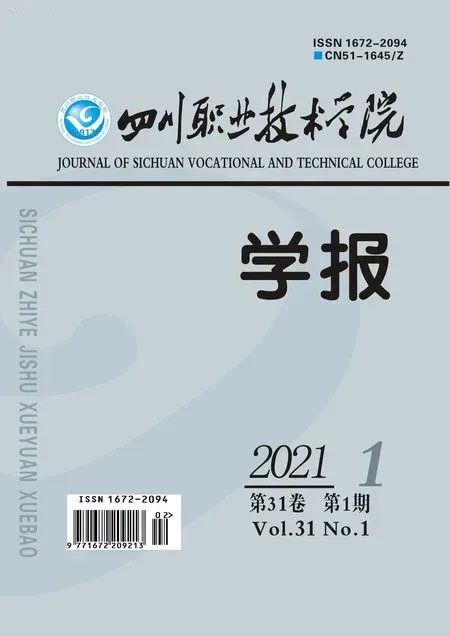略論《穆斯林的葬禮》的敘事手法
宋莉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昆明 650500)
霍達是一名中國回族女作家,著有多種體裁的文學作品,除小說以外,還有報告文學、影視劇本、散文等,并有多種文字的譯本。在她的諸多創作中,最受讀者青睞的是小說,其成就及影響較大。1987年創作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一經發表便反響強烈,此著作被公認為“我國第一部成功地表現回族人民悠久歷史和現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具有民族史詩的品格和不可替代的文學地位與審美價值。”[1]序1并于1991年獲中國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小說曾通過廣播、電影媒介,以及各種文字的譯本進行傳播,可謂是文學典范,值得一讀再讀。它以一個穆斯林家族三代人的悲劇,主要揭示了民國時期和新中國前期的家國興衰、回族人民的生活和傳統玉雕技藝舉步維艱的歷史。其中小人物的悲劇命運,具有較強的感染力,通過咀嚼這些悲劇,使人產生對歷史、政治、倫理、宗教以及人性等問題的思索。作者運用多種敘事手法,更好地呈現悲劇、揭示主題;也突出了小說中的悲劇美,其文學價值和藝術魅力也從中產生。本文借用小說敘事學相關寫作理論,分析該作品中的敘事手法以及在不同敘事手法下凸顯的悲劇意味和藝術效果。
一、時間的控制
時間的控制,指的是對文本時間的加工與處理。“文本時間,也稱敘事時間,則是故事內容在敘事文本中具體呈現出來的時間狀態。”[2]這樣的時間狀態,在《穆斯林的葬禮》中有拉長、延長之處,在文本時間的控制中,作者采用了“增加敘述頻率”和“設置懸念”的敘事手法。文本內容的悲劇性也在這些敘事形式下,得到更好地呈現。
(一)增加敘述頻率,拉長文本時間
敘述頻率與敘事話語次數及事件發生次數有關。“除了時序、時距之外,文本時間與故事時間形成的第三種關系為頻率,它是指一個事件在故事中出現的次數與該事件在文本中敘述的次數。這樣,事件與話語之間的重復關系就包括四種:A.一次講述一次發生的事;B.一次講述多次發生的事;C.多次講述一次發生的事;D.多次講述多次發生的事……第四種敘述頻率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件不斷地發生,故事中也一再重復地敘述。”[3]
本文所論及的是上述第四種敘述頻率。在這里,先以魯迅的《祝福》為例,如祥林嫂多次向人訴說兒子阿毛的慘遇,她的反復訴說也多次被敘述,即作者多次敘述人物的多次訴說。雖是話語重復,卻表現出另一層含義:暗示人們終將聽厭祥林嫂的傾訴,逐漸從同情轉向厭煩。如此一來,也揭示出人情的冷漠和祥林嫂悲劇的必然性。可見,這種重復是增加敘述頻率引起的,它并不是多余之舉,反而具有深層的意義。
同樣,在《穆斯林的葬禮》的第十四章《月落》里,作者也采用增加敘述頻率的手法。主要是為了在形式上拉長文本時間,使悲劇在這樣的時間控制下,出其不意地發生,達到難以預料又似乎在情理之中的效果。另外,在內容上不僅使人物的心境得以展現,也更加突出韓新月的死,引發讀者對人物悲劇命運的種種思考。《月落》篇中,主人公韓新月臨死前,曾多次問身邊人“所及時間和是否天亮”的問題,這樣的問話在她臨死前是不斷發生的,作者也一再重復地敘述。如:
“嫂子……幾點了?”[1]553
“幾點了?”[1]555
“天……怎么還不亮呢?……”[1]555
“怎么……天還不亮?太陽……還不……出來?”[1]555
“天……亮了嗎?”[1]556
從以上語句可以看出,“幾點了?”和“天怎么還不亮呢?”各問了兩次,“天亮了嗎?”問了一次。讀者通過上下文,便可得知這些問話其實都指同一個問題,即“是否進入白日時間”。并且,新月的問話頻率是有所增加的,加起來共有五次。具有相似語境的這些問話,作者都一一寫出,也就是多次敘述多次發生的事,而不是簡單概括,最終導致文本時間被拉長。作者一次次地敘述韓新月的頻繁發問,是增加敘述頻率的表現,所呈現的藝術效果較豐富,但更重要的是達到拉長文本時間,突出悲劇內容的效果。
首先,敘述頻率的增加,讀者結合上下文可得知人物的內在心境。每一次的問話,都體現了她期待、焦急的心境。她期待能夠一睜眼就能看到戀人,又焦慮時間過得太慢,隨著問話頻率的增加,這種心情也就越加強烈。因此,展現人物心境是其效果之一。其次,敘述頻率增加,引起問話的重復,而這些問話具有間接性。從人物的第一次問話到最后一次發問,作者用了四頁的篇幅,文本時間便在人物的間接性重復問話中被拉長。在韓新月的每一次問話過程中,還穿插其他的動作和行為:她憧憬美好的娛樂時光;回憶與陳淑彥的同窗歲月;又想到自己惡化的病情;詢問東方位置;請求嫂子喂她喝水、別上校徽等。這些動作和行為,作者都細膩地呈現給讀者,并未一筆帶過,故增加了文本時間的長度。這是增加敘述頻率所產生的另一藝術效果。
在人物的多次問話中,讀者可以感受到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對戀人的期待,以及對生命的渴望。文字給讀者展現的似乎是風平浪靜的情景,但緊接著韓新月的突死,卻如同狂風暴雨、電閃雷鳴一般,令人猝不及防。新月的突死,雖然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回過頭來細品她的問話,其實不難發現:作者通過增加敘述頻率,已經為下文中新月的死埋下了伏筆。她的每一次問話,實際上是把故事逐步推向高潮。因此,作者以人物的不斷問話來增加敘述頻率,主要是拉長文本時間,敘事速度相應變緩,可讓讀者在慢節奏下,細細體會出韓新月對愛的期待、對生的渴望,而后又赫然呈現韓新月死亡的悲劇。這樣的設置可達到出人意料的效果,能更好地將這個美麗少女的死引向故事的高潮,讓悲劇意味滲透出來,這便是此手法真正的藝術價值所在。總而言之,增加話語的敘述頻率,拉長文本時間,點出人物在期待與遺憾中死去,濃烈的悲劇意味才盡可能得到體現。顯然,重復性敘事手法,并不是多此一舉,而是為了更好地引出后文所述的悲劇。
(二)設置懸念,延長文本時間
“懸念”這一詞源于法語,原意是“懸著的原因”[4]234。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貝爾認為,“懸念拖延了問題最終得到解決的時間。”[4]234讀者在閱讀具有懸念的文本時,總是因為不知道后事如何,才會繼續讀下去,直到找到答案為止。實際上,這是懸念的藝術效果所引起的,它可使文本時間延長、情節延續,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和閱讀興致,使小說情節發展引人入勝。
在《穆斯林的葬禮》中,作者為了醞釀悲劇,讓讀者去探尋與品味故事,采用了設置懸念的手法。運用這一手法,作者所寫的篇幅會隨之增加,不會謎底全出,導致戛然而止。增加了篇幅,也就延長了文本時間。作者之所以這樣控制文本時間,第一,為了將事實真相暫時隱藏起來,令讀者始終保持著閱讀興趣,最后在層層的懸念之中,漸漸揭開悲劇故事的神秘面紗。第二,在有所延長的文本時間里,使讀者逐步挖掘悲劇背后的深刻意味。小說《穆斯林的葬禮》是一部長篇著作,作者所設置的懸念不止一個,它既有總懸念(大懸念),也有不少小懸念穿插于總懸念之中。無論哪一類懸念,都是為表現悲劇而服務。
譬如第二章《月冷》中,關于韓新月長久的疑惑,作者并未直接給出答案,不僅是她百思不解的困惑,也是留給讀者探尋的問題。因此,作者在這一章中留下了懸念,直到第十三章《玉歸》和第十四章《月落》中才給出答案。從設懸到釋懸,中間隔了十個章節。全書除了序曲和尾聲,共有十五個章節,第二章中設下的懸念就占據了全書的大部分,可見,這是貫穿于整部小說的大懸念或者總懸念。在這樣的大懸念下,必然使文本時間有所延長。
在《月冷》篇中,韓新月一直疑惑:為何母親(韓太太)與自己存在較強的“距離感”?然而,自己與姑媽(韓家收養的婦人)更像母女那般親密。韓新月對此疑惑不解,讀者通過新月的視角,自然也是不解。關于這個問題,作者設下懸念。作者設置的懸念還有以下幾個:為什么韓太太對于新月報考北大西語系表示不滿?為什么韓子奇與韓太太吵架,姑媽調和一下,他們就心領神會地中止了?姑媽的話真有那么“權威”嗎?這些都是此篇中懸著的原因。
韓子奇、韓太太和姑媽三人之間,似乎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事實上,這些秘密與新月的身世有關,她的身世之謎具有懸念。文本一直延長到第十三章《玉歸》中才初次交代了新月的身世,讀者只有讀到這里才開始釋懸。韓新月其實是韓子奇與梁冰玉(韓太太的妹妹)的私生女,這個答案只有讀者才知曉。主人公新月又是如何得知自己身世的?作者將其放在第十四章《月落》中進行揭示。在此章中,當塵封多年的信被打開時,新月自己才終于解開疑惑,她的身世之謎才得以完全揭曉,文本中的大懸念便終于了然。這封信出自梁冰玉,其內容可以解新月的心頭之惑,讀者也能從這封信的內容中得知所有的真相。
韓新月的“身世之謎”幾乎貫穿于整部小說,是小說中的大懸念。作者在第二章中設下了懸念,一直延長到第十三至十四章中,才逐漸釋懸,此手法令文本時間得到延長。這樣的延長,恰好能將多個悲劇隱藏起來,保持讀者的好奇心。同時,經過長久的探尋并得知真相后,其悲劇性內容就越加顯得深刻。如當懸念一旦被揭開,展現給讀者的竟是韓新月不能言說的身世苦痛,還展現了韓子奇與梁冰玉的愛情悲劇,他們都因《古蘭經》中“嚴禁同時娶兩姐妹”的戒律而將愛情葬送。梁氏姐妹親情關系破裂,從此訣別,天各一方。梁君璧、梁冰玉和韓子奇三人的觀念各不同,導致悲劇發生,但悲劇發生的根源是人性與宗教教義的沖突。當讀者帶著興趣去尋找答案,揭開懸念時,雖“回答”給讀者的是多個悲劇性故事,但也讓讀者驚奇地發現悲劇的原因,使讀者對韓新月的身世感到憐惜,也對其中感人的愛情故事惋惜不已,進而體會到悲劇之美。更重要的是,從悲劇中反思人性與宗教文化的沖突和矛盾。作者設置這樣的大懸念,將韓新月的身世進行隱藏,充分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又由一定的篇幅釋懸,讓讀者幾乎閱讀完整部小說才能知曉答案,這顯然延長了文本閱讀時間。同時,也讓讀者咀嚼到了悲劇,引發讀者對悲劇的思考。
除了大懸念,小說中還有小懸念的設置。通過小懸念,也可延長文本時間,以此逐漸揭開悲劇故事。第四章《月清》中,關于韓太太為何熱情招待陳淑彥,作者便設下懸念。此篇中最后寫道:“韓太太卻在心里謀劃著另一件大事,這件事,現在還只有她一個人知道。”[1]94作者寫完這一句就收尾了,一直延長到第十章《月情》中,當韓太太親手操辦陳淑彥與韓天星的婚禮時,這個懸念才逐漸揭曉。這一懸念處于小說的大懸念之下,屬于小懸念。讀者在探尋這個小懸念時,可以得知韓太太的“計謀”。從第四章的設懸到第十章的釋懸,中間隔了五個章節,文本時間得到延長。在這些延長的篇章里,作者并不是一點都沒有提及韓太太的“計謀”,而是從側面一點點地讓讀者領會,直到第十章《月情》中,謎底才完全揭開。這樣既始終保持著讀者的閱讀興趣,又不會因為篇幅長而讓讀者失去興致。
在延長的篇章里,作者敘述了韓太太的一系列行為,如:她主動幫助陳淑彥(韓新月的同窗)解決畢業后的工作問題;總是邀請陳淑彥做客,并讓她留宿于博雅宅。表面上是為了讓她與新月敘舊、結伴,實際上是制造陳淑彥與兒子的見面機會。除此之外,韓太太巧妙地將兒子韓天星和容桂芳這對情侶拆散,隨后又撮合韓天星和陳淑彥。從這些側面的跡象表明:韓太太已將陳淑彥視為目標兒媳,并且想要掌控自己兒子的婚姻大事,親手“締造”兒子的未來。從所延長的篇章里,讀者似乎可以揣測到她的心思,揭開之前的懸念,但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陳淑彥會是最終的兒媳嗎?這又會迫使讀者繼續保持好奇心。
作者在第四章末尾設置懸念,又在第十章當中釋懸,不僅延長了文本閱讀時間,而且在讀者探索的整個過程中,可以更加清晰地領悟到:自由戀愛成為封建家長制下的犧牲品,而韓天星與陳淑彥的結合,只是具有親情外殼的婚姻關系,并沒有真正的愛情,其中的悲劇意味不言而喻。
二、空間的安排
作者對于小說涉及的空間,采用了不同的敘事手法對空間進行巧妙安排。讀者分析這些空間,便可清晰了解小說中所敘述的悲劇故事,并領悟出:在具有悲劇性的空間里,悲劇的發生在所難免。從不同空間的角度上,思考多樣的悲劇內容。
徐岱先生認為:“故事中的人物活動空間,可以被進一步分割為大空間(時代、社會背景)和小空間(具體活動場所、環境)。”[5]根據這一說法,本文將作者在小說中所安排的空間分為兩部分:社會空間和自然空間,即上文所述的大空間和小空間,并探討大、小空間的安排和敘事手法的運用以及藝術效果、文學價值的體現。
(一)社會空間
作者對于小說的社會空間安排,采用了以小見大的手法。即從小的方面看見大的方面,從局部看到整體,由小題材、小事件和細節來揭示重大主題、反映深廣內容。小說敘寫了一個穆斯林家族和部分漢人的來往,以及他們各自的經歷,由小人物的歷程揭示社會空間,具有延伸放大的效果。讀者通過延伸可知:人物所處的社會空間具有復雜性,并且其復雜性體現在“內憂”和“外患”兩方面。“內憂”表現在:國內回漢兩個民族之間的文化沖擊與融合,以及文革這一政治背景;而“外患”表現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國這一戰爭背景,以及世界二戰之下德軍空襲英國,導致生靈涂炭、民不聊生的殘酷歷史。這樣內憂外患的社會空間便具有一定的悲劇色彩。
這些社會空間的復雜性在小說中并不是直接點明的,它是通過人物的生活折射出來的。作者用人物的活動、事物中的細節這些小方面,反映出當時的社會背景,即“以小見大”。透過此手法,也能使讀者在品讀文本時,發掘其中更深遠的藝術世界。首先,先說“內憂”方面,通過以小見大表明國內回漢民族之間沖突的例子,如小說中對校園“清真食堂”的細節描寫。與漢人食堂相比,回族食堂數量少,所處位置偏僻,外觀不起眼,人員容納量小,地勢低,就餐環境差等,以這些細節表明:回漢食堂有差別,而且這似乎是稀松平常的小事,在當時的社會生活里,它屬于小的方面,但從中折射出回漢民族表面是融合的,而實際上被區別性地對待,仍是有沖突的,這便是可窺見的大方面。
此外,兩民族之間的文化沖突最突出的表現是宗教信仰的差異。關于這一點,作者采用以小見大的手法,較好地呈現了這種差異。僅僅是一個回族人和一個漢族人的對話,卻代表了所有的回族與漢族之間的信仰隔閡。在第十二章《月戀》中,作者詳寫了韓太太(回人)與楚雁潮(漢人)的對話,通過敘寫韓太太與楚雁潮在信仰上的看法,便折射出當時的社會空間里,回族與漢族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折射出中國曾經在民族的問題上,產生無法調和的矛盾;也折射出穆斯林教義與現代文明的強烈沖突。但是,回漢民族也有融合之處,仍然有兩者通婚的特例,如韓子奇與韓太太的結合。韓子奇實際上并不是回族人,只是巧合之下歸入了伊斯蘭教,因此他才可以與韓太太通婚,他們的結合也暗示回漢融合的歷史必然性,引發讀者對民族新生與發展的思考。顯然,通過人物活動的細節與生活中的小事例,表明了在當時的社會空間下,回漢兩個民族既有沖突又有融合的復雜性,這便是以小見大手法的運用,可將讀者的眼光放置到更深遠的社會背景,進而引發深層思考。
社會空間里的內憂之處,還體現在“文革”浩劫上。對于這一背景的揭示,作者仍采用以小見大的手法。如:韓子奇臨死前被劃為“資本家”,遭遇批斗,并被要求交代自己的“罪惡歷史”,他所收藏的玉器藏品都被充公,連居住的四合院也成了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些是人物的個人經歷,卻暗示了一個大的社會空間(社會背景),即文革政治運動。而社會空間的外患之處則表現在:因抗日戰爭,韓子奇與梁冰玉被迫遷至倫敦,在倫敦同樣遭受戰爭的摧殘。由于世界二戰中德軍對英國的空襲,使他們不得不躲進防空壕,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這些也屬于人物的活動經歷,暗示人民處于水深火熱的戰爭之中,體現了中外社會空間里的外患之處。可見,作者通過以小見大的手法,將復雜的、悲劇性的社會空間隱于人物的活動與經歷之中,使讀者從小的方面看見大歷史、大沖突,也從中發現人物的悲劇命運。同時,在延伸擴大的效果中,文本的歷史厚重感得到加強。
(二)自然空間
徐岱先生曾進一步指出:小空間具有“地域和地點”之分,它與大空間相比,偏重于自然因素。我們可以把這個“小空間”稱之為“自然空間”。關于自然空間下的“地域和地點”,本文先從小的方面說起,即先說“地點”,再說“地域”。
在《穆斯林的葬禮》中,“地點”又有相似地點和不同地點之分。相似地點的呈現,是通過戲中戲手法實現的。小說中,對于“墓穴”這一地點,作者為了更好地呼應“葬禮”二字,則運用了戲中戲手法加以突出,增強了故事的戲劇性效果。此外,“墓穴”這一自然空間,本身就具有悲涼的意味,小說的悲劇性敘事特點便越加顯著。不同地點和地域空間的切換,是通過平行蒙太奇手法實現的。作者在章節內部采用此手法,不僅使自然空間具有流動跳躍的效果,也形成兩條線索在內涵上的對照反差,或營造兩地事件的緊張氛圍。并且,讀者在這些切換的空間里,可看到人物命運受思想、社會和戰爭的牽制。
具體而言,作者運用戲中戲手法,使小說中呈現出具有相似性的地點。這里所說的“戲中戲”是一個戲劇概念,指的是戲中套演著其他戲,在原本的戲劇進程中插入其他戲劇故事或情境。本文所言的“戲中戲”手法,則是指作者借用了這個戲劇概念,在小說中又插敘了別的戲劇。如在小說中,作者敘寫韓新月和楚雁潮的愛情故事時,又巧妙地插敘了《哈姆雷特》中“莪菲莉婭”與“哈姆雷特”的愛情故事。兩個愛情故事里都出現了“墓穴”這一地點。
在第八章《月晦》中,楚雁潮與韓新月被邀請出演舞臺劇《哈姆雷特》的男女主角時,韓新月表示贊同,但楚雁潮卻認為這出戲太苦,原因是其中有一幕場景為:“哈姆雷特”扮演者需在“莪菲莉婭”的葬禮中上場,并且跳下女主角的墓穴。相愛之人竟在墓穴見最后一面,陰陽相隔之痛是無法言說的。文中也有部分劇中臺詞,展現給讀者的是戲中“墓穴”一幕。可使讀者在讀小說文本時,也領略了一番戲劇的精彩片段。不僅如此,在第十四章《月落》中,也出現了“墓穴”這一地點,而它的主人竟是曾經被邀請擔任“莪菲莉婭”角色的韓新月。按照回族的喪葬風俗,亡人的遺體在埋葬前,首先需要親人試坑。然而,楚雁潮完全不顧風俗禮儀,為了給愛人試坑,毅然跳下新月的墓穴。他并不是新月的親人,而是作為新月的戀人,懷著悲痛與愛意果斷跳下墓穴,這與戲中情景如出一轍,呈現了戲劇性效果。更重要的是,戲中墓穴與韓新月的墓穴具有相似性,兩者都是葬禮中的地點,這便在無形之中揭示:無論是戲中的愛情故事,還是楚雁潮和韓新月的愛情故事,都同樣是悲劇,兩個悲劇通過戲中戲手法這樣疊加,具有強烈的沖擊力,更顯濃烈的悲劇意味。
此外,在平行蒙太奇手法下,小說里的不同地點和地域實現了自由切換。“蒙太奇,是法語的音譯,原是建筑學的術語,意為構成裝配。后借用到電影藝術中來,指鏡頭的剪輯、交換和組接。”[6]在敘事文體中,蒙太奇手法就是類似于電影的藝術手法,而平行蒙太奇是眾多蒙太奇手法之一,指的是“兩條或兩條以上情節線索(不同時空、同時異地或同時同地)的并列表現、分頭敘述而統一在一個完整的情節結構之中。”[7]其作用是形成兩個或多個事件的關聯度。作者在小說的章節內部運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法,屬于上述中兩條情節線索同時異地的并列表現情況。在不同地點或地域(空間)的切換中,使之具有流動跳躍的效果,避免單一化。著名學者曹文軒也認為:環境的自然流動可避免閱讀疲憊,產生游歷快意。在此手法下,兩條線索的關聯可營造故事的緊張氛圍,或形成兩地事件在內涵上的對照反差效果,從而引發讀者對知識分子、市井小民,以及歷史背景下小人物命運的思索。
在第四章《月清》中,作者以“東方熹微”這一時刻,分別敘述了北大二十七齋和博雅宅兩地的情形,使不同地點中的事幾乎同步呈現。在二十七齋的女生宿舍里,韓新月仍在睡夢中做著美夢。然而,博雅宅內的韓太太已經醒來,她堅信“禮拜強于昏睡”,醒來之后便虔誠地進行“晨禮”。在“晨禮”前的“小凈”中,因撫摸自己的臉而想起新月,不僅感嘆歲月的蹉跎,也憶起往事,觸發了煩惱。此處,作者以平行蒙太奇手法,將新月所在的地點切換到博雅宅,形成兩個自然空間的流動跳躍。二者雖是并列表現、分頭敘述的,但這樣的組接與切換可達到對比反差的效果。如:二人在思想觀念、年齡與容貌、心緒與煩擾等方面存在較大反差。從兩個地點的轉換中可以看出:兩人都是穆斯林,卻對“晨禮”這一行為表現不一,體現兩人不同的思想觀念。新月是一個知識分子,因受現代文明的影響,漸漸將“晨禮”省去,而韓太太身為市井小民,一直固守自己多年的習慣。在年齡與容貌的比較上可知,新月已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有自己的理想目標,而韓太太盡管仔細地進行“小凈”,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年華已逝,早無年輕時的風采與活力。在心緒與煩擾方面,新月顯然是快樂的,她已步入理想的大學,正朝著美好的未來前進,似乎暫時沒有心煩之事,但韓太太不同,她一想到新月,便想起多年前的事情。往事經常攪擾她,令她在晨禮中,不得不反省著過去。從以上對比反差中,也凸顯韓太太身上的悲涼意味。
同樣,作者對兩個地域空間的切換,也采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法。在第十一章《玉劫》中,作者分別敘述了倫敦和北平所發生的事,使同一時段(1940年)發生在不同地域的事件幾乎同步呈現。此篇中,中國北平和英國倫敦兩個區域的戰爭都是持續的,這加深了故事情節的緊張情緒。韓子奇和梁冰玉在倫敦待了三年,可是戰事不斷,令他們安穩的生活與學習出現了麻煩。作者又把空間切換到北平,韓子奇離開北平的三年后,韓太太等人也因戰事,過著一籌莫展的生活。通過平行蒙太奇手法,“倫敦”與“北平”兩地域實現了自由切換和組接,兩地所發生的事件都是令人憂心的,它們牽動著讀者,營造了故事的緊張氛圍,由此可生發出這樣的疑慮:在持久的戰爭中,韓子奇、梁冰玉、亨特以及韓太太等人的命運將會如何?這便使讀者對歷史所裹挾的小人物的命運產生關注與思考。
綜上所述,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中,作者運用多種敘事手法,使小說呈現節奏分明、張弛有度、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然而,形式即內容,在不同的敘事手法下,也體現多維度的文學價值:展示歷史政治中被裹挾的小人物的命運,同時也展開對歷史社會荒誕性的追問;對知識分子和中國傳統玉雕技藝命運的關注與思索,以及對民族發展道路的探求。這些內容有助于我們對人的歷史政治、社會文化、民族問題進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