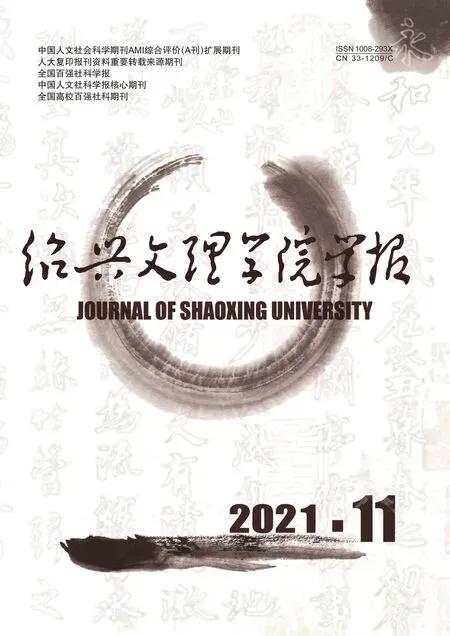從“讀書”到“從戎”
——抗戰時期竺可楨的愛國主義教育思想探析
龐 毅
(浙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1936年4月,竺可楨出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淞滬會戰后,由于杭州面臨淪陷的可能,竺可楨遂率領浙大師生西遷,開始了流亡辦學的歷程。
面對日寇入侵、國破家亡的處境,社會各界抗日救國的熱情日益高漲,如何應對戰時危局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大學生是應該繼續讀書,還是投筆從戎,也成為當時的討論熱點之一。竺可楨執掌浙大十三年,尤以抗戰時期為多。作為浙大校長,竺可楨的愛國主義教育思想不僅對浙大師生有很大影響力,而且對當時社會也有一定的影響力。通過爬梳該時期竺可楨的日記、書信、文集和當時人的相關回憶,可以發現,竺可楨的愛國主義教育思想經歷了三次比較明顯的轉變,簡要言之,即從主張大學生努力讀書,到主張讀書的同時也要為地方與前線服務,再到主張大學生投筆從戎。
目前,關于竺可楨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但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竺可楨的德育思想、科學思想,以及竺可楨執掌浙大期間黨國權力與浙大自治間的緊張關系等方面,尚未有人對抗戰時期竺可楨愛國主義教育思想轉變展開研究(1)相關研究主要有:田正平:《一位大學校長的理念與情操——〈竺可楨日記〉閱讀札記》,《教育研究》2015年第12期;朱華:《竺可楨科學救國思想初探》,《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陳紅民、段智峰:《抗戰期間竺可楨主持浙大的一個側面——解讀竺可楨與朱家驊的幾封往來函件》,《晉陽學刊》2010年第5期;趙良亮:《竺可楨的知識、思想與困境——以竺可楨日記為考察對象》,上海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李嘉偉:《竺可楨的科學思想研究》,渤海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劉妍:《竺可楨德育思想研究》,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何方昱:《國家權力的侵入與大學自治的難局——以浙江大學導師制的興衰為中心(1936—1945)》,《史林》2009年第6期;何方昱:《黨化教育下的學人政治認同危機:去留之間的竺可楨(1936—1949)》,《史林》2010年第6期;何方昱:《戰時浙江大學校園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史林》2015年第3期;楊思信:《戰時浙江大學的訓育與風波——以竺可楨日記為考察中心》,《甘肅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冀偉娜:《黨化教育視角下的竺可楨與浙江大學(1936—1949)》,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謝忠強:《竺可楨與民國時期的歷法改革》,《甘肅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深入挖掘該時期竺可楨愛國主義教育思想,不僅有助于豐富竺可楨的研究,也有助于推進戰時愛國主義教育的討論(2)到目前為止,抗戰時期愛國主義教育的研究焦點是知識青年從軍問題,主要是從國民政府的政策與態度入手展開研究,較少關注個體,涉及到個人觀點的也只是摘引報刊上的個別言論,未作比較全面的探討。參見金以林:《戰時大學教育的恢復和發展》,《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2期;周春雨:《抗戰后期十萬知識青年從軍熱潮述評》,《軍事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江沛、張丹:《戰時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述評》,《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1期;侯德礎:《略論抗戰后期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民國檔案》2006年第2期;付辛酉:《從“青年學生志愿從軍”到“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民國檔案》2013年第2期;徐一鳴:《抗戰后期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研究》,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陳偉:《抗戰時期蔣介石與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軍事歷史研究》2015年第3期;呂光斌:《全面抗戰初期戰時教育思想的論爭與多重變奏》,《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王哲從青年學生視角討論了抗戰時期“讀書還是從戎”的問題。參見王哲:《讀書還是從戎?國統區青年學生抗戰觀之爭論》,《史學月刊》2019年第3期。。
一、“讀書”:以為國儲才
抗戰初期,大片國土陷于敵手,諸多高校紛紛內遷,大學教育出路何在?曾引發了一場有關戰時教育方針的爭論。從現存相關資料來看,竺可楨主張大學生在后方努力讀書,以為抗戰建國儲備人才。
竺可楨希望浙大學子學有所成,服務社會,做社會各界的領袖分子。1939年2月4日,竺可楨對一年級新生訓話時,明確指出“諸位到浙大所負的使命”[1]461,不僅僅是學一點專門知識,畢業以后可以自立謀生,而是“希望你們每個人學成,以將來能在社會服務,做各界的領袖分子,使我國家能建設起來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日本或是旁的國家再也不敢侵略我們”[1]462。原因無他,一是對得起國家,一是對得起在前線殺敵的將士。竺可楨指出,現在國家財源匱乏,而大多學生要靠國家貸款以維持生計,“每個學生所用國家的錢,仍需一千元左右”[1]462。同時,“現在戰場上要的是青年生力軍,不叫你們到前線去在槍林彈雨之中過日子,而讓你們在后方”[1]462。所以,竺可楨激勵浙大學子要努力讀書,把建國重任擔當起來。“國家用這許多錢,不派你們上前線而在后方讀書,若不把這種重大責任擔負起來,你們怎能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前方拼命的將士?”[1]462
竺可楨認為,大學生在后方讀書,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抗戰建國考慮。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美等國提供了經驗教訓。1941年竺可楨發表在《星期評論》上的文章,詳細闡述了這一觀點。竺可楨指出,一戰時,英美等國都曾送大量的大學生上前線,但由此造成大學生損失不少,后來才認識到這實為失策。竺可楨以英國牛津大學物理學助教莫士萊(Henry G. Moseley)為例,痛惜這位科學天才因參加一戰而英年早逝,進而認為,二戰爆發后,英美等國勸學有專長的大學生留在后方,中國也應引以為鑒[1]551-552。
其次,于大學生而言,建國責任大于抗戰工作。竺可楨堅信抗戰必勝,他認為“抗戰是三、五年的問題,建國是三、五十年的問題”[2]704-705,大學生是將來社會各界的領袖,若參戰犧牲,戰后建國的重任將后繼乏人。“大學生為將來社會之領袖,國家的柱石,理應身先士卒,沖鋒陷陣,方不愧為全國青年之表率。國家為了愛護將來的領袖人物起見,不把大學生送往前線去沖鋒殺敵,則他們應如何奮身圖報,努力上進,能把將來建國的重任擔當起來,方可對得起戰死沙場的勇士們,方不愧今日之程嬰。”[1]551-552
第三,即便在戰時,國家仍需要大量人才,大學生則呈現供不應求之勢。1940年8月16日,竺可楨在浙大第十三屆畢業典禮的致辭中提到,“在抗戰以前,畢業同學每屆畢業時,有失業之憂;但在抗建時期,各項建設,質量上都蓬勃地發展,處處都要大批的人才來參加,故最近一二年的畢業同學,都有供不應求之概”[1]514。所以,大學生盡管未赴前線,也責任重大。
第四,戰時參加社會服務工作與前線殺敵同等重要。對于有些同學可能存在未親赴前線而感到慚愧的想法,竺可楨指出,“諸君應明利義之辯,要把抗建的大業看得透徹,切不可妄自菲薄。我們要知道,學土木工程的能造一條有價值的公路或鐵路,和親上前線去殺敵的一樣于國家有益,其他學教育、經濟、政治等等的,能忠勤于自己的事業,在抗戰時期,與直接去制造飛機大炮同樣地重要”[1]514-515。
面對主張國內大學教育應為戰時服務的聲音,竺可楨是不認同的。1938年,國民政府提出“戰時教育即平時教育”理論,對此,竺可楨深表贊同。在1938年《教育部訂定之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中,明確指出,“自抗戰發生以來,國人咸感覺過去我國之教育未能完全適合戰時之需要,惟教育本身原無所謂戰時與平時之分,平時教育實應包含戰時之準備,戰時教育之未能適合戰時需要,正因平時教育未盡完善之故。在此時期,吾人自應將過去教育之缺點,切實加以整頓及改善,以樹立整個教育系統之基礎”[3]25。方案頒布以后,關于大學教育的討論一錘定音,竺可楨表示,“幸而我們的中央政府即決定了維持高等教育”,“在戰時維持大學、維持高等教育,實是高瞻遠矚的良謨”[1]551-552。
二、“讀書”與“從戎”之間:為地方與前線服務
1937年11月,竺可楨率領浙大師生西遷建德,由此開啟了流亡辦學之旅,后被稱為“文軍長征”。盡管竺可楨主張應在后方讀書,但也提倡要為辦學的地方服務。如他所言,“吾人處茲大時代,絕不應袖手旁觀。昔在泰和,固嘗多所工作,以獻替于地方、國家,今在敵愾興奮軍政嚴肅之廣西,更應勉事后方工作,以策前方軍事勝利之早日獲得,責無旁貸,不容一日荒隳天職也”[1]472。與此同時,竺可楨也主張為前線將士捐款捐物,并逐漸認識到大學生在前線“亦有用處”,遂積極支持浙大學子赴前線服務。
在竺可楨看來,深處后方的大學生,心中更應有國家。1940年7月8日,竺可楨在總理紀念周上對浙大師生講話時,勉勵學生要把國家放在心中,“要知國家所以培養大學生之主旨,即期吾人有深刻之國家觀念;在大后方作精神上之鼓勵;決非深處室內靜待前方打勝仗也!歐洲戰事,交戰國家凡年已屆二十歲之青年,均得參戰,今日吾人安處后方,自應奮勵自勉,自強不息而深省也!”[1]510
心中有國家觀念,對深處后方的大學生來說,除了讀書外,則要為地方服務。在浙大立校十三周年紀念日上,竺可楨即勉勵浙大師生:“于所在地之種種設施,革革興興,盡心竭力以赴。時際非常,吾人之責任尤重!無論精神物質,兩不可忽。文化之推進,職責所在,固應重視;第物質環境之改善,關系民生至切,亦須注意。例如開辟荒地,使耕地加多;改良種植方法,使產量增加;避免破壞,減少消費,成效可與增加生產相埒。其間接直接,積極消極,與抗建有裨益者,均為大學所當顧及而努力”[1]512。
其實,在浙大西遷之初,竺可楨就十分注意為辦學所在的地方發展服務。浙大遷到江西泰和后,竺可楨就組織浙大師生修建防洪堤,興辦示范農墾場。據蘇步青回憶,“學校搬到泰和以后,竺校長了解贛江是一條經常泛濫的禍水,每年都要吞滅無數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同時,學校設在這岸畔,安全也有問題。竺校長就請土木系和其他系的師生,幫助泰和人民建造了一條15里長的防洪長堤”[4]3。在了解泰和沙村“荒廢多年”,竺可楨便與泰和縣長魯繩月商談沙村墾殖問題,并親自召集沙村墾殖委員會[5]232-238。后一共開墾土地六百畝,以安置災民。
由于敵機破壞,浙大籌備組織了校救火隊。竺可楨認為,浙大校救火隊擔負的任務,不僅是浙大的消防安全,同時還要為地方消防服務。“本校之救火機,他日不但能為本校校舍謀安全,更愿為全城市民服務。”[1]509竺可楨認為,大學生參加救火隊,即是為抗戰建國服務。“希望同學報名參加,以為準備萬一被炸時,不但為本校宿舍盡責,亦當對全市負責。因消極的保護后方財產,其意義與積極的增加后方生產,同時即盡力于抗戰建國也。”[1]511
除了鼓勵和引導為地方服務以外,竺可楨也積極支持大學生為前方將士服務,其中,影響最大的便是浙大戰地服務團。首批浙大戰地服務團成立于1939年末,工作時間是1940年1月1日到2月2日,主要工作是救護、宣傳、聯絡軍民與歌詠戲劇,活動的前線在廣西大塘、遷江與賓陽一帶。1940年2月25日,竺可楨參加戰地服務團工作檢討會,在日記中寫道,“據諸生報告,知前方確有大學學生工作之需要,遷江附近人民尚不知有抗日之戰;大塘一日間運到傷兵急待包扎者數十人;軍民間形勢之隔閡;最初大家以為前方無大學生之需要者,后乃改變觀念云”[5]410。由此,竺可楨認為,戰地服務團應常態化,以使大學生更多地為前線服務。“談及戰地服務團,希望能組織一永久之機關,每人可前去一年,則于抗戰前途必大有利益。此次最佳之結果即為大學生在前方確有用處,非如一般人所意想,以為前方用不到大學生也。既證明大學生可在前方能有供獻,則在全民抗戰時期,應踴躍參加。”[5]410但實際情況并不如竺可楨所期許那樣,直到1944年第二批浙大戰地服務團才成立。據當時服務團團長支德瑜回憶,“竺校長在一月十三日舉行歡送茶會,授予綴有‘國立浙江大學戰地服務團’和校徽的團旗。他打開團旗時,激動得流了淚,說:‘這是代表浙江大學的,你們要記牢!’”(3)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湄潭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征集辦公室《貴州省湄潭縣文史資料》第5輯,1988年,第159-160頁。由此可見竺可楨對戰地服務團的重視與支持。
浙大師生為前線服務的工作還有很多,都得到了校長竺可楨的支持,比如,編演愛國戲劇,“為征屬募款”。竺可楨認為,歌詠、戲劇對抗戰而言,有“激勵士氣”之功。在浙大學生組織中,歌詠戲劇類組織早已存在,但在劇本編排上有不少問題。有鑒于此,竺可楨建議在劇本的選擇上,一定要突出愛國主義精神的主題,以為抗戰服務。在1941年1月20日第十二次總理紀念周上,竺可楨提到,“劇本的選擇,確實應當加以注意,偶一不慎,流弊即生。戲劇的主旨在激勵愛國愛群的精神,及倡發高尚的道德與人格。愛情固是戲劇中的要素,但須有偉大的愛,例如兩漢的尊崇伍員,宋以后的尊崇岳飛等。吾人當知中國若不偉大,則不能抗戰至今,所以凡是足以表示中國此種偉大精神的戲本,方可選用;壞的劇本,可以使人誤入歧途,為害頗大。今后希望同學中表演所用的劇本,應再三考慮,鄭重選擇,然后方能實負抗建之責”[1]535。
另外,竺可楨積極支持浙大師生慰勞過境之軍隊。1944年浙大學生成立了“戰時服務隊”,向過境的軍隊贈送食物、香煙、毛巾和草鞋等慰問品。對此,竺可楨十分關心。1944年11月2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九點自治會代表會主席支德瑜、服務部長郭可信來,談戰時服務隊工作情況:今日在丁字口設獻金臺,捐得二萬余元;又義賣物品買豬三只,以慰勞過境之九十八軍”[5]799。竺可楨還組織義賣,為前方將士募集寒衣。“明日本校舉行義賣,為前方將士募集寒衣,此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亦即所以盡吾人一點微小的責任而已!”[1]528
竺可楨主張大學生在后方努力讀書,同時也支持浙大師生為所在地服務,在認識到大學生對前線有所幫助后,也積極支持浙大學生到前線服務。努力讀書以及為地方與前線服務是抗戰前期竺可楨愛國主義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三、“投筆從戎”:從鼓勵從軍到強制參軍
從1941年開始,由于抗戰形勢的變化以及大學生處境的改變,竺可楨的愛國主義教育思想也發生了改變,經歷了從鼓勵浙大學子從軍,到強制其參軍的轉變。
鼓勵浙大學生參軍。1941年10月20日,竺可楨在總理紀念周講話時,首次表示鼓勵浙大學子參軍。他指出,此次抗戰,我國的大學生“安居后方,雍容受業”,“頗少直接之貢獻”。進而以一戰期間美國大學生做比較,“當時彼邦學子,一聞宣戰,其中百分之九十,輒行自動加入戰爭,否則其女友亦鄙夷之”[1]554。竺可楨為何要發此言論?與當時軍隊需要大學生加入有關。“惟此日軍中,需學識高深之人孔亟,如建造空軍,一次即須十人,其程度非大學修業一年不辦,以有是基礎而后始克繼予深造也。”[1]554所以,竺可楨鼓勵浙大學子參軍,“同學得茲報國立身之良機,則幸勿交臂失之可也”[1]554。目前,學界相關研究表明,1942年之前國民政府并沒有積極動員青年學生參軍(4)參見付辛酉:《從“青年學生志愿從軍”到“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民國檔案》2013年第2期,第131頁。。所以,竺可楨的認識可能是出于實際需要而改變的。
從鼓勵從軍到“固應從軍”。1943年末,國民政府發起了“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并頒布了《學生志愿服役辦法》,鼓勵青年學生參軍(5)參見侯德礎:《略論抗戰后期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民國檔案》2006年第2期,第118頁。。不過,竺可楨認為,大學生“不但志愿從軍固應從軍”,各個大學也應該做抗戰工作,“留校者亦應學習與軍事有關之科目,以備異日向前后方作軍事工作”[2]793。
竺可楨的認識不僅僅是在開會時的公開表態,而且是內心真實的想法。在動員浙大學生從軍的會上,竺可楨“勸學生憑自己良心驅使,不要觀望”[2]794-795,但在得知報名者中,全是女生,無一男生后,他在日記中寫道,“須眉未免減色云”[2]795。可見,當時竺可楨是切實主張大學生投筆從戎的。
建議大學生強制參軍。1944年11月3日,竺可楨在給陳訓慈的信中(6)陳訓慈,字叔諒,浙江慈溪人。時任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提出了更加激進的想法,即要求大學教育應加入軍事教育內容,大學生則應強制參軍。“我意在抗戰時期,尤其在反攻時期,大學課程應加以改變,應與軍事部門取得聯絡,采取英美大學辦法,授學生以軍事技術教育:如建筑橋梁,毀壞公路,運用軍事無線電,修理汽車,管理運輸,擔任翻譯(為配合盟軍)等,訓練一年后即強迫在部隊中服務。惟女生及殘廢者得免役。”[1]619
為什么竺可楨的思想到抗戰后期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呢?1944年7月1日,在浙大第十七屆畢業生典禮上,他表達了當時主張變化的一些原因。
首先,大學生人數增加,從“求過于供”到“求供已足”。竺可楨指出,由于國民政府實行“戰時大學教育與平時大學教育初無二致”[1]614,所以,盡管在戰時,但“專門以上學校之數量與學生比較戰前有增無減”[1]614,大學畢業生“最近兩年求供已足相應,有若干科目并且有供過于求之勢”[1]614。并且,他認為在抗戰結束以前,這種趨勢不會改變。
其次,反攻時期兵源要求提高。竺可楨指出,抗戰前期中國軍隊缺乏重炮、機械化部隊和飛機,而現在這一情況已完全改觀,但這些武器的使用,“非目不識丁的農夫可以短期內訓練,使能得心應手”[1]615。同時,“無線電的操縱,各種精細通訊網的組織,醫藥衛生常識的應用,工兵機械的使用,統非有大量知識青年加入軍隊不可”[1]615。所以,竺可楨認為,大學生參軍有助于提升軍隊戰斗力,而且也是“責無旁貸”的。
再次,英美等國人士的輿論壓力。竺可楨提到,一位美國教授對中國一方面大量“囤積”本國合格入伍的知識青年,一方面卻從“西半球運送美國青年來抵這個缺”[1]615大惑不解,在一封公開信中,言辭激烈地指出“為了爭取中國的獨立和民權,雖犧牲全體大學畢業生四分之一的生命,亦是值得的”[1]615,中國若亡國,知識青年何談“戰后建國的重任”;并且,“中國若要做一個戰勝國,她的大學必須立刻建設在抗戰基礎上,來訓練成千成萬軍隊所需要的飛機師、無線電服務員、炮手、譯員、工兵等等”[1]615。竺可楨的朋友、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也批評中國大學師生“不能為戰爭盡力”[1]615。所以,竺可楨認為英美等國大學生正在為抗戰而努力奮斗,“豈不是我們的大學尚在靠人成事,尚想坐享其成”[1]615。
最后,大學生投筆從戎,方能問心無愧,又能起到宣傳示范作用。竺可楨指出,抗戰是全民抗戰, 而“惟有我們的知識階級, 尚少投筆從戎”[1]615, 大學生“今乃退處后方安全之地,縱前方士兵不來責備,捫心自問,亦自有愧”[1]616。竺可楨認為,過去數年暑假,大學生去宣傳兵役,效果不佳,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大學生自己不當兵。“大學生要宣傳兵役最好是自己當兵。”[1]616
竺可楨愛國主義教育思想的轉變與抗戰形勢的改變息息相關,即他認為“抗戰已到了反攻時期,大學的使命也與平時不同,急切地需要與軍事配合,以求達到抗戰勝利的目標”[1]616。所以,竺可楨認為不僅應該“獎勵大學生去入伍,而大學本身也應該去做抗戰的工作”[1]616。
四、結語
通過梳理抗戰時期關于竺可楨救國思想的各種文獻可以發現,竺可楨愛國主義教育思想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轉變:從主張大學生努力讀書,到主張讀書的同時也要為地方與前線服務,再到主張大學生投筆從戎。
無論是主張努力讀書,抑或為地方與前線服務,還是投筆從戎,竺可楨愛國主義教育思想的出發點都是以救國為中心。在竺可楨看來,大學生在后方努力讀書,是因為大學生要做社會各界的領袖,以擔當起抗戰后建國的重任;為地方與前線服務,則可以為后方與前線“盡一點微小的責任”;投筆從戎,則是為抗戰勝利作出直接的貢獻。竺可楨思想轉變的背后與整個抗戰形勢和大學生的處境密切相關。需要指出的是,竺可楨思想轉變之后,并不會在實踐中就否定之前的做法,凡是對抗戰有利的工作仍在進行,但是在對學生的引導上開始發生改變。
透過梳理抗戰時期竺可楨愛國主義教育思想的轉變,可以推進對抗戰時期知識青年從軍的認識。既有研究主要認為,戰時知識青年從軍主要是國民政府政策的推動,但竺可楨的個案揭示出,知識青年特別是大學生從軍,與當時知識分子的救國意識變化亦有關系。從前文可知,竺可楨主張浙大學子投筆從戎至晚始于1941年,而國民政府出臺積極動員學生從軍的政策要到1942年以后。也就是說,竺可楨思想認識的變化,是個人自主性的反映,而非簡單迎合國民政府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