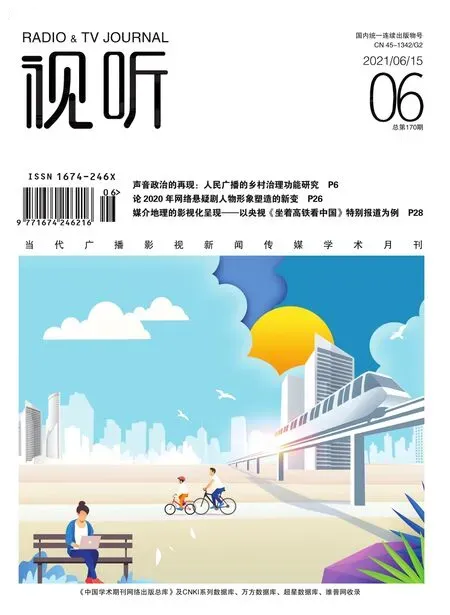從“Z世代”看移動視頻APP的人工智能應用
□ 穆芊澄
一、Z世代成為互聯網文化消費的主力群體
Z世代是美國及歐洲的流行語,指的是在1995—2009年間出生的人,也就是人們熟知的95后,這類人從小就受到互聯網、即時通訊、短訊、MP3、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電子科技產品的影響,被稱為“互聯網土著”。人民網研究院2019年組織編寫的移動互聯網藍皮書《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報告》中的《類型·結構·邏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文化產業》一文中指出,“Z世代正在成長為中國互聯網文化消費的主力群體。”QuestMobile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Z世代的用戶量接近3.25億,占比遠高于其他群體。在總人口增長數量有限的情況下,Z世代的互聯網使用情況和增長率使其成為各大移動應用平臺爭搶的受眾基礎。Z世代作為獨特的互聯網使用群體擁有以下幾點特征。
一是擁有互聯網和新媒體的使用偏好。Z世代作為互聯網的“土著民”,成長在充滿互聯網基因的壞境中,對互聯網有著強烈的依賴性,是移動社交平臺的主要參與者。娛樂、求知、交友成為他們使用互聯網的三大訴求。移動視頻平臺作為不斷發展的新媒體,逐漸從只能觀看視頻這一單一使用模式轉變為基于視頻分享的交流分享平臺,滿足了Z世代對互聯網的使用需求。
二是樂于“嘗新”“嘗鮮”。Z世代這一時代的人群,在短時間內享受著電子科技的更迭換代,智能手機、智能手表、VR眼鏡、可穿戴電子設備、智能家居等新技術形態和應用的不斷涌現,使Z世代相比其他年齡層受眾群體更能快速接受新事物的出現,并且表現出極強的興趣感。
三是擁有自己圈層的獨特符號。年輕和多元是Z世代的代名詞,他們擁有更為廣泛的興趣愛好,互聯網溝通鏈接的功能使他們能在網絡中找到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并在各種社交平臺中組建獨特的社交圈層,不斷吸引著更多同樣興趣的“盟友”加入。這些圈層也在發展中構建了一套套獨特的語言符號,像二次元圈層中的“漢服娘”“華夏衣冠”“魏天佑韓”,這些語言文字成為劃分不同圈層的符號載體。這個特點也可以理解為Z世代的受眾有著“標簽偏好”,也就是說,在購買和選擇使用一個產品或服務時,不光看重產品或服務本身,也會看重它背后的標簽,因為這個標簽就代表“我是什么樣的人”。
綜合來看,移動視頻App想要吸引Z世代成為其用戶并具有一定黏度,就必須滿足其追求個性、趣味的內容需求和高智能、多元化的使用需求。那么人工智能的應用和發展就成為移動視頻平臺奪取Z世代這一炙手可熱的用戶群體的重要武器。
二、大數據算法下的圈層劃分
哈佛大學的客座教授針托馬斯·可洛波洛斯對Z世代提出過“圈層效應”,也可以叫做“Z世代效應”。越來越多的老牌商業因無法走進這些圈層而喪失了“討好”年輕人的能力,面臨著流量無法變現、轉化率降低的窘境。而以嗶哩嗶哩彈幕網(下文簡稱B站)和抖音為代表的移動視頻App正是因為能夠打入圈層并成功劃分不同種類的圈層,才成為聚集一大批年輕用戶、滿足其文化消費需求和保持著高度的用戶黏性的成功案例。
(一)內容分發
以B站為例,B站現在采用內容三類分級法。第一大類有番劇、國創、放映廳、紀錄片、漫畫、專欄、直播、動畫、音樂、舞蹈、游戲、科技、數碼、生活、VLOG、鬼畜、時尚、廣告、娛樂、影視,總計20個頻道。這20個頻道下面包含多個小類,以番劇這一頻道為例,番劇下包括連載動畫、完結動畫、資訊和官方延伸4個小類。最后是以標簽形式存在的第三級類別。這種劃分細致的內容分類與騰訊視頻、愛奇藝、優酷等老牌網絡視頻平臺相比擁有更多的媒介層級,用戶可精準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的視頻內容,這種劃分方式為Z世代用戶構筑了一個個的“部落圈層”。
以往的媒體平臺,如百度、獵豹、搜狐等搜索引擎網站,內容分發的方式通常有三種:第一,按時間和點擊量的排序將內容展示給用戶;第二,采用網站編輯推薦的形式將內容展示給受眾;第三,依靠用戶手動搜索或定向關注對其展示內容。這種內容分發方式所掌握的每個用戶的偏好信息不多,且內容分類也不夠細致,很難滿足Z世代受眾圈層的喜好和需求。B站的大數據算法利用人工智能記錄下每個用戶的瀏覽內容和瀏覽行為,通過將這些操作行為歸類,為每個用戶繪制出一份專屬信息圖表,這些信息包括受眾的性別、年齡、地理位置、興趣愛好、政治傾向甚至是情感狀態。然后再將專屬的視頻內容精準地投放給受眾,用戶的瀏覽行為發生得越多,所繪制的個人信息的圖表也就越詳細。通過大數據算法分析出用戶可能感興趣的視頻內容,實現最快速度的從內容分發到被用戶打開的效率模式。
(二)數據反饋
作為一個擁有15個內容分區、7000多個文化圈層的年輕社區,如今B站的活躍用戶量已經達到了1.1億。B站的數據來源主要包括播放量、點擊率、評論量、投幣數和收藏量,同時也會涉及到用戶的性別比例、年齡層段、地域分布等,這些數據會跟著App的運營實時更新。但是數據的收集并不是最緊要的任務,如果不能將收集到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利用,就無法獲得最真實有效的信息,因此對于移動視頻App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將已收集的數據進行處理反饋。以B站為例,用戶在屏幕中顯示的內容都是有優先級順序的,平臺將視頻的播放量、彈幕數、投幣量和收藏量進行統一計算,得出一個綜合分數后優先推送分數高的內容,再進行新一輪的數據反饋,將最受受眾歡迎的視頻優先展示。人工智能還會記錄每個用戶的使用習慣,分析出用戶的瀏覽習慣,比如用戶注意力會最先集中到屏幕的哪個位置,便把最優先推送的視頻自動適配到此位置,從而極大地提升視頻的點擊率。
三、沉浸式體驗中的互動儀式鏈
互動儀式鏈理論是由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在2003年提出的,他認為互動的基礎是獲得情感能量,這是人類交流互動的核心要素。根據這一理論,互動儀式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基本包括四個方面:第一,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場所里;第二,對局外人設定了某種界限;第三,人們的注意力需要集中到相同的對象或活動中;第四,人們分享所產生的共同的情緒或者相同的情感體驗。當這些因素累積到一定程度,關注的焦點到達高峰,這些要素彼此作用會產生四種結果:群體團結、個體的情感能量爆發、有代表性群體的符號或神圣物、個體主動維護群體意識。
如今移動視頻App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做到了將傳統的視頻觀看平臺轉變為社交娛樂平臺,用戶不再需要聚集于一個真實的場景,而是通過虛擬的身體和場景進行互動儀式。以短視頻App抖音為代表,它的定位是潮流、音樂和記錄美好生活,通過用戶自制短視頻與人工智能的專業應用相結合,獲得粉絲的點贊、評論和轉發。15秒的短視頻產生碎片化娛樂,帶給用戶沉浸式的體驗。平臺中擁有較多高黏度的用戶,愿意主動分享自己的生活片段,參與到這場可以實現自我展示的社會互動過程中,并獲得共通的情感體驗。
(一)虛擬身體獲取儀式參與感
柯林斯認為,儀式的發生是身體經歷的過程,但在如今人工智能化的新型媒體平臺,身體在場變為虛擬身體在場,通過這個平臺,所有使用者同在一個舞臺。抖音是目前國內領先的短視頻社交平臺,也是最受Z世代喜愛的社交媒體平臺。抖音的成功依賴于其新穎的視頻制作玩法,其中語音識別技術、人臉識別技術、體感識別技術等人工智能技術與視頻玩法的融合營造出了年輕人喜愛的氛圍,滿足了他們樂于“嘗新”、喜歡新科技的使用偏好。以上這些技術的支持來自今日頭條人工智能實驗室(簡稱AI lab)。2017年讓抖音大火的新功能“尬舞機”就是依靠人體關鍵點檢測技術,這項技術可以檢測到圖像中包含的人體的各個關鍵點位置,從而實現用戶的動作姿勢與目標動作的準確匹配。通過這種簡單的舞蹈動作加上有律動的節奏和音樂,用戶制作屬于自己的短視頻并與廣大發布者進行互動交流或PK,用虛擬的身體參加儀式交流,實現了身體隨時隨地在場的虛擬集合。
(二)虛擬情境共享情感體驗
抖音的人臉識別AI技術在其AR特效、貼紙等功能上也有完美的體現。2019年抖音與央視春晚合作,推出了一系列以春節為主題的貼紙和視頻錄制特效,如“吃餃子”“拜年”“拉春聯”等,當用戶作出拜年的手勢時,屏幕中就會出現金元寶、春聯、燈籠等春節元素的圖案,并可以觸發多種春節相關的背景音樂,用戶可以通過這些豐富的視頻制作玩法參與各種活動,通過視頻進行社交互動,從而傳遞濃郁熱烈的節日氛圍,達到中國年闔家歡聚、歡樂吉祥的情感體驗。這樣的抖音像是一個舞臺,年輕人在這里進行創作和表演,并在分享和交流中獲得情感共鳴。
柯林斯認為,互相關注的焦點是儀式運作的關鍵要素。視頻發布者的目的是提升關注量和點贊數量,這些關注者們在同一場域中集中觀看同一個視頻,通過點贊和評論,表達自己的感情。在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感情能量,能夠促使用戶繼續觀看視頻,從而產生情感動員,完成互動儀式鏈。
四、結語
Z世代作為“互聯網土著”,是目前移動視頻App的忠實追隨者和使用者。移動視頻App要想謀求自身發展和繼續保持這一類受眾的使用黏性,就必須擁有互聯網思維,了解受眾的喜愛偏好和使用需求,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不斷開發出吸引Z世代用戶的新穎內容和全新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