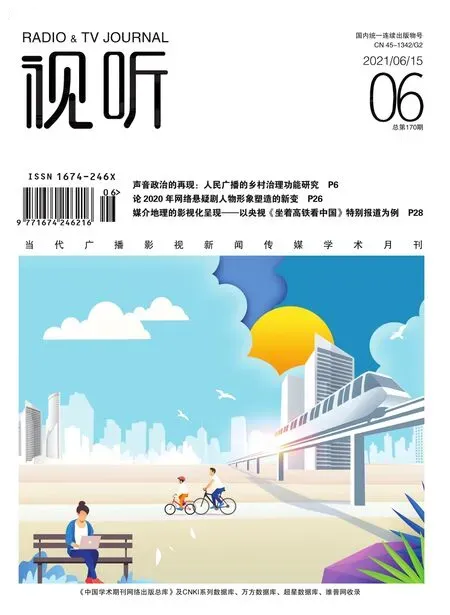中國廣告產業的變與不變
□楊浩
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傳感器,廣告產業與中國經濟一同迅速成長。然而,近些年中國廣告市場總體遇冷,尤其是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我國廣告市場在2020年更是出現應激式下滑。為此,在數字化生存的當下,我們有必要充分挖掘和把握廣告產業前進方向,重新審視其中的變與不變,厘清產業鏈上各個主體之間的關系,穩步前進,在關鍵之際推動廣告行業的持續發展。
一、昨天:廣告產業鏈式結構相對穩定
邁克爾·波特曾提出產業價值鏈理論,即廣告產業鏈是將廣告服務作為核心,憑借廣告的供需關系而圍繞在廣告產業及其衍生出的產業周圍的各企業,以某種特定方式聯結起來的鏈式組織。在傳統廣告產業鏈中,廣告活動一般是以“廣告主——廣告公司——廣告媒介——廣告受眾”這樣的鏈式結構運行。
處在產業鏈上游的廣告主往往作為整個廣告活動的起點,他們企圖將自己的產品推向受眾,樹立品牌形象,占據市場份額,這就需要通過產業鏈中游的廣告代理商即廣告公司設計廣告創意、制作廣告內容并選擇合適的廣告媒介,最后再由產業鏈下游的廣告媒體平臺發布廣告,到達目標消費群體。
在新媒體出現之前,廣告產業的運作幾乎都是以這樣一個方式進行。如此典型的線性單項式結構,使得各個主體間的屬性基本恒定,產業鏈結構比較穩定,傳播方式較單一,受眾往往是被動接受廣告。換句話說,廣告主如果不發布相關需求,就沒有接下來的廣告活動,也不會有任何廣告信息送達至受眾手中。
二、今天:主體邊界模糊,關系多樣化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和傳播手段的豐富,廣告受眾的地位不斷提升,由產業鏈末端帶來的變化倒逼著上游做出相應改變。在以受眾為中心的時代,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廣告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必須做出相應反應,謀求變化,以此贏得更大市場份額,獲取足夠多利潤,這樣才能維持自身的生存發展。
(一)廣告主:變的是購買方式,不變的是品牌價值
在傳統廣告產業鏈中,廣告主主要采用媒體購買的方式,即確定了用戶群之后,通過廣告公司確定相應的媒介資源,使廣告信息有效傳遞給受眾。這個過程的本質仍然是對媒體進行購買,最終投放效果主要看媒介資源是否有力,而不能跟隨受眾需求做到精準投放,這就會造成主觀性強和決策效率低等,因而遭受詬病。
程序化購買出現后,可以先通過對用戶數據進行分析,精確用戶畫像,找到目標受眾,然后購買這些受眾瀏覽的廣告位,其整個過程變為對受眾的購買。如今數字化技術的不斷升級優化以及人工智能的不斷普及,為廣告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多樣的渠道,智能穿戴設備的發展更為廣告購買帶來無限可能。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出現,為廣告主提供了遠超人類的數據分析和處理能力,能更為精確地監測潛在用戶數據,并通過對數據的判斷提供最優購買方案。如此高效、便捷的購買方式,大大提高了投放效率,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找到最優方案,使廣告信息傳播能夠實現高效、精準、實時動態的智能化。
然而,在追求受眾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廣告主追求高曝光率、高轉化率,甚至可以說是追求流量。許多廣告主在驗收廣告公司的投放成果時,甚至試圖以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關鍵績效指標)的形式量化效果,如以投放微博過程中積累的轉發、評論、點贊、閱讀數為指標,卻忽視了品牌價值的建構。然而,奧格威的“品牌形象論”告訴我們,在任何時代下,廣告主都不能忽視品牌價值的作用,品牌與品牌間的差異是在長期運營中得到消費者認可的,價值終會得到釋放,品牌將帶給企業忠實消費者,最終獲取盈利。
(二)廣告公司:變的是技術形式,不變的是內容本質
在傳媒環境與市場環境競爭尚不激烈的早期,盛行廣告代理制,廣告公司可以通過這種代理關系獲得營收,達到盈利目的,而廣告主為了獲得較好的傳播效果,只需選擇在受眾基數大的全國性或地區性媒體上投放廣告即可。然而在經濟下行和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下,產業鏈上游和下游的強勢崛起以及同行的競爭加劇,使廣告代理制無法獲得原有的利潤空間,廣告公司的兩大核心服務,即創意策劃和媒介購買,已不再完全打動廣告主。
兩股“去乙方化”的風暴正在營銷圈醞釀:媒體自營廣告和品牌自營內容。一方面,一些產品的品牌方還有媒體開始涉足創意領域;另一方面,互聯網媒體巨頭們憑借自身搭建的平臺生態,掌握了大量的媒介資源,以技術和數字資源涉足廣告產業。在DSP(Demand-Slide Platform,需求方平臺)平臺上,網絡媒體巨頭甚至跨過了傳統廣告公司,以技術掌握的用戶畫像為資本,直接與廣告主溝通,為其提供可行的營銷方案,將品牌信息精準送達受眾。
為了適應環境,廣告公司不得不適應形勢,將創意代理變為技術驅動。無論是業界阿里“鹿班”、京東“莎士比亞”、“利歐集團AI段子手”等智能廣告運作的應用,還是學術界關于智能廣告理論的構建,都在積極推動廣告運作流程向智能化創新的方向發展。廣告公司在進行人才選擇時甚至更傾向于招聘那些能寫代碼、能解決技術問題、能搞懂定量分析的營銷人員。
但是從實際操作來看,無論是基于數字驅動的智能廣告產業,還是依靠算法精準推薦的高人氣直播間,始終不變的都是對優質內容的堅持。百度在2017戛納國際創意節上提交的作品《Know You Again》就是技術與內容兼具的最好詮釋。百度運用AI技術為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人群設計了一款特殊的眼鏡,患者戴上這副擁有人臉識別技術的眼鏡之后,眼鏡可以自動讀取所視對象的外貌特征,通過細微差別判斷出身份并傳遞給受眾。這則借用技術外殼、堅持內容本質的創意廣告獲得了當年的銀獅獎。
(三)廣告媒介:變的是中介方式,不變的是營銷內核
2019年以來,基于個人關系的廣告媒介和基于稀缺資源的廣告媒介逐漸走向大眾視野。前者是通過無數個傳播者的個人連接具備了相當的傳播權力,成為一張龐大的社會流動信息網絡的節點,建構了一種生活化的信息流動;后者則是一對多的信息傳播,形成了一種中心發布和統一把關的權威信息流動。這兩種廣告媒介都是傳統廣告時代不曾有的中介方式,尤其是當這兩種方式相結合,加之數字技術的應用,一種新興的推廣場景就出現了,即電商直播間。
電商直播帶貨完美契合了廣告主對于垂直化、個性化市場的需求,這種新的中介方式也讓一大波明星、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有了大展拳腳之地。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央視主持人朱廣權與淘寶帶貨主播李佳琦的“小朱配琦”組合,全覆蓋宣傳,最后形成頂級流量,直播觀看次數達到1.22億,收入近四千萬,這是頂級資源形成的帶貨效果。
直播帶貨大火也驗證了產業鏈中的上游對于營銷本質的向往,畢竟廣告最終的目的是盈利。美國學者羅伯特·斯考伯和謝爾·伊斯雷爾曾經預言,場景時代將是互聯網下一個新時代。在每一個高人氣的電商直播間,都具備一個能說會道、了解產品的主推人員,他們扮演的依然是營銷人員的角色,如“口紅一哥”李佳琦、帶貨女王薇婭等,他們負責在短時間建構一個消費情境,從而影響受眾的購買行為。
(四)廣告受眾:變的是個性標簽,不變的是自我愉悅
廣告營銷經典理論從4P理論變為4C理論,無不凸顯受眾角色的重要性。如今4I原則的提出,更是讓廣告主們看到與個體受眾互動的價值。然而移動互聯網時代消費者的聚合使得廣告主可以利用大數據技術對消費者的媒介屬性、消費時段、使用位置進行監測,自然意義上的“消費者”已成為數字系統中可跟蹤分析、可預測行為的“消費者畫像”。正如上文所說,不同于媒體購買,廣告主受眾購買是通過對廣告受眾的平臺數據使用以及呈現出的個性化標簽進行分析,做到精確定位、精準投放。此外,廣告受眾在參與程度高、體驗感知強的廣告面前,更加會展現出自身的個性化標簽。
但無論廣告受眾的權力如何變化,他們對于自我愉悅的追求是始終不變的。契克森米哈最早提出心流體驗的概念,指的是個人通過專心致志地從事一項活動,達至欣然自樂的“忘我”境界。在廣告領域,當消費者處于心流體驗狀態時,將完全被廣告內容所吸引,沉浸其中,保持心情愉悅,流連忘返,并最終觸發購買行為。在2020年的“雙十一”購物節中,淘寶推出“超級星秀貓瓜分20億紅包”的活動,引發了一波全民云養貓的熱潮,5人組隊通過完成簽到、逛主界面、瀏覽店鋪等任務,就可參與瓜分紅包。與此類似的游戲化廣告還有很多,如星巴克“隨行卡”、拼多多“搖紅包”等,都是抓住了廣告受眾對于自我愉悅的需求。
三、明天:內容與技術相銜,感性與理性并重
智能化將是傳媒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廣告產業也將勢必受到智能時代的影響。技術公司、互聯網企業、MCN機構、電商平臺等紛紛布局廣告產業,使原來縱向的產業鏈條變得更加扁平化,產業鏈上的各個主體邊界也將愈發模糊,多元主體將更進一步影響廣告生產模式。
然而,技術的創新始終離不開優質內容的配合,否則技術終將是技術,技術的過度使用反而會引發大量廣告倫理問題。這需要我們更加注重廣告人員素養,將人文感性與技術理性相平衡,塑造高度的行業自律,將優質信息內容配合智能技術生產,達到更優的廣告效果。同時,未來如何立足于社會管理的視角,構建以法律為主導、以內容為本質、以技術為外殼的廣告產業,構建一套人文感性與技術理性并重、人與社會和諧的廣告新生態,將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