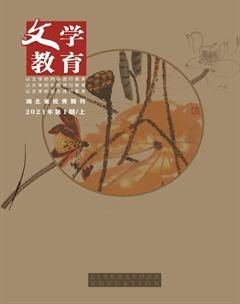作家聲音
●阿來認為游歷是創作的一部分
“不管是書本上的學習,還是在大地上行走、人群中行走,我的生活都是對自己寫作的積累。”在日前騰訊舉辦的騰云峰會上,作家阿來接受采訪時這樣說。在當天的騰云峰會上,阿來與戴錦華、葛劍雄、韓啟德、饒毅等文化和科技大家,就文化與科技的融合邊界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談到自己的創作經驗和心得, 阿來介紹,之前《塵埃落定》也不是刻意要寫的故事,是自己在大地上行走的經歷,“我不想寫作變成博士論文,不是按照市場要求一步一步每天都寫。如果在寫作過程中真正體會到藝術創作帶來的激情跟忘我的境界,我覺得必須是沉下心來的。”“有時候必須穿越一下,到另外一個世界體驗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阿來表示,生活是像藝術一樣的,像藝術家一樣的生活,學習、讀書。讀書,然后到現場,有的是讀當地文化史料,就到當地去,有時候一次去不行,回來看書又發現問題就再去。他介紹,“前年我去智利,當地大學請我去教學,我就制定了二十天旅行計劃,我拿著一本聶魯達的詩,在詩集當中把這些地名勾出去,我要去這些地方,為什么?是因為詩人寫到了。我覺得要像一個作家一樣生活,然后學習,包括游歷都變成自己創作的一部分。”在阿來看來,寫小說是深入生活、了解歷史,提升自己、豐富自己的過程。“我不把它看成是市場行為,趕緊寫一本書多賣點錢、多點讀者,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提升自己,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葉兆言稱寫南京就像從小三的角度看家庭
日前,“2020花地文學榜”年度短篇小說得主、《南京傳》作者葉兆言與評論家張檸、作家黃國欽圍繞“城市與文學”的話題展開對談。葉兆言認為,文學就是文學,重要的是誰在寫作。“其實很多被劃定為鄉村文學的作家寫的也就是城市。限定詞沒有那么重要。”張檸則認為,城市文學與鄉村文學最大的區別在于寫作對象。“鄉村文學側重書寫人和自然的關系。而在鄉村和城市人的思維方式交往方式差距極大,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事物都不同。書寫城市必須處理人和陌生人的事物關系,城市人每天都在更新換代,在高度緊張的生活狀態下生活。城市的書寫和生活都充滿了不確定性。”談到《南京傳》,葉兆言說:“為南京立傳,只是找到了寫作的興趣點。不存在地方文學地方特色。”對葉兆言而言,他以南京作為窗口寫中國歷史。“在中國歷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看,南京是中國歷史的副中心,可以通過它的失敗、創傷,來看中國歷史。從南京來看中國歷史,就像從小三的角度看家庭。”
●王蒙認為我們的文藝生活不能停留在段子上
王蒙日前在廣州大劇院就“我們的文藝生活”這一主題發表演講。現場還舉辦了舞臺劇《活動變人形》的啟動儀式。對于自己的小說能“立”上舞臺,王蒙表示很幸福。《活動變人形》是王蒙的代表作,對于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舞臺,王蒙表示:“在舞臺上用很接近生活本身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們想想,我們曾經是什么樣的,走過了什么樣的歷程,我們得到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活動變人形那一代人基本上已經離開我們了,但他們還有眼淚沒有流完,還有美夢沒有做完,還有很多愿望需要我們后世的人去做。”“我非常感謝廣州的藝術家們,廣州大劇院能下決心,把這個作品在舞臺上‘立起來,讓更多的人更直接地去感受這個故事。”王蒙說。談到“我們的文藝生活”這個話題,王蒙表示,“我想起了英國女王說過的一句話:英國寧可失去英倫三島,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亞。這表達了英國對莎士比亞的尊敬。”王蒙說,“我們對文學藝術、對戲劇、對話劇需要應有的尊重、熱愛。你看,我們的《紅樓夢》就把中國文藝扎得牢牢實實的,就能讓后代研究幾百年。”“創造人們喜聞樂見、又能對人們有所引領的作品,這是文藝工作者的本分。”王蒙說,“我們的文藝生活不能停留在抖音、手機段子上,否則就太對不起我們自己了,太對不起我們的文明了。”
●潘向黎說總希望對人存有善意
近日,潘向黎的短篇小說集《白水青菜》在朵云書院旗艦店首發。集中收錄了潘向黎二十余年寫作最具代表性的十四篇小說,包括《白水青菜》《我愛小丸子》《奇跡乘著雪橇來》《永遠的謝秋娘》等。潘向黎認為,短篇小說里的故事走向和性格表現、寫作者采取的寫作策略等,是冰山露在海面上的一角。“為什么露出這么一小塊,水下面肯定有個人的大量潛意識,這些意識有的自己也不太清楚,有的自己有所識別。”“同樣寫一個故事,我絕對不會寫披頭散發,廝打成一團,或者去單位砸場子之類的場面。”潘向黎說,“我總希望對人存有善意,無論出于什么樣的困境,貌似絕境,也希望能有些余地,留些祝福。這可能是一個女作家心底比較柔軟的一面。”“編這本書的時候我突然覺得上海已經不是一個元素,已經成為我創作乃至人生的一個底色。上海已經進入了我的審美、我的價值觀,進入我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