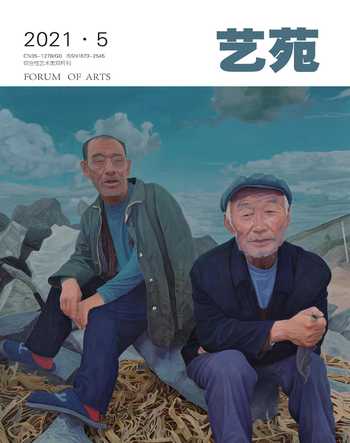漢畫像的美學式研究路徑
李新
摘 要: 《方花與翼獸:漢畫像的奇幻世界》從美學、圖像學等角度對漢畫像中的六個專題展開綜合研究。作者注意到漢畫像中基于現實又超越現實的成像方式,重視從想象力、比興思維等方面分析造像的思維方式,從層累的傳統文化、多元的外來文化和地域性文化等方面總結漢畫像的審美特征,還借助圖像辨識、形式分類和還原方位等方法,重點闡釋了六類圖像的象征內涵、審美精神,呈現出“點—線—面”的闡釋路徑,突出了“飛升化仙”的共同主題。
關鍵詞:漢畫像;美學式研究路徑;想象;象征
中圖分類號:J52 文獻標識碼:A
朱存明主編的《方花與翼獸:漢畫像的奇幻世界》作為《漢學大系》叢書的一種,2020年12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本書以漢畫像中的圖像為中心,選取漢畫像中的“方花紋”“靈芝草”“云化鳥”“虹”“翼獸”、《列仙傳》與漢畫像中的神仙形象對比等六類專題展開研究。作者們重視“經典闡釋與主題研究并重,歷史的考據與新出土文物的互證,古典文獻與出土簡牘對讀”[1]4的研究路徑,不僅僅基于圖像所處的“原境”[2]7展開研究,而且借助圖像學、符號學、象征主義等方法,聚焦漢畫像創造的思維方式和成像的審美特點,從美學角度(1)探究了漢畫像的象征內涵、審美精神和美學意義,對于漢畫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和借鑒意義。
一、基于漢畫像創造的思維方式
漢畫像是漢代藝術的重要遺存,是創作者基于現實又超越現實、借助想象力和比興等思維、 立意于象的結果。朱存明在本書的《前言》中指出:“‘漢畫’一下子把漢代的天與地、神與鬼、人與獸、美與丑、善與惡、吉與兇、災與異等展現在人們面前。”[1]1概括出漢畫像題材的豐富性和以象表意的創造性。從本書的論證方式和研究角度可以看出,作者們重視從思維方式角度對漢畫像展開研究。
作者們注意到了靈芝草、“云化鳥”“翼獸”等圖像中包含的現實因素,以此為出發點發掘圖像的內在意蘊。如“靈芝草可以致幻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菌類含有的裸蓋菇素——賽洛西賓。”[1]106“云化鳥”圖像是漢代人看到鳥兒或隱或現地飛行于云氣之間,激發了創作者的想象。[1]138“嚴格說來,虛擬想象的動物也是以自然界的動物為原型的。”[1]292這表明,漢畫像中不僅寫實、敘事的圖像,如庖廚圖、樂舞圖、狩獵圖、歷史故事等是現實世界的表現,而且非現實的圖像在某種程度上也寄寓了現實的因素。作者們探索漢畫像的現實因素,有助于理解圖像創造的原理、目的和功能等,是探究圖像的象征意義和美學內涵的重要基礎。
本書還注意到了這些圖像基于現實又超越現實的特點,重視主體想象力在創造圖像中的作用。第二章中指出靈芝草之所以表現為三種形態,是因為“任何圖像的創造首先來自于創造者內在心靈的需要”[1]70,突出了主體心靈在漢畫像創造中的主導地位。漢畫像創作中,主體借助想象力組合符號的過程,是“立意于象”[3]822的過程,也是象征意義生成的過程。第五章作者認為翼獸是“作為人們想象化的形象,把符號不同而文化功能相同的動物圖像進行了拼接組合”而創造出來的。[1]319創作主體以“意”擇象,但每一符號或圖像都不是隨意刻畫的,而是為“意”所制約,為“意”服務的。朱存明在《漢畫像之美》中就指出漢畫像是漢代現實、精神和文化等的“鏡像”,“人只能生活在一個現實世界,人不可能生活在一個死后的世界,但卻可以幻想一個死后的世界”[4]21。漢畫像中翼獸的“羽翼”大部分是為突出表現翼獸的神性而有意添加的,寄寓著羽化飛升的內涵和意義。主體借助想象力使多種符號集于單幅圖像中,以表達象征意義和文化內涵。
作者在論證靈芝草、虹、“云化鳥”“翼獸”等圖像時,根據形、音、義等方面的相似性解讀漢畫像中的圖像,是一種基于比興思維展開的研究。文中指出,靈芝因“T”字的形狀,而被類比為昆侖山、仙臺或“華蓋”,與西王母成為固定配置[1]86;“虹”與“橋”同形同構,漢代人便將其類比為登仙之橋[1]247;受傳統鳥圖騰崇拜的影響,漢代人認為人或者獸生出雙翼就可以羽化飛升。[1]322這些都符合漢代人的藝術創造思維方式。漢代人是借助譬喻取象、依類象形、立意于象等方式創造的藝術意象,體現了先秦比興思維在圖像創造中的應用。這也是漢畫像的象征意義得以生成的重要方式。作者們從形、音、義等象形、類比的思維方式出發,對漢畫像展開分析,有助于拓展漢畫像的象征意義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書作者們在研究圖像的過程中,從現實因素、想象力、比興思維等角度對漢畫像中的圖像展開研究,屬于美學式的研究范式。從這三個角度解讀漢畫像中圖像的象征意義,對于研究漢畫像的審美意識、審美價值和文化內涵,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同時,這三個角度從不同側面展現了漢畫像的創造規律,對于從美術史角度研究漢畫像也具有一定啟發意義。
二、聚焦漢畫像創造的審美特征
本書選取的六類專題在體現漢畫像創造的審美特征方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從圖像志溯源或跨文化視域等不同角度對圖像展開分類、比較和闡釋,體現出漢畫像創造的層累性、地域性和多元性等特點。
本書作者們重視從歷時的角度對圖像的形式和意義展開溯源,發掘圖像中積淀的、層累的文化元素。書中將“方花紋”遠溯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史前陶器上的花瓣紋和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上的花朵紋飾。本書還認為“云化鳥”圖像遠承新石器時期的云紋、鳥紋,近續商周器物上云鳥紋結合的紋飾圖案。作者們一方面溯源了這些圖像的形式演變,構成了關于它們的美術研究和藝術研究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探索與圖像內在意義相關的文化、思想和觀念的源頭,進一步深入分析圖像的內涵和意義。如作者根據“云化鳥”意象的地域分布特點,認為它與早期的東夷文化和鳥圖騰等有關,這就為解讀“云化鳥”意象中的再生、飛升等意義提供了理論依據。[1]157這種研究方法致力于發掘圖像的演進脈絡,在古今比較中,凸顯漢畫像的審美特征和獨特的時代意義。
本書對比同一圖像在不同地域的表現形式和表現風格,深入研究它們的審美精神和美學內涵。第二章、第三章主要是以地區為依據對圖像做出分類,如各地區的云化鳥圖像也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卷云形態的云化鳥集中于山東地區,蔓草云形態的云化鳥集中在陜西地區,流云形態的云化鳥散見于徐州部分地區。”[1]158這種區分屬于圖像志的、藝術學的方法,為進一步探究圖像的審美意識和審美特征提供重要依據。同一類的圖像之所以表現為不同的風格、樣式,與墓主人、創作者(工匠)的審美意識有直接關系。巫鴻就指出:“作為個人‘紀念碑’的裝飾,圖像母題又反映了主顧贊助人或工匠的思想、品味和個人喜好。”[5]12因而,根據漢畫像的地域性特點,分析各地區的表現方式和創造觀念,研究造成差別的審美意識、藝術觀念和文化因素等,從整體上把握該圖像的形式和內涵,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和闡釋該圖像在漢代的文化意義。
本書還重點關注了漢畫像中的外域文化,從跨文化的多元性視域研究漢畫像。作者認為兩漢時期是翼獸受外來影響而發展的關鍵期之一。[1]283-284“漢畫像中翼獸造型特征與羽翼的具體形態,受外來的獅首格力芬或帶翼獅的影響。”[1]268這是因為漢代打通絲綢之路,促進了與西域等外域文化的往來和交融,外來的思想、文化和藝術等大大激發了漢代人的想象力。漢代人從中吸收了羽翼等符號,用來表征飛升化仙等意義,是突破層累、彰顯創造的重要方式,豐富了漢畫像中圖像的表現形式。本書作者是從美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對漢畫像中“翼獸”圖像的象征意義展開分析,發掘出漢代翼獸文化不同于漢以前翼獸文化的獨特之處。
本書從歷時層累、地域性和跨文化的多元融合等三個角度,各有側重地對“云化鳥”“翼獸”等圖像展開了細致研究。這三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有機地體現在各個專題的研究中。如翼獸的研究,既注意到了“翼化”現象的層累性,同時側重從跨文化的多元視域探究漢代翼獸中體現的西域、中亞等新元素。漢畫像中的圖像是在多元層累的基礎上,結合地域性的審美意識和文化內涵,創造出飽含象征意義的藝術意象。聚焦漢畫像創造的審美特征展開研究,較為合理、細致和全面地對漢畫像中的圖像作出分類和分析,豐富和發展了漢畫像研究的路徑和方法,對其他圖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集中漢畫像的主題展開研究
本書各章分別選取了方花紋、靈芝草、“云化鳥”、虹、翼獸和列仙圖等六類圖像展開研究。它們之間并不是孤立的、割裂的,而是從不同角度體現了相似的主題——“飛升化仙”。這種基于某一類圖像,從整體上對這類圖像的內涵、圖式和意義等展開研究的基礎上,重視由單類圖像的專題性研究與多類圖像的譜系式研究相結合的路徑。
本書作者們重視圖像志、藝術學和美術學等研究的基礎作用,結合圖像的辨識、形式分類和還原方位與配置等方法,對圖像展開細致分析。如第一章以“方花紋的名實之辯”為始,第二章以“靈芝草的圖像判定”為端等。這種圖像辨識研究增強了主題立論的說服力,為圖像的分類研究等提供依據。作者們在比較、歸納中總結各類圖像的獨特規律,從不同角度對它們作出分類。如“云化鳥”圖像分為卷云化鳥、蔓草化鳥、流云化鳥等三大類,又詳細劃分出多種類型。[1]158“虹”圖像分為龍首龍身、雙首一身、單道、雙道等類別。[1]206-215這種“微觀研究”有助于分辨同類圖像之間的異同,發掘它們的形式特點和規律。作者們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進一步結合圖像的方位和配置,還原圖像的“原語境”。如第一章根據方花紋出現的方位——藻井、棺蓋、墓室頂蓋、祠堂頂蓋、銅鏡鈕等位置,總結出它的“頂”和“中”的特點;第二章總結出芝草與西王母、伏羲女媧、羽人和四象等的配置規律。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依據單幅圖像解讀它們的美學內涵和象征意義帶來的誤判,是重要的和必要的,體現了嚴謹的研究態度和科學的研究方法。
本書作者更加重視漢畫像中圖像的表征功能,探究圖像的象征內涵和審美精神,從而提煉出共同的主題。他們認為,不僅芝草、翼獸等圖像具有象征性,方花紋和云化鳥紋等具有裝飾性的圖像也具有象征意義。“漢畫像中的方花紋就是用抽象簡潔的符號來表達漢代人對生命永恒的追求。”[1]45“云化鳥這種紋飾在漢畫像中具有宇宙不同層次分界線的意義。”[1]138這就將裝飾功能和象征意義統一起來了。這是由漢畫像的創造方式決定的。漢畫像是創造者借助想象力和比興思維等立意于象的成果,是為死者服務的現實世界的“鏡像”,其中每一個圖像和符號都具有它獨特的內涵和意義。朱存明在《漢畫像的象征世界》中就提出了漢畫像的“宇宙象征主義”,認為漢畫像的世界是一個“巨大的象征體”,其中包含著漢代人思想文化和審美意識等,是漢代人認識、表現世界的重要方式。[6]76但是每一類圖像的象征意義又不是唯一的,如靈芝草圖像包括“不死仙藥”“有德瑞應”“升仙憑證”等;虹圖像包括“司雨之神”“升仙之橋”“龍宮之門”“天穹之蓋”等象征意義,體現了漢畫像內容的豐富性和漢代文化的多樣性。本書作者以具體圖像為中心,從“象征”的角度更深入地研究圖像的象征功能、美學特征和美學意義等,區別于從藝術學和美術考古等方向對圖像的形式和創造規律的研究,是探究漢畫像和漢代的美學觀念和審美精神的重要方面。
在單類圖像的象征意義的基礎之上,突出多類圖像的共同主題和譜系,是本書的重要特點。本書選取的六類圖像盡管在圖像形式、圖像配置等方面存在不同之處,表現為各自不同的具體內涵和象征意義,但它們并非是零散的和隨意組合的,而是共同指向了“飛升化仙”的主題。“方花紋”寓意煉形飛升、“靈芝草”是服食升仙的仙草、“云化鳥”是漢代氣化飛升思想的表現、“虹”是登仙的橋梁、“翼獸”表征著漢代羽化飛升的觀念、第六章則是從圖文互釋的層面研究漢畫像中的列仙形象。六類圖像分別從升天式、登仙式、羽化成仙式(2)三個角度表現了兩漢祈求飛升化仙的時代主題。但由于主體、地域、時期等不同,其表現同一主題或相近主題時所采取的表現形式會有差異。這種主題性的研究以具體的圖像研究為基礎,比較、歸納多類圖像所表征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發掘其中蘊含的共同主題,有助于從宏觀角度把握漢畫像的美學內涵、象征體系和時代意義,也為研究漢代的文化觀念和思想體系提供了理論支撐。
本書各章的研究體現出從“點”到“線”再到“面”的闡釋路徑,是一種圍繞主題展開的專題性、譜系式研究。作者們以漢畫像中的同類圖像的辨識、分類、配置等為基礎,聚焦“象征主義”的視角,由象揭意,通過解讀單類圖像的象征意義、審美精神和美學內涵,總結多類圖像中共同蘊含的主題和意蘊,鮮明地體現了美學式的圖像學譜系研究。這種研究路徑對其他主題和專題的漢畫像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結 語
總而言之,本書從美學、圖像學等角度對漢畫像中的六類圖像進行綜合研究,體現為從分類研究到整體研究、從形式分析到內容分析的全方位、多層面的研究路徑。這種研究旨在通過解讀漢畫像,發掘其中蘊含的審美意識、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等,實現多類圖像的主題研究和譜系建構。這是基于金石學、考古學、文化學和藝術學的研究之上的美學式的研究范式,,探尋漢畫像的美學意義和審美境界。本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表明,漢畫像中蘊含、融匯了早期文明和外域文明的思想、文化和藝術元素等,體現了漢代文化綿綿不斷的繼承性、生生不息的創新性和多元交融的包容性。漢畫像基于傳統,開拓進取的創新品質,對當下的藝術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我們可以反思優秀傳統文化中積淀的精華,結合新的時代因素和外來文化,創造出凸顯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的優秀文化和藝術。這也凸顯了漢畫像研究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注釋:
(1)巫鴻、朱存明等學者們都詳細了漢畫像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演進歷程。如巫鴻在《武梁祠》中,提到了金石學的研究、19世紀以來的綜合研究、藝術學的研究、考古學的研究等方法,他采取的是在圖像志基礎上,展開圖文互釋的研究方法。參見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三聯書店,2006年,第39-80頁。朱存明提出了漢畫像研究的四種歷史范式——金石學式、考古學式、文化學式和藝術學式等,他在《漢畫像之美》中采取基于四種研究范式的美學式研究方法。參見朱存明:《漢畫像之美:漢畫像與中國傳統審美觀念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3-48頁。
(2)朱存明認為漢畫像中的升仙有三種樣式:升天式、登仙式和羽化成仙式。朱存明:《漢畫像的象征世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方花是煉形升天的工具、靈芝草屬于服食升仙的仙藥;虹橋等是登仙的媒介;云化鳥、翼化則是羽化成仙的方式。
參考文獻:
[1]朱存明.方花與翼獸:漢畫像的奇幻世界[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20.
[2]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M].北京:三聯書店,2006.
[3]黃暉.論衡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7.
[4]朱存明.漢畫像之美:漢畫像與中國傳統審美觀念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5]巫鴻.公元2世紀的天界圖像[M]//鄭巖.陳規再造:巫鴻美術史文集卷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6]朱存明.漢畫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林步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