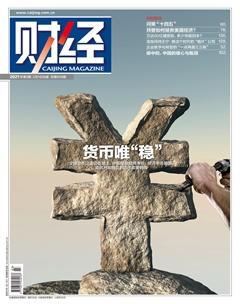經(jīng)濟(jì)紓困,須激發(fā)更多城市潛力
李鐵 徐勤賢

未來,通過降低就業(yè)和居住的門檻,發(fā)揮城市眾多的數(shù)量和低成本優(yōu)勢(shì),結(jié)合中心城市的發(fā)展,可能成為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的重要政策選項(xiàng)之一。圖/IC
最近我們注意到,一些學(xué)者對(duì)2021年及未來中國的經(jīng)濟(jì)增長十分樂觀。
得出這種判斷大致有幾個(gè)依據(jù):一是中國已經(jīng)順利擺脫了疫情影響,目前是全球唯一實(shí)現(xiàn)正增長的主要經(jīng)濟(jì)體;二是一些發(fā)達(dá)國家仍然處于疫情危機(jī)的困擾之中,一枝獨(dú)秀的中國必然會(huì)帶動(dòng)強(qiáng)大的市場吸引力;三是中國自身的經(jīng)濟(jì)增長動(dòng)力仍然在發(fā)揮作用,特別是后疫情時(shí)期,2021年會(huì)實(shí)現(xiàn)報(bào)復(fù)性增長;四是中美貿(mào)易關(guān)系在美國新一屆領(lǐng)導(dǎo)班子上臺(tái)之后,不會(huì)繼續(xù)惡化。
通過對(duì)內(nèi)外發(fā)展環(huán)境的對(duì)比分析,中國的經(jīng)濟(jì)增長將會(huì)出現(xiàn)好的發(fā)展趨勢(shì),甚至在2021年會(huì)達(dá)到接近兩位數(shù)的增長。有一些研究機(jī)構(gòu)樂觀估計(jì),2021年經(jīng)濟(jì)增速最高可達(dá)到11%,最低也能達(dá)到8%-9%,也有學(xué)者預(yù)計(jì)為6%。
我們看來,要進(jìn)行經(jīng)濟(jì)預(yù)測(cè),不能僅以某一年的發(fā)展結(jié)果作為分析基礎(chǔ),還是要在長期趨勢(shì)分析的基礎(chǔ)上再進(jìn)行判斷。同樣,我們要面對(duì)的不是如“歐美發(fā)展勢(shì)頭放緩,或其他國家仍處于疫情危機(jī)之中”這樣的相對(duì)變化,而是中國自身經(jīng)濟(jì)的增長趨勢(shì)。雖然疫情后中國由于防疫得力占有一定優(yōu)勢(shì),但是影響宏觀趨勢(shì)的國際國內(nèi)格局并沒有發(fā)生根本的變化。
因此我們判斷,2021年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可能看起來比2020年會(huì)好一些,但是從長期增長態(tài)勢(shì)看,還不能過于樂觀。
導(dǎo)致經(jīng)濟(jì)下滑的因素并未被遏制
從2010年-2020年的GDP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看,剔除疫情嚴(yán)重的2020年,經(jīng)濟(jì)增長已呈現(xiàn)大幅下滑的趨勢(shì),即使2020年底前有了恢復(fù)性增長,也并沒有改變這種下滑趨勢(shì)。
從2005年-2019年的GDP增長速度看,2007年GDP增速達(dá)14.2%,到2019年下滑到6.1%(圖1)。分階段來看,“十一五”時(shí)期(2006年-2010年)GDP年均增長速度為11.3%,“十二五”時(shí)期(2011年-2015年)降至7.5%,而“十三五”時(shí)期(2016年-2019年)降至6.6%,如果算上2020年,“十三五”增速會(huì)更低。
圖1:2005年-2019年GDP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jì)局《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2020》。制圖:顏斌
影響GDP增長的因素很多,包括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等,但是主要體現(xiàn)在投資、外貿(mào)和消費(fèi)三個(gè)方面。我們僅從2010年到2019年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就可以看出明顯的經(jīng)濟(jì)下滑趨勢(shì)。
一是投資增長速度下滑明顯。2010年全社會(huì)固定資產(chǎn)投資增長速度為23.8%,持續(xù)下滑到2019年的5.1%(圖2)。
圖2:2010年-2019年全社會(huì)固定資產(chǎn)投資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jì)局《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2020》
二是消費(fèi)增長速度持續(xù)下滑。2010年社會(huì)消費(fèi)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為18.3%,持續(xù)下滑到2019年的8%(圖3)。
圖3:2010年-2019年社會(huì)消費(fèi)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2012 年-2020 年)
三是對(duì)外貿(mào)易呈現(xiàn)波動(dòng)式下滑態(tài)勢(shì)。2010年-2012年全國貨物進(jìn)出口總額的增長速度由34.7%連續(xù)下滑到6.2%,2013年稍有提速后又連續(xù)下滑到2015年的負(fù)7%,之后2017年增速回升到14.2%后又呈現(xiàn)連續(xù)下滑趨勢(shì),2019年下滑至3.4%(圖4)。
圖4:2010 年-2019 年全國貨物進(jìn)出口總額及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1)貨物進(jìn)出口總額來自于《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2020》;(2)貨物進(jìn)出口總額增長速度來源于歷年統(tǒng)計(jì)公報(bào)。
2010年-2019年的投資、消費(fèi)和進(jìn)出口三個(gè)方面的數(shù)據(jù)總體上均呈現(xiàn)下降趨勢(shì),僅進(jìn)出口貿(mào)易總額曾經(jīng)有過劇烈波動(dòng),在2015年曾經(jīng)見底,之后又出現(xiàn)了恢復(fù)性增長,但是也沒有擺脫持續(xù)下滑的態(tài)勢(shì)。
中國的工業(yè)形勢(shì)也不樂觀。一是工業(yè)增加值增速下滑明顯。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增加值同比增長速度從2007年的18.5%下降到2019年的5.7%(圖5)。
圖5:2005年-2019年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增加值同比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jì)局,國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2005-2019年)
二是工業(yè)制成品產(chǎn)銷也處于下滑態(tài)勢(shì)。2019年家用電冰箱生產(chǎn)量比2013年減少了787萬臺(tái),而產(chǎn)量同比增速從2010年的23.02%下降到2019年的負(fù)1.11%,銷量在2014年超過9200萬臺(tái),到2019年下降到不到8000萬臺(tái)。全國家用洗衣機(jī)生產(chǎn)量的同比增長速度從2010年的25.62%下降到2019年的2.27%,雖然家用洗衣機(jī)銷量仍維持在7400多萬臺(tái)的高位,但是銷量增速從2010年的24.13%下降到2019年的3.25%。汽車銷量雖然從2010年的1806.19萬輛增加到2019年的2576.9萬輛,增長速度從32.37%下降到2019年的負(fù)8.2%。
目前,尚未看到各種政策和內(nèi)外部環(huán)境的利好,如大規(guī)模引進(jìn)外資、貨幣增發(fā)、財(cái)政刺激,以及外貿(mào)環(huán)境變化等。至少從前10年甚至前15年的經(jīng)濟(jì)走勢(shì)來看,即使沒有疫情和中美貿(mào)易關(guān)系的巨大變化,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導(dǎo)致的經(jīng)濟(jì)下滑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當(dāng)下,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續(xù)蔓延,有些人對(duì)中國一枝獨(dú)秀持樂觀態(tài)度,但顯然忽視了一個(gè)基本事實(shí),全球經(jīng)濟(jì)形勢(shì)惡化,中國并不能獨(dú)善其身。中國雖然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后三個(gè)季度仍能保持正增長,但這是相對(duì)優(yōu)勢(shì),并不意味著引起經(jīng)濟(jì)下滑的因素都得到遏制。
中美貿(mào)易關(guān)系沒有根本改善,疊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仍然會(huì)對(duì)中國2021年的經(jīng)濟(jì)增長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
在拜登接任美國總統(tǒng)后,中美貿(mào)易關(guān)系會(huì)不會(huì)立即發(fā)生扭轉(zhuǎn),還需要時(shí)間來驗(yàn)證。而川普留下的政治遺產(chǎn),可能仍會(huì)對(duì)未來的中美關(guān)系產(chǎn)生不利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疫苗接種速度滯后于疫情傳播速度,對(duì)全球貿(mào)易的影響應(yīng)該會(huì)貫穿2021年全年。近期外貿(mào)對(duì)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應(yīng)該是穩(wěn)定的。國內(nèi)的投資取決于貨幣和金融政策,“保穩(wěn)定,防風(fēng)險(xiǎn)”是基本出發(fā)點(diǎn),可能不會(huì)出現(xiàn)投資浪潮,因此投資對(duì)經(jīng)濟(jì)的帶動(dòng)能力有限。
消費(fèi)則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就業(yè)的增長。2000年-2019年,中國就業(yè)人數(shù)從7.8億下降到7.74億,而增長速度從2001年最高的1.3%下降到2019年的負(fù)0.15%(圖6)。從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人數(shù)看,2019年比2014年增加了604萬人,五年間平均每年增加100萬人(圖7)。而2020年三季度末,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勞動(dòng)力為17952萬人,比上年同期少了384萬人。雖然是受到了疫情的影響,但什么時(shí)候能恢復(fù)到2019年的就業(yè)水平,仍取決于經(jīng)濟(jì)增長的幅度。而經(jīng)濟(jì)下滑導(dǎo)致的就業(yè)下降,也會(huì)直接影響到消費(fèi)的動(dòng)力。
圖6:2000年-2019年就業(yè)人數(shù)及同比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就業(yè)人數(shù)來源于《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2020》,增長速度根據(jù)就業(yè)人數(shù)計(jì)算
圖7:2009年-2019年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人數(shù)(萬人)

資料來源:歷年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cè)調(diào)查報(bào)告
城市是中國未來經(jīng)濟(jì)增長的最大潛力
中國確實(shí)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并不等于已經(jīng)從發(fā)展困境中解脫出來。中央提出“國內(nèi)國際雙循環(huán)”的基本出發(fā)點(diǎn),就是要在外部環(huán)境十分不確定的情況下,更好發(fā)揮內(nèi)循環(huán)動(dòng)力。而內(nèi)循環(huán)或者說是拉動(dòng)內(nèi)需的基本政策前提,還是要建立在防范金融風(fēng)險(xiǎn)和各種債務(wù)風(fēng)險(xiǎn)的壓力下。
顯然,建立內(nèi)循環(huán)增長的動(dòng)力機(jī)制需要新思路,要在提高質(zhì)量的基礎(chǔ)上,從提高效率、挖掘潛力入手,而不是遵循以往增發(fā)貨幣,刺激債務(wù)增長,過度激發(fā)地方政府積極性的老路。
如果從“保就業(yè)、促增長”的角度出發(fā),就不能忽視如何通過增加更多就業(yè)來刺激消費(fèi)的作用。據(jù)統(tǒng)計(jì),中國的14億人口中,中等以上收入人口占4億,中等以下收入人口為10億。如何讓更多較低收入人口進(jìn)入到中等收入群體,需要解決現(xiàn)有未充分就業(yè)的城鎮(zhèn)人口和約2億農(nóng)村閑置勞動(dòng)力的就業(yè)和收入提高問題。在現(xiàn)有就業(yè)總?cè)丝诨A(chǔ)上,在未來一段時(shí)間必須要繼續(xù)增加就業(yè)數(shù)量。
解決就業(yè)問題,不能依靠農(nóng)業(yè),也不能把重點(diǎn)放在農(nóng)村,因?yàn)楣I(yè)和服務(wù)業(yè)等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的最佳就業(yè)空間一定是在各類城市。在穩(wěn)定現(xiàn)有8.5億城鎮(zhèn)常住人口的就業(yè)外,還要增加近2億農(nóng)村人口進(jìn)入各類城鎮(zhèn)就業(yè),這是促進(jìn)消費(fèi)的最基本保證。要把更多人口納入非農(nóng)就業(yè)渠道帶動(dòng)消費(fèi)增長,可利用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更多在城市。
可以說,城市是未來刺激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最大潛力。
按照人們的慣常理解,中國的城市只是現(xiàn)有的684個(gè)設(shè)市城市。這個(gè)概念需要糾正,這是中國行政區(qū)劃的一種特殊設(shè)置方法,現(xiàn)實(shí)中的設(shè)市城市實(shí)際上是包括中心城市和各類城鎮(zhèn)在內(nèi)的行政區(qū)。而實(shí)現(xiàn)產(chǎn)業(yè)就業(yè)增長的空間,顯然需要更為明確的城市政策來支撐。
那什么是城市?應(yīng)該是各類不同規(guī)模和稱呼不同的空間上的實(shí)體城市。否則中國有8.5億的城鎮(zhèn)常住人口,卻只有不到700個(gè)城市,這在中國城市化進(jìn)程中怎么也說不過去。如果將城鎮(zhèn)建成區(qū)人口10萬或5萬,甚至是3萬的城鎮(zhèn)定義為空間獨(dú)立的實(shí)體城市,那中國的城市數(shù)量最多可達(dá)到接近5000個(gè)。其中既包括縣城,也包括幾十萬人口和數(shù)萬人口的特大鎮(zhèn)和大鎮(zhèn),還有各類遠(yuǎn)離城市主城區(qū)的市轄區(qū)、新區(qū)或產(chǎn)業(yè)園區(qū)等。
如此眾多的城市在吸引要素進(jìn)入和承接大城市功能疏解的過程中,會(huì)發(fā)生不同的作用。其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按照新的城市標(biāo)準(zhǔn)來確定中國的城市空間格局,并通過市場的作用,在不同人口規(guī)模的城市間配置要素和資源。
這些資源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勞動(dòng)力和土地。中國有14億人口,其中城鎮(zhèn)戶籍人口6億多人,在各類城鎮(zhèn)就業(yè)的農(nóng)民工2.9億,還有約8000萬的城鎮(zhèn)間流動(dòng)人口,未來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還有近2億的新增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要進(jìn)入城鎮(zhèn)。他們的就業(yè)、居住和消費(fèi),以及公共服務(wù)需求都要在城市里解決。而且因?yàn)樗麄円验L期的消費(fèi)和投資從農(nóng)村、原居住地轉(zhuǎn)移到就業(yè)所在地的各類城市,這也會(huì)帶動(dòng)投資的增長。
但是這些人口會(huì)在什么樣的城市定居落戶,是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在現(xiàn)在的各類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主城區(qū)嗎?顯然不是,因?yàn)檫@里的就業(yè)和生活成本是他們無法承受的。另一方面這些城市因利益結(jié)構(gòu)固化導(dǎo)致了包容性不足,會(huì)對(duì)他們進(jìn)行排斥。所以,需要更多與他們的就業(yè)能力和收入水平相接近的城市才可以承載這些勞動(dòng)力資源。這就要求在現(xiàn)有的設(shè)市城市之外,尋找已經(jīng)存在的、符合勞動(dòng)力需求特征的實(shí)體城市空間。
事實(shí)上,這樣的城市大量存在。在中心城市周邊存在大量三五萬人口的小城市,可以起到緩解主城區(qū)高房價(jià)的壓力。在現(xiàn)有的中心城市主城區(qū),由于優(yōu)質(zhì)服務(wù)和資源集中,房價(jià)居于高位。即使多年來已經(jīng)對(duì)投資和投機(jī)性購房采取了行政限制性措施,仍然無法平抑房價(jià)。根本的辦法是通過大城市周邊的小城市來緩解主城區(qū)的房價(jià)壓力。
隨著城市人口規(guī)模越來越大,居住郊區(qū)化也會(huì)隨之出現(xiàn),會(huì)充分發(fā)揮周邊小城市承接疏解的作用。需要注意到,在經(jīng)濟(jì)增長動(dòng)力不足的同時(shí),住房投資的增長速度仍然處于正增長。2019年房地產(chǎn)開發(fā)投資額高達(dá)13萬億元,比2010年高出近9萬億元(圖8)。雖然商品房銷售面積的增長有所停滯,但是商品房銷售額仍然高達(dá)近16萬億元,仍然是凈增長。如果利用好中心城市周邊數(shù)量眾多的小城市,不但可以帶動(dòng)一部分住房投資,也會(huì)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中心城市主城區(qū)的高房價(jià)。
圖8:2000年-2019 年房地產(chǎn)開發(fā)投資額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jì)局《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2020》
中國外出務(wù)工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大約有1.8億。從近幾年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看,其中有20%的農(nóng)民工購買了住房,但絕大多數(shù)并不是在就業(yè)地和人口流入地區(qū)購買的住房,而是為了解決未來子女教育和老人就醫(yī)問題,在家鄉(xiāng)的縣城購買的住房,這是一個(gè)現(xiàn)實(shí)趨勢(shì)。
人口流入地區(qū)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舉步維艱,但是人們的投資和消費(fèi)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多元化的途徑。如果他們把長期投資和消費(fèi)預(yù)期選擇在家鄉(xiāng)的縣城,不僅會(huì)帶動(dòng)住房投資的增長,而且也會(huì)帶動(dòng)基礎(chǔ)設(shè)施和公共服務(wù)投資的增長。
有關(guān)部門提出了要加強(qiáng)中西部地區(qū)縣城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實(shí)際上就是在推進(jìn)城市化進(jìn)程中,開辟另一類城市空間。這些基礎(chǔ)設(shè)施和公共服務(wù)的投資,也會(huì)成為未來拉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的潛在動(dòng)力。
小城市也會(huì)成為中國工業(yè)發(fā)展的新載體。隨著產(chǎn)業(yè)園區(qū)的開發(fā)成本高企,過去通過房地產(chǎn)開發(fā)的高收益來填補(bǔ)招商引資和產(chǎn)業(yè)園區(qū)投入成本的方式已經(jīng)不可持續(xù)。尋求新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空間,降低產(chǎn)業(yè)進(jìn)入成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周邊的小城市來實(shí)現(xiàn)。小城市的成本相對(duì)主城區(qū)更低,既可以降低產(chǎn)業(yè)進(jìn)入成本,同樣也可以成為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的重要潛力和動(dòng)力。更重要的是,在小城市更容易推進(jìn)農(nóng)村集體建設(shè)用地入市的改革,也有利于調(diào)動(dòng)小城市周邊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參與小城市建設(shè)和工業(yè)發(fā)展的積極性。
上世紀(jì)80年代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國發(fā)達(dá)地區(qū)經(jīng)濟(jì)蓬勃發(fā)展的基礎(chǔ)。而未來在中心城市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同樣可以利用小城市低成本的優(yōu)勢(shì),進(jìn)行產(chǎn)業(yè)疏解,同時(shí)為小城市提供更多工業(yè)和服務(wù)業(yè)就業(yè)機(jī)會(huì)。
中國未來的經(jīng)濟(jì)增長,要發(fā)揮城市數(shù)量多的優(yōu)勢(shì)。連接城市間的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促進(jìn)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發(fā)展,不是僅僅依靠大城市就可以實(shí)現(xiàn)的,而是要充分利用大中小不同規(guī)模城市的作用,在空間上進(jìn)行統(tǒng)籌規(guī)劃,按照市場方式合理配置資源和要素。
未來,通過降低就業(yè)和居住的門檻,發(fā)揮城市眾多的數(shù)量和低成本優(yōu)勢(shì),結(jié)合中心城市的發(fā)展,可能成為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的重要政策選項(xiàng)之一。
(本文根據(jù)作者在新浪年度經(jīng)濟(jì)人物論壇上的主旨發(fā)言整理,有增刪;編輯:朱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