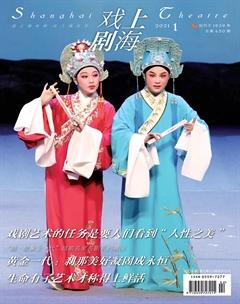“小”劇場(chǎng),戲曲的“大”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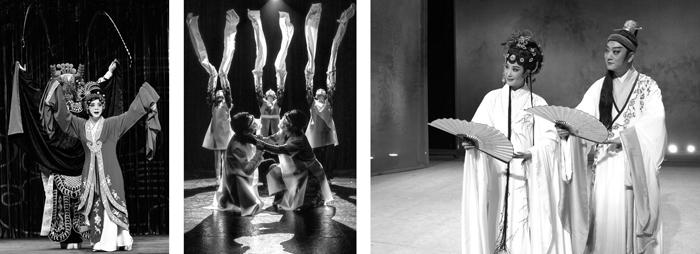
編者按:上海的小劇場(chǎng)戲曲展演已經(jīng)走過了6年,2020年舉辦的第6屆展演正式升格為“中國小劇場(chǎng)戲曲展演”,掛上了“國字號(hào)”,具有了更明確的行業(yè)標(biāo)桿意義。從2015年到2020年,這個(gè)年度性的戲曲活動(dòng)越來越受到全國戲劇界的重視,吸引了越來越多從業(yè)者的參與。本次上海越劇院青年創(chuàng)作沙龍以“云筆會(huì)”的方式邀請(qǐng)了一線的青年戲曲從業(yè)者,以此為題來談?wù)勊麄儏⑴c小劇場(chǎng)戲曲創(chuàng)作的感受,以及他們理解的小劇場(chǎng)戲曲。
小劇場(chǎng)戲曲實(shí)踐感想
俞鰻文|青年導(dǎo)演
大概因?yàn)槲沂且孕?chǎng)話劇出道的,所以切換到小劇場(chǎng)戲曲也比較早、比較自然,創(chuàng)作了《夫的人》《望鄉(xiāng)》《流光歌闋》《宴祭》《桃花人面》等作品。我的小劇場(chǎng)戲曲代表作品主要可分為兩個(gè)方向,即西方經(jīng)典文學(xué)的東方化和中國古典故事的當(dāng)代化,它們亮相過全國各地的小劇場(chǎng)戲曲節(jié)。我在小劇場(chǎng)創(chuàng)作中所堅(jiān)持的實(shí)驗(yàn)性、樣式感,跟我自身“西學(xué)中業(yè)”的發(fā)展軌跡是分不開的。于我而言,小劇場(chǎng)不僅是演出區(qū)域的空間,它更應(yīng)是創(chuàng)作維度的空間,所以“小劇場(chǎng)”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護(hù)航我去求索戲曲的可能性,可能性即是生命力。而這種“可能性”并不僅僅是樣式上的探索,它可以是講故事的結(jié)構(gòu)、可以是表演的方式等等。對(duì)我來說,大劇場(chǎng)、小劇場(chǎng)都不可避免有我個(gè)人的審美屬性,它們對(duì)我作為一名舞臺(tái)劇導(dǎo)演的專業(yè)能力的考察側(cè)重不同,所以我?guī)缀醪粫?huì)把它們放在一起比較。
忻雅琴|(zhì)青年演員
2018年我第一次參與創(chuàng)作了小劇場(chǎng)戲曲《再生·緣》,這完全打破了之前我的所學(xué)所感,也給我?guī)砹撕艽髥l(fā)。站在創(chuàng)作者的角度,我有幾點(diǎn)分享和體會(huì):一是小劇場(chǎng)戲曲為我們年輕演員帶來了很大的創(chuàng)作空間。《再生·緣》的創(chuàng)作打破了我們往常“被安排”的創(chuàng)作思路,演員走到了前面,開始了前置性創(chuàng)作,主動(dòng)性更強(qiáng),經(jīng)過實(shí)踐我們也深刻體會(huì)到主動(dòng)創(chuàng)作的益處。二是小劇場(chǎng)的創(chuàng)作打開了我們傳統(tǒng)表演手段。《再生·緣》不但是在傳統(tǒng)題材上有所汲取,更重要的是演出樣式的改變,我們打破傳統(tǒng)鏡框式舞臺(tái),嘗試性地運(yùn)用了“沉浸式”概念,觀眾與演員的距離近了,對(duì)演員的細(xì)節(jié)性表演要求就更高了,特別是觀眾作為演出的一部分,也增加了不確定因素的發(fā)生,演員如何運(yùn)用自己的表演將觀眾“帶回”演出,這是我們傳統(tǒng)表演舞臺(tái)上很難遇到的“考題”。
裘丹莉|青年演員
當(dāng)下的小劇場(chǎng)戲曲基本是題材先鋒的實(shí)驗(yàn)性戲曲為主,希望能贏得當(dāng)下年輕人的喜愛。對(duì)戲曲我內(nèi)心也充滿著“新鮮感”的渴求,看了很多小劇場(chǎng)戲曲,我覺得不少作品帶給我驚喜。2019年,我參與了小劇場(chǎng)戲曲越劇《宴祭》的創(chuàng)作,擔(dān)任了該劇的策劃和主演,這也是我第一次參與了小劇場(chǎng)戲曲創(chuàng)作。《宴祭》取材于西方故事,對(duì)于如何把西方故事改編成適合越劇來演繹的東方故事,在和編劇們和導(dǎo)演一次次的探討過程中,最后定的主題是:一個(gè)極致的、唯美的愛情故事,在“愛情”之外,又生發(fā)了東方式的主題——大仁大義、至情至性。我們?cè)O(shè)定《宴祭》的觀眾群是以80后到90后的年輕觀眾為主,但在后來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們還是決定要照顧到越劇很多老觀眾們的觀感體驗(yàn)。實(shí)驗(yàn)性、先鋒性的創(chuàng)作,并不是完全拋卻了以前所有的表演方式一股腦兒地棄舊圖新,而是應(yīng)該在保留戲曲傳統(tǒng)藝術(shù)精髓的本體上,再進(jìn)一步探索和創(chuàng)新。就越劇而言,昆曲和話劇是越劇的兩個(gè)“奶娘”,越劇吸取昆曲程式化的寫意,也結(jié)合了話劇的寫實(shí)——博采眾長的吸取和探索,并不代表越劇要變得“純?cè)拕』保@樣只會(huì)造成劇種特征的弱化。我概念中的小劇場(chǎng)戲曲,是先鋒的、時(shí)尚的,也是具有劇種特色的本體性和審美風(fēng)格的。看小劇場(chǎng)越劇作品,觀眾一聽一看覺得這就是越劇!越劇該有的流派特色和古典神韻都在,但展現(xiàn)方式可以是新穎的、大膽的、讓人耳目一新的!帶著本體的核心與時(shí)俱進(jìn)、兼容并包、兩相融合,才能做出屬于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優(yōu)秀小劇場(chǎng)戲曲作品。
趙? 斌|青年音樂創(chuàng)作者
我曾參與過越劇《再生·緣》、越劇《小城之春》等小劇場(chǎng)戲曲作品的音樂創(chuàng)作。我個(gè)人感覺,小劇場(chǎng)給予我們的創(chuàng)作空間是非常“大”但又非常“難”的。“大”主要體現(xiàn)在藝術(shù)包容與藝術(shù)創(chuàng)新方面,只要符合本劇種的前提下,各種音樂元素、唱腔元素都可以加入進(jìn)來,對(duì)創(chuàng)作者來說既有實(shí)驗(yàn)性,又有挑戰(zhàn)性,要嘗試如何讓戲曲藝術(shù)更貼合社會(huì)發(fā)展與現(xiàn)代觀眾的審美趣味。一說起戲曲,可能很多觀眾就認(rèn)為傳統(tǒng)京劇是聽不懂、不好聽、節(jié)奏太慢,那我們小劇場(chǎng)戲曲就是要先做一種讓觀眾能感興趣、能進(jìn)入劇場(chǎng)來觀看的,讓觀眾通過小劇場(chǎng)來喜歡我們戲曲、進(jìn)入戲曲的審美。比如我擔(dān)任《再生·緣》的音樂設(shè)計(jì),導(dǎo)演給我的要求是音樂要有電影感,因?yàn)檫@部戲是沉浸式越劇體驗(yàn),需要有強(qiáng)烈的代入感。我借鑒了電影中類似宇宙空間這樣的場(chǎng)景的音樂,用一個(gè)特別慢速的長音八拍來把觀眾帶入主題,使觀眾快速進(jìn)入劇中。還有在伴奏手法上,加入流行、古典、搖滾等不同音樂風(fēng)格來伴奏我們的越劇唱腔,使很多第一次看戲的觀眾眼前一亮,被我們?cè)絼∶陨狭恕?/p>
其次,“難”也是最大的問題,因?yàn)槊總€(gè)劇種都有自己的本體,雖說我們是小劇場(chǎng)創(chuàng)新,但是其他任何手段上的創(chuàng)新,都不能把聲腔與念白丟了,這是我們地方劇種最大的特點(diǎn),也是最大的象征。所以唱腔上我們非常扎實(shí)地傳承本劇種的特點(diǎn)與特色唱腔流派,在傳承之后再考慮創(chuàng)新。比如在小戲《小城之春》中,我擔(dān)任唱腔與音樂設(shè)計(jì),在音樂上大刀闊斧的同時(shí),對(duì)唱腔我堅(jiān)持保留原汁原味的越劇流派唱段,因?yàn)樵绞谴蟾母锏膭∧吭揭A魝鹘y(tǒng)唱腔,不然就聽不出你是哪個(gè)劇種的了。然后,流派還必須分明,我在劇中為各個(gè)主人公分別設(shè)計(jì)了花旦王派、呂派,小生尹派,老生張派,比較有代表性的越劇唱腔板式“囂板”和“流水”也運(yùn)用其中,讓人一聽就知道是越劇。這也是老先生教我們的:夾縫之中求生存!既要?jiǎng)?chuàng)新更要傳承好!
小劇場(chǎng)戲曲的探索意義
魏? 睿|青年編劇
二十余年來,小劇場(chǎng)戲曲方興未艾,是古老戲曲藝術(shù)和現(xiàn)代文明共同孕育的新生命,踴躍地成為創(chuàng)新的先鋒,開辟出一方綠洲,充滿自由的藝術(shù)新鮮空氣。
藝術(shù)家們對(duì)小劇場(chǎng)戲曲的定義基本已達(dá)成共識(shí),小劇場(chǎng)并不指小型劇場(chǎng)里的戲曲演出,而是指戲曲創(chuàng)作敢于突破傳統(tǒng)固有思維模式,敢于挑戰(zhàn)既定價(jià)值理念,以獨(dú)立的思辨精神,新穎的表現(xiàn)形式,以小見大,別有洞天,用戲劇真文學(xué)傳達(dá)人性深度。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小劇場(chǎng)戲曲并非憑空出現(xiàn),而是有意無意間向20世紀(jì)80年代中國現(xiàn)代戲曲黃金時(shí)代致敬,有掀起新一輪“文藝復(fù)興”之希望。在思想空前大解放的80年代,戲曲藝術(shù)在文學(xué)層面完成了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劇作家們激情迸發(fā),才華釋放,然而二度創(chuàng)作層面尚未尋找到全新的轉(zhuǎn)型途徑,這一輪戲曲藝術(shù)的脫胎換骨便被動(dòng)地中斷了。這不能證明現(xiàn)代戲曲脫離了時(shí)代發(fā)展,而是證明了一個(gè)殘酷的事實(shí):現(xiàn)代戲曲剛剛萌芽便淺嘗輒止地停止了發(fā)育,面臨淪為案頭劇的危機(jī)。相比同時(shí)代話劇,戲曲慢了一拍。如今,隨著上海和北京兩地一年一度小劇場(chǎng)戲曲節(jié)的舉辦,小劇場(chǎng)戲曲越來越普及,為都市年輕受眾所歡迎。我認(rèn)為,小劇場(chǎng)戲曲一方面在文學(xué)性思想性上努力對(duì)接80年代的高峰,另一方面在二度創(chuàng)作上不斷創(chuàng)作新語匯,揚(yáng)棄傳統(tǒng),學(xué)習(xí)借鑒話劇、影視、舞蹈等藝術(shù)的優(yōu)勢(shì),彌補(bǔ)80年代未完成的遺憾,雖然成長之路艱辛,但是相信“文藝復(fù)興”終會(huì)姍姍來遲。
鐘海清|青年編劇
近些年,隨著小劇場(chǎng)戲曲節(jié)的舉辦,每年都會(huì)涌現(xiàn)出數(shù)量可觀的作品。對(duì)新銳編劇或體制外的編劇而言,創(chuàng)作小劇場(chǎng)戲曲劇本是一種很好的選擇,既可以自由表達(dá)自己的想法,劇本也容易被劇團(tuán)采納。但是現(xiàn)在一些小劇場(chǎng)戲曲的創(chuàng)新形式已被大劇場(chǎng)的作品所接納和借鑒,而小劇場(chǎng)戲曲的創(chuàng)意和形式也似乎走到了一個(gè)瓶頸,想再提升恐怕還有待實(shí)踐。小劇場(chǎng)戲曲的藝術(shù)性是因?yàn)樗闹黝}有新意、有反思,將現(xiàn)當(dāng)代西方文藝思潮融進(jìn)來。它的商業(yè)性,在于相對(duì)容易操作的運(yùn)營空間,以及吸引到一些年輕化的文藝觀眾群體。當(dāng)下兼有藝術(shù)性、商業(yè)性的小劇場(chǎng)戲曲作品一般來源于原本就有實(shí)力的戲曲院團(tuán),能夠在劇本質(zhì)量、演出質(zhì)量上有所保障。因此重點(diǎn)不是小劇場(chǎng)戲曲作品所體現(xiàn)的藝術(shù)性和商業(yè)性,而是如何在作品的質(zhì)量上更有所保證。小劇場(chǎng)戲曲有其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主體和演出機(jī)制,跟小劇場(chǎng)話劇不一樣。然而本質(zhì)上同樣追求思想性、藝術(shù)性,以及探索新的觀演關(guān)系。因此它們不是看齊的關(guān)系,而是都要繼續(xù)在思想性和探索性上有所追求。在我的概念中,小劇場(chǎng)戲曲應(yīng)該不僅僅有創(chuàng)意、有形式、有風(fēng)格,還可以追求文學(xué)性,追求文化內(nèi)涵,以及劇作技法。
王柔桑|青年演員
無論從現(xiàn)代觀眾的欣賞習(xí)慣、新媒體時(shí)代的特點(diǎn),或是從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需求來看,如今眾多短小精悍、易于傳播的藝術(shù)形式展現(xiàn)出了極強(qiáng)的競(jìng)爭(zhēng)力,這一切正是信息化時(shí)代帶來的不可抵擋的發(fā)展潮流。同樣,中國傳統(tǒng)戲曲也正面臨如何順應(yīng)時(shí)代變化發(fā)展的課題,也許小劇場(chǎng)戲曲正是在這股時(shí)代潮流下應(yīng)運(yùn)而生的一種探索吧。我認(rèn)為,作為專業(yè)的戲曲藝術(shù)團(tuán)隊(duì)除了質(zhì)量上乘的大型“拳頭”作品,同時(shí)也應(yīng)該大力探索、鼓勵(lì)、發(fā)展小劇場(chǎng)形式的劇目,為傳承、弘揚(yáng)中國傳統(tǒng)戲曲做出切實(shí)的貢獻(xiàn)。
也許有人擔(dān)心戲曲小劇場(chǎng)表演形式會(huì)被話劇同化,但從藝術(shù)特征來說,每個(gè)傳統(tǒng)劇種都有它獨(dú)特的屬性,只要遵從藝術(shù)的傳承規(guī)律,揚(yáng)長避短、吐故納新,就不會(huì)被歷史淘汰。再說,戲曲的本質(zhì)即“歌舞演故事”,因此我認(rèn)為小劇場(chǎng)戲曲只要本質(zhì)不變,適時(shí)適度地改變表現(xiàn)形式未嘗不可。同時(shí),正因?yàn)樾?chǎng)戲劇容量小、時(shí)間短、距離近,使得觀眾對(duì)于作品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契合度、立意高度、思想深度,以及對(duì)演員的表現(xiàn)力要求更高了。我想作為戲曲人更要力求充分發(fā)揮表演能力,要么在思想性和表演節(jié)奏上更貼近現(xiàn)代觀眾的審美觀,要么就把傳統(tǒng)戲曲的四功五法做到極致、精益求精。
徐? 偉|青年導(dǎo)演
在筆者看來,大家對(duì)于“小劇場(chǎng)”這個(gè)概念的界定存在模糊,好像很多人認(rèn)為在小劇場(chǎng)演出的戲曲就是小劇場(chǎng)戲曲了,所以當(dāng)下會(huì)存在著“大戲小演”的情況,大家只是把戲放到了小型劇場(chǎng)進(jìn)行演出,有了小劇場(chǎng)的“表”,卻未有小劇場(chǎng)的“里”。除體量外,大多數(shù)的小劇場(chǎng)戲曲與大劇場(chǎng)的作品似乎并未存在明顯的差異。但小劇場(chǎng)運(yùn)作的特點(diǎn)是實(shí)驗(yàn)性,“通過調(diào)整觀、演距離,進(jìn)行小規(guī)模的探索和實(shí)驗(yàn),來實(shí)現(xiàn)話劇自身的突破與提高”。當(dāng)我們將“小劇場(chǎng)”這一舶來的概念嫁接到中國傳統(tǒng)的戲曲身上時(shí),我們要追求的亦應(yīng)該是其精神的“里”,要探索試驗(yàn)的是傳統(tǒng)戲曲藝術(shù)在新時(shí)代的發(fā)展方向及可能性,畢竟戲曲藝術(shù)的產(chǎn)生是有其歷史局限性的,我們不能將它供上高高的神壇,而是要找到它在當(dāng)代的位置。
從這個(gè)角度來說,賦予其當(dāng)代意識(shí),應(yīng)該是小劇場(chǎng)戲曲探索的最主要方向。這個(gè)當(dāng)代意識(shí)要包括其當(dāng)代思想、當(dāng)代內(nèi)容、當(dāng)代語匯、當(dāng)代觀演關(guān)系,從實(shí)驗(yàn)和探索入手,開辟傳統(tǒng)戲曲藝術(shù)在新時(shí)代發(fā)展的各種可能性,這樣小劇場(chǎng)戲曲才能真正抓住“小劇場(chǎng)”這一概念的“里”。藝術(shù)性及探索性在前,商業(yè)性在后,而且強(qiáng)調(diào)商業(yè)性,也非“小劇場(chǎng)”的精神內(nèi)核。小劇場(chǎng)戲曲不同于小劇場(chǎng)話劇,其探索之路可能會(huì)更加艱難,畢竟這是一條嫁接的路,所以我們應(yīng)該給予小劇場(chǎng)戲曲更寬容的態(tài)度,去接受它所有可能的實(shí)驗(yàn),當(dāng)然,不管如何試驗(yàn),“以歌舞演故事”的本體寫意性這一戲曲藝術(shù)的根本特點(diǎn)不可偏頗,這也是戲曲藝術(shù)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