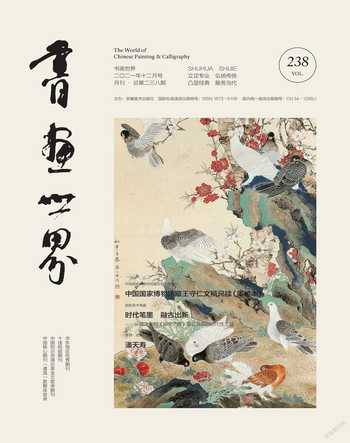三見三羊
唐躍





于興洋
于興洋,中國山水畫創(chuàng)作方向碩士,國家二級(jí)美術(shù)師,就職于新華學(xué)院藝術(shù)學(xué)院。現(xiàn)為安徽省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安徽省書法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安徽青年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理事、安徽省書畫院特聘畫家、合肥市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理事、合肥市政協(xié)書畫院畫師、蚌埠市書畫院特聘畫家。
于興洋的作品上經(jīng)常可見“三羊”的落款,很有些“洋”字拆開來入畫的感覺。至于說“三見”,未必很準(zhǔn)確,但確實(shí)有那么三次,我對(duì)興洋畫作的印象特別深刻,還能形成前后的邏輯鏈接,從而對(duì)興洋山水畫的認(rèn)識(shí)逐步走向深入。
初次見到興洋的畫作,似乎是在2019年12月舉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安徽省書畫院建院40周年作品展”上。開幕式那天,我坐在前排,面對(duì)著登臺(tái)致辭的各位嘉賓,在致辭者身后的展墻上,布置著兩幅八尺整張大小的山水畫,很奪人眼球。開幕式結(jié)束后,我靠近細(xì)看,發(fā)現(xiàn)兩幅畫不僅畫題同為“黟山新韻”,落款也同為“于興洋”三字,于是,這個(gè)名字令我日后無法忘卻。再看畫面內(nèi)容,畫的都是黃山,都是層巒疊嶂、巍峨高聳的氣勢(shì),但畫法上一則方勁,一則圓潤(rùn),放在一起并不感到重復(fù);還能明顯看出來,兩幅畫都體現(xiàn)了較為深厚的傳統(tǒng)筆墨功力,尤其是對(duì)新安前賢繪畫的傳承和發(fā)揚(yáng),同時(shí)注重設(shè)色渲染,以云霧繚繞、蒼松繁茂作為山勢(shì)的烘托,稍加淡化絕俗孤高、空寂清淡的遺世意趣,呼應(yīng)了熱情洋溢、蓬勃向上的時(shí)代主題。
兩個(gè)月后,興洋送我一幅《溪山幽境圖》,使我有機(jī)會(huì)再次接觸到他的山水。畫作篇幅不大,只有若干近景,呈現(xiàn)了自畫面右側(cè)逶迤而下的一段荒坡,歪歪斜斜地立著的幾棵雜樹,以及疏木掩映著的書屋。從敞開的柴門看進(jìn)去,屋里有一張案幾,幾上有一瓶插花,并沒有看到人。荒坡的右側(cè),落了“三羊”兩字窮款,右下鈐有一枚“臥游”朱文印章,顯然是從倪高士、漸江僧一路下來的畫風(fēng),非常典型。這幅畫不是為參加畫展而作,沒有任何主題,純屬朋友之間的雅玩,所以有些炫技,仿佛對(duì)著我說:看看這位新安傳人畫得咋樣!我自然喜歡這種畫境,簡(jiǎn)約,清凈,心遠(yuǎn)地偏,書屋里沒有人,好像是等待哪位閑云野鶴般的雅士坐進(jìn)去。左上還有些留白,也是等待幾句淺斟低吟的填充。于是,我脫口賦成七言絕句,把讀畫的感受和人生的感悟都表達(dá)出來:“孤嶺荒坡向粉霞,枯枝野草向天涯。平生欲問緣何事,一案書香一圃花。”隨后拜托潛園主人江健龍題寫增色,畫面雖然很小,卻是詩書畫印俱全。
又過了幾個(gè)月,“案上云煙—于興洋國畫作品展”在時(shí)代美術(shù)館揭幕,我又一次欣賞到興洋的山水畫,而且欣賞到了數(shù)十幅畫作所構(gòu)成的完整風(fēng)貌。此次相見所得到的印象,比起初次相見和再次相見來,更為全面,也更為深入。這些作品有著很清晰的師承痕跡,縈繞著很濃郁的漸江學(xué)人、梅壑散人、垢道人等新安前賢的氣息,在清峻、幽曠中寄托著高逸的情懷。不僅如此,興洋在師法新安畫風(fēng)的前提下,適當(dāng)借鑒梅清和石濤的畫法,回避了從清峻走向荒寒、從幽曠走向冷寂的創(chuàng)作路線。賀天健先生在比較漸江、梅清兩人畫黃山的異同時(shí)說過,漸江得黃山之質(zhì),梅清得黃山之影。言下之意,漸江畫黃山時(shí)注重質(zhì)感,更多地把主觀情感傾注進(jìn)去,梅清畫黃山時(shí)注重影像,雖然相對(duì)外在,卻也愈加生動(dòng)。興洋明白其中的奧妙,所以下筆時(shí)汲取了梅清的特點(diǎn),比如行筆流暢豪放,運(yùn)墨酣暢淋漓,用線靈動(dòng)盤曲,富有運(yùn)動(dòng)感,等等,借以弱化、調(diào)和新安畫派那種偏于生澀、冷峻的面貌。具體說來,展出的山水畫大致分為三種情形,如《山水六條屏》《秋山林木圖》《溪山話別圖》《幽居圖》等,近似梅清筆法,畫出山勢(shì)的盤旋曲折,畫出山彎的云煙變化,顯得峭拔秀美,氣韻充沛;另如《漸江詩意圖》《清人詩意圖》《山亭圖》《亭小得山高》等,師承漸江僧的構(gòu)圖和筆法,但在線條處理上,把那些接近幾何體的堅(jiān)挺直線畫得稍加柔和,不再枯瘦,在設(shè)色處理上也是稍加濃郁,增添了些許暖意;再如《叢樹寒煙》《疏流寒柯》等直指荒寒的作品,畫面上的樹木呈現(xiàn)為叢狀,并非獨(dú)立的,甚至是倒掛的一棵或者兩棵,氛圍稍加渲染,并非單純的大片空白。如此一來,似乎不是徹骨的隆冬嚴(yán)寒,更像早春時(shí)節(jié)的乍暖還寒。
看著興洋的畫,不由想到一個(gè)話題:我們應(yīng)當(dāng)怎樣繼承前賢和弘揚(yáng)傳統(tǒng)?或者說,我們應(yīng)當(dāng)怎樣舉起新安畫派這桿旗?怎樣打好這張牌?當(dāng)下安徽畫壇,無不為這塊土地上有過漸江僧和新安畫派感到驕傲,也都想舉好這桿旗,打好這張牌,但比較成功的實(shí)踐范例并不太多。平心而論,漸江僧和新安畫派不那么容易傳承。新安畫派帶有遺民文化的特點(diǎn),漸江僧等明代遺民不滿清人統(tǒng)治,追求遺世獨(dú)立,所以畫面顯得非常荒寒、枯寂和清冷,當(dāng)下無論如何不能這樣畫。畫家可以有獨(dú)立性,但不能追求出世,不能追求遺世獨(dú)立,不能逃脫充滿生機(jī)的、正在進(jìn)步和發(fā)展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興洋的機(jī)敏之處在于,他以漸江僧等新安前賢為底色,把梅清、石濤的筆法融合進(jìn)來,整體上自然和諧,既繼承了新安畫派等優(yōu)秀傳統(tǒng)精華,又避免了傳統(tǒng)中與現(xiàn)實(shí)有抵觸的內(nèi)容。可以說,興洋的山水畫提供了一條師承傳統(tǒng)的有效路徑,提供了一個(gè)具有普遍意義的范本。面對(duì)興洋的山水畫,一看畫面構(gòu)圖和筆墨韻味,就知道他在師法新安畫派;如果深入看下去,又能看出他有獨(dú)到之處,看出他把傳統(tǒng)放在時(shí)代發(fā)展的背景下重新審視,進(jìn)而生發(fā)出新的筆意。他的山水畫卷,結(jié)合《凈界》之類的花卉作品,總體上展現(xiàn)出一個(gè)經(jīng)過凈化的祥和境界,表達(dá)了對(duì)寧靜而又美好的生活的向往。
其實(shí),我接觸興洋的山水畫不止以上三次,真正的第一次應(yīng)當(dāng)追溯到15年以前。與興洋熟悉以后,我注意過他的入展獲獎(jiǎng)簡(jiǎn)歷,才知道他出道很早,2004年就以一幅《云擁山朦朧》入選過第七屆安徽省藝術(shù)節(jié)的書畫展。展覽由省文化廳主辦,我那時(shí)任職于文化廳藝術(shù)處,具體負(fù)責(zé)辦展事宜,一定過眼了那幅山水作品,只是眼光不濟(jì),沒有記住這位頗具潛力的畫家,以至于多年后遇見他,貌似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再有一次,就是最近,幾位畫家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發(fā)出一個(gè)畫展預(yù)告,即將在蘇州彬龍美術(shù)館開展的“憶江南—長(zhǎng)三角三省一市優(yōu)秀青年中國畫作品展”邀請(qǐng)了于興洋等幾位安徽畫家參展,并展示了興洋的一幅山水畫新作《宋人詩意圖》。看到這幅作品,我感到興洋所意寫的漸江僧已臻妙境,幾可亂真,轉(zhuǎn)而又有了新的期盼。現(xiàn)今,興洋潛心師法前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顯著成果,接下來需要融古為我,化繭成蝶,獨(dú)樹一幟,畫出更鮮明的個(gè)性,形成更嶄新的風(fēng)范。也就是說,興洋如今面臨著新的藝術(shù)轉(zhuǎn)折點(diǎn),希望他能站上新安前賢的肩膀,奔向更高的山岡。
2021年4月15日
約稿、責(zé)編:史春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