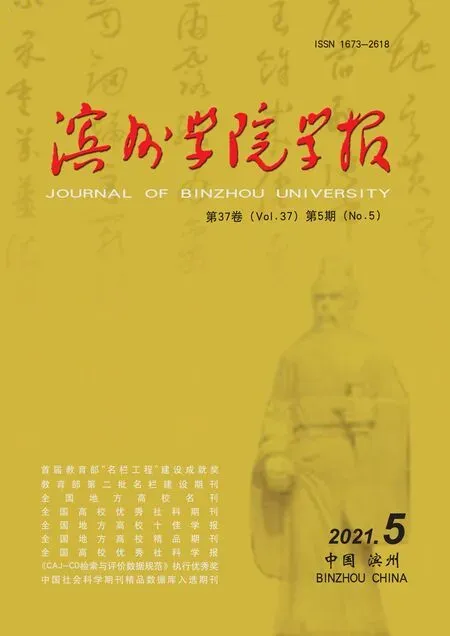劉臺拱《論語駢枝》中《詩經》條目研究
秦躍宇,張永俊
(1.湖州學院 人文學院,浙江 湖州 313000;2.魯東大學 文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0)
劉臺拱(1751-1805),字端臨,乾嘉時期揚州學派寶應劉氏家族家學杰出代表,其侄劉寶楠少時即從之研治經學而作《論語正義》終成清代經學大師。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贊譽劉臺拱、劉寶楠與劉恭冕并為“寶應劉氏三世”。現存劉臺拱著述基本收于兩處,即《劉端臨先生遺書》與《劉氏遺書》,其中的《論語駢枝》是劉臺拱代表作。后世較為系統涉及《論語駢枝》的著述,有劉寶楠《論語正義》、程樹德《論語集釋》及近人毛子水《論語今注今譯》。然限于體例,《論語駢枝》在其中多以文獻參考的形式出現。本文擬從《論語駢枝》所涉《詩經》四個條目出發,歸納劉臺拱《論語》研究的闡釋邏輯及其治學特點。
《論語駢枝》共十六個條目,目前尚未有整理出版,主要內容是劉臺拱針對前賢時彥對《論語》所做的闡釋,通過校勘、論證等方式提出不同于以往注家的辨析和觀點。其中四個涉及《詩經》條目,是圍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子所雅言”參驗經文展開討論,凡所發明,旁引曲證,與經文上下吻合而無稍穿鑿。通過《論語駢枝》中《詩經》條目管中窺豹,可見劉臺拱不局限于前人注釋與訓解的學術追求,是直接揭示《論語》古義與孔子本義,進而融入自己的新見。
一、關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這一條目闡發的對象,源自《論語·學而》篇所載孔子與子貢的一次對話。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劉臺拱引證《爾雅》中《釋器》與《釋訓》的相關內容后,緊接著提出自己的闡釋,他認為:“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矣,獨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
首先,劉臺拱認為,“無諂無驕”側重點在“質”,是一種道德上的品性;而“貧而樂,富而好禮”偏向于“學問之功”,則是一種后天的修養,側重點在學問躬行。其次,他又強調了孔子與顏淵的好學特性。子貢聰穎且悟性高,能引《詩經》闡發孔子之義,同時得到孔子的認可,并有“告諸往而知來者”的評價。最后,劉臺拱認為《論語集解》與皇侃、邢昺的解釋含混不清;朱熹的注釋沒有引用《爾雅》,而是提出了“已精益精”的新觀點。對于后者,劉臺拱主張朱熹的注解雖然“比例雖切”,但是卻對孔子本義無所引申。關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朱熹將“切”“磋”與“琢”“磨”分別放在一起考量,并且認為二者之間是遞進關系,所以才會有“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之說。[1]58劉臺拱先引《爾雅·釋器》解釋字義,后指出“如X如Y”是一種在《詩經》中得到成熟運用的句法,再次強調一字一義。
總的來說,劉臺拱針對這一條目的解經邏輯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一整體,是從“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上升到“貧而樂,富而好禮”的方法。具體而言,結合《爾雅·釋訓》可知,“道學”與“自修”是這一方法的兩種途徑,兩者分別體現在“如切如磋”與“如琢如磨”。因之可見“切”“磋”“琢”“磨”皆一字一義,彼此之間是平行關系。揭示出這一層關系之后,劉臺拱順理成章地指出朱熹的闡釋存在商榷之處。最后,他提出自己的建議,想要更準確地把握子貢與孔子這次對話的內涵,《爾雅》舊義應值得重視。劉臺拱對這一條目作的解釋,劉寶楠《論語正義》也有所引用,并實際繼承了劉臺拱的觀點。這一條目運用的解經方法為經書互證,主要體現為《論語》《詩經》《爾雅》互證。
二、關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學術界歷來有諸多討論,劉臺拱認為歷代對“哀而不傷”的認知與解讀存在很大的差異。首先,其否定《毛詩序》與鄭玄對“哀而不傷”釋讀,認為二者皆“回穴難通”,并不能追溯孔子本義。其次,劉臺拱認為朱熹以《關雎》詩句來分配哀、樂之情的說法雖合理可通,但亦存勉強之處。朱熹言:“《關雎》,周南國風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2]66朱熹在具體的釋經過程中,用“憂”代替了“哀”。對這一解讀,劉臺拱以為“義之不愜”,因為朱熹的解釋混淆了“哀”與“憂”兩種不同的情感。南宋程大昌在《考古編》中提出,孔子此章之旨在于評價《關雎》音樂中所蘊含的感情,而非談論詩義。程大昌言:“魯大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于淫。雖哀矣,而不至于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詩之義也。”[3]10這與劉臺拱認為《論語》這一章實際所指是依據合樂而言有契合之處,相似點在于二人都認為這一章的討論范圍是“樂”。不過,劉臺拱也指出“程大昌聲音之說尤為無據”。程大昌以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涉及范圍僅就《關雎》一首樂言之,這實際與劉臺拱在后文提出的觀點相左。
劉臺拱先引《左傳》與《樂記》中相關文獻說明“哀”與“樂”,“噍殺”與“啴緩”反義對舉之例;然后又認為反義對舉不能并存于同一首樂曲中,因為不符合“性情之正”。通過以上兩條論據,劉臺拱否定了程大昌的“聲音之說”。推尋眾說,未得所安,劉臺拱在這個條目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由之可見,劉臺拱指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據《關雎》《葛覃》《卷耳》三首音樂組成的合樂而論,而非僅指《關雎》之樂。
劉臺拱關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論證可分為三步。首先,引用《左傳》襄公四年、《儀禮·鄉飲酒禮》與《禮記·學記》中的相關文獻記載,指出由三首詩樂組成一個合樂是樂章之通例。接下來,援引《左傳》襄公四年與《國語·魯語》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記載,即有關叔孫穆子聘于晉的記錄,指出同樣作為兩君相見之樂,《左傳》只書《文王》,而不言《大明》與《綿》,《國語》卻將此三者對舉。這就表明,此處《左傳》中的《文王》實際所指,是包括《大明》與《綿》在內的三首樂曲。其次,指出《儀禮》合樂《關雎》《葛覃》《卷耳》,以及《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僅言“關雎之亂”,將《葛覃》與《卷耳》省略。通過這些具體的實例,劉臺拱進而歸納出在實際行文過程中,舉一以賅三也是一種通例。最后,劉臺拱指出“樂而不淫”者,是就《關雎》與《葛覃》而言;“哀而不傷”者,是就《卷耳》言之。并且,進一步從《關雎》《葛覃》《卷耳》三篇的詩義出發,對這三篇詩蘊含的哀樂之情做一梳理。結果發現,《關雎》是“樂婦匹也”,《葛覃》之樂在于婦得其職,《卷耳》哀義在于思念征夫。文末,他再次補充說明了《葛覃》包含于“樂而不淫”的合理性。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季札聘于魯而觀周樂,為之歌《豳》后,季札贊嘆“樂而不淫”。劉臺拱之所以認為“樂而不淫”指《葛覃》,是因為《豳風》中的《七月》與《葛覃》具有相通之處,這就為“樂而不淫”與《葛覃》互相發明提供了間接證據。劉寶楠全文引用劉臺拱的觀點后,所作案語指出,劉臺拱精湛之處在于以《卷耳》中的“維以不永傷”證“哀而不傷”。《論語正義》曰:“謹案:《駢枝》以《卷耳》‘維以不永傷’,證‘哀而不傷’,其義甚精。”從發現問題到提出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劉臺拱結合經史文獻,通過層層推導得出結論,邏輯之嚴密與論證之精湛不得不讓人嘆服。顧頡剛對劉臺拱的相關論述,盛贊為“得此詳盡之闡述,而后《論語》此章始有最透辟與最系統之解釋”。[4]269《論語駢枝》中還有另一條目也涉及對《詩經》中音樂體系的認識,為了更概括地呈現劉臺拱對該部分的探討,現將《論語駢枝》中次序稍后的條目移到前面作一考察如下。
三、關于“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根據《禮記·樂記》中“始”“亂”對舉之例,劉臺拱認為,“始”代表音樂開始,“終”表示音樂結束。最后,明確奏樂之體例。劉臺拱認為,一套完整的音樂演奏,也即“一成”,由歌、笙、間、合四個部分組成。并且指出,一成之樂始于“升歌”,終于“合樂”,笙間在其中。這也就證明,“亂”是指“合樂”。對照劉臺拱關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條目的注解互相參證,可見這里更明確地指出合樂由三篇詩樂組合而成。單舉《關雎》明“亂”,實際上已將《周南》中的其他兩篇《葛覃》與《卷耳》囊括其中,而行文中省略后兩者,則符合“舉上以賅下”的體例。劉臺拱在該條目中的論述如下:“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賅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嘆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后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間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所謂“升歌言人”,指向魯樂師摯;“合樂言詩”,指向《關雎》;“互相備也”,指向文法前后呼應。通過劉臺拱的論證可知,其將“亂”作為合樂體現之一端,進而解釋了“亂”在具體行文中的含義。結合《論語駢枝》其他條目關涉《詩經》“合樂”與“始亂”的辨析,可發現劉臺拱就“詩”在《論語》及其他先秦典籍行文中的體例,主要是指“舉上以賅下”。同時,也涉及談論“樂”在《論語》及其他先秦典籍行文中的程式,側重點在“亂”。這樣,體現出研究者不僅擁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并且為之做出了邏輯清晰的探討。總而言之,在具體的闡釋過程中,劉臺拱通過援引經史文獻互相發明,一步步推導得出自己的結論,行文審慎,結論堅實。
四、關于“子所雅言”
《述而》篇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章“雅言”所指究竟為何?后世有兩種說法比較通行。第一種,認為“雅言”為“正言”。持此觀點者,有鄭玄、何晏、毛奇齡等人。鄭康成注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何晏《集解》訓為“正言”。第二種,則持“雅言”為“常言”的觀點,如程顥與朱熹等人。朱熹《論語集注》訓“雅”為“常”,認為“詩”“書”“禮”三者“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論語駢枝》首先認同鄭玄“正言其音”的說法,但否定鄭玄以為“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雅言”的一種表現的觀點。其次,劉臺拱援引《禮記》中《文王世子》與《雜記》的相關內容,證明“執禮”成詞,有源可尋,認為“執禮”義即“詔相禮事”。孔子生長于魯國,所用日常語言多是本國方言,即魯語。但是,孔子重視先王典訓,所以在對待誦詩、讀書與執禮這三件事時,必正言其音,皆嚴格使用“正言”。再次,劉臺拱借劉熙《釋名》與張晏《漢書注》釋“爾雅”為“近正”,從而證明“雅”訓為“正”有理可據。接著,又闡述了《爾雅》產生的原因。劉臺拱所持之觀點,與近人黃侃“是則《爾雅》之作,本為齊壹殊言,歸于統緒”[5]361之說并無二致,或者黃侃先生是受其啟發亦未可知。同時,劉臺拱由此及彼,聯系到《詩經》中的《風》與《雅》的命名緣由,以及詩序排列依據——“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而“王”正是憑借“雅言”,達到正王朝、撫邦國諸侯之目的。最后,劉臺拱舉《荀子》中《榮辱》與《儒效》二篇作為旁證,認為“雅”“夏”古字通,“雅”之為言“夏”也。也就是說,劉臺拱認為“雅言”就是“王都之音”。
綜合而言,劉臺拱的觀點認為“雅言”即“正言”,與“方言”相對而論。換言之,“雅言”也即西周王都之音。多有學者將《榮辱》與《儒效》對舉,進而說明“雅”與“夏”之關系,如清代“二王”父子王引之與王先謙、近人黃侃與周祖謨等人。但最初通過“雅”將《論語》與《爾雅》《詩經》《荀子》齊置一處相互發明,進而構成一條嚴密的邏輯線索,劉臺拱實是第一人。即便是管中窺豹,亦足以見出其論學視角之獨特。其后劉寶楠所作《論語正義》不僅接受劉臺拱的觀點及論證,而且推舉以為劉臺拱“發明鄭義,至為確矣”。
《論語駢枝》的核心思想,是回歸孔子本義與《論語》本義。劉臺拱熟悉經書文獻,援引博洽,持論公允,通過考釋古義及文獻互證所得出的觀點,其精審往往出眾于以往注家。通觀《論語駢枝》,劉臺拱運用的論證方法主要有四種:第一,經書互證;第二,總結凡例;第三,追本溯源,揭示致誤之由;第四,文理與情理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詩經》的內容在《論語》與其他先秦典籍中多有引用與討論,而劉臺拱對“合樂”的認識非常獨到。三首詩樂組成一個合樂是樂章之通例,因為同屬一個合樂,所以行文中出現舉一以賅三的體例,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舉例來說,《關雎》《葛覃》《卷耳》是一組合樂,行文中經常只舉《關雎》,但實際則包括了《葛覃》與《卷耳》。同理,《鵲巢》《采蘩》《采蘋》與《文王》《大明》《綿》這兩組合樂,也符合舉一以賅三的體例。劉臺拱認為一套完整的音樂演奏,也即“一成”,由歌、笙、間、合四個部分組成。并且,又指出一成之樂始于“升歌”,終于“合樂”,笙間在其中,也就證明了“亂”是指“合樂”,而合樂由三篇詩樂組合而成。劉臺拱對“合樂”有著系統的認識,在論證過程中所援引的經史文獻能相互發明,進而一步步得出自己的結論。如此而言,其結論的確可謂真正具備了說服力與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