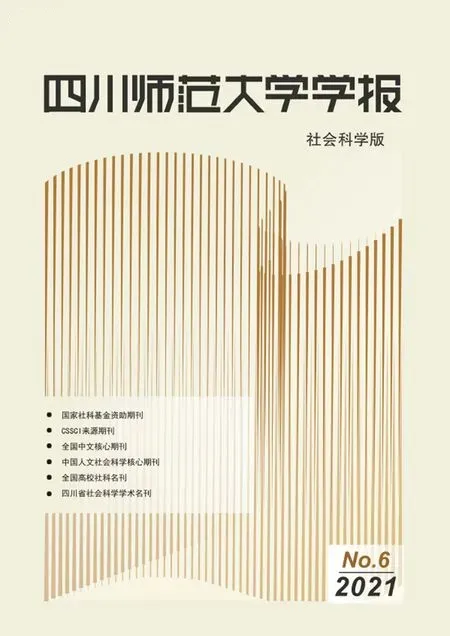鄉村振興視域下西南民族村寨的保護與活化
傳統村落作為少數民族的原始聚居地,承載了該民族的歷史、文化與記憶,村寨的瓦解,也即代表該民族及其文化的消散(1)馮驥才《傳統村落的困境與出路——兼談傳統村落是另一類文化遺產》,《民間文化論壇》2013年第1期,第8頁。。隨著現代化、城鎮化速度加快,傳統村落的保護問題日益緊迫。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提出“加強對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傳統村落和鄉村風貌、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保護”,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民族村寨保護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要地位,民族村寨保護工作迎來了全新的機遇和挑戰:既須傳承和弘揚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賦能鄉村振興,又要符合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要求和價值目標,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提高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現代遺產保護的關鍵理論發展來自于奧地利學者Alois Riegl,其基于價值理論解釋的遺產保護,揭示了遺產價值的多樣性與相互之間的沖突(2)John Pendlebury,“Conservation Values, the 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 and the Conservation-planning Assembl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 no.7 (November 2013): 709-727.,使得地方政府最初偏重以歷史文化價值實現靜態保護的傳統博物館模式遭到質疑。在反思傳統“靜態”保護方式的基礎上,20世紀70年代,一種新型博物館模式——生態博物館模式發端于法國,并迅速向世界各地傳播。生態博物館模式的保護理念是通過原生地的整體性保護,以“活態”呈現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促進當地的可持續性發展。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受文化人類學“活歷史”的啟發,文化遺產所具有的“活態性”引起學者的關注(3)費孝通《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94頁。。其作為一種新的態度或方式,重新闡釋了對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的理解。2009年,基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實踐經驗,國際文化財產修復與保護研究中心(ICCROM)提出“活態遺產保護方法”(Living Heritage Approach,簡稱LHA),正式定義了活態遺產(living heritage)的概念。這是非西方文化在對自身遺產保護實踐反思的基礎上,對現代遺產保護理念的質疑與補充。
我國對傳統村落的認知也在不斷發生轉變,由最初歷史的、靜態的物質集合體轉向了活態的、多元的人類基本社會生活單元,更強調激發以村落居民為主體的內生動力來實現傳統村落內在文化體系的傳承和發展。保護方法逐漸由單純“基于物質的保護”轉向“基于價值的保護”,“以開發促保護”的文旅發展模式逐漸活躍起來,被視為近年來保護傳統村落多元價值的重要活化方式之一。西南民族村寨作為我國最早一批引入國外活態遺產理念進行保護實踐的傳統村落,在實踐中引發了一系列的生態、文化及社會問題,使得我們對民族村寨的保護與活化如何實踐本土化產生了新一輪的思考。民族村寨的性質既不同于物質文化遺產,也不同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民族村寨的保護不能完全借鑒物質或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有的保護法規、理念或方法。民族村寨所處的文化生態背景應是活態化保護實踐中的重要考慮因素,對民族村寨文化生態背景的深入探討,有助于真正實現我國民族村寨的保護與活化。
一 西南民族村寨保護與活化的實踐及窘境
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我國與挪威王國合作,將西南民族村寨作為實施活態保護的對象,分別在貴州六枝梭戛、黎平堂安、錦屏隆里、花溪鎮山四個民族村寨建立了生態博物館,其中梭戛生態博物館是亞洲第一座民族文化生態博物館。在活態遺產概念的影響下,以保護活態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為導向,保護實踐工作逐步由貴州、云南等西南民族地區向中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擴展。
西南民族村寨初期的保護實踐,以民族文化為特色資源,有效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生態博物館模式在西南民族村寨具體實踐中的效果并不理想,許多問題不斷凸顯,突出表現為三點。一是生態博物館實踐打破了原來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模式(4)孟凡行等《生態博物館建設與民族文化發展——以梭戛生態博物館為中心的討論》,《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7年第4期,第128-140頁。。在現代文化的沖擊下,民族村寨原來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模式被打破,村寨居民面對自身的“傳統”表現出不自信。在新的開放環境下,早期因政府和外來專家、學者的引導與支持,村民的生產生活能較有序地開展,但在中后期,隨著相關專家和學者的退出,這份對“傳統”的不自信逐漸顯露,使得生態博物館的實踐進度放緩甚至停滯。此外,村寨青壯年為追求“現代化”蜂擁進入城市打工,村寨出現主體缺位的“空心化”,對西南民族村寨也構成巨大的威脅。二是在生態博物館實踐中外來資本進入后引發了各種問題。民族村寨保護工作需要大量的維護資金,光靠政府投入是難以持久的。在政策激勵下,大量社會資本得以進入民族村寨保護工程。這種外來資本進入,雖然緩解了民族村寨保護的資金壓力,促進了傳統村落的保護開發,但由于資本的逐利性,使得其在傳統村落的保護開發中急功近利,過度的商業化、建設性破壞和生態環境污染等問題不斷凸現。三是生態博物館管理方式忽視對村寨精神文化的關照。民族村寨的特殊性決定了其承載的民族傳統文化是村落發展的源動力,這要求對民族村寨的保護不僅僅是保護建筑物、場所等物質遺產,還需注重民族文化的保護與活化。目前,我國生態博物館實踐主要采用當地政府牽頭推動和管理、專家學者及開發商等參與、村民配合的管理模式,但這一管理模式并不能激發村寨的內生活力,以實現對民族文化的活化。并且,當前生態博物館管理模式設置的評估指標,多以短期單一的經濟社會指標為主要依據,把文化資源資本化,忽視村寨精神文化關照,保護思路缺乏長遠規劃。
西方生態博物館理論把村落作為一個承載傳統文化的客體化處理,使被包容在村落生態博物館這個“文化客體”之中的村民失去其主體性(5)劉宗碧《生態博物館的傳統村落保護問題反思》,《東南文化》2017年第6期,第103、105頁。,從而成為以他者構建實踐的村落“活態化”。而活態遺產保護方法所強調的“文化延續”,更注重從精神層面去保護和傳承文化,有忽略物質遺產保護與變化之嫌疑。因此,無論是西方后工業時代提出的生態博物館理念,還是基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實踐經驗提出的活態遺產保護方法,都是源于各自民族發展的歷史文化背景而提出的,其相關理論和實踐經驗并不能直接硬性地移植到中國的保護實踐中。中國西南民族村寨的保護與活化,應根據其形成的環境和所處的文化背景特點,在批判地汲取國外先進理念和方法基礎上,因地制宜地開展活態化保護實踐。
二 西南民族村寨的文化生態背景
我國地域遼闊,擁有復雜多樣的自然生態系統。各民族在面對自身所處的生態系統時,為求生存和發展,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與當地生態系統相適應的文化體系;在該文化體系運作時,會持續反作用于當地生態環境。在自然環境與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各民族聚居的村落孕育而生。受社會歷史因素影響,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民族村寨顯現出自身發展的獨特性。在自然、文化和歷史等共同作用下,西南民族村寨形成了自身文化生態背景的獨特性。
(一)半封閉的生產生活狀態
西南地區地形以高原、山地為主,地形起伏急劇,是我國地緣地貌最為復雜的區域,為分布在此的民族村寨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一方面,阻隔了與外界的聯系,較好地保存了民族村寨的傳統性與完整性。“禮失而求諸野”,便可用于描述西南地區“傳統”的保存狀態。在城市已遺失了的傳統禮節、傳統文化等,在西南民族村寨中尚能找到。另一方面,這道天然屏障使西南地區成為中國交通最困難的區域,居民總體生活水平較低。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文旅產業的發展,西南民族村寨已不再是完全閉鎖的原生地。鄉鄉通公路,村村有電訊,現代文化和新事物不斷涌入村寨,悄然地改變著村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東部地區完全開發的村落狀態不同,西南地區村落表現為半封閉的生產生活狀態,其鮮明的特征是西南民族村寨能以日常生產生活方式自然傳承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在現代化沖擊下,西南民族村寨表現為傳統性與現代性共存。例如,村民根據其生活習慣聚集于村頭寨尾等傳統公共區域相互交流,但電視、手機和互聯網等現代通訊工具與技術的發展,又使得村民的生活交流方式擴展到網絡虛擬空間;傳統的節慶聚會仍然開展,但在服飾、工具等用品上嵌入了現代元素;產業化理念、高新科技手段及現代產業評估指標體系等也運用到傳統生計方式上。但這種共存狀態極易受外力影響而失去平衡:過度保護,將難以滿足村民對生活水平提高的期望,影響村民參與村寨保護工作的積極性;大力開發,民族村寨將難以抵擋現代化的沖擊,出現傳統的斷裂、村寨社會秩序的紊亂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因此,在規劃村寨保護思路時,應考慮西南民族村寨半封閉生產生活狀態的特殊性,在民族村寨文化認同的持續延伸中保持其民族特色。
(二)存續的村寨共同體
在各民族的長期歷史實踐中,民族村寨已與周圍的生態環境、寨內生活的居民融為一個“文化生態共同體”。因此,村寨空間形態、布局結構和村寨居民對村寨空間的利用與維護,都能體現村寨內存在的共同體意識。
1.空間形態與布局結構中映射的共同體意識
西南民族村寨的選址、空間格局和布置等,經過該民族與所處自然環境的長期磨合,在祖輩世代傳承的信仰和理念影響下,以當地社會文化運轉的內在邏輯構思形成,映射著村寨的共同體意識。例如西南地區的黔東南侗寨,其選址以蜿蜒起伏的山脈為“龍脈”,山脈遇溪流、平壩而止之處為“龍頭”(侗族也稱之為“坐龍嘴”),是修建村寨的最佳位置。這樣的選址是侗族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共同作出的文化選擇,也是該民族生存智慧的體現,能較合理地配置村寨周圍自然環境的各要素,使村寨與其所處環境交融形成為一個“共同體”。其次,侗寨的整體形態呈現為以鼓樓為中心的內聚向心式布局。從村寨橫向布局來看,鼓樓作為議事、聚會等活動中心,被整個家族聚居圍繞;在縱向布局上,鼓樓則以絕對的高度與氣勢統率整個侗寨空間。侗寨各構成要素始終以代表侗族族姓的鼓樓為中心布局,反映了侗族居民群體內部具有秩序化的強烈內聚向心意識。以寨門為重要節點構成的侗寨邊界,構成村寨領域的象征,限定社會生產生活空間領域的范圍,逐漸成為侗寨居民心中的“邊界”,在意念上強化聚落群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另外,村寨內部布局緊促的干欄式民居,與寬敞的生活公共空間(如鼓樓坪、戲臺廣場及風雨橋等)形成鮮明對比。這種空間差異的布局,強調的正是“集體感”,映射出強烈的村寨共同體意識。由上可知,民族村寨鮮明的空間形態與布局結構特征,便是以建筑和景觀等物質實體將侗寨共同體的內部認同形象化、具象化。
2.日常生活與組織活動中延續的共同體意識
村寨的實體實景構造,靜態地映射村落共同體意識,而村寨中的日常生產生活及組織活動,則是通過對村寨實體實景及其空間的使用和村寨秩序的維護,動態地延續村寨共同體意識。一方面,村寨居民定期舉行的慶典、儀式、聚會等,都是固定選擇在寨內具有代表性或重大象征意義的建筑物內或周圍進行,例如黔東南侗寨寨內重要的議會、聚會等活動都會在鼓樓進行。圍繞群體選擇的象征物或場所進行的生活實踐活動及由此聯系的社會關系網,成為共同體內部認同延續的重要方式。這時,文化的認同也延伸至文化性的傳統與生活方式中(6)喬納森·弗里德曼《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郭建如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48頁。。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和社會政治等因素,西南鄉村社會中個人和家庭對村寨的依賴程度較高。例如侗族村寨向心式的空間布局,體現的就是對宗族、家族血緣組織的依賴。這種對“集體”概念的依賴形成了村寨共同體的自治傳統。主要是以血緣關系為核心、以地域關系為紐帶結成社會組織結構,以強烈的共同認知與感情為基礎,使各民族村寨凝聚成一個強大的共同體,保證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群落獲得生存和發展。例如侗族村寨的“卜拉”、“款”,苗族村寨的“鼓社”、“議榔”、“理老”,瑤族村寨的“瑤老”等,這些傳統社會組織中的優秀傳統和文化影響并沒有消失。很多侗族村寨當地的“老人協會”(內部稱作寨老組織),承擔著諸多社會管理的功能。寨內的婚喪喜慶活動、成員間的糾紛以及對孤寡、年老、體弱者的照顧等,也多以傳統社會組織為單位而自覺行動,體現了各族村寨中廣泛存在的互助合作、扶危幫困、相互依賴等共同體意識。過去以共同認知為基礎而達成“款約”、“榔規榔約”等,作為各村寨歷史中形成的習慣法,因擁有較好的群眾基礎,逐漸演變為“鄉規民約”,繼續發揮功能作用,維護各民族村寨內部的團結。
(三)生態多元化的傳統生計方式
西南地區地理環境復雜、地勢險要,以山為屏的相對封閉性,使得生活于此的民族對自然高度依賴,逐漸形成了人與自然互利共存的基本準則:一方面,規范族人對自然資源有節制的利用與保護行為;另一方面,強調以自然為本源的價值體系,尊重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合理配置和多元利用。該基本準則中所蘊含的生態理念與生存智慧,不僅使得該民族所處的自然生態系統良性延續,還滿足了該民族生存和發展所需的多種資源和能源,發展出生態多元化的傳統生計方式。
以貴州從江縣的“稻-魚-鴨”共生模式為例。其是當地侗族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環境下,為解決耕地嚴重不足問題,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的一套生態農業生產方式。稻田為魚和鴨提供生存繁衍的庇護場所;魚和鴨以稻田中的蟲害和雜草為食,來回游動,無形中為稻田松土,其排泄的糞便作為有機肥,有助于稻田良好的生長。可以看出,“稻-魚-鴨”共生模式,與普通的稻田單作不同,其主要基于稻、魚、鴨以及昆蟲等生物生長特點和生長空間、時間分布的層次,引入了復雜的食物網和生態鏈,增強該生產模式下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功能,實現對當地生態資源的生態多元化利用。目前,從江縣“稻-魚-鴨”共生復合系統已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另外,侗族擁有豐富的林木資源,這也使得其傳統生計方式表現為以農業為主、兼營林副業。在對林木資源的認知與利用中,生成了“林-糧”間作的生計模式。此生計模式主要根據林木的生長特點和農作物的生長習性,間作不同的糧食作物或經濟作物,充分利用空間進行立體化布局,化解山多田少的困境,獲得了林、糧雙收的效益。為更好管理和利用林木資源,侗族對村寨周邊的山林資源進行了分類劃層,風水林-經濟林-雜木林的林木圈層圍繞村寨依次向外展開,各圈層的林木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用途,與族群的信仰、習俗和民族文化等相互關聯。總之,這些傳統生計模式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原則,是西南地區民族生存智慧的結晶,兼顧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保證民族村寨生計與生態得以延續。
三 西南民族村寨保護與活化的思考
西南民族村寨在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生態特征,正確認知并利用好其文化生態特征,能激發西南民族村寨整體性活化的本土內生力。基于對西南民族村寨文化生態特征的思考,關于西南民族村寨的保護與活化,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1.原住居民的主體性
從民族村寨存續的村落共同體可以看出,村民所具有的共同情感流動于村寨中,由此產生的社會關系網使得村寨得以延續。在村寨的社會關系網中,每個個體都是具有自我認同、村寨共同體歸屬感的個體,是主動融入的個體,有保持自己傳統的民族自覺。但在現代文化的沖擊下,這份“自覺”變得有些模糊,需借助村落中的一些特定紀念物、建筑物或歷史場所以及在特殊歷史節點的共同記憶等來重新喚醒這份“自覺”,重塑鄉村綿延不絕的內聚力(7)陳彪《鄉土情結與振興鄉村:中國鄉村人類學研究進路與展望》,《廣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第99頁。。西方生態博物館理念作為一種“為了將來而保護和理解某種文化整體的全部文化內涵的手段”,以活態模式將包含重要共同記憶的文化遺產在原生地進行保存與展示,是一個很好的保護思路。在西南民族村寨實踐中,保存和展示村寨的核心資料室是生態博物館建設的核心,但其不能只是被當作對外宣傳的窗口,更重要的是應面向本村寨居民(8)孫華《西南少數民族村寨調查》,《中國文化遺產》2007年第2期,第55頁。,使其能夠更充分地了解自己的村寨及價值,以喚醒其“自覺”來維護村寨的重要傳統。任何對村寨進行創造性“保存”的主體都應是村寨居民,若以外來者的想象和期待去保存和展示民族村寨,只會使其脫離當地社會生活情境,喪失生存延續的文化環境(9)劉志偉《傳統鄉村應守護什么“傳統”——從廣東番禺沙灣古鎮保護開發的遺憾談起》,《旅游學刊》2017年第2期,第8頁。。
村寨是地方性社會及文化建構的產物,村寨所構建的生產生活空間除了承載著特定生活于其中的人所創造的場所和物以外,還流動著特定生活于其中的人所創造的場記憶與文化。空間的范疇已通過“人”的創造,超越了具體的物、實存的場所,從有限、靜止且封閉的具象化得到延展,生成流動的意義文化,建構了空間的內在性部分。從這一點來說,特定社會的“人”總對應著特定的“空間”,兩者相互定義,構成了整個文化有機體及文化遺產本身。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在日本奈良舉行會議,形成了《奈良真實性文件》,該文件強調了文化遺產的價值應從其所歸屬之文化涵構中衡量(10)《奈良真實性文件1994》,《中國長城博物館》2013年第2期,第6-8頁。。顯然,該會議文件已認識到文化遺產的價值產生于地方性的社會生產生活中,并相應地要求突出文化遺產的創造者——原住居民在遺產價值認知中的主體性。2011年,國際文化財產修復與保護研究中心(ICCROM)將活態遺產項目更名為“活態遺產——促進以人為中心的保護方法”,進一步肯定了遺產社區中人的主觀能動性,尊重其文化選擇,強調原住居民積極主動參與傳統村落的保護實踐能更好地實現文化遺產的多元活態化,成為活態遺產保護方法區別于先前保護方法的關鍵。可見,西南民族村寨的保護與活化,應是一個以村寨的原住居民為主體,通過促進原住居民自身發展來實現文化保護的問題。
2.村寨管理的自治性
民族村寨保護實踐的開展與探索發現,由村寨居民共同生活體驗而形成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是存在并流動于村寨內空間的“文化意義”,也是民族村寨重要的文化遺產。“文化意義”通過形塑人的行為與村寨空間互動,延續村寨共同體意識。由此,民族村寨保護的內涵延伸到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與當地文化社會網絡。但“文化意義”所具有的流動性和變動性,也促使保護工作需要更精細敏銳的動態化管理模式。作為村寨的創造者、使用者和文化傳承的主體,村寨居民是很好的動態化管理者,能把握好這種“變化”是在繼承傳統之上的延續。這種保護理念的改變,要求對民族村寨的保護不能再是以往自上而下的被動式管理模式。在西方國家文化遺產保護中,公眾參與占據主導地位,而國家更多的是通過遺產教育和法律政策的制定等來喚起民眾的遺產保護自覺、保障公眾的參與渠道。例如英國通過明晰產權,將遺產歸為公眾所有,從而為公眾在遺產保護管理過程中獲得合法的話語權(11)楊慧萌、于勁翔《公眾參與下的建筑遺產保護——英國建筑保護信托之啟示》,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編《城鄉治理與規劃改革——2014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282頁。;意大利政府以設立“文化監督人”、“遺產領養”等制度,將遺產的使用權和管理權交付給公眾(12)史夢頔、董恒年《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意大利模式解讀與啟示》,《文化學刊》2018年第2期,第6-8頁。。但西方的實踐經驗并不能完全與我國的鄉村保護與建設實踐接軌,如何建立起以遺產地居民為主體的“自組織”社會系統,對當前我國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尤為重要。
費孝通提出中國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13)費孝通《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2頁。,深刻闡述了我國幾千年鄉村社會發展中孕育著自己的內部秩序、文化機制和行為道德等自治傳統,維護該村落共同體的自我運行。例如,由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層疊構成的“卜拉”、“款”、“鼓社”、“議榔”、“瑤老”等自治傳統及其文化,依然能獲得該族群的強烈認同。因此,民族村寨可以依托“傳統自治”重建原有價值觀念與精神信仰,提高原住居民的文化自覺,以地方主體視角主動開展實踐,形成基于當地傳統的“自下而上”的遺產保護管理模式。而依托“傳統自治”的關鍵,在于保護實踐中以尊重當地傳統為前提,激活其文化生態共同體強烈的認同感,通過相關法律政策將“傳統自治”的文化精髓融入保護實踐中,使民族村寨居民對遺產的保護管理得到法律保障。“傳統自治”作為依托于習慣、信仰及禁忌等內容而形成的重要傳統文化資源,不僅能發揮凝聚人心的作用,提高居民公共參與的積極性,還能維護鄉村的生產生活秩序,從而鞏固當地社會治理的心理基礎,產生獨特的價值意義及社會效益,而且以“自治傳統”及其文化為基點展開傳統民族村落保護實踐,發掘少數民族鄉村治理的資源結構及其背后的運行邏輯,能培育鄉村治理的多元主體,實現自上而下的國家政權建設和國家治理實踐與自下而上的鄉村社會力量互動和互嵌,形成國家與地方、官方與民間的有機治理格局(14)周丹丹《少數民族鄉村治理中的傳統社會組織研究——以侗族寨老組織為例》,《江淮論壇》2016年第6期,第33-34頁。,創新鄉村振興背景下以傳統為根基的鄉村現代治理體系。
3.經濟發展的獨立性
隨著傳統村落保護實踐的開展,西南民族村寨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價值得到挖掘,通過對其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市場化運作,村寨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但在市場經濟浪潮沖擊下,村寨原本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外界社會資本的進入、新產業的引進以及村寨居民對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期望等,使傳統民族村寨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凸顯,表現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
經濟發展的獨立性,應是各民族村寨得以長久性延續的重要保障。如侗寨面對所處的自然生態系統,通過文化調適而形成的“稻-魚-鴨”共生和“林-糧”間作等傳統生計模式,兼顧生態和經濟雙重效益,使侗寨得以延續。這種兼具多重功能與價值的傳統生計模式,是當地居民在長期實踐中積累形成的一套地方性知識體系,能與當地生態系統良好匹配以保障村寨的延續,本身也構成了村落文化活態遺產的一部分。憑借這套地方性知識體系,當地居民獲得更多的自信與話語權,使當地經濟發展具有獨立性。而面對外來引入產業,村寨居民所掌握的這套地方性知識體系并不適用。因對外來引入產業的有限認知而常處于被動地位,更多依賴于專家、學者等其他外來社會主體的引導與幫助;也因自身對該產業整體性認知不足,為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極易引發污染環境、人為破壞文化遺產等問題。完全依賴新產業的引入,繁榮業態背后隱藏的是原民族村寨社區被溶解于現代新社區的威脅。由此看來,有效解決村寨經濟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矛盾的關鍵在于其傳統生計模式的傳承與創新,通過不斷調整,使其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的多元化和現代化。這樣的生計模式往往以傳統農業為主,關注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只要當地生態系統不發生大的變化,原住居民憑借世代所積累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就足以應對。而政府、專家等社會主體只需協助原住居民對其熟悉的傳統產業進行升級與宣傳,有序地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如此既能體現原住居民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原住居民的主觀能動性,又保證了當地經濟發展的獨立性,為傳統村寨的保護與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最重要的是,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兼顧了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具有可持續性,成為延續村落共同體的重要保障。
綜上,在鄉村振興視域下,民族村寨的保護與活化要真正達到實施有效,必須深入探討不同地域民族村寨文化生態背景的差異。西南民族村寨因自然、社會、歷史和文化等因素,具有區別于其他地域民族村寨生成和發展的獨特性。深入剖析民族村寨的文化生態背景是有效開展保護工作的前提,需從空間和時間的雙向維度去審視。西南民族村寨作為文化遺產,更是當地居民生活的“家園”,沉淀了歷史上該族人民生存智慧的結晶,寄托著該族人民濃厚的認同情感,不等同于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簡單加總。村寨與生活在此的居民、與周圍的生態環境已融為一個“文化生態共同體”,對西南民族村寨的保護即是對這個共同體的整體性保護。隨著民族村寨內居民與村寨空間的互動,民族村寨本身也在不斷變化發展,化為“活體”。在多樣性文化繁榮的全球化時代,西南民族村寨的保護和活化應以尊重當地的傳統為前提,注重村寨居民在保護實踐中的主體性,培育村寨居民作為文化持有者自我發展的內在活力,在日常生產生活中促使民族村寨所蘊含的民族傳統文化脈絡得到發展性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