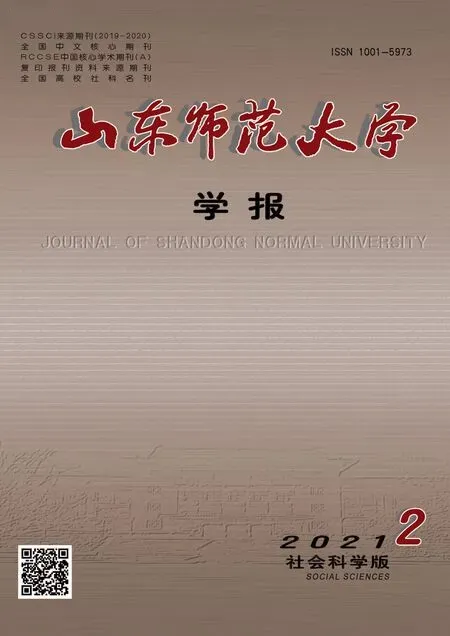新世紀(jì)以來的新移民小說發(fā)展芻議*①
豐 云
( 德州學(xué)院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山東 德州,253000 )
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文學(xué)的小說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相當(dāng)繁榮的狀態(tài),每年有10多部長篇小說出版,大量的中短篇小說發(fā)表于國內(nèi)文學(xué)期刊,在各類小說排行榜和文學(xué)評獎中也不時可以見到新移民作家的名字。在這20年的發(fā)展歷程中,新移民小說在主題的拓展上發(fā)生了諸多變化。因此,在新世紀(jì)的第三個十年開始之際,梳理一下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小說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展現(xiàn)出來的新的特質(zhì)是很有必要的。
一、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小說的跨域特質(zhì)
新移民文學(xué)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產(chǎn)生、發(fā)展的,因此,其發(fā)展的每一階段都與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進(jìn)程有著微妙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20世紀(jì)的新移民小說,其主題集中于異國場景中對故鄉(xiāng)的深情回望或者新移民在移居地的生存窘迫、文化震撼、成功炫示等幾類。這正是與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相契合的。在交通成本、甚至通訊成本高昂且不夠便利的時期,故鄉(xiāng)是重洋阻隔的難以回歸之地,遙遠(yuǎn)的地理距離讓移民帶著對親人的濃烈思念而下意識地美化著故鄉(xiāng):小橋流水,稻香蛙聲,鄉(xiāng)情淳樸,平和靜謐。在唯美的霧靄背后,那影影綽綽的故鄉(xiāng)有時不免有幾分虛化。而從國門初開的落后發(fā)展中國家初抵西方最發(fā)達(dá)區(qū)域的新移民的窘迫、悲歡與文化不適,也是他們最切膚的生存體驗。進(jìn)入新世紀(jì)之后,中國飛速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以及對全球化進(jìn)程的進(jìn)一步融入,不僅改變著本土國人的生活,也對全球的華人移民發(fā)生著潛在的影響。華人移民的生存狀態(tài)和文化心態(tài)都在某種程度上回應(yīng)著這種變化。他們通過回國定居、回國創(chuàng)業(yè)和參與同故國的經(jīng)貿(mào)文化往來活動而越來越深度地介入到故國的經(jīng)濟(jì)與文化發(fā)展變遷之中,這使得他們在生存狀態(tài)上成為“跨國華人”。“從文化認(rèn)同的角度來看,跨國華人既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重要載體,也是在東西文化融合與創(chuàng)新基礎(chǔ)上形成的第三文化(Tird Culture)的建構(gòu)者。”(1)劉宏:《當(dāng)代華人新移民的跨國實踐與人才環(huán)流——英國與新加坡的比較研究》,《中山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9年第6期。華人移民的跨國生存狀態(tài)以及他們的跨域經(jīng)驗,對于新移民文學(xué)的發(fā)展自然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新移民文學(xué)的發(fā)展是從20世紀(jì)80年代的“留學(xué)生文學(xué)”起步的,很多作者的寫作開始于中文網(wǎng)絡(luò),其原初的創(chuàng)作動機(jī)確實具有排遣異國孤寂、抒發(fā)個人愁緒與感慨的偶然性和無功利性。但當(dāng)“留學(xué)生文學(xué)”發(fā)展到新移民文學(xué),且開始成為內(nèi)地的閱讀熱點,并引起研究者關(guān)注之后,這種自發(fā)性和無功利性漸趨改變。因為新移民雖然身在中國以外,但作品的發(fā)表和出版大多是以中國海峽兩岸和香港、澳門的華語文壇為依托的。在其后的發(fā)展歷程中,非中文寫作者——戴思杰(法國)、山颯(法國)、哈金(美國)、李翊云(美國)、李彥(加拿大)、應(yīng)晨(加拿大)等人的作品一般發(fā)表和出版于所在國,但其部分作品仍會被譯成中文在國內(nèi)廣為傳播;中文寫作者的作品則絕大部分是首發(fā)于國內(nèi),僅有少量在國外的華人出版社出版。因此,新移民作家雖然工作、生活于海外,但通過作品的發(fā)表、出版、評獎和影視改編等一系列的文學(xué)活動,事實上建構(gòu)起了一個跨國社會場域。而新世紀(jì)以來,隨著國內(nèi)文壇對新移民文學(xué)研究的日益重視,各地舉辦的相關(guān)筆會、研討會、評獎等文學(xué)活動日漸豐富,新移民作家群體中的很多作者與國內(nèi)的互動越來越多,一些作者甚至是半年時間在國內(nèi)生活、半年時間在國外生活,成為從生活上到創(chuàng)作上的全方位的跨國華人。這種生存狀態(tài)使得新移民文學(xué)的跨域特質(zhì)愈益顯著,具體而言,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作家本身的跨國環(huán)流狀態(tài)
一些作家的現(xiàn)實生活存在著明確的回流或環(huán)流狀況。比如王芫(美國),她的寫作起步于國內(nèi),曾是北京市作協(xié)的簽約作家,出版有《什么都有代價》《幸存者》等作品;2006年移民加拿大,2012年回國;2015年再次移民到美國;移民后有中短篇集《路線圖》出版,同時也在國內(nèi)某些媒體寫作專欄。曾曉文(加拿大)1994年赴美,2003年通過技術(shù)移民再次遷移至加拿大。江嵐(加拿大)在移居加拿大數(shù)年后,又轉(zhuǎn)赴美國高校任教。張惠雯(美國)1995年赴新加坡留學(xué),后留居,2010年再次移民到美國。陳思進(jìn)和雪城小玲這對夫婦作家也是先移居美國,再移民至加拿大。嚴(yán)歌苓在留居美國后,因丈夫的工作關(guān)系而在世界多國不斷遷徙,目前居住德國。多次遷移的經(jīng)歷,對他們的創(chuàng)作都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既豐富了創(chuàng)作的素材,也提供了多重視野。還有一些作家開始回流祖國,比如施雨(美國)、莊偉杰(澳大利亞)都在出國定居多年后“反向留學(xué)”,在福建師范大學(xué)攻讀了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并先后回國內(nèi)工作。秋塵(美國)和呂紅(美國)也分別在北京師范大學(xué)、華中師范大學(xué)攻讀了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陳謙(美國)2018年受聘成為廣西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的客座教授,每年為本科生開設(shè)“創(chuàng)意寫作工作坊”課程。施瑋(美國)每年也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時間生活在中國,在北京宋莊還有畫室。老作家木心,生命的最后五年,也在故鄉(xiāng)烏鎮(zhèn)度過。其他如王威(美國)、陳永和(日本)等也都處于跨國生存狀態(tài)。當(dāng)然這種回流并非是新世紀(jì)才開始出現(xiàn)的,有的新移民作家在20世紀(jì)末已經(jīng)開始進(jìn)入跨國生存狀態(tài),如少君(美國)、薛海翔(美國)等。只是,在20世紀(jì),這種情況為數(shù)較少。同時,新移民文學(xué)社團(tuán)也日漸增多,且與國內(nèi)文壇、高校、傳媒等交流日漸密切。比如洛杉磯華文作家協(xié)會、日本華文作家協(xié)會、歐洲華文作家協(xié)會、新移民作家筆會等,都先后與中國作協(xié)、世界華文文學(xué)學(xué)會等國內(nèi)官方的組織或?qū)W會聯(lián)合舉辦了華文文學(xué)論壇、研討會等諸多活動。這些跨國文學(xué)活動經(jīng)常得到各級僑辦等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顯示出新移民祖籍國對移民跨國文化交流活動的強(qiáng)大推動性。可以說,新移民作家的跨國社會場域,基本上是以國內(nèi)的大中城市為節(jié)點,以文學(xué)研討會、創(chuàng)作筆會等文化活動為經(jīng)絡(luò)來構(gòu)建的。另外,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為新移民作家跨國社會場域的構(gòu)建提供了重要的技術(shù)支持,如創(chuàng)建于美國的“文心社”網(wǎng)站和諸多新移民作家微信群等都已發(fā)展成為聯(lián)結(jié)海外新移民作家和國內(nèi)新移民文學(xué)研究者的重要網(wǎng)絡(luò)園地,部分新移民作家甚至是通過這些網(wǎng)絡(luò)園地而進(jìn)入國內(nèi)學(xué)術(shù)視野的。
(二)從“雙重邊緣”到“全面內(nèi)轉(zhuǎn)”的文學(xué)生產(chǎn)
新移民文學(xué)的漢語文本從始至終都是以中國的海峽兩岸以及香港、澳門的華語文壇為依托的,在其初期,確乎處于“雙重邊緣”的境地:在新移民作家生活的移居地,無論是北美、歐洲、澳洲還是日本,華語作品都屬于華裔族群內(nèi)部的文學(xué),對主流的文壇而言存在感是很低的,因為非華裔能夠并且有意愿閱讀的人數(shù)是極少的,最多有個別作家作品能被部分高校的文學(xué)研究者作為族裔文學(xué)引入課堂,影響力限于小圈子;在中國當(dāng)代文壇,新移民文學(xué)一度也被忽視、被邊緣,甚至被貶為“海外打工文學(xué)”。嚴(yán)歌苓曾經(jīng)頗為不平地說過:“為什么老是說移民文學(xué)是邊緣文學(xué)呢?文學(xué)是人學(xué),這是句Cliche。任何能讓文學(xué)家了解人學(xué)的環(huán)境、事件、生命形態(tài)都應(yīng)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邊緣。文學(xué)從不歧視它生存的地方,文學(xué)也從不選擇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產(chǎn)生正宗文學(xué)的地方。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應(yīng)該生發(fā)正宗的、主流的中國文學(xué)。”(2)嚴(yán)歌苓:《波西米亞樓》,西安: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第118頁。新世紀(jì)以來,這種雙重邊緣的境地顯然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在國內(nèi),每年有大量的新移民文學(xué)作品被推出,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等都是主力。《人民文學(xué)》《當(dāng)代》《北京文學(xué)》《收獲》《小說月報》《花城》《江南》等很多純文學(xué)期刊也都發(fā)表大量新移民文學(xué)作品。海外的華文期刊與國內(nèi)部分文學(xué)研究期刊之間也存在互動交流,如美國舊金山的雜志《紅杉林》就與汕頭大學(xué)主辦的《華文文學(xué)》保持定期交流。各類文學(xué)獎項中不乏新移民作家的名字,嚴(yán)歌苓、李彥、陳謙、陳河、張翎、袁勁梅、張惠雯、薛憶溈等都多次獲獎。顯然,在國內(nèi)文壇,新移民文學(xué)已經(jīng)成功擺脫了邊緣地位,參與到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審美品格和敘事類型的建構(gòu)中。當(dāng)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在努力謀求“走出去”、獲取外在世界的充分關(guān)注時,新移民文學(xué)——主要是漢語創(chuàng)作,卻一直沿襲著相反的路徑“全面內(nèi)轉(zhuǎn)”。雖然經(jīng)歷了多元文化的洗禮,但華人第一代移民大多仍然以獲得故國世界、母語文化的價值認(rèn)同為精神追求,于是新移民文學(xué)顯現(xiàn)出越來越強(qiáng)烈的文學(xué)生產(chǎn)的目的性,即獲取國內(nèi)文壇和讀者群的最大肯定,包括圖書發(fā)行量、影視改編版權(quán)、獲獎、入排行榜、評論反響等。這使許多作家在強(qiáng)烈的讀者意識支配下,在敘事方式上追求腳本化、畫面感;部分作家對主題的選擇也更為審慎,盡量不觸碰一些爭議性話題,也不乏一些追逐國內(nèi)熱點的情形。于是有意識地規(guī)避有關(guān)的限制性規(guī)定就成為必然,那么在寫作中不可避免地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審查、自我規(guī)約。而新移民文學(xué)最初引起內(nèi)地文壇的關(guān)注恰恰在于其掙脫言說桎梏的那種自由表達(dá)。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一些海外華文作家是通過海內(nèi)讀者和學(xué)界而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即為國內(nèi)——不一定只是讀者——寫作,成為文學(xué)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的 ‘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這甚至成為許多作家從事創(chuàng)作的主要動力和目的。因此,在寫作中許多作家必然極力去適應(yīng)國內(nèi)的價值尺度,成為當(dāng)代中國的一塊文學(xué)‘飛地’。”(3)張福貴:《“世界華文文學(xué)”學(xué)科性的三個概念》,《江漢論壇》2013年第9期。至于在移居地的邊緣狀態(tài),對于漢語文本而言,可能是短時間內(nèi)很難改變的。華裔族群要實現(xiàn)對主流文化的“反抗遮蔽”“抵制遺忘”或“文化協(xié)商”,恐怕還是應(yīng)該借助于獲得語書寫。因為以獲得語寫作的作家在移居地能夠憑借無障礙的文學(xué)表達(dá)獲得主流文壇的承認(rèn),哈金、李翊云、李彥、應(yīng)晨、山颯等都獲得過所在國的主流文學(xué)獎項。他們的部分作品以中譯本回流至國內(nèi)后,也受到了國內(nèi)文壇和研究者的重視,從而實現(xiàn)了雙重的文化融入。
(三)跨國華人形象的增多
新移民小說中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對華人移民的回流和環(huán)流現(xiàn)象的描寫,表現(xiàn)出移民回流或者環(huán)流對于移民群體現(xiàn)實生活的深度沖擊,跨國華人形象也相應(yīng)地日漸增多。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時代,資本與人才在各國間越來越自由地穿梭,形成一股涌動不息的生機(jī)之流。而中國已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因此在中國與他國之間的資本和人才流動也是這股生機(jī)之流中的重要一束。在新移民小說中,這種跨國流動通常被敘述為高科技人才的“海歸”創(chuàng)業(yè)或者是被稱為“海鷗”的跨國生存。對于已經(jīng)在移居國落地生根的華人新移民來說,“海歸”意味著生活方式和文化認(rèn)知上的再次沖擊。黃宗之、朱雪梅(美國)的《平靜生活》(單行本易名為《幸福事件》)、陳謙(美國)的《無窮鏡》、曾曉文(加拿大)的《撈人》、秋塵(美國)的《盲點》、堯堯(加拿大)的《你來,我走——一個中國女人的移民日記》等許多作品都對跨國華人是否回歸故國、回歸后的二次文化沖擊以及“海鷗”式生存所帶來的家庭分隔兩國造成的親情、愛情的耗損等問題進(jìn)行了思考。對于跨國華人而言,他們構(gòu)建的跨國社會場域聯(lián)結(jié)著兩端——移居地與故國。這兩端通過全球化進(jìn)程而產(chǎn)生著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產(chǎn)生著某些越來越趨同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元素,但它們畢竟是兩個建基于不同制度、文化傳統(tǒng)和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空間。作為穿行于兩端的跨國移民,既有對雙重情境的切身體認(rèn),又有一定程度上的雙向情感疏離。因而,他們能夠較為客觀地認(rèn)知、深度地比較兩種文化、兩種制度,使得這種雙向開放的場域成為移居地文化與故國之間的第三文化空間。當(dāng)然,由于一定程度上的雙向的情感疏離,他們在心理上的國族歸屬感也可能有所弱化。“要理解當(dāng)今全球化背景下人類社會文化的變遷,需要重新審視甚至突破傳統(tǒng)以民族國家為視角的方法和理論,以一種動態(tài)的、聯(lián)系的、整體的視角來探究跨國流動性對跨國移民的身份認(rèn)同、文化適應(yīng)和社會融合的影響。”(4)余藍(lán)、郭世寶:《跨國移民時代加拿大多元文化課程建構(gòu)——基于跨國主義與跨文化主義》,《比較教育研究》2019年第7期。這些因素必然使得新移民小說創(chuàng)作產(chǎn)生新變。因此,新世紀(jì)以來的新移民小說創(chuàng)作在主題上的深度嬗變、在華人移民形象塑造上的多重突破,都是值得關(guān)注和思考的。
當(dāng)然,我們也應(yīng)該承認(rèn),新移民小說的新變可能只是存在于一部分作品中。因為在新移民小說繁榮的另一面,是其蕪雜性。新移民小說雖然在數(shù)量上不斷攀升,但精品仍是少數(shù),還有數(shù)量不少的作品屬于通俗的婚戀小說,充滿著一見鐘情、艷遇、出軌等習(xí)見情節(jié)。這些小說如果不是有一個故事發(fā)生的異國背景的話,與國內(nèi)的通俗文學(xué)別無二致。作者雖然身體嵌入到新的國度,但精神上也許沒有,因為在他們的寫作中對移居國的呈現(xiàn)是表層的和膚淺的,“無法以一種有穿透性的視點切入其中”(5)陳曉明:《無法終結(jié)的現(xiàn)代性——中國文學(xué)的當(dāng)代境遇》,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第121頁。。移居國在他們的敘事中始終只是一個僵硬的布景。也有一些作品,從技巧層面看,圓熟、精致,卻缺少敘事的真誠和移民生活的煙火氣,只滿足于講述傳奇故事,像流水線上生產(chǎn)的無瑕疵商品,雖然是合格的閱讀物,卻未免缺少了幾分心靈的沖擊力。因此,有學(xué)者認(rèn)為,部分新移民作家的寫作“遠(yuǎn)離新移民血肉征戰(zhàn)的沙場”,在“‘象牙塔’閉門造車”,“批量出產(chǎn)國內(nèi)歷史傳奇和當(dāng)代都市傳奇。……移民文學(xué)最常見的身份意識、文化困惑等已被她們拋棄”(6)羅玉華:《新移民文學(xué)的原罪與原味——重評〈北京人在紐約〉和〈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及其歷史影響》 ,《寧波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科學(xué)版)》2019年第1期。。主張新移民文學(xué)一定要書寫何種類型的主題,這或許是一種苛求,但新移民文學(xué)從誕生之初就被視為具有“跨國”“跨民族”“跨文化”“雙重經(jīng)驗”的寫作,如果無法體現(xiàn)這些特性,那么是否可以被視為真正意義上的移民文學(xué)也是值得討論的。
不過,正如陳曉明在評點新世紀(jì)十年的長篇小說時所指出的:“‘佳作難覓’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永恒的’問題”,但是,尋常之作“也構(gòu)成了這個時代的文學(xué)氛圍,如果沒有這些基礎(chǔ)和氛圍,也不會有‘佳作’從中脫穎而出。”(7)陳曉明:《無法終結(jié)的現(xiàn)代性——中國文學(xué)的當(dāng)代境遇》,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第212頁。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些尚顯粗糙的作品,或許作為構(gòu)成新移民文學(xué)底色的一部分也是有關(guān)注價值的。
二、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小說創(chuàng)作概覽
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新移民文學(xué)發(fā)軔之初較有影響的一些小說作者,在進(jìn)入新世紀(jì)以后出現(xiàn)了較大的分化。譬如蘇煒(美國)與查建英(美國)都是新移民文學(xué)發(fā)展初期杰出的作家,查建英的中篇小說《叢林下的冰河》《到美國去,到美國去》是新移民文學(xué)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但她在寫作了數(shù)量不多的中短篇(結(jié)集為《留美故事》)后就放棄了小說寫作,成為文化學(xué)者。蘇煒在1988年出版的短篇集《遠(yuǎn)行人》是“留學(xué)生文學(xué)”的代表作品,新世紀(jì)以來陸續(xù)有《迷谷》《米調(diào)》以及《磨坊的故事》等長篇小說問世,近年主要致力于散文隨筆的寫作。曹桂林(美國)、周勵(美國)等都屬于成名作具有極大影響、但學(xué)界評價很有爭議的作者。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在1992年出版時曾暢銷百萬冊,之后其沒有再發(fā)表小說作品,2006年出版的《曼哈頓情商——我的美國生活與勵志實錄》屬于紀(jì)實散文,2020年出版的《親吻世界:曼哈頓手記》則是旅行散文。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由于同名電視劇的熱播而影響深遠(yuǎn),之后其繼續(xù)創(chuàng)作了《綠卡》《偷渡客》等,但反響有限,新世紀(jì)以來只出版了《紐約人在北京》一部作品。至于以英文寫作的張戎(英國)、閔安琪(美國)各自的成名作《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和《紅杜鵑》都存在很大爭議,其后各自所創(chuàng)作的歷史小說作品也在國內(nèi)受到了批判。
此外,林湄(荷蘭)、戴舫(美國)、章平(比利時)、薛海翔(美國)、少君(美國)、宋曉亮(美國)、欣力(美國)、丹娃(美國)、方思(美國)、畢熙燕(澳大利亞)、抗凝(澳大利亞)、劉奧(澳大利亞,亦用劉澳)、蔣濮(日本)、華純(日本)、樊祥達(dá)(日本)、吳民民(日本)、張石(日本)等都在20世紀(jì)90年代開始創(chuàng)作。林湄出版有長篇《淚灑苦行路》《漂泊》等,戴舫出版有長篇《第三種欲望》,章平有長篇《孑影游魂》《冬之雪》以及很多中短篇,薛海翔有《早安,美利堅》《情感簽證》等,少君出版有《現(xiàn)代啟示錄》《大陸人生》等,宋曉亮有長篇《涌進(jìn)新大陸》《切割痛苦》《夢想與噩夢的撕扯》、中篇《無言的吶喊》等,欣力有《聯(lián)合國里的故事》,丹娃有《風(fēng)雨花季》《毀譽(yù)婚變》《紐約情殤》等,方思有《紐約遺恨》《金子街的女人》《緩慢的絞刑》等,畢熙燕有《綠卡夢》,抗凝有小說集《女人天空》,劉奧有《云斷澳洲路》《蹦極澳洲》,蔣濮有《東京有個綠太陽》《不要問我從哪里來》,華純有《沙漠風(fēng)云》,樊祥達(dá)有《上海人在東京》《上海新貴族》等,吳民民有《中國留學(xué)生心態(tài)錄》,張石有《東京傷逝》等。這些作品在新移民文學(xué)或海外華文文學(xué)研究界都引起過關(guān)注。新世紀(jì)以來,部分作者依然在堅持寫作,林湄出版了長篇《天望》《天外》,戴舫出版了中短篇集《獵熊之什》,章平出版了“紅塵往事三部曲”《紅皮影》《天陰石》《桃源》以及《樓蘭秘史》,畢熙燕有長篇《天生作妾》,薛海翔發(fā)表了非虛構(gòu)作品《長河逐日》,欣力出版了長篇《紐約麗人》,丹娃有科幻小說《穿梭魔域》,抗凝推出了長篇財經(jīng)小說《金融危機(jī)600日》,劉奧有《澳洲黃金夢》,少君有《人生自白》《少年偷渡犯》,吳民民有《世紀(jì)末的晚鐘》《海狼》,宋曉亮有《傳奇老北漂》等中短篇作品。但總體來說,他們在新世紀(jì)的小說創(chuàng)作數(shù)量不多。
還有一些作者,猶如電光朝露,在小說寫作圈子一閃而過,如《娶個外國女人做太太》的作者武力(澳大利亞),在2000年出版了紀(jì)實作品《我與五個英國小鬼佬》之后因患病歸隱,后成為從事企業(yè)培訓(xùn)的“潛能開發(fā)”訓(xùn)練導(dǎo)師。曾因出現(xiàn)于紀(jì)錄片《流浪北京》中而廣為人知的張慈(美國),在出版過長篇小說《浪跡美國》后,主要從事專欄寫作,出版有散文集《我的“西游記”:從云南到加州》,之后轉(zhuǎn)型成為紀(jì)錄片制作者,拍攝過紀(jì)錄片《哀牢山的信仰》《硅谷中國人》等。音樂人劉索拉曾是中國先鋒派小說的佼佼者,出國后主要從事音樂創(chuàng)作,新世紀(jì)以來僅見《女貞湯》和《迷戀·咒》等少數(shù)作品出版。而《漂流北美》的作者陳霆(加拿大)、《自由女神俱樂部》的作者紀(jì)虹(美國)、《美國圍城》的作者鄔紅(美國)、《紐約的天空》的作者殷茵(美國)等大批作者,現(xiàn)在都已很難檢索到他們的創(chuàng)作信息。這種情形在新移民文學(xué)中十分常見,其與新移民文學(xué)作者寫作的業(yè)余性質(zhì)有關(guān)。一時興起,淺嘗輒止,或者工作繁忙、家事所累,難以分身,都是可能的原因。也有一些作者主要在所在國的華人報紙發(fā)表作品,在國內(nèi)少為人知,如施國英(澳大利亞)、黃惟群(澳大利亞)等。在新世紀(jì)最初幾年,也有一批作者,如美國的嚴(yán)力、程寶林、石小克、魯鳴、木愉、沈理然、裔錦聲,英國的蘇立群、張樸等,都是在發(fā)表了一兩部小說后淡出。(8)其發(fā)表的作品,嚴(yán)力有《母語的遭遇》《遭遇9·11》,程寶林有《美國戲臺》,石小克有《美國公民》《基因之戰(zhàn)》,魯鳴有《背道而馳》,木愉有《夜色襲來》《黑白美國》,沈理然有《長島火車》,裔錦聲有《華爾街職場》,蘇立群有《混血亞當(dāng)》,張樸有《輕輕地,我走了》。他們有的在大學(xué)任教,致力于學(xué)術(shù)研究;有的供職于金融行業(yè),無暇分身;有的主要從事音樂劇、影視編劇工作等。20世紀(jì)90年代后期,還曾有一些影響較大的海外題材小說,是由當(dāng)時正在留學(xué)或訪學(xué)的國內(nèi)作者創(chuàng)作,如王小平的《刮痧》、王周生的《陪讀夫人》、劉觀德的《我的財富在澳洲》、朱世達(dá)的《哈佛之戀》、李蕙薪的《月是故鄉(xiāng)明——北京姑娘在東京》等,今天來看是不能歸入新移民小說的。
在20世紀(jì)影響較大的作家中,嚴(yán)歌苓(美國)和虹影(英國)的作品數(shù)量是最多的。她們的寫作均起步于國內(nèi),20世紀(jì)90年代就有大量作品問世。新世紀(jì)以來,她們依然保持了比較密集的創(chuàng)作節(jié)奏。嚴(yán)歌苓幾乎每年均有長篇推出,如《一個女人的史詩》《寄居者》《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金陵十三釵》《赴宴者》《陸犯焉識》《媽閣是座城》《補(bǔ)玉山居》《床畔》《舞男》《老師好美》《芳華》《小站》《穗子的動物園》《666號》等,其多數(shù)作品成為出版市場上的暢銷之作,影響很大;虹影在新世紀(jì)出版了《孔雀的叫喊》《阿難》《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術(shù)師》《康乃馨俱樂部》《好兒女花》《小小姑娘》《羅馬》等多部小說。
張翎(加拿大)也在20世紀(jì)90年代開始寫作,出版了長篇《望月》,發(fā)表過一些中短篇,但她的主要作品發(fā)表并引起關(guān)注是在21世紀(jì)。繼2001年推出《交錯的彼岸》后,先后有《郵購新娘》《金山》《睡吧,芙洛,睡吧》《陣痛》《流年物語》《勞燕》《廊橋夜話》等長篇出版,并有數(shù)量頗多的中短篇發(fā)表,結(jié)集為《雁過藻溪》《盲約》《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胭脂》《死著》《一個夏天的故事》《向北方》等等。
當(dāng)然,有消失的,也就有新起的。新世紀(jì)以來,一些作家仿佛是突然間盛開的花朵,其作品技巧的成熟、創(chuàng)作節(jié)奏的密集等都令研究者矚目,譬如李彥、陳謙、陳河、袁勁梅、曾曉文、薛憶溈、黃宗之與朱雪梅夫婦、秋塵、施瑋、施雨、張惠雯等人。
李彥1995年在加拿大出版了英文小說《紅浮萍》,并獲得1995年度加拿大全國小說新書提名獎。新世紀(jì)以來,先后有《嫁得西風(fēng)》《羊群》《海底》《呂梁簫聲》等作品問世,《紅浮萍》中文版也在國內(nèi)出版。最近幾年,她轉(zhuǎn)向了非虛構(gòu)寫作,有《不遠(yuǎn)萬里》《校園里那株美洲蕾》等作品出版和發(fā)表。
從旅居阿爾巴尼亞經(jīng)商到移民加拿大的陳河,是新移民文學(xué)中異軍突起的典型。其創(chuàng)作從2006年在《當(dāng)代》發(fā)表中篇《被綁架者說》開始,十幾年來出版了《沙撈越戰(zhàn)事》《紅白黑》《在暗夜中歡笑》《米羅山營地》《甲骨時光》《外蘇河之戰(zhàn)》等多部長篇小說,并有《黑白電影里的城市》《布偶》《女孩和三文魚》《去斯可比之路》《義烏之囚》等多部中短篇小說集。他對域外戰(zhàn)爭主題的關(guān)注、對東歐華商形象的塑造取得了很大成功。
硅谷工程師出身的陳謙從2002年發(fā)表中篇《覆水》開始,陸續(xù)發(fā)表了不少中短篇作品。《蓮露》《繁枝》《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樓》《虎妹孟加拉》以及新作《哈蜜的廢墟》《木棉花開》等對女性心理創(chuàng)傷的深度挖掘在新移民小說中無出其右;而《望斷南飛雁》《無窮鏡》與早期的《愛在無愛的硅谷》等作品對中產(chǎn)階級女性自我實現(xiàn)的探討,也是頗具深度的;《愛在無愛的硅谷》被視為第一部塑造硅谷華人形象的長篇小說。
美國克瑞頓大學(xué)的哲學(xué)教授袁勁梅的小說對故事性的追求遠(yuǎn)遜于在思想內(nèi)涵上的著力。從早期的中短篇集《月過女墻》,到后來的《羅坎村》《老康的哲學(xué)》《九九歸原》《忠臣逆子》《青門里志》,再到2016年的長篇《瘋狂的榛子》,她的敘事追求始終都落腳在中西文化的比照上。
退休前在加拿大某建筑公司擔(dān)任IT總監(jiān)的曾曉文,其創(chuàng)作也是從國內(nèi)起步的,但作品產(chǎn)生廣泛影響則在移民之后。從2006年發(fā)表長篇《夢斷德克薩斯》(后改名為《白日飄行》)開始,先后有《夜還年輕》《移民歲月》《中國芯傳奇》(與孫博合著)等幾部長篇問世,以及《金塵》《鳥巢動遷》《寡婦食物指南》等大量的中短篇小說發(fā)表于國內(nèi)的文學(xué)期刊,并結(jié)集為《愛不動了》《蘇格蘭短裙和三葉草》《重瓣女人花》等。
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薛憶溈雖然是在新世紀(jì)引起關(guān)注的作家,但他的創(chuàng)作開始于20世紀(jì)80年代的中國。移居加拿大之后,他從2003年發(fā)表短篇小說《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開始,陸續(xù)出版了《流動的房間》《不肯離去的海豚》《首戰(zhàn)告捷》《與狂風(fēng)一起旅行》等多部短篇集,還有長篇《白求恩的孩子們》《空巢》《希拉里、密和、我》,以及舊作翻新的長篇《遺棄》、短篇集《深圳人》等,2020年發(fā)表了《“李爾王”與1979》。
洛杉磯的黃宗之、朱雪梅夫婦,本職是醫(yī)藥研究,業(yè)余從事寫作。從2001年出版《陽光西海岸》開始,他們先后創(chuàng)作了《未遂的瘋狂》《破繭》《平靜生活》(又名《幸福事件》)《藤校逐夢》《艱難抉擇》等多部長篇,以及《科技泄密者》等中短篇,對教育主題十分關(guān)注。
舊金山的秋塵,退休前供職于舊金山市政府,在公職之余創(chuàng)作。新世紀(jì)以來,先后發(fā)表了數(shù)量不少的中短篇,長篇則有《時差》《九味歸一》《盲點》《青青子衿》等數(shù)部。其創(chuàng)作對辦公室政治這一主題的切入在新移民文學(xué)中是比較早的。
已經(jīng)“海歸”的施雨創(chuàng)辦的“文心社”網(wǎng)站為海外華人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對推動新移民文學(xué)的發(fā)展有很大的貢獻(xiàn)。她基于自己的外科醫(yī)生從業(yè)經(jīng)歷而創(chuàng)作的《刀鋒下的盲點》《紐約情人》《下城急診室》等長篇,是為數(shù)不多的涉及美國醫(yī)療行業(yè)的新移民小說。洛杉磯的施瑋,既是詩人、畫家,也是小說家,出版有長篇《放逐伊甸》《紅墻白玉蘭》《世家美眷》《故國宮卷》等,還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說發(fā)表。
張惠雯(美國)在新移民作家群體中是相對比較年輕的作家,主要致力于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其作品在國內(nèi)多次獲獎,受到評論界的矚目。她出版有短篇集《在南方》《兩次相遇》《一瞬的光線、色彩和陰影》等,善于描寫中產(chǎn)階級女性的細(xì)膩心理。
老作家木心,2006年被畫家陳丹青引介至內(nèi)地后,因其文字風(fēng)格的古意氤氳而被學(xué)者孫郁視為“民國的遺民”,吸引了諸多年輕讀者。他的作品以詩歌、隨筆為多,往往文白相間、文采斐然,而小說數(shù)量較少,但《愛默生家的惡客》和《溫莎墓園日記》兩個短篇集中的作品有著油畫般的豐富層次與光影色彩,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還有很多較受關(guān)注的作家,如舊金山的呂紅,主編美國著名的華文文學(xué)雜志《紅杉林》,在努力為人做嫁衣之余,自己也鐘情創(chuàng)作,先后出版有長篇《美國情人》、小說集《午夜蘭桂坊》等。其中,《美國情人》是新移民文學(xué)中為數(shù)不多的觸及美國華人社區(qū)政治生活的作品。舊金山的范遷出版有《古玩街——柏克萊童話》《錯敲天堂門——曼哈頓童話》《丁托雷托莊園》《桃子》《風(fēng)吹草動》《失眠者俱樂部》《錦瑟》等長篇小說。加拿大多倫多的孫博,從2000年的長篇小說《男人三十》開始,出版了《回流》《小留學(xué)生淚灑異國》《茶花淚》《中國芯傳奇》(與曾曉文合著)等多部作品。舊金山的沙石,通過中短篇集《玻璃房子》以另類筆墨觸及移居國的底層群體,而他的長篇《情徒——一個中國人的美國故事》更是以元小說的手法對新移民作家群體本身進(jìn)行了毫不留情的諷刺,其辛辣極為少見。曾以《傷痕》進(jìn)入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盧新華,在移居美國后沉寂數(shù)年,進(jìn)入新世紀(jì)后重拾創(chuàng)作,2004年推出長篇《紫禁女》,2013年出版長篇《傷魂》。日本的元山里子(原名李小嬋,中日混血)的非虛構(gòu)作品《三代東瀛物語》《他和我的東瀛物語——一個日本侵華老兵遺孀的回憶錄》,對自己的中日跨國家庭的滄桑歷史和丈夫元山俊美從侵華日軍到反戰(zhàn)人士的艱辛歷程的述說,在日本新移民文學(xué)中也是獨(dú)特的存在。加拿大文章的《失貞》對于新移民在留居與歸國上的情感掙扎有著獨(dú)特的切入角度,她的《剩女茉莉》則是敘事圓熟的職場小說。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陸蔚青的“紐曼街”系列是對移居地的邊緣人群和底層人群進(jìn)行描摹的精彩短篇。加拿大的笑言的《香火》以子嗣問題為切入點,對文化的融合與傳承提出了新的見解。曾以《花季雨季》少年成名的郁秀(美國),新世紀(jì)以來,陸續(xù)推出了《太陽鳥》《美國旅店》《不會游泳的魚》和《少女玫瑰》,始終對成長小說興趣濃厚。
部分作家雖然作品數(shù)量不甚多,但甫一出手即是較為成熟的作品。如日本華文作家陳永和,大器晚成,其《光祿坊三號》和《一九七九年紀(jì)事》將常見的故鄉(xiāng)敘事以懸疑筆法寫出了新意,語言精致流暢;美國學(xué)者作家王瑞云的《戈登醫(yī)生》《姑父》等短篇,對人性的裂變、創(chuàng)傷的深重與人類情感的復(fù)雜給出了精彩的表達(dá);德國的海嬈,其《早安,重慶》是新移民作家中少數(shù)能夠真正切入當(dāng)下中國變遷之腠理的作品;比利時的謝凌潔創(chuàng)作的長篇《雙桅船》對二戰(zhàn)創(chuàng)傷的書寫既有強(qiáng)烈的故事性,又含蘊(yùn)豐富的知識內(nèi)容;孫康青(美國)的《解碼游戲》是敘事節(jié)奏把控很好的犯罪小說。美國華裔文學(xué)批評家林澗在致力華人文學(xué)研究20余年后,又以自己的英文回憶錄《我的教育:一位好學(xué)生的回憶》和中文回憶錄《一號汽車:舊上海的故事》而成為新移民寫作群體的一員,其基于舊上海家族往事的中文回憶錄被稱為“后現(xiàn)代的回憶錄”,“因為用了后現(xiàn)代的文本拼貼的手法,給出了后現(xiàn)代的政治與文化闡釋;作者是‘尋根問祖’的后人,更是解構(gòu)豪門神話與拜金主義迷思的哲人,她的回憶是她說與讀者的話語——她不僅在說,更是在催促著讀者思考、思辨、完成那個形而上的提升與轉(zhuǎn)變”(9)潘雯:《重溫林澗的“后現(xiàn)代”——論美華文學(xué)的跨國研究》,《華文文學(xué)》2019年第2期。。
除此以外、歐陽昱(澳大利亞)的《淘金地》、倪湛舸(美國)的《異旅人》、陳思進(jìn)和雪城小玲(加拿大)的《心機(jī)》、董晶(美國)的《七瓣丁香》、黃鶴峰(美國)的《西雅圖酋長的讖語》、余澤民(匈牙利)的《匈牙利舞曲》《狹窄的天光》《紙魚缸》、余曦(加拿大)的《安大略湖畔》、鐘宜霖(英國)的《唐人街:在倫敦的中國人》、穆紫荊(德國)的《情事》《活在納粹之后》、江嵐(美國)的《合歡牡丹》、方麗娜(奧地利)的《蝴蝶飛過的村莊》《夜蝴蝶》、王琰(美國)的《落日天涯》《我們不善于告別》《歸去來兮》、凌嵐(美國)的《離岸流》、老木(捷克)的《新生》《義人》、海云(美國)的《金陵公子》、常琳(加拿大)的《雪后多倫多》、融融(美國)的《素素的美國戀情》《夫妻筆記》、應(yīng)帆(美國)的《有女知秋》、楓雨(美國)的《八零后的偷渡客》、李鳳群(美國)的《大風(fēng)》《大野》、夫英(美國)的《洛杉磯的家庭旅店》、劉瑛(德國)的《不一樣的太陽》、柳營(美國)的《姐姐》、亦夫(日本)的《無花果落地的聲響》、于仁秋(美國)的《請客》、葉周(美國)的《丁香公寓》、陳九(美國)的《挫指柔》、孟悟(美國)的《逃離華爾街》、南希(美國)的《娥眉月》《足尖旋轉(zhuǎn)》、黑孩(日本)的《惠比壽花園廣場》《貝爾蒙特公園》、吳越(美國)的《最寒冷的冬天是舊金山的夏季》《當(dāng)時已惘然》、吳帆(美國)的《二月花》、虔謙(美國)的《玲玲玉聲》等都是受到研究者關(guān)注的作品。
除了漢語作品以外,使用獲得語寫作的作家新世紀(jì)以來也發(fā)表了不少作品,主要有加拿大的李彥、應(yīng)晨,美國的哈金、裘小龍、李翊云,法國的戴思杰、山颯、黃曉敏,以及英國的魏薇等。李彥繼《紅浮萍》之后,又出版了英語小說《雪百合》;哈金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新郎》《落地》,長篇《瘋狂》《戰(zhàn)爭垃圾》《南京安魂曲》《通天之路:李白傳》等。裘小龍出版了系列偵探小說《紅英之死》《石庫門驪歌》《外灘花園》《紅塵歲月:上海故事》《紅旗袍》等。李翊云出版有短篇集《千年敬祈》《金童玉女》,長篇《漂泊者》《無因無果》等。戴思杰有長篇《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狄的情結(jié)》《無月之夜》等。山颯有《圍棋少女》《柳的四生》《裸琴》等。法國尼斯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黃曉敏出版有《翠山》和《蓮花》。應(yīng)晨于20世紀(jì)90年代就在加拿大開始寫作,先后出版了法語小說《水的記憶》《自由的囚徒》《再見,媽媽》《磐石一般》《懸崖之間》等。她獲得費(fèi)米娜文學(xué)獎和加拿大總督獎提名的作品《再見,媽媽》于2002年在國內(nèi)出版了中文版,是她目前唯一在內(nèi)地翻譯出版的作品。魏薇出版有《幸福的顏色》和自傳體小說《一個壯族姑娘》。
總體而言,目前比較活躍的新移民小說家,其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在進(jìn)入新世紀(jì)后面世的。不過,有部分作家雖然出版的作品數(shù)量很大,也的確存在不斷重復(fù)自身的狀態(tài)。在他們頻繁推出的作品中,表層故事雖然不斷變換,但作品內(nèi)涵、人物類型卻鮮有變化。對于這些作家而言,如果沒有真正的突破,靠自我復(fù)制和稀釋自己的文學(xué)才情來提高作品數(shù)量,多少有點虛假繁榮的意味。而且,不可否認(rèn),新移民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模式化是明顯的,即留學(xué)/移民+愛情,部分小說過度執(zhí)著于對強(qiáng)烈戲劇性的追求,習(xí)慣通過艷遇、性描寫和極端事件來推動敘事進(jìn)程。這或許是由于新移民作家群體有著大致相似的生活經(jīng)歷、生活體驗和共同的情感結(jié)構(gòu),以及文本生產(chǎn)背后新移民群體相對穩(wěn)定、一致的生存本相,使得許多以個體經(jīng)驗為書寫資源的小說有著同質(zhì)化傾向。從研究和解讀的角度來看,當(dāng)然存在著價值和意義不斷稀釋、闡釋空間不斷逼仄的狀況。但從創(chuàng)作者的角度來說,即便經(jīng)驗相似、體驗雷同,但千萬人的書寫亦不能抵消個人的訴說沖動。這是寫作者最原始、最強(qiáng)烈的文本生產(chǎn)動力。
三、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小說的主題嬗變
在新移民文學(xué)發(fā)展的最初階段,有很多作品偏好表現(xiàn)異國生存苦痛。這些作品盡管都是以移居地為敘事背景,但這個背景經(jīng)常很模糊,讀者透過這些文本所窺見的往往并非是一個客觀的、層次豐富的異域國度。除了生活細(xì)節(jié)的碎片外,當(dāng)?shù)氐恼紊睢⒔?jīng)濟(jì)運(yùn)行、教育機(jī)制、文化事件、藝術(shù)活動等,或者缺失,或者面目模糊,移居地仿佛只是置放在現(xiàn)實生活背后的混沌布景。新世紀(jì)以來,由于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極速發(fā)展,特別是2010年以后新媒體的崛起,信息的傳播方式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無數(shù)涌向西方世界的留學(xué)生和跨國從業(yè)者都在通過新媒體傳達(dá)域外的各種信息和風(fēng)土人情。這種傳達(dá)更為及時、甚至迅速,而新媒體“所有人向所有人傳播”的特性也使得這種傳達(dá)所輻射的范圍更廣闊,由此造成新移民文學(xué)原本具有的異域時空下的現(xiàn)場感已經(jīng)不再是其獨(dú)有的敘事表征,讀者也就不再對域外的人與事具有那么強(qiáng)烈的淺表性好奇。在這種時代語境之下,部分有自覺性和判斷力的新移民作者已經(jīng)意識到,不能再繼續(xù)沉溺于個人的異域悲情或者在不同文化之間、不同國度之間轉(zhuǎn)運(yùn)西洋景和生活碎片,而應(yīng)從文化比較、尤其是一些制度建設(shè)、社會運(yùn)行機(jī)制等方面做更多的勾畫。在新世紀(jì)以來出版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小說開始擺脫舊日的標(biāo)簽,走出淺表的景觀化描述,更為注重對現(xiàn)實經(jīng)驗、尤其是異國情境中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教育、族裔文化特性等重要社會層面上的文化思考,再現(xiàn)和傳達(dá)中國文化與世界的對話和溝通。在這些溝通中,華人移民開始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從單純地反思自身到客觀地認(rèn)知雙方。
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小說的發(fā)展,從主題的豐富性來說,宛如一場正在綻放的絢爛煙花,有多個精彩的爆點。一方面,20世紀(jì)新移民文學(xué)發(fā)軔之初比較集中的主題依然在延續(xù)中,譬如生存苦痛、故鄉(xiāng)敘事等。另一方面,隨著部分新移民生存境遇的改變,一些新移民作家開始從初抵異國的“漫游者”式的膚淺、獵奇的凝視向定居者的介入式觀察轉(zhuǎn)變。這使他們對居住國的教育運(yùn)行、醫(yī)療制度、職場文化、生態(tài)意識等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的思考更趨深入和闊達(dá)。由此,他們也力圖在創(chuàng)作中勾勒出移居國的立體多維面目,滌蕩部分獵奇和觀光文本所創(chuàng)造出的刻板印象,從而構(gòu)建一個更具認(rèn)知價值的新移民文學(xué)的意義場。同時,作為跨國華人,部分作家對居住國與故國之間的歷史勾連與文化往復(fù)產(chǎn)生濃厚興趣,從而發(fā)掘出許多掩埋在歷史煙塵中鮮為人知的故事。這些變化反映在創(chuàng)作上,也就產(chǎn)生了一批有深度的新移民小說以及非虛構(gòu)性敘事作品。
雖然新移民文學(xué)已經(jīng)走過40年歷程,但從目前的創(chuàng)作態(tài)勢看,由個人經(jīng)驗出發(fā)的創(chuàng)作仍是新移民小說最主要的類別,如著重于移居經(jīng)歷中生存苦痛描寫的類自敘傳、故鄉(xiāng)敘事等主題。有的研究者認(rèn)為,書寫新移民群體圍繞生存、求學(xué)、居留權(quán)獲取等問題產(chǎn)生的情感痛楚和精神迷茫,以及對事業(yè)成功的炫示等主題的作品主要存在于新移民文學(xué)發(fā)展的最初階段。事實上,這類主題的書寫是具有一定延續(xù)性的。綜觀新世紀(jì)以來的新移民小說創(chuàng)作,這類書寫數(shù)量上依然很大,從新世紀(jì)之初至今,不斷在出版。如葉周(美國)的《美國愛情》(2001)、融融(美國)的《素素的美國戀情》(2002)和《夫妻筆記》(2005);少君(美國)的《人生自白》(2003);凌之(澳大利亞)的《海鷗南飛》(2004);曾曉文(加拿大)的《夢斷德克薩斯》(2006);夏爾(澳大利亞)的《望鶴蘭》(2008);堯堯(加拿大)的《你來,我走——一個中國女人的移民日記》(2009)、劉加蓉(美國)的《洛杉磯的中國女人》(2009);鐘宜霖(英國)的《倫敦愛情故事》(2010);洪梅(美國)的《夢在海那邊》(2012);老木(捷克)的《新生》(2016)、王海倫(加拿大)的《楓葉為誰紅》(2016);牧童歌謠(美國)的《北美楓情》(2018);岳韜(荷蘭)的《一夜之差》(2019)等。這種延續(xù)性應(yīng)該說是新移民文學(xué)的一種常態(tài)。在這種類別的新移民小說中存在一種常見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模式——出國留學(xué)/定居+情感波折+事業(yè)成功,可以說是新移民小說情節(jié)元素的“三件套”。
陳思和曾多次指出,海外華文文學(xué)一直是靠從國內(nèi)向國外橫向移植來延續(xù)的,因此新移民文學(xué)之“新”是永恒的。在筆者看來,新移民文學(xué)呈現(xiàn)兩端開放的狀態(tài):一方面,永遠(yuǎn)有剛剛抵達(dá)的“新”移民匯入華人移民群體,因此也就永遠(yuǎn)有人在書寫初抵異國的生存苦痛、鄉(xiāng)愁與故國回憶;有些作者雖然并非是初抵異國,但他們開始寫作、開始書寫個人生活經(jīng)驗的時間點卻是各有不同的。生存苦痛和鄉(xiāng)愁于新移民文學(xué)或可視為老生常談,于寫作者個體卻是無可取代的切身經(jīng)驗,不吐不快。正因為如此,這類主題的書寫長盛不衰。另一方面,留居日久、寫作多年的移民作家,則在寫盡回憶和淺表的新奇之后,逐漸向縱深開掘,許多作家開始關(guān)注留居國的制度運(yùn)行和周遭其他種族的生存世相。因此,由于移民個體的生活經(jīng)驗與文學(xué)經(jīng)驗各有不同,必然產(chǎn)生風(fēng)格各異、主題紛繁的作品,它們以各自的方式在共同書寫著新移民文學(xué)史。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小說在主題上的嬗變,突出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回歸主題的嬗變、故鄉(xiāng)敘事和歷史敘事的嬗變、底層書寫、生態(tài)書寫、創(chuàng)傷書寫和中產(chǎn)階級話語的書寫等。
(一)回歸主題的嬗變
新移民作家群體最初大多是以留學(xué)、訪學(xué)的方式開始去國離家的。“歸”與“不歸”的選擇一直是他們必然要面對的人生課題。這種選擇的猶疑、痛苦不僅關(guān)乎個體的人生路徑走向,而且承載了許多道德上的自我批判、尊嚴(yán)上的心理失衡。因此,回歸主題在新移民小說中的嬗變映射的是中國的國力發(fā)展、在世界舞臺上的話語分量以及對全球化的融入進(jìn)程等諸多政治、經(jīng)濟(jì)和社會性問題。在早期的留學(xué)生文學(xué)中,回歸與否常常關(guān)乎道德的承擔(dān),在國家需要面前,對個人前途利益的考量,使主人公們不自覺地有一種羞愧、甚至是負(fù)罪感。這反映了在留學(xué)大潮的初期,赴外留學(xué)知識分子群體的強(qiáng)烈的社會責(zé)任感。新世紀(jì)以來,回歸主題開始淡化政治色彩,回避道德承擔(dān),而凸顯尋常的蕓蕓眾生在“留”與“歸”的選擇上對個體尊嚴(yán)的現(xiàn)實考量。如黃宗之、朱雪梅夫婦的《陽光西海岸》、樹明的《暗痛——兩個中國男人在美國》等都是如此。這種書寫從一個側(cè)面說明,隨著國家的發(fā)展重心轉(zhuǎn)向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國家的政治和文化空間趨于寬松,民眾已經(jīng)不再像過去那樣自覺不自覺地動輒將個人的生活選擇涂抹太多的政治色彩,個體生活開始回復(fù)到正常的社會氛圍中。而黃宗之、朱雪梅《平靜生活》、孫博的《回流》、文章的《失貞》、堯堯的《你來,我走——一個中國女人的移民日記》、洪梅的《夢在海那邊》,以及孫博與曾曉文合著的《中國芯傳奇》等作品中對回歸的探討,既過濾掉了早期回歸主題中的道德承擔(dān)和悲情色彩,也甚少關(guān)涉新移民脆弱的個體尊嚴(yán),而是開始將“海歸”現(xiàn)象視為華人移民的一種理性選擇,客觀呈現(xiàn)出跨國華人群體在回歸選擇上的個體復(fù)雜性,在得失的糾結(jié)背后既有經(jīng)濟(jì)驅(qū)動,也有個人價值實現(xiàn)以及家庭利益考量等多維因素。他們的回歸行為是全球化時代高技術(shù)人才的正常而理性的行動,也是跨國華人生活的真實圖景。
(二)故鄉(xiāng)敘事的嬗變
故鄉(xiāng)書寫作為依托于個體經(jīng)驗而產(chǎn)出的文學(xué)敘述,是新移民文學(xué)的重要主題之一。新世紀(jì)以來的故鄉(xiāng)書寫仍以延續(xù)性的家族敘事為主,如李彥的《紅浮萍》、元山里子的《三代東瀛物語》、陳永和的《一九七九年紀(jì)事》等,這些家族敘事通常都是以家族的歷史變遷為坐標(biāo)軸的。民族和國家大歷史所表述的治亂興衰中勢必要舍棄億萬普通個體和平凡家庭碎片般的小歷史,而從個體或者家族的小歷史來呈現(xiàn)時代的復(fù)雜性正是文學(xué)的使命之一。這些家族的歷史是民族歷史的縮微映像,是20世紀(jì)時代光影的點點投射。新移民作家在異域時空中以新的視野審視家族傷痛,書寫家族記憶,既是對自身記憶框架的建構(gòu),也是“一種國族文化和歷史的自我詮釋與重審”(10)湯俏:《北美新移民文學(xué)中的家國尋根與多重認(rèn)同》,《當(dāng)代文壇》2020年第3期。。
海嬈的《早安,重慶》與上述作品的厚重沉郁不同,它主要截取的是當(dāng)下生活的片段,通過鄭長樂一家在社會轉(zhuǎn)型期經(jīng)歷的下崗、拆遷、買房、養(yǎng)老、殘疾人和重病患者的醫(yī)療保障等問題,將底層群體的悲苦、無奈、堅忍與守望互助、積極樂觀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字里行間既沒有情感的過度宣泄和夸張矯飾,也沒有居高臨下、隔靴搔癢的空洞評議,唯有真摯的情感靜靜流淌,勾勒出一道中國大地上升斗小民的蜿蜒的生命軌跡。
在這些傳統(tǒng)的故鄉(xiāng)書寫之外,袁勁梅的故鄉(xiāng)書寫顯示出獨(dú)有的特色。她對中西文化的比照是基于新經(jīng)驗的新思考,是依托現(xiàn)代科學(xué)與現(xiàn)代政治哲學(xué)理論來展開的關(guān)于責(zé)任與批判思維的思考。因此,袁勁梅的新故鄉(xiāng)敘事既尖銳地戳破了早期故鄉(xiāng)敘事的唯美面紗,也毫不客氣地拋棄了眼淚和訴苦。她帶著愛之深責(zé)之切的強(qiáng)烈鄉(xiāng)情拿起手術(shù)刀,解剖傳統(tǒng)中國在走向現(xiàn)代化的歷程之中,一方面頑固延續(xù)著文化中的落后與保守、另一方面努力擁抱經(jīng)濟(jì)和科技新潮流,在二者的絞接中所發(fā)生的奇異變形。雖然作者在言辭激烈之下不免有不及義之處,但她提出的問題正是一個處于急劇變化發(fā)展中的民族所必須面對、必須思考的。
(三)歷史敘事的嬗變
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作家的歷史敘事作品蔚為繁盛,這些作品的寫作源起大多與作者的移民身份、移民經(jīng)歷有關(guān)。這些作品的敘事風(fēng)貌也與他們作為移民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有密不可分的關(guān)聯(lián),在文本中通常存在多國時空勾連、多族裔共處。顯然,當(dāng)他們作為跨國移民頻繁往來于故國與居住國之間時,作為文化居間者,他們已經(jīng)不僅僅滿足于單純地回望故國或者是講述在居住國落地生根過程中的辛酸與成功,而是利用作為文化居間者的身份便利,以移民的特有敏銳觸角,搜尋、打撈在兩種甚至是多種文化交接處的歷史遺跡,將移居國的歷史文化與故國的歷史文化勾連在一起,敘述出一個個曾經(jīng)湮沒于歷史塵煙中的跨國故事,從而展現(xiàn)出新移民文學(xué)的跨文化視野。
李彥的非虛構(gòu)寫作,其筆墨主要集中于一些與中國歷史產(chǎn)生過交集的加拿大歷史人物,如加拿大的明義士家族、白求恩、托馬斯·亞瑟·畢森等,先后發(fā)表了《小紅魚兒你在哪里住——甲骨文與明義士家族》《不遠(yuǎn)萬里》《校園里那株美洲蕾》等作品。作為新移民作家,將定居國與故國之間的歷史關(guān)聯(lián)納入書寫版圖,以文學(xué)的方式在傳播史上增加一節(jié)鏈條是深具價值的。
薛海翔的《長河逐日》、元山里子的《他和我的東瀛物語——一個日本侵華老兵遺孀的回憶錄》都是對家族中的二戰(zhàn)/抗戰(zhàn)歷史的非虛構(gòu)敘述。《長河逐日》是薛海翔尋找自己人生來處的跨國之旅,是對家史的書寫,也是對20世紀(jì)上半葉的青年革命者群體所做的文學(xué)素描。因此,他的書寫以時間的線性歷程為經(jīng),以父母所處的不同空間為緯,穿梭編織,逐步收攏,由此完成了一次家族的尋根。在追蹤父母的革命軌跡時,他還把父母的口述、相關(guān)回憶文章以及其他可以印證父母人生經(jīng)歷的歷史文獻(xiàn)都嵌入文本之中,使家史成為一段國史、甚至“輻射至整個亞洲的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大潮的歷史”的縮微映現(xiàn)。《他和我的東瀛物語——一個日本侵華老兵遺孀的回憶錄》不僅對元山俊美作為曾是侵華日軍一員的懺悔和反思、以及他后來的積極反戰(zhàn)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解說,而且對日本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演變歷史、日本左翼和右翼之間不懈斗爭的歷史也作了很多介紹。元山里子以侵華老兵遺孀的內(nèi)部視角,提供了更具細(xì)節(jié)化的文本,使這部非虛構(gòu)作品不僅在新移民文學(xué)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而且在有關(guān)中日關(guān)系的書寫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袁勁梅的《瘋狂的榛子》和陳河的系列戰(zhàn)爭小說的戰(zhàn)爭書寫均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礎(chǔ)之上,既進(jìn)入了戰(zhàn)爭的本相,又在本相之上關(guān)注戰(zhàn)爭創(chuàng)傷、戰(zhàn)爭倫理和戰(zhàn)爭中復(fù)雜的政治糾葛。《瘋狂的榛子》以對美國第14航空軍的中國抗戰(zhàn)歷史的發(fā)掘為敘事主線,但真正的主旨則是文化比照。作品通過戰(zhàn)爭帶給軍人的PTSD(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來努力闡釋戰(zhàn)爭與和平的邏輯聯(lián)系,指出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不只是身體與心理上的,更是道德上的,強(qiáng)調(diào)區(qū)別戰(zhàn)爭倫理與和平倫理的重要。陳河的戰(zhàn)爭書寫則選取了一個特殊的切入點,即中國國界之外的華人戰(zhàn)爭史實,《沙撈越戰(zhàn)事》《怡保之夜》《米羅山營地》和《外蘇河之戰(zhàn)》等均是域外戰(zhàn)爭書寫。2020年發(fā)表的中篇《天空之鏡》則是以尋訪格瓦拉的一個華裔戰(zhàn)友奇諾為敘事主線,近乎非虛構(gòu)寫作。陳河比較關(guān)注戰(zhàn)爭中復(fù)雜的政治糾葛所導(dǎo)致的悲劇和荒誕性,以及人在殘酷環(huán)境中的自處與作為。其戰(zhàn)爭美學(xué)呈現(xiàn)為一種悲涼的質(zhì)地。而陳河作品中通常存在的多族裔的共處與交接使得戰(zhàn)爭的正義性與多國政治利益的考量絞結(jié)在一起,戰(zhàn)爭的殘酷、愛情的純真與政治的荒誕也絞結(jié)在一起,營造出廣闊的敘事空間。
嚴(yán)歌苓的許多作品都可視為歷史敘事,其中《寄居者》《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金陵十三釵》以及新作《666號》等也都涉及抗日戰(zhàn)爭。這些作品普遍具有強(qiáng)烈的傳奇性,如《寄居者》和《666號》都存在身份錯置,《小姨多鶴》是隱藏身份,《金陵十三釵》是身份/身體替代。因此,她的敘事通常關(guān)注的是戰(zhàn)爭背景下的人性裂變和情感糾葛,而非對戰(zhàn)爭本身的思考。其中,《金陵十三釵》與哈金的《南京安魂曲》、鄭洪的《南京不哭》都涉及“南京大屠殺”,在部分史實細(xì)節(jié)上也存在一致性。“南京大屠殺”是我們民族的巨大創(chuàng)傷,除了歷史學(xué)、政治學(xué)、社會學(xué)等學(xué)術(shù)研究之外,以文學(xué)敘事書寫這一創(chuàng)傷性歷史事件,也是具有極大意義的。從此意義上說,這幾部“南京大屠殺”題材的小說具有非凡的文學(xué)價值。并且由于它們均由美籍華人作家完成,對它們的對照性閱讀也常常成為文學(xué)研究的題目。張翎的《勞燕》與袁勁梅的《瘋狂的榛子》在敘事元素上存在一定相似性,都有戰(zhàn)爭中的愛情,都涉及抗戰(zhàn)中的中美合作。不過,《勞燕》相對來說更關(guān)注戰(zhàn)爭中女人的情感歷程而非歷史本身。
(四)底層書寫
全球化時代,大規(guī)模的、普泛的遷徙和流動,幾乎已成為現(xiàn)實生活的常態(tài)。全球流散人口成分復(fù)雜,既有技術(shù)與文化精英、跨國商人,也有合法與非法的勞工群體。當(dāng)跨國華人的中上層盡享全球化時代的迅捷交通和發(fā)達(dá)資訊所帶來的優(yōu)裕生活之時,身處底層的勞工群體、尤其是非法移民,卻可能面對物質(zhì)和精神的雙重窘迫。因此,關(guān)注底層華人移民群體的生存,關(guān)注所在國當(dāng)?shù)氐牡讓觿诠と后w,描摹他們悲喜交織的精神世界,也應(yīng)該是新移民文學(xué)的書寫重點之一。鐘宜霖的《唐人街:在倫敦的中國人》仿佛是移民版的“72家房客”,透過敘述者截取的房客生活片斷,我們得以窺見在中國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和擁抱全球化的浪潮中,那些缺少知識資本、經(jīng)濟(jì)資本的底層民眾是如何渴望通過國際遷移來改變?nèi)松崿F(xiàn)夢想的。夫英的《洛杉磯的家庭旅店》以一個華人移民群居的家庭旅店為中心,呈現(xiàn)了一些身無所長、夢想大于能力的底層移民勉力生存的現(xiàn)實。沙石的《玻璃房子》關(guān)注寂寞的單身花匠、失戀落魄的作家、妻離子散的倒霉父親、在種族歧視壓力下心力交瘁的職員等移民群體中失意的灰色個體,在荒誕的故事中,以另類的方式揭開了種族區(qū)隔、階級區(qū)隔之下底層移民的精神壓抑。方麗娜的《蝴蝶坊》則把視點聚焦華人移民中的性工作者身上,對于這些既要忍受同胞的歧視,也要面對街頭黑惡勢力的劫掠、還會時刻面臨遣返風(fēng)險的底層女性來說,身后的家園并不是她們的退路,只會令她們無顏面對。她們的生活始終籠罩著灰色的陰霾,出路十分狹窄。
而曾曉文的《金塵》、陳河的《在暗夜中歡笑》《紅白黑》、楓雨的《八零后的偷渡客》、范遷的《桃子》、少君的《少年偷渡犯》等,都明確涉及華人移民生活中經(jīng)常諱莫如深的地下生態(tài)鏈:偷渡以及偷渡后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途徑獲取居住國合法身份的運(yùn)作過程——這是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運(yùn)行著的黑色或灰色產(chǎn)業(yè)。這條地下生態(tài)鏈上,有獲利頗豐的黑幫,有利用法律漏洞從中牟利的律師,更多的是裹挾其中的非法移民。這些作品將偶爾出現(xiàn)在媒體上的新聞事件,具象化為一個個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的傳奇故事,使得這一伴隨移民歷史而生的問題不再是移民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房間里的大象”,而成為記錄移民歷史和移民群體悲歡的一個重要側(cè)面。
此外,陸蔚青的《紐曼街往事》、李彥的《泥藕的羞慚》《吉姆老來得子》、穆紫荊的《老貓旺空》等作品都屬于新移民文學(xué)中的跨族群書寫,或者說是“在地敘事”。這些作品聚焦的是所在國本土居民及其他移民群體的底層,關(guān)注他們具體的日常的生活狀態(tài),觀察他們精神世界中的悲喜。這種書寫為我們更為全面地了解新移民文學(xué)發(fā)生地的社會面貌提供了重要的樣本,因為“如果不了解海外華人定居于其中的那些非華人的生活、傳統(tǒng)和態(tài)度,就無法理解海外華人的經(jīng)歷。”(11)[美]孔飛力:《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xiàn)代移民史》,李明歡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4頁。
雖然由于這些寫作者本身都是知識分子,生活狀態(tài)上屬于中產(chǎn)階級或者中產(chǎn)階級之上,作為底層生活的旁觀者,他們是否能夠真正理解底層,為底層發(fā)聲,是受到很多評論家質(zhì)疑的。但是,能夠突破個人生活圈層邊界、關(guān)注底層群體精神世界的寫作,在一定意義上使新移民文學(xué)對移民經(jīng)驗的表述更加全面和豐富,也使我們能夠從多維度生發(fā)對于華人新移民群體和他們留居國的文學(xué)認(rèn)知。
(五)生態(tài)書寫
在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生劇烈變化的當(dāng)下,如何構(gòu)建人類與自然環(huán)境的相處模式成為當(dāng)下的熱點議題之一。而新世紀(jì)以來的華人移民文學(xué),也有一些作品涉及生態(tài)文學(xué)中的動物關(guān)切、人類中心主義批判等主題,展現(xiàn)了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文學(xué)具有的超越性視野。
陳河的《猹》、李彥的《大雁與烏龜》、曾曉文的《鳥巢動遷》、朱頌瑜的《大地之子穿山甲》等作品以人與動物之間愛恨交織的相處關(guān)系,昭示出一個重要的哲理——自然并非是為人類而存在的。動物作為獨(dú)立的生命個體,也不僅僅是作為滿足人類需求的客體而存在。如果人類對動物的愛憎只是一種自說自話的情感投射,或者是一種基于自身需求的價值取舍,那么人類在動物面前就沒有任何價值超越性可言。在人類與動物的關(guān)系框架中,人類真正可以體現(xiàn)自己價值超越性的地方只能是擔(dān)負(fù)起對動物的道德義務(wù)。而陳謙的《虎妹孟加拉》通過留學(xué)生玉葉與孟加拉虎的故事將思索從人與動物的關(guān)系一直延展到現(xiàn)代社會中人倫親情的淡漠。
袁勁梅的《父親到死,一步三回頭》通過父親作為一個魚類生物學(xué)家,終生致力于環(huán)境保護(hù)、卻始終未能阻止環(huán)境持續(xù)惡化的悲涼描述,對現(xiàn)代性、“人類中心主義”提出了痛切譴責(zé)。黃鶴峰的《西雅圖酋長的讖語》則是一篇涉及“生態(tài)整體主義”以及環(huán)境正義的作品。小說以兩代印第安人與白人之間發(fā)生的愛情故事為敘事線索,從多個側(cè)面展現(xiàn)了古老的印第安文化,頌贊以印第安人為代表的美洲原住民文化所具有的萬物有靈、自然平衡的生態(tài)整體主義觀念。
從這些生態(tài)主題的作品來看,新移民作家的書寫已經(jīng)超越了簡單的族裔視角,開始深度切入居住國的重要社會議題,而且在對故國的關(guān)注上也超越了普泛的鄉(xiāng)愁和懷舊,開始發(fā)揮他們作為跨國華人群體的價值,對故國的社會發(fā)展路徑投入了更多的關(guān)注。
(六)創(chuàng)傷書寫
巨大的情感容量和哲思空間使得創(chuàng)傷書寫成為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主題類別。新世紀(jì)以來,新移民作家也先后推出諸多創(chuàng)傷書寫的作品,其中以陳謙的創(chuàng)作最具代表性,她的《繁枝》《蓮露》《哈蜜的廢墟》和新作《木棉花開》等持續(xù)關(guān)注女性在家庭空間中遭遇的心理創(chuàng)傷及其療愈的艱難,包括性侵、遺棄、親情畸變等,為讀者推開了一扇又一扇潛藏著秘密的沉重之門。袁勁梅的《瘋狂的榛子》、曾曉文的《巴爾特的二戰(zhàn)記憶》、謝凌潔的《雙桅船》、戴舫的《手感》等都是對人類戰(zhàn)爭、種族屠殺等極端境遇的創(chuàng)傷書寫。陳謙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樓》和王瑞云的《姑父》是對政治創(chuàng)傷的書寫。張翎的《余震》聚焦自然災(zāi)難帶來的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
新移民文學(xué)中的創(chuàng)傷書寫,涉及的類型較為豐富,很多作品都深刻觸及華人移民群體精神生活的本相,從不同的痛點介入現(xiàn)實和歷史的褶皺中,掀開其下被遮掩的嚴(yán)重創(chuàng)傷,探索療愈的可能,其書寫中的悲憫是被忽視和回避的黑暗世界中的一縷柔光。
(七)中產(chǎn)階級話語
新移民作家群體在其居住國基本都屬于中產(chǎn)階級,但與國內(nèi)的中產(chǎn)階級構(gòu)成不甚相同的是其知識分子背景更加深厚,因為這一群體是以赴外留學(xué)者為主力形成的,這一背景決定了他們的書寫中既包含對自身階層屬性中淺薄、平庸、保守等特質(zhì)的批判,也彰明較著地將自身階層屬性中的正面價值進(jìn)行了精彩的表達(dá)。陳謙的《愛在無愛的硅谷》《望斷南飛雁》《無窮鏡》和王芫的《路線圖》主要表達(dá)中產(chǎn)階級女性如何在各種現(xiàn)實的撕扯中拼力追求個人實現(xiàn);張惠雯的《醉意》《失而復(fù)得》《歲暮》、曾曉文的《重瓣女人花》、畢熙燕的《天生作妾》都表現(xiàn)中產(chǎn)階級女性婚姻中的沉悶、家庭中其他成員對于婚姻本身的干擾,以及家庭之內(nèi)女性在試圖保持精神獨(dú)立、自足時所遭遇的世俗阻擊。而秋塵的《盲點》、裔錦聲的《華爾街職場》、文章的《剩女茉莉》、孟悟的《逃離華爾街》、董晶的《實驗室的風(fēng)波》等作品表達(dá)的是職場中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認(rèn)知和社會角色的評估。呂紅的《美國情人》、陸蔚青的《喬治競選》、余曦的《安大略湖畔》、陳思進(jìn)和雪城小玲的《心機(jī)》、抗凝的《金融危機(jī)600日》等都是涉及對居住國在政治選舉、法律體系、金融體系等基本社會制度方面的深度觀察的作品。黃宗之、朱雪梅夫婦的《破繭》《藤校逐夢》是對華人移民教育焦慮之下的中西理念碰撞和重塑的書寫。
四、反思和展望
新移民文學(xué)的發(fā)生是新移民群體對自己跨域生活經(jīng)驗的表達(dá),他們的創(chuàng)作“既有群體趨同性,更有內(nèi)部差異性”(12)黃萬華:《“出走”與“走出”:百年海外華文文學(xué)的歷史進(jìn)程》,《中山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9年第1期。,這使得新移民文學(xué)的面貌極為復(fù)雜,也因此對新移民文學(xué)的各種特質(zhì)、趨勢和發(fā)展階段的概括可能都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譬如,有的研究者闡釋新移民文學(xué)時常常會以鄉(xiāng)愁、漂泊等作為內(nèi)涵上的標(biāo)簽,對于移民文學(xué)而言,這通常是比較突出的文字底色。早期的華人移民由于歷史、政治的原因而追求落葉歸根,于是,在他們生活在異域的大部分時間里,身體安置在異國,靈魂卻始終不曾落地,而是處在隨時起身攜帶身體回歸故國的預(yù)備狀態(tài)。這使得相關(guān)的文學(xué)表述格外強(qiáng)調(diào)鄉(xiāng)愁與漂泊。這種表征不僅在19世紀(jì)中葉到20世紀(jì)前期的華人移民文學(xué)中存在,而且在以白先勇、於梨華等為代表的“臺灣留學(xué)生文學(xué)”中也是色彩濃烈的存在。但在新移民文學(xué)中,雖有許多文本、尤其是那些以新移民初抵異國的打工求生為主題的作品中彌漫著鄉(xiāng)愁和漂泊感,但更多作品的敘述立場是推崇落地生根的。新移民視移居國為“繼母”或者“養(yǎng)父”,努力成為所在國的模范族裔,努力融入所在國的文化,并使自己的子女成為主流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鄉(xiāng)愁和漂泊感總體上是不斷淡化的。在新世紀(jì)、特別是近10年以來,伴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蓬勃發(fā)展,地球村日益成為現(xiàn)實,曾經(jīng)由于空間分隔、通訊不便而被阻隔開來的世界各地的華人移民,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逐漸聚集形成虛擬空間中的各類社群。高度發(fā)達(dá)的通訊,早已將地球兩端連接得近乎無縫接合。在這種時代氛圍中,如果說鄉(xiāng)愁和漂泊感是新移民群體的共同精神屬性,恐怕是值得質(zhì)疑的。尤其是中青年作家,很多是最近10年之內(nèi)移居他國的,他們是互聯(lián)網(wǎng)改變世界的最直接受益者,而且由于持續(xù)性的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中國與發(fā)達(dá)國家之間的經(jīng)濟(jì)差距已經(jīng)大大縮小,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話語權(quán)也越來越強(qiáng),這都使得他們在移民之初已經(jīng)具有了更多的經(jīng)濟(jì)與文化自信,對于族裔文化與所在國的主流文化之間的共處有了更為通達(dá)的心態(tài)。但也不能否認(rèn),依然會有一部分人在體味著鄉(xiāng)愁與漂泊感。因為作家個體的生活方式是千差萬別的,既有很多“海歸”或“海鷗”呈現(xiàn)跨國生存狀態(tài),也有人身體“落地生根”在移居國,但精神通過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深度介入中國當(dāng)下現(xiàn)實生活,有可能“身在國家領(lǐng)土邊界之外,卻在想象的民族邊界之內(nèi)”(13)吳前進(jìn):《跨國主義的移民研究——?dú)W美學(xué)者的觀點和貢獻(xiàn)》,《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7年第4期。。當(dāng)然,也還會有一部分人維持雙向疏離狀態(tài),他們與所在國文化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認(rèn)知中的故國也凝固在離開的時刻。對后者而言,鄉(xiāng)愁與漂泊感也許是永遠(yuǎn)的個體情感。因此,漂泊與鄉(xiāng)愁的標(biāo)簽,對新移民作家而言是需要審慎地加以個體化區(qū)分的。所以,筆者觀察到的新移民小說主題嬗變的發(fā)生或許不是源于內(nèi)生性的、必然的循序漸進(jìn),不是絕對的階段性變化,而是由創(chuàng)作者的現(xiàn)實生活狀態(tài)而促發(fā)的。這些新的特質(zhì)并不會覆蓋、取代或超越之前的文學(xué)主題。尤其是對于華文寫作而言,幾乎永遠(yuǎn)是第一代移民在創(chuàng)作,必然始終存在著一些由遷徙而產(chǎn)生的相似情緒,也就必然始終在生產(chǎn)一些對這些情緒進(jìn)行具象化表達(dá)的作品,那也就很難擺脫一些常規(guī)的書寫模式。
新移民作家在異域空間中書寫,我們作為隔離在那個空間之外的研究者,最關(guān)注的是新移民群體如何立體地呈現(xiàn)自己的行進(jìn)歷史,如何為自己的異域生存和發(fā)展作證,如何傳達(dá)移民群體的生活況味,如何多維度呈現(xiàn)移民生活的粗糙和豐滿,如何捕捉移民群體中蕪雜而又生機(jī)勃勃的追夢之音,從而為華人/華文文學(xué)提供新的文學(xué)經(jīng)驗。這是新移民文學(xué)立身之所在,也是研究者研究的價值之所在。因此,在書寫的主題與敘事的風(fēng)貌上,新移民文學(xué)必然應(yīng)具有其獨(dú)有的特質(zhì),這是除了作者身份之外,我們判斷、界定新移民文學(xué)的依據(jù)。但是,在研究過程中,筆者也時常產(chǎn)生許多困惑與猶疑。我們所認(rèn)定的這些特質(zhì)是否經(jīng)得起推敲呢?從近年來的部分小說創(chuàng)作來看,它們在作品主題與敘事風(fēng)貌上幾乎與新移民文學(xué)別無二致。譬如南翔的《洛杉磯的藍(lán)花楹》、於可訓(xùn)的《移民監(jiān)》、唐穎的《上東城晚宴》,都是在美國發(fā)生的華人故事。《洛杉磯的藍(lán)花楹》是中國訪問學(xué)者與洛杉磯當(dāng)?shù)氐呢涇囁緳C(jī)之間的愛情故事和文化碰撞。《移民監(jiān)》是隨子女移居國外的老年華人移民在美國生活的精神不適與觀念解放。《上東城晚宴》雖然本質(zhì)上是一場都市中的情愛迷失,但通過短暫旅居在紐約的上海劇作家里約的視角所展開的紐約華人藝術(shù)家群體的生存百態(tài)卻被刻畫得入木三分。同時,隨著里約在紐約的漫游,紐約的咖啡館文化以及紐約這個世界藝術(shù)之都所特有的多族裔藝術(shù)家匯聚在一起而氤氳出的自由、頹廢和掙扎的迷離氣息也被描繪得極為精彩。這種傳神和精彩,我們很少在真正的新移民小說中讀到。從這幾篇作品來看,如果具備一些國外生活的基本經(jīng)驗,那么國內(nèi)作家創(chuàng)作的風(fēng)貌類似、甚至更具水準(zhǔn)的海外華人題材小說在描摹華人移民的生活質(zhì)感上是毫不遜色的。南翔與於可訓(xùn)都是教授作家,多年的文學(xué)研究賦予了他們足夠開闊的文學(xué)視野,南翔早前就已有《東半球·西半球》涉及移民題材。唐穎向來被視為當(dāng)代都市小說的重要作者,但通過她的非虛構(gòu)作品《與孩子一起留學(xué)》來看,她其實是在中國生活的“美國綠卡持有者”,或許可以算是一類特殊的跨國華人。與一般的華人移民在定居多年后“海歸”的歷程不同,她雖然早已擁有美國綠卡,但在陪同孩子留學(xué)之前,家庭生活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變化,一直定居在中國。《與孩子一起留學(xué)》所描寫的正是她作為陪讀家長與兒子一起面對“文化休克”的過程。但是,唐穎在此之前從未被視為新移民作家。如何界定其身份和創(chuàng)作,是一個令人有些困惑的問題。
在這種對照下,新移民作者如何體現(xiàn)出自己獨(dú)特的敘事立場呢?新移民小說作為中國當(dāng)代小說的特殊局部的特質(zhì)又該如何界定呢?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不過,新移民文學(xué)仍處在變化發(fā)展過程中,具有多種的生長可能。因此,這一疑問也許可以暫且擱置,留待觀察更好。隨著大批的新移民成為“跨國華人”,他們的跨域經(jīng)驗一定會更加豐富,移民可能只是他們“跨越國界流動的人生軌跡中的某一個停留點”,因為“跨國遷移可以是多次的、循環(huán)的和反復(fù)的”(14)[加拿大]郭世寶:《從國際移民到跨國離散:基于北京的加拿大華人研究的“雙重離散”理論建構(gòu)》,丁月牙譯,《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7年第3期。。在循環(huán)往復(fù)的遷移中,移民的多次文化沖突和對世界、對人性的探尋都應(yīng)該會形成更多、更新鮮的經(jīng)驗,進(jìn)入新移民文學(xué)的書寫領(lǐng)域。所以,跨國華人群體的擴(kuò)大,使得新移民文學(xué)賴以生長的土壤也將發(fā)生變化,新移民文學(xué)或許不會再是當(dāng)初異域時空下寂寞而熱忱的文字懷鄉(xiāng),而是在連通著多國時空的“第三文化”空間中縱橫捭闔的現(xiàn)代舞蹈。
同時,我們也需冷靜地看到,跨國華人在構(gòu)建“第三文化”空間時如果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識和開闊的精神境界,那么所謂“對兩個國家、兩種文化的同步嵌入”也可能只是表層的,是虛浮無根的,而雙向疏離卻會加深。譬如很多新移民作家的中國書寫多呈回溯式,對中國當(dāng)下現(xiàn)實生活的表現(xiàn)相對來說數(shù)量較少,通常是擷取了社會新聞中的片段敷衍而成。在這些片段背后真實的社會生活,作者其實缺乏感同身受的理解,一般是通過采訪、采風(fēng)等短暫的了解作為現(xiàn)實支撐。有些作品雖有大量篇幅是以當(dāng)下中國為背景的,但筆墨更集中于個人之間的情感糾結(jié)而非中國的煙火人生,有隔窗看景的視野局限。因此,在作品的寫作過程中,作者不自覺地還是會回到自己固定的精神理路上,并不是對現(xiàn)實真正的介入式觀察。如海嬈的《早安,重慶》、薛憶溈的《空巢》、張翎的《死著》等對中國現(xiàn)實生活有深度觀察和思考的作品仍屬少數(shù)。另一方面,新移民作家對所在國的介入式觀察和文化關(guān)切雖有很大推進(jìn),但也尚有局限。雖然新移民文學(xué)是所在國的族裔文學(xué),以族群的自我表達(dá)為主要的敘事追求,但作為移居者,理解所在國本土居民的思想脈絡(luò)、族裔沖突,關(guān)注人類的共同命運(yùn)、共同的情感訴求與共同的精神創(chuàng)傷也應(yīng)是新移民作家寫作的價值旨?xì)w。以“9·11”事件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群體性創(chuàng)傷事件,但在美國華人移民作家的筆下極少得到深刻的展現(xiàn),他們在作品中涉及這一事件時,通常的關(guān)聯(lián)的方式是設(shè)置一個情人、伴侶或朋友,用他/她死于“9·11”來完成主人公的一次情感歷程,或者將作品中的某個人物死于“9·11”作為主人公人生選擇發(fā)生重大改變的契機(jī)。在新移民文學(xué)中,不曾產(chǎn)生一部類乎《特別響,非常近》這種深刻表達(dá)“9·11”創(chuàng)傷體驗的作品。這是部分新移民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疏離于所在國現(xiàn)實生活的一個折射。
這種在一定范圍內(nèi)存在的雙向疏離、雙面滑脫的狀態(tài)提示我們,跨國華人構(gòu)建“第三文化”的過程是復(fù)雜的,是朝向多種可能性的,從目前新移民文學(xué)的發(fā)展現(xiàn)狀來看,與社會學(xué)家、移民史研究學(xué)者從政治、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中得到的對移民的觀察未必完全一致。如何認(rèn)知和理解新世紀(jì)以來的新移民文學(xué)仍是需要持續(xù)追蹤和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