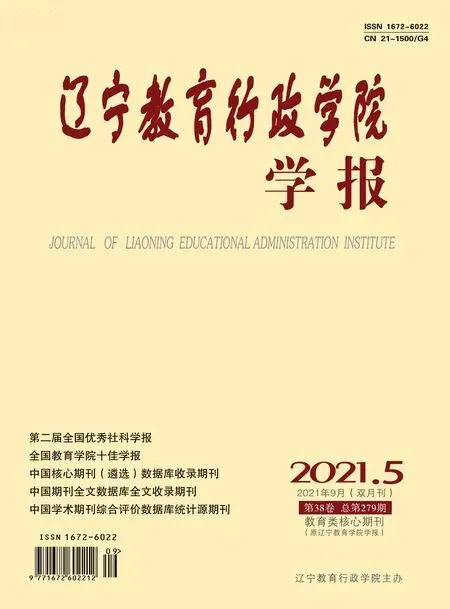我國與歐盟刑事司法合作中附條件引渡模式初探
栗 崢
(沈陽師范大學 法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2018年11月,我國從保加利亞引渡回在逃13年的姚錦旗,這是我國首次從歐盟國家引渡涉嫌職務犯罪的嫌疑人,標志著我國與歐盟國家在打擊職務犯罪方面的司法合作進一步深入。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條約數據庫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4月,我國與8個歐盟成員國的引渡條約及與13個歐盟成員國的司法協助條約已經生效[1]。近年來,從打擊普通的跨國犯罪,到懲治嚴重的國際罪行,我國與歐盟及其成員國的刑事司法合作越來越密切。
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引渡,同時還有驅逐和遣返等模式。引渡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司法合作形式,是以條約和互惠為原則和基礎的。引渡是指“一國的主管機關應他國主管機關的請求,將在本國境內被他國指控犯罪或判刑的人交給請求國審判或處罰的國際司法協助行為”[2]。隨著世界上廢除死刑的國家越來越多,“死刑犯不引渡”逐漸成為各國在審查引渡申請時適用的原則。同時,越來越多保護被請求引渡人基本權利的內容,體現在引渡相關的國際法律文件和國家實踐中,成為被請求引渡的國家拒絕引渡的強制性或任擇性理由。這樣的實踐,對于我國與歐盟的刑事司法合作模式建立及我國量刑承諾制度的完善有重要的影響。
一、我國與歐盟成員國家的刑事司法合作概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條約數據庫的記載,截至2021年4月,我國與8個歐盟國家簽訂的引渡條約已經生效。這8個國家分別為保加利亞、法國、立陶宛、羅馬尼亞、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時[1]。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于2000年12月28日起實施。《引渡法》中對被請求引渡人基本權利保護的內容主要在第八條第4款、第7款、第8款和第九條第2款中有所規定。(以下簡稱《引渡法》)實施后,第一個生效的我國與歐盟國家簽訂的引渡條約為2007年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班牙王國引渡條約》②我國《引渡法》實施前生效的引渡條約有兩個,是分別與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簽訂的引渡條約,而彼時,這兩個國家尚未加入歐盟。立陶宛與我國引渡條約生效雖然是在我國《引渡法》實施之后,但立陶宛在條約生效時也尚未加入歐盟。。
(一)引渡條約中拒絕引渡的強制性規定
我國與歐盟及其成員國簽訂的引渡條約中,規定了保護被請求引渡人基本權利的強制性條款。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死刑犯不引渡”的強制性規定
對比2007年前后,我國與歐盟成員國簽訂的引渡條約中保護被請求引渡人基本權利條款,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關于“死刑犯不引渡”的內容。2007年之前的引渡條約中未將“死刑犯不引渡”作為強制性或任擇性條款。而2007年之后,我國與歐盟國家的引渡條約中,有直接③我國與西班牙的引渡條約第三條第8款中規定了“死刑犯不引渡”的強制性條款:“根據請求方法律,被請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被判處死刑”時,應當拒絕引渡,“除非請求方作出被請求方認為足夠的保證不判處死刑,或者在判處死刑的情況下不執行死刑”。2015年生效的我國與法國的引渡條約中也有措辭相同的“死刑犯不引渡”條款。和間接④我國與葡萄牙的引渡條約第三條第8款規定:“執行請求將損害被請求方的主權、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其他重大公共利益,或者違背其法律的基本原則”時,應當拒絕引渡。我國與意大利的引渡條約第三條第7款也有類似的規定。根據歐盟法律和兩國的法律,這種規定雖然沒有直接規定“死刑犯不引渡”,但是基本上排除了死刑犯被引渡的可能性。兩種方式體現了“死刑犯不引渡”原則。
2.“可能遭受酷刑和非人道待遇不引渡”的強制性規定
我國與意大利的引渡條約第三條第6款規定⑤《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意大利共和國引渡條約》第三條第6款。:“如有充分理由相信,被請求引渡人在請求方就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曾經遭受或者可能遭受酷刑或者其他殘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處罰”,應當拒絕引渡。
3.“缺席審判不引渡”的強制性規定
我國與西班牙、法國及葡萄牙的引渡條約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班牙王國引渡條約》第三條第7款、《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法蘭西共和國引渡條約》第三條第6款、《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萄牙共和國引渡條約》第三條第7款。中,都有“請求方根據缺席判決提出引渡請求,并且沒有保證在引渡后重新進行審理”的情況應當拒絕引渡的規定。
(二)引渡條約之外的救濟制度
打擊有組織跨國犯罪需要一種充分尊重基本權利的司法合作模式,但也必須有效。拒絕引渡因可能侵犯基本權利而犯下嚴重罪行的人,幾乎等同于宣告被請求引渡的人無罪。這種合作模式顯然違背了打擊犯罪的最基本利益,因此是不可取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引渡法提供了兩種選擇:“或引渡或起訴”⑦“或引渡或起訴”原則在引渡法中往往被用于解決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帶來的管轄權上的問題,與國際刑法中的普遍管轄權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和附條件引渡。
1.“或引渡或起訴”原則的適用困難
根據“或引渡或起訴”的原則,拒絕引渡的國家必須承諾對被拒絕引渡的人進行起訴,如果在請求國已經作出裁決,則必須承諾在其監獄系統中執行裁決。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大部分證據和證人都在被拒絕引渡的請求國。雖然可以通過新的司法協助請求提供證據,但常常存在國家拒絕合作的情況。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開始審判也有侵犯被起訴人基本權利的危險,隨后,當收集到足夠的證據時,可能會由于“一事不再理”原則,新的審判無法進行。“或引渡或起訴”原則雖然在理論上行得通,但是在實踐中較少應用,效果也不甚理想。因此,附條件引渡被視為更好的選擇。
2.附條件引渡及量刑承諾的適用優勢
附條件引渡是指“被請求引渡的國家在同意引渡請求的同時,要求請求國承諾一定的條件,保證在引渡后實施或不得實施某種行為的引渡活動”[3]。歐洲的附條件引渡模式已經在兩個領域內發展:死刑定罪和缺席審判。在司法合作領域,不判處或不執行死刑是最直接的條件。在歐盟國家內部的司法合作中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國家通常會允許移交本國國民或居民,附帶條件是他們隨后被遣返服刑。外交法和引渡法傳統上都包含關于禁止的待遇的所謂外交承諾,在我國,此種外交承諾也被稱為量刑承諾。
附條件引渡中的外交承諾是指請求引渡的國家的外交部門在進行司法合作的外交活動時,對被請求引渡國同意引渡后,保證被請求引渡人基本權利的承諾。從國際法來看,外交承諾是國家行為,對做出承諾的國家有拘束力。
二、我國與歐盟國家附條件引渡合作中的量刑承諾實踐
我國《引渡法》的第50條規定了量刑承諾問題:“被請求國就準予引渡附加條件的,對于不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可以由外交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被請求國作出承諾。對于限制追訴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于量刑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在對被引渡人追究刑事責任時,司法機關應當受所作出的承諾的約束。”該條規定了量刑承諾的前提是附條件引渡;承諾的條件是不損害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承諾的決定主體是最高人民法院;承諾的性質是外交承諾,具有國際法拘束力。
歐洲人權法院對歐盟成員的附條件引渡采取逐案審查的方式,會根據每個案件的情況做出具體的承諾。我國在與歐盟成員的附條件引渡合作中,在堅持國家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應厘清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承諾保護基本權利的范圍有何限制;第二,是否接受被請求國履行承諾的監督及監督的方式。
(一)承諾的內容和范圍
歐洲人權法院處理過量刑承諾相關案件并做了一些重要裁決。在這些裁決中,法院解釋了一個當存在或可能存在死刑或禁止待遇時適用的,相當復雜的引渡相關量刑承諾標準。關鍵問題除了犯罪嫌疑人是否會被判處死刑之外,還包括犯罪嫌疑人是否會遭受酷刑等殘忍和非人道的待遇,訴訟權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請求國能否保證被請求國對于案件進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等問題。
1.承諾的內容
我國與歐盟的附條件引渡中,量刑承諾的內容可以包括“不適用死刑”的承諾、“禁止酷刑”的承諾及程序性權利承諾。
(1)“不適用死刑”承諾
在歐洲人權法院對威尼斯案①Venezia(decision No.223/1996,27 June 1996).意大利憲法法院推翻了《1983年意大利與美國引渡條約批準法》(包括有條件引渡條款)和《刑事訴訟法》第698條。理由是,涉及死刑的有條件引渡與1947年《憲法》第27條所隱含的明確禁止死刑的生存權相悖,因此即使美國政府做出了承諾,仍然不能引渡。得出這一結論有兩個理由:第一,因為該條約對美國政府有效地確保被請求引渡的個人不會被執行的能力提出了懷疑;第二,由于條約和意大利法律在審議擔保是否充分時授予司法部長自由裁量權。這種自由裁量權被認為與生命權不相容。的裁決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只有在絕對、毫無疑問地保證不實施死刑的情況下,才可能對死刑案件進行有條件引渡。任何不確定性,無論其程度如何,都應導致拒絕引渡。可以預見,我國與歐盟成員國的量刑承諾中,“不適用死刑”承諾會是實現引渡的前提條件。是否做出“不適用死刑”承諾應該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權衡之后做出。例如,在一些跨境追逃案件中,承諾“不適用死刑”有利于維護國家經濟利益,打擊犯罪。因此,在與歐盟國家的附條件引渡中,“不適用死刑”承諾通常會被視為絕對必要條件,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2)“禁止酷刑”承諾
在阿爾穆阿亞德訴德國案①Al-Moayad v.Germany(2007)阿爾穆阿亞德是一名與也門政府關系密切的伊瑪目,美國要求從德國引渡他。美國保證他不會被非軍事法庭起訴,也不會受到折磨。中,歐洲人權法院公開表示,它擔心“美國官員的審訊方法與歐洲公約第3條的標準不符”,但該案由于阿爾穆阿亞德在被引渡后將被拘留在美國,這在評估酷刑風險時可以被合理地認為是在待遇方面極小的差別。因此,本案的被請求引渡人被同意引渡到美國。比較“不適用死刑”承諾和“禁止酷刑”承諾,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在權衡酷刑的風險、監獄系統的狀況或請求國的保證時,歐盟國家被允許一些自由裁量,而不像對待死刑不引渡規則那樣絕對。我國批準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禁止酷刑承諾與我國保護人權立場相符,不存在任何的沖突,因此對此條件應積極承諾。
(3)程序性權利承諾
當被請求國認為存在侵犯正當程序權利的風險時,可以在特定擔保下準予引渡,例如,具有完全程序性和實質性權利的新審判。這也適用于對監獄系統狀況有疑問的情況:在允許定期探訪的情況下,該人可以被移交。此種承諾與前兩種承諾相比,并不是絕對必要條件,我國在進行此內容的承諾時,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被請求的國家的要求進行承諾。
2.承諾所涉具體權利的范圍
如果司法合作建立在請求國要與被請求國執行相同的人權標準的前提下,司法合作就會被嚴重束縛,甚至在實踐中無法實現。另外,要求在司法合作中,人權標準統一相當于使區域性人權法院承諾會給國家在建立、解釋基本人權核心方面做出讓步變成一紙空文。通過司法合作向其他國家施加一個特定的基本權利標準,如果過于絕對,會影響到國家間的友好關系。因此,我國在從歐盟國家附條件引渡時應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在不屬于絕對條件的領域與歐盟國家進行談判,對于沒有依據的無理要求應該拒絕。
(二)履行承諾的監督及監督的方式
歐盟及其成員國在輸出其保護被請求引渡人基本權利的理念時,會出現審查外國司法制度的情況。對于其判定的司法制度不完善的國家,歐盟往往會拒絕引渡,即使對方已經做出承諾。歐盟及其成員國的一些持“人權至上”理念的人會認為,向司法制度“落后”的國家派遣的“公正觀察者”可以充當一種有助于本國法官發展訴訟程序的“法庭之友”。同時,有些國家的法官認為,如果外交官、司法合作國的法官、非政府組織或任何其他類型的公正觀察員能夠在刑事審判期間出席,附條件引渡的執行和監督將變得簡單。
我國在與歐盟國家做出量刑承諾的時候,應警惕上述觀點中可能干涉我國司法管轄權的條件。對于符合國家利益和案件情況的,在平等基礎上的監督可以承諾,而對于干涉司法獨立權的條件應該堅決拒絕。
(三)我國已有成功案例實踐
在“賴昌星遣返案”中,承諾包含了允許加拿大方面在其服刑期間探視的內容[4]。后續實踐中,我國嚴格遵守了不判處死刑的承諾,依法對賴昌星進行公正審判,充分保障賴昌星的訴訟權利,允許加方在賴昌星服刑后去探視等[4]。
“黃海勇引渡案”中,我國對秘魯政府所做出的承諾不僅包括不判處死刑的承諾,還包括不會遭受酷刑等非人道的待遇的承諾,保障外逃人員充分享有的訴訟權利的承諾,被引渡人在執行刑罰的時候享有醫療服務的承諾,在案件審判的時候邀請被請求國參加庭審的承諾及對于案件執行情況進行監督的承諾等[5][6][7]。
上述與外國司法合作的成功實踐雖然不是發生在我國與歐盟之間,但是通過實踐表明,中國具有較為完善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國政府信守承諾、言出必行。
三、結語
綜上所述,歐盟已經建立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模式,在引渡和附條件引渡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中對我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引渡條約在打擊我國與歐盟成員國之間跨國犯罪方面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附條件引渡是歐盟及其成員國引渡條約之外的首選方式,鑒于量刑承諾在附條件引渡中的決定作用,量刑承諾必須以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為中心,在堅持國家主權的基礎上,權衡利弊,對量刑承諾的內容根據個案的情況逐步厘清,同時,對可能出現干涉司法權的不恰當要求應該拒絕承諾。量刑承諾有助于我國同外國的司法合作,有助于懲治犯罪,發揮法律的震懾作用。雖然目前量刑承諾制度不夠完善,但是隨著國家與外國的相關司法合作活動的增多,以及相關理論的發展,量刑承諾制度會日漸完善,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