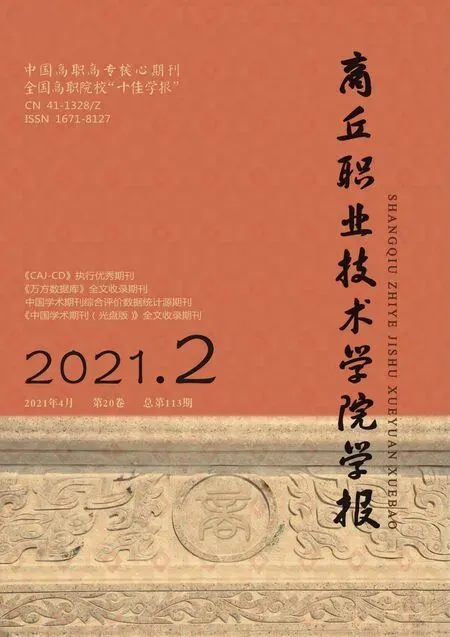《燦爛千陽》中的女性創傷研究
李可心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0)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從美國民權運動中分離出來并得到蓬勃發展,同時婦女和兒童遭受的暴力、虐待、強奸等創傷以及婦女和兒童的權益保障,成為女權政治主旋律。”[1]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創傷不僅成為社會中的一個熱點,而且成為文學中一個重要的題材。在《燦爛千陽》這部小說中,歷經人生苦難的胡賽尼把女性創傷作為一個創作主題,以悲憫的情懷書寫了阿富汗女性在成長的過程中所承受的痛苦與傷害,并對女性用何種方法走出、實現自我做出了思考,對第三世界女性給予深切關懷與同情。這也是胡賽尼作為一個文學家對社會所做的努力與貢獻。
一、殘酷的成長之傷
人們在成長的旅途中會遇到各種問題,當這些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主題時,就幻化成一個個變化莫測的人生之旅。與生俱來有著纖細柔美特征的女性,在成長的旅途中更容易受到傷害[2]。這些傷害可能來自童年的不幸,也可能來自宗教與社會的壓迫,而這些傷害所造成的身體和心理上的創傷是難以磨滅的。那些悲慘的記憶時時在夢魘中纏繞,令人難以逃脫。
(一)來自家庭
童年是生命的起點,對一個人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人們在童年遭到的傷害,尤其是情感上的冷暴力,都極其容易給自身留下難以治愈的創傷。父母是孩子獲得關愛和保護的重要保障,因此,他們給孩子造成的傷害則是最直接的,破壞性是最大的。
瑪麗亞姆的出生就不被父親和世人所認可,她是“哈拉米”(私生女),她沒有一個完整的家。母親的辱罵和離世,讓她沒有得到過母愛的滋養;父親的拋棄讓她對親情絕望 、跌入深淵。這些來自家庭的傷害是帶有毀滅性的,尤其是父親最后的拋棄,直接導致了瑪麗亞姆的悲劇。為“抹去父親最后的恥辱”,剛剛失去母親的幼小的瑪麗亞姆被迫嫁給一個年長的從未謀面的異鄉人。在阿富汗這樣的父權制社會,她是父親的私有財產,是一件廉價的“商品”,唯獨不是一個“女兒”。趙冬梅曾提到,“早期的受虐經歷能夠影響甚至阻礙一個人發展穩定的自我感覺。”[3]創傷者會失去對家庭、友誼以及對共同體的依賴,打碎了在與他人關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建構,與他人隔離成為其心理創傷的核心經驗[4]。瑪麗亞姆面對丈夫的暴行,她選擇了沉默,變得少言寡語,癡呆抑郁,她的主體已死,變成“陰暗的閣樓”中一個落滿了灰塵的無用的擺設。因為童年的不幸,她不得不在孤立無助中獨自承受著沉重的身體傷害和殘酷的心靈劫難,這一切使自卑深入骨髓,最終導致了她失去了青春年華,過早地老去。
(二)來自宗教
《燦爛千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表現了阿富汗所特有的文化共性。阿富汗信仰伊斯蘭教,信奉《古蘭經》,認為其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阿富汗,有很多女性從生命的開始到生命的終結都處在男人的掌控之下,沒有自由可言,陷入一個又一個的泥潭里。
《古蘭經》保留了一夫多妻制,這種傳統的延續使婦女在兩性關系上處于被動地位,她們大多數是男人的附屬品,沒有獨立性可言。拉希德把瑪麗亞姆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房子里面是瑪麗亞姆的唯一可以活動的范圍。即使他帶著瑪麗亞姆出去,也要讓她戴上卡布。卡布就是對女子身份的一種抹殺,是男權意識對女子主體意識的一種剝奪。卡布就像一個隱身衣,把婦女隱藏起來,使她們的私人空間進一步壓縮,只剩下卡布里稀薄的空氣。戴上卡布的瑪麗亞姆看不到前面的路,只能跟著丈夫小心翼翼地前行,行動完全由丈夫指揮。面對六次流產,瑪麗亞姆堅信這是真主對自己的懲罰,在面對拉希德的暴力的時候,她一邊承受著身體上的傷痛和失去孩子的巨大心理創傷,一邊還要卑微地請求丈夫的寬容,默認丈夫的再娶。除此之外,國家與法律也保護男性的權利。當有婦女反抗,那些警長只會說:“一個男人在家里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政策規定我們不會干涉家庭的私事。”女性一旦逃跑,則會受到嚴厲懲戒,處以極刑。
(三)來自戰爭
從1973年到2001年,阿富汗戰亂頻繁,國家動蕩不安,人們每天生活在爆炸聲中,每天都在等待命運的審判。作品中有很多地方都寫到了這場戰爭,但不像諸多紀實小說對沖突事件的直面表達和詳細的敘述那樣,作者則用側影、印象等書寫手法勾勒出戰爭的丑惡面貌:“他們的影子在墻壁上移動。呼嘯聲,接著是爆炸聲……在一片哭喊聲和嗆人的煙霧中,有人正在掙扎地爬出來,瘋狂地用雙手去扒一堆廢墟,從里面將他們的姐妹、兄弟或者子孫拉出來。”[5]戰爭會奪去無數人的生命,會使人們喪失美好的感情,會留下無盡的罪惡與傷痛。
殘酷的戰爭奪去了萊拉父母的命,讓她所愛的人都離開了她。一夜之間,什么都成了灰燼,只留下她和腹中的孩子。在拉希德的欺騙下,為保護腹中的孩子,正值芳華的她不得不嫁給年老丑陋的拉希德,不得不成為拉希德的傳宗接代的工具,忍受著身體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
戰爭留給人們的創傷永遠都不會消失,就算逃離,心中的傷疤還會時時作痛,夢魘還會時時纏繞。死去的人永遠被埋在黑暗的地下,活著的人承載著傷痛艱難地茍活著,美好的生活在炮火之中變得破敗不堪,不能復原。
二、走出創傷,因愛綻放
(一)寬厚的母性
胡賽尼在極大程度上真實地再現了女性在殖民統治、階級統治和性別壓迫三重控制下所承受的創傷,對她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時,又賦予她們博大的母性,以治療她們所受的創傷。作者同情悲苦又頑強的瑪麗亞姆、羸弱又勇敢的萊拉。作者深情地關懷著這些孱弱身軀所承受的創傷與疼痛,竭力表現其血肉之中所蘊含的綿綿不息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是女性與生俱來的母性,正是這種強大深沉的母性,讓那些在創傷中苦苦掙扎的女性得以復原,重新找到自我。
為了保全腹中的孩子,萊拉屈辱地嫁給了拉希德。婚姻的不幸并沒有使她自我覺醒,但是,母性卻讓她的反抗意識覺醒了。她不想讓自己的女兒阿茲莎重蹈覆轍,于是,她第一次堅定了逃跑的打算。而阿茲莎的出生也讓瑪麗亞姆嘗到了做母親的幸福,讓她感受到了被人需要、被人愛的幸福與喜悅。面對失去心愛的人的煎熬,她們的反抗意識高漲,當拉希德再次向她們實施暴力的時候,她們選擇了反抗。尤其是瑪麗亞姆,她給了拉希德致命的一擊,即使她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她也無怨無悔。
瑪麗亞姆和萊拉的身上有著地母般的無私之愛。正是這種博大深沉的愛,讓她們擁有了承受沉重的苦難和撫平無盡的創傷的巨大力量。母性,因為至柔,所以至剛。
(二)傾聽與訴說
萊拉和瑪麗亞姆是兩個活在男性社會和帝國主義社會的底層女人,她們慘遭男性的欺壓。尤其是瑪麗亞姆,她將自己囚禁在陰暗的閣樓,封閉的空間隔絕了外界的一切,在這無盡的黑暗與孤獨中,她得不到任何的支持和援助,獨自孤獨地咀嚼著內心細碎的傷痛。隨著一次次的傾訴,兩個傷痕累累的靈魂在黑暗中慢慢地靠近,最終她們成為各自靈魂中重要的支柱。在一次家庭暴力中,萊拉救了瑪麗亞姆,利用這次契機,再加上阿茲莎對瑪麗亞姆的感化,她們互相傾訴那些爛在心中的丑陋的秘密,從此以后,兩個人就成了堅定的靈魂同盟。按照埃里克康的說法:“那些本來毫無瓜葛,但是卻有過創傷經歷的人找到對方,依賴這個共同紐帶的力量結成了某種伙伴關系。”[6]瑪利亞姆在訴說的過程中,逐漸地認識到自我,并對自我進行了重新的認識與判斷,從而主體意識開始蘇醒。
萊拉和瑪麗亞姆在相互講述過程中舒緩了焦慮情緒,釋放了壓抑情緒,精神困擾得到解脫。同時,在講述與傾聽的過程中,作為講述者的瑪麗亞姆和作為傾聽者的萊拉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情感關系。兩個孤寂的靈魂在傾訴中漸漸地靠近,成為彼此的依靠,傷口開始逐漸愈合,奄奄一息的“向陽花”重獲新生,燦爛綻放。
(三)純潔愛情
萊拉和塔里克的純潔愛情是黑暗中的一縷陽光,照亮了生命的晦暗的一角。即使戰爭奪去了年幼的塔里克的一條腿,但堅強的他依然是萊拉的勇士,為她驅散陰霾。“為了你,我會開槍殺人的,萊拉。”即使肩負的責任讓塔里克不得不離開萊拉,可是他卻堅定地告訴萊拉:“我一定會回來的。”塔里克給了萊拉一個活下去的希望——孩子。當多年前的陰謀被揭發:塔里克并沒有死,萊拉忽然感覺世界明亮了。看到塔里克的一瞬間,萊拉心中產生了“一絲不計后果的希冀”。女性是感性的,她們渴望純潔美妙的愛情,她們可以勇敢地為自由與幸福而戰。在小說的最后,塔里克一直陪在萊拉的身旁,給予她鼓勵與安慰。正是這份純潔的愛情成了萊拉在黑暗的日子里的一束光,支撐著她走出陰暗,擁抱光明,最終得到了救贖和幸福。
愛,存于內心。任何生命都需要愛,愛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和人發展的本質力量。“創傷導致了心靈的傷害”,而純潔的愛情則可以成為彌補心靈傷害的精神力量。
(四)寬容與寬恕
寬容是伊斯蘭教的基本精神。瑪麗亞姆在幼年時受到了老毛拉的教誨,老毛拉向她灌輸的《古蘭經》中所倡導的寬容精神一直影響著瑪麗亞姆。在面對最終處決的時候,瑪利亞姆果斷地選擇一個人承擔所有責任。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與幸福,她突然發現: 一個被父親視為恥辱的“哈米拉”,一個被丈夫欺凌的婦女,卻在生命的終點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得到了夢寐以求的自由與幸福,終于可以像一個“人”了。她不會埋怨世界的不公,她會感謝世界給予她的最后的快樂時光。她的身上有著人性中不可磨滅的善良,她堅強而美麗。萊拉最終也寬恕了曾經傷害過他們的人,當她再次回到喀布爾,回到瑪麗亞姆小時候住過的石頭小屋,看到扎里勒寫給瑪麗亞姆的信,看到了那遲來的道歉與懺悔時,她釋然了。同時,她也看到了生命力的頑強。萊拉已經拋開一切新仇舊恨,創傷也在逐漸地復原。唯有寬容他人,寬恕他人,才能忘記傷痛,撫平傷痕,獲得新生。
生命的長河中雖然會遇到悲傷與痛苦,但每一個悲傷的后面緊接著就是希望的誕生。美麗的心靈會永遠如太陽般溫暖,就和題目“燦爛千陽”一樣。
三、獨特的創傷敘事
“創傷文學通過創傷敘事再現創傷事件。創傷文學充分利用創傷對人的心理影響力,以創傷為媒介創作出更觸動心弦的作品。”[7]沒有力量也要創造力量,人們為之嘆為觀止,這是文學性創傷敘事藝術手段方面的目的,也是文學作品構思、情節安排、人物塑造方面的目的。
(一)復線結構
《燦爛千陽》中運用復線結構,即瑪麗亞姆和萊拉的雙線敘述,構成了一種重復。同一語言結構的重復可以引導讀者有意識地去思考其背后的隱含意義,從而體會小說中的深層韻味。復線結構既能夠使故事情節更加豐富,也能夠使人物的情感更加飽滿,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立體,更加貼合現實。
在小說中,有兩處的重復對照體現了作者的用心。一是在第三部分中,瑪麗亞姆回憶父親來找她的情景:“他在那站了好幾個小時,等著她,不時呼喚她的名字,就像她曾經在他的屋子外面呼喚他的名字一樣……隔著窗簾的縫隙,他們的目光相遇了。”這個情景和第一部分中“幼小的瑪麗亞姆獨自一人翻過山坡去見父親卻被擋在門外,在門外蜷縮著過了一夜,在被迫離開的時候卻和藏在窗簾后面的父親目光相遇了”的故事情節相呼應。這一前后細節的對比使扎里勒對瑪麗亞姆所造成的巨大的創傷及其愧疚之情更加真實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二是在第三部分中,瑪麗亞姆再次觀察拉希德的外貌:“他的頭發已經灰白,但依然和過去一樣粗硬……他依然有著寬厚的肩膀……和一個比他身體的其他任何部位先進入房間的隆起的腹部。總的來說,瑪麗亞姆覺得這些年來自己衰老了不少,相比之下,他的情況好得太多了。”這兒的拉希德和她第一次在“婚禮”上見到的拉希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時的瑪麗亞姆才十幾歲,拉希德已四十多歲。通過這兩個情節的對比,讀者能夠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瑪麗亞姆婚后的不幸,巨大的傷痛讓她過早地衰老,從一個懵懂的女孩直接跨越到了老婦人,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她都沒有經歷過。這種寫法能夠讓讀者自己走進人物,真實地品味其傷痛。
(二)第三人稱內視角轉換
第三人稱內視角將視線聚焦到某個人的身上,以他的視角來展開敘事。他作為敘述者的視角受到了角色身份的限制,這種限制造成了敘述的主觀性,不能敘述本角色所不知的內容,但也造成了身臨其境的真實感。而第三人稱內視角的轉換,可以使敘事者的思想自由轉換,從而可以突破敘事視角的限制,使故事情節更加豐富多彩。
以小說第三部分為例。第27章,以瑪麗亞姆的視角敘述萊拉被救的過程,她被迫去照顧受傷的萊拉,對萊拉的求救選擇忽視,兩人都緊閉心門,尤其是瑪麗亞姆。第28章,視角轉換到了萊拉,主要講述了萊拉在接到心愛的塔里克“去世”的噩耗后心靈所承受的巨大傷痛。第29章,視角又轉換到了瑪麗亞姆,她觀察到拉希德娶萊拉的真正目的,但她無力改變,一次次的暴行在她羸弱衰老的身軀上早已留下了太多的傷疤,她的內心已支離破碎,生命的花還沒有來得及綻放就早早地被掐掉。同時,通過瑪麗亞姆的視角,讀者會有一個疑問:為什么之前強硬的萊拉會答應嫁給拉希德,是否有隱情呢?隨后的第30章就以萊拉的視角講出了原因:為了保護胎兒,她不得不嫁。萊拉自我犧牲的悲痛和其在瑪麗亞姆視角中堅強的形象相互映襯,加深了其創傷。而萊拉答應嫁給拉希德的決定也加深了瑪麗亞姆的創傷,她不得不接受丈夫的再娶,兩個活在“地獄”的女性因為各自傷痕累累、早已衰弱的心而敵視對方。接下來的第31章,就通過瑪麗亞姆的視角來展現萊拉帶給她的不幸以及其對萊拉的敵對。
第三人稱人物視角的轉換,可以多角度、多層次地呈現人物的創傷心理,帶給讀者更好地讀書體驗。胡賽尼在講述拉希德娶萊拉這一事件的時候,不僅深入詳細地展現了兩位女性的內心創傷及其逐漸加深的過程,還真實地再現了兩位女性由于種種原因所造成的隔膜,以及相互敵對的情景。同時,這個事件也是兩人走出創傷、獲得新生的契機。在瑪麗亞姆被拉希德暴打的時候,萊拉在他的拳腳下救出了瑪麗亞姆。敘事視角的轉換,讓兩個人心底里的善良更加直觀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而這是第一敘事視角很難做到的。在整部小說中,第三人稱內視角的轉換不僅體現了作者在敘事結構上的精心設計,又豐滿了瑪麗亞姆和萊拉這兩位創傷人物的形象,彰顯了小說的創傷主題。
(三)敘事空間的變遷
在小說的敘事結構中,主人公活動空間的變更是了解人物內心活動的一個重要線索。小說中敘事空間的變遷,常常可以起到推動情節的發展和深化主旨的作用。而“榮格認為,對創傷經歷的正常的心理反應是從受傷的場景中退縮。在文學作品則表現為:創傷主體對創傷事件發生地點的逃離”[8],但是,在創傷沒有復原之前,創傷記憶會一直如影隨形。敘事空間的變遷使創傷記憶的延遲性得以呈現。
在小說中,瑪麗亞姆的活動空間軌跡為遠離村莊的泥屋——父親扎里勒的大房子——丈夫拉希德的小房子——監獄,而萊拉的活動空間軌跡則是喀布爾的家——拉希德的小房子——穆里——瑪麗亞姆幼年住過的泥屋——喀布爾。從瑪麗亞姆的活動空間軌跡來看,她一直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創傷性經歷的幸存者往往會選擇“封閉的地域空間以躲避創傷”[9],瑪麗亞姆一度覺得躲在閣樓會很舒服,這是她潛意識中對創傷的規避。拉希德的小房子作為小說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空間,象征著阿富汗強大的根深蒂固的男權,是男性欲望投射的客體。瑪麗亞姆最終以最決絕的方式離開了這個囚禁她傷害她的狹隘空間。瑪麗亞姆在狹小的監獄里度過了最后的時光,監獄似乎是另一個“石頭屋”,從生命的開始到終結構成了一種巧妙的重合。而在這狹小的監獄中,瑪麗亞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寧靜和滿足,這也意味著創傷在這里得到了復原。歷經痛苦的瑪麗亞姆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走出了創傷,找到了自我。
萊拉的活動空間軌跡的起點和終點都是喀布爾,這種重復既是創傷治愈的過程,也是生命的循環。當萊拉再次回到故鄉喀布爾,感覺很奇怪,發現這座城市已經變了,人們在種樹苗,蓋新房子,把鮮花插在火箭彈的空彈殼中,這座城市已經抹去了被戰火焚燒的傷痕,煥然一新,身上流淌著新鮮的血液,朝氣蓬勃。這帶給了萊拉極大的震撼與安慰,這座煥發著生機的城市象征著那些從戰火中、從創傷中走出來的傷痕累累但不失希望的人們,他們在努力地生活,努力地迎接未來。
四、結語
《燦爛千陽》沒有華麗的語言,沒有宏大的敘事框架,但是卻將故事敘述得扣人心弦,耐人尋味。本文從女性創傷的角度對《燦爛千陽》的創傷主題和創傷復原進行了分析,并且結合創傷敘事對小說做了研究探討。
創傷人物的經歷可以使讀者更深入地了解阿富汗民族的創傷,這也反映出作者的創作動機。阿富汗是作者一直牽掛的故鄉,她一直試圖用文字來探索故鄉當下困境的原因,并且試圖尋找故鄉人走出創傷的方法。創傷復原的過程,也是自我救贖、自我成長的過程。如同瑪麗亞姆和萊拉,她們承受了太多的苦難,她們也會在黑暗中迷失方向,但是她們依舊會向往光明,會像向陽花那樣努力地生長,并等待著綻放的那一刻。除此之外,作者擅長使用多種敘事方法來彰顯創傷主題,這也使小說感人至深,讓讀者對女主人公的創傷經歷感同身受。治療的探尋,能夠給那些正在創傷中苦苦掙扎的讀者指引道路,這也是胡賽尼本人創作的魅力和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