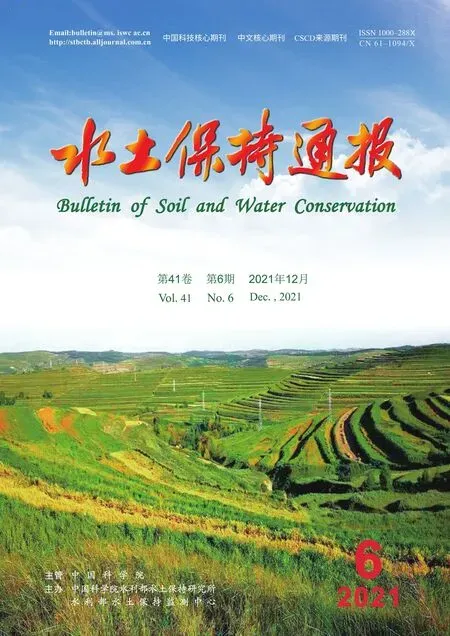三峽庫區重金屬含量空間分布及污染狀況
郭宜薇, 丁文峰, 朱秀迪, 崔 威
(1.長江水利委員會 長江科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10; 2.水利部 山洪地質災害防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10; 3.長江水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 湖北 武漢 430051; 4.河海大學 水利水電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8)
重金屬具有不易降解的生化毒性、累積性、持久性和遷徙性[1],而河流生態系統的重金屬污染更具有隱蔽性和潛在性,不僅會對水域生態環境造成影響,降低沿岸土壤中微生物的數量與酶的活性從而對土壤的地吸收代謝產生抑制,還可直接或間接進入食物鏈,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2]。在研究河流健康方面我國起步較晚,早期多將重點放在研究河流的化學污染上,近年來,河流生態系統的健康問題越來越受關注[3],劉昭[4]、黃宏偉等[5]分別針對清江流域和漓江流域運用USEPA水環境健康風險評價模型對水體重金屬污染機理和風險評估開展研究,在評價方法、重金屬空間分布、重金屬遷移轉換規律、重金屬賦存形態和生物有效性等方面取得了許多進展。三峽庫區是長江流域重要生態屏障,庫區內土壤重金屬污染情況與整個長江流域的生態安全息息相關。多年來,許多學者針對三峽庫區干流及其支流流域中的重金屬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展開研究,方志青等[6]對三峽庫區支流河口重金屬空間分布進行研究并使用地累積指數法與生物毒性效應評價方法對重金屬污染程度做出評價;王圖錦[7]就三峽庫區消落帶重金屬遷移轉化特征展開研究;黃迪等[8]對土壤重金屬生物有效性評價技術的進展作出總結。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僅關注于水體重金屬污染或沉積物泥沙重金屬污染,較少開展從支流到干流、從坡面到河流沉積物的全鏈研究,故無法全面對庫區重金屬污染情況做出評價。基于此,本文通過對三峽庫區支流、干流以及不同坡位的土壤和沉積泥沙采樣,獲得Cr,Cu,Pb,Zn和Mn這5種重金屬元素含量,運用單因子污染指數法、內梅羅綜合指數法、地累積指數法、地累積指數法和生態風險指數法等方法對三峽庫區坡面土壤與消落帶沉積泥沙中重金屬含量特征開展研究,以期為三峽庫區重金屬污染評價提供理論與數據支持。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三峽水庫上自重慶主城區,下至宜昌,總面積達1.20×104km2(圖1),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為14.7~18.2 ℃,總降水量為1 200~1 400 mm。為長期保留有效庫容,在每年汛期(6—9月)時將水庫水位降至145 m運行,而在汛期末將水位提高至175 m運行[9],形成一條落差達30 m,面積達349 km2的暴露區域即消落帶[10]。三峽庫區地貌以丘陵為主,土壤類型以紫色土、沖積潮土和黃壤為主[11],庫區周邊人口密集,導致土地超負荷利用,庫區內主要經濟活動為農業活動[12],且坡耕地大約占耕地面積的65.15%。此外庫區內水土流失情況嚴重,大約有57.15%的土地存在水土流失的問題[13],生態較為脆弱。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三峽庫區生態環境越來越重視,自2000年以來退耕還林政策在庫區內大力推廣,且退耕還林面積逐年增大[14]。
1.2 樣品采集與分析
根據三峽庫區遙感數據,支流產沙情況,人口密度及耕地分布情況,于2017年6月(消落帶顯露期)進行野外考察及采樣,使用手持GPS獲取精確坐標,沿長江自上游重慶段向下游依次在五步河、御臨河、龍河、磨刀溪、澎溪河、大寧河和香溪河共設53個采樣點(圖1)。每個采樣點采集混合土壤兩份(采樣深度0—10 cm),每份約500 g,所有樣品密封后帶回實驗室于陰涼處室溫風干后,剔除雜物后用四分法取部分樣品過2 mm的尼龍篩。

圖1 三峽庫區采樣點分布
過篩后的每個樣品,分別稱取0.100 g進行微波消解,消解結束后,用濃度為1%的硝酸溶液進行定容,混合均勻,待測。同時進行空白樣品的制備,作為對照。之后選取鉻(Cr)、銅(Cu)、鉛(Pb)、鋅(Zn)、錳(Mn),根據采集的泥沙樣品的元素濃度的范圍配置不同濃度的標準溶液。標準溶液制備完成后,使用IACP6000等離子體電子耦合光譜儀按照混合溶液濃度由低到高的順序依次進行發射強度的測量。測量結束后,以測出的發射強度值作為縱坐標,以混合溶液的濃度值作為橫坐標,繪制標準曲線。再依次將制備好的泥沙樣品溶液在相應標準曲線的條件下進行指定元素濃度的測定,過程中若有個別樣品的元素濃度超出標準曲線的界限,需要將該樣品進行稀釋后再進行測定。測定完成后,按照公式(1)進行相應泥沙樣品中金屬元素的含量ω(mg/kg)的計算。
(1)
式中:ω為泥沙樣品中金屬元素的含量(mg/kg);l1為泥沙樣品溶液中金屬元素的測定濃度(mg/L);l0空白溶液中金屬元素的測定濃度(mg/L);V0為消解結束后試樣的定容體積(ml);m1為泥沙樣品的稱取量(g)。通過分析空白試劑,重復樣品以及參考材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發布的GBW07309(GSD-9)水系沉積物成分分析標準物質〕進行質量控制,相對標準偏差均低于10%。
采用Excel 2020分析上述5種重金屬含量與生態風險;用ArcGIS 10.5分析各重金屬含量分布。
1.3 研究方法
1.3.1 單因子污染指數法和內梅羅綜合指數法 ①單因子污染指數法主要用于對某區域土壤中某單一元素進行污染評價。Pi為重金屬i的單因子污染指數,當Pi越小時,則表示該土壤污染風險值越小。 ②而內梅羅綜合指數法是建立在單因子指數法之上的多因子綜合評價方法,它將單因子污染指數的平均值和最大值歸納到一起進行污染評價,可以更全面的反映土壤的污染情況[15],本研究將內梅羅綜合污染指數記作NI。 ③重金屬單因子污染指數法與內梅羅綜合指數法的計算公式以及分級見文獻[16]。
1.3.2 地累積指數法 地累積指數法是一種能直觀地反映重金屬在沉積物中的富集程度的方法,其通過計算研究區域土壤所含重金屬i的含量與其背景值的比值,對該地區的重金屬污染程度進行評估[17],本研究將為地累積指數記住作Igeo。Igeo越大,則表示土壤所含重金屬含量越高。地累積指數法污染法計算公式以及污染等級分級見文獻[18]。

表1 重金屬綜合生態危害毒性系數
2 結果與分析
2.1 三峽庫區坡面土壤與消落帶沉積泥沙重金屬含量特征
三峽庫區消落帶泥沙與坡面土壤中重金屬含量水平詳見表2,重金屬富集系數詳表3。在消落帶沉積泥沙中除Cr,Cu外,Pb(20.18 mg/kg),Zn(35.72 mg/kg),Mn(604.21 mg/kg)的平均含量均高于三峽庫區土壤重金屬背景值,在坡面土壤中,除Cr,Pb外,Cu(25.15 mg/kg),Zn(71.24 mg/kg),Mn(669.17 mg/kg)的平均含量均高于三峽庫區土壤重金屬背景值。無論是在消落帶沉積泥沙還是在坡面土壤中皆以Mn的含量增加最為顯著,分別是背景值的2.49與2.76倍。變異系數反映各采樣點重金屬濃度的平均變異程度,當變異系數大于0.50,表明重金屬濃度存在空間差異,重金屬分布可能受人類活動的影響[21-23]。從變異系數來看,坡面土壤中Cu,消落帶沉積泥沙中Pb的變異系數相對較高,分別為0.65和0.51,表明其積累受人為因素影響更劇烈。Luo等[24]的研究表明三峽庫區內Cu的主要由農業活動所產生;龔宇等[25]的研究表明三峽庫區內Pb主要來自于工業活動;此外,張顯強等[26]的研究表明,三峽庫區內植物對Cu的轉運能力較強而吸附能力較弱。本研究的坡面采樣點均位于坡耕地,農藥化肥的不當使用使得重金屬的污染加劇,所以Cu受流域內農業活動影響較大,而Pb在消落帶泥沙沉積物中波動較大是由于周邊工廠污水排放,重金屬隨細顆粒的沉積泥沙遷徙并沉積于部分區域。

表2 三峽庫區重金屬含量

表3 三峽庫區重金屬富集系數
富集系數反映土壤和沉積物中重金屬富集程度受人類活動影響程度[27],土壤中的Cu,Zn,Mn,消落帶沉積泥沙中的Zn,Mn的富集系數較高,分別為1.01,1.02,2.76,1.11和2.55,這表明Zn和Mn在消落帶沉積物和坡面土壤中富集,而Cu僅在坡面土壤中富集。此外,Pb與Zn在消落帶沉積物中的富集系數較坡面土壤中的富集系數高,表明Pb和Zn不僅源于周遭工、農業活動,還來自于坡面土壤,即隨坡面土壤遷徙至消落帶并沉積(表3)。此外,研究區域內坡面土壤與消落帶沉積泥沙中的Cr,Cu,Pb,Zn和Mn的超標率分別為12%,28%,0.00%,48%和96%。消落帶沉積泥沙中Cr,Cu,Pb,Zn和Mn的超標率分別為0%,32.14%,17.86%,32.14%和100%,表現為以Mn和Zn為主導的多種重金屬復合污染。Mn常被視為是自然來源的特征且作為參照元素被用于測定人類活動對重金屬富集的影響[2],在本研究中Mn與Cr,Cu,Pb和Zn的皮爾遜相關系數分別為0.544,0.688,0.656和0.689,且在0.01水平處顯著相關,表明研究區域內Cr,Cu,Pb和Zn部分源于自然母質。但由于Mn和Zn超標率較高,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因此除母巖風化外,其還源于農業面源和工業點源,這與Luo[24]的研究結果類似。
總體而言,研究區域坡面土壤與消落帶沉積泥沙中重金屬含量大小順序均為:Mn>Zn>Cr>Cu>Pb,而劉麗瓊等[11]對在2008年沿長江江岸采集的50個三峽庫區消落帶表層土壤樣品的研究表明,沿江兩岸消落帶土壤重金屬含量為:Zn>Cr>Pb>Cu,與本研究的結果稍有不同。這可能是由于長江兩岸城市化程度高于庫區其他流域,人類活動使得土壤中Cu的含量增加。此外研究區域內Mn污染最為嚴重,Pb污染程度較低,與莫孝福等[28]在2013年基于單因子污染指數法三峽庫區消落帶不受Pb污染研究結果不同,這是由于2013年后,庫區內農工業發展迅速、廢水排放量增多導致Pb污染加劇。
2.2 三峽庫區消落帶沉積泥沙和坡面土壤重金屬空間分布
三峽庫區坡面土壤與消落帶沉積泥沙重金屬空間分布圖如圖2所示。重金屬元素Cr,Cu,Pb,Zn和Mn自上游至下游的分布特征呈多峰型,Cr,Cu和Zn在御臨河、五步河流域和大寧河流域出現兩個峰值,且在消落帶沉積泥沙中的含量遠高于坡面土壤,表明這3種元素在御臨河、五步河及大寧河流域存在自坡面向消落帶遷徙、沉積。Mn在大寧河及香溪河流域的坡面土壤中存在峰值,Pb在大寧河流域存在峰值,且在坡面土壤中的含量遠高于在消落帶沉積泥沙中的含量。這是由于御臨河、五步河流域主要位于重慶市、大寧河貫穿巫溪縣,周遭人類活動例如生活污水排放、交通面源污染、工業廢水排放導致該流域內Cr,Cu和Zn含量較高,且由于城市化加劇,植被覆蓋減少,水土流失加劇,重金屬與細顆粒泥沙結合并隨著其流入消落帶并沉積,導致消落帶沉積泥沙中重金屬含量較高。

圖2 三峽庫區Cr,Cu,Pb,Zn,Mn分布
總體而言,5種重金屬元素沿江的整體分布呈現上游和下游較高,中游較低的趨勢,表明上游及下游的重金屬污染情況較嚴重。這是由于上游靠近重慶主城區,重金屬含量受城市生活污水與工業廢水排放以及交通工具尾氣排放影響,下游奉節縣畜牧業較為發達,巫山縣與巫溪縣為發展工、農業,化肥使用量與廢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加劇了重金屬污染[29]。中游多為林地與荒地,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少,因此重金屬含量較上、下游少。
2.3 三峽庫區消落帶沉積泥沙重金屬污染評價
2.3.1 單因子污染指數法和內梅羅綜合指數法 針對單因子污染指數法對各采樣點的重金屬含量進行分析后發現,僅Mn的單因子污染指數平均值(Pia)大于2,為中度污染,Zn的Pia為1.07,為輕度污染,其余3種重金屬的Pia均小于1,為無污染,表明研究區域內存在Mn與Zn污染。研究區域內各個采樣點中的Cr,Cu,Pb,Zn和Mn點位總污染率分別為7.55%,30.19%,9.43%,37.74%和96.23%,污染程度從重到輕分別為Mn,Zn,Cu,Pb和Cr。研究區域內沉積物重金屬單因子污染指數及各重金屬不同等級污染點位所占比例詳見表4。

表4 三峽庫區土壤重金屬單因子污染指數及各重金屬不同等級污染點位所占比例
研究區域內內梅羅綜合(NI)指數范圍為1.27~7.33,平均值為2.93,表現為中度污染。三峽庫區土壤重金屬內梅羅綜合指數法評價結果顯示(圖3),大寧河流域的采樣點13(坡面土壤)、御臨河流域的采樣點32(消落帶沉積泥沙)、龍河流域的采樣點42(坡面土壤)和香溪河流域的50(消落帶沉積泥沙)存在較高值。香溪河流域的NI較其他流域大,這是由于香溪河流域內不僅農業活動發達,流域內還存在磷礦廠,礦區的廢水與礦渣的不合理排放加劇了重金屬污染[30]。御臨河流域靠近重慶市區,居民城市污水與工業污水排放及交通尾氣排放使得御臨河流域的NI較高。此外,流域內存在大量坡耕地,農藥與化肥的不當使用也使得重金屬污染程度增加。大寧河流域NI值偏高的原因是大寧河沿岸有采石場,采石活動會加劇重金屬污染,且流域內坡耕地較多,在坡耕地上使用的農藥和化肥會部分隨地表徑流、地下潛流及滲流作用遷徙至消落帶[31],黃歲梁等[32]的研究表明沉積泥沙粒徑越小與之結合的重金屬含量就越高,殘留在坡面土壤的部分重金屬與細顆粒泥沙相結合并隨其向消落帶遷徙、沉積。

圖3 三峽庫區土壤重金屬內梅羅綜合指數法評價
2.3.2 地累積指數法 由圖4可知,研究區域內5種重金屬元素Igeo平均值特征呈現為:Mn>Zn>Cu>Pb>Cr,分別為0.69,-0.56,-0.72,-0.97和-1.20。除了Mn元素為輕度污染,其余4種重金屬元素皆為清潔。Cr在所有采樣點中的Igeo值都小于0;Cu的清潔點位占比為90.57%,采樣點46(位于香溪河消落帶)的Igeo值最大,為偏中度污染,其次在御臨河與五步河流域皆存在輕度污染。Pb的清潔點位占比為96.23%,輕度污染點位占比為3.77%,僅采樣點37(龍河消落帶沉積泥沙)與采樣點51(位于御臨河沉積泥沙)存在輕度污染;Zn的清潔點位占比為88.68%,輕度污染點位占比為11.32%。在龍河、大寧河、御臨河與五步河均有采樣點存在輕度污染。Mn的清潔點位占比為9.43%,輕度污染點位占比為64.15%,偏中度污染點位占比為24.53%,中度污染點位占比為1.89%,僅采樣點57(香溪河消落帶沉積泥沙)為中度污染,其余皆為輕度、偏中度污染。結果顯示,無論在坡面土壤還是消落帶沉積泥沙中皆為Cr的污染程度最輕,Mn的Igeo值遠高于其他幾種元素,污染最重,這是由于三峽庫區內Cr的主要來源為自然源的母巖風化[33],人類活動對其影響較小,且植物對Cr的吸附能力較強[26],近年來,隨著三峽庫區植被恢復,吸收Cr的植物增多,使得研究區域內Cr污染程度最輕。一般而言Mn的主要來源為自然母質風化,不會造成污染,但隨著人類活動的加劇,農業面源、工業點源及城市面源與點源都會提供Mn,且植物對其的吸附及轉運能力都較差[10],因此其污染程度最重。目前并沒有研究得出三峽庫區Mn的明確來源,因此后續研究需要對研究區內Mn的來源做進一步的分析。此外,消落帶沉積泥沙較坡面土壤污染程度高,重金屬更易在消落帶沉積泥沙中沉積,這是由于庫區內多為坡耕地,農藥化肥使用量較大且水土流失較為嚴重,重金屬與細顆粒泥沙結合后,向消落帶遷徙并沉積在消落帶中。而且每年消落帶會被定期淹沒,消落帶中的重金屬元素在還原狀態與氧化狀態中轉換,對重金屬的遷移產生影響,導致消落帶重金屬污染程度較高。御臨河流域較其余幾個流域的重金屬污染種類更多,即存在Cu,Pb,Zn和Mn的污染,其原因是御臨河位于重慶市區,周圍居民區、工業區及農業區較其他流域更多,人類活動對其的影響程度更大,污染類型更為多樣,工業活動提供了Pb,Zn和Mn,而Cu則是由農業活動所提供[34-35]。


表5 三峽庫區各流域消落帶沉積泥沙與坡面土壤中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系數

圖5 三峽庫區土壤重金屬綜合生態危害指數評價結果
3 結 論
(1) 三峽庫區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較為突出,土壤中Cr,Cu,Zn和Mn在御臨河、大寧河、龍河和香溪河流域呈明顯富集,其中Mn含量在消落帶沉積物中與坡面土壤中較高,分別為三峽庫區土壤背景值的2.49與2.76倍,點位超標率分別為96%和100%。
(2) 單因子指數法、內梅羅綜合指數法及地累積指數法結果表明,土壤中Cu,Zn和Mn存在局部污染,且污染主要集中在大寧河、御臨河、龍河和香溪河流域的坡耕地及消落帶沉積泥沙中。且重金屬污染物存在由坡面向消落帶沉積泥沙遷徙并富集的現象。
(3) 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顯示目前研究區域內暫無生態風險,但Cu在香溪河、五步河和御臨河流域內,Pb在龍河流域的生態危害指數波動較大,表明Cu,Pb存在局部污染,潛在生態危害高于研究區內其他流域。
(4) 受農業面源污染等因素影響,三峽庫區土壤中存在Cu,Zn和Mn的污染,且重金屬會在消落帶沉泥沙中富集沉積,對三峽庫區造成了潛在的生態風險,須采取積極的防治、修復措施,以減輕該區域內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
(5) 本研究選取的采樣點存在不足。例如多數取于產沙較嚴重的8個流域。坡面采樣點皆位于坡耕地,采樣點所在地土地利用類型不夠豐富等,后續研究可針對這一點增加城市及工礦用地、林地、草地等采樣點,進一步地對研究區域潛在的重金屬污染與生態危害做出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