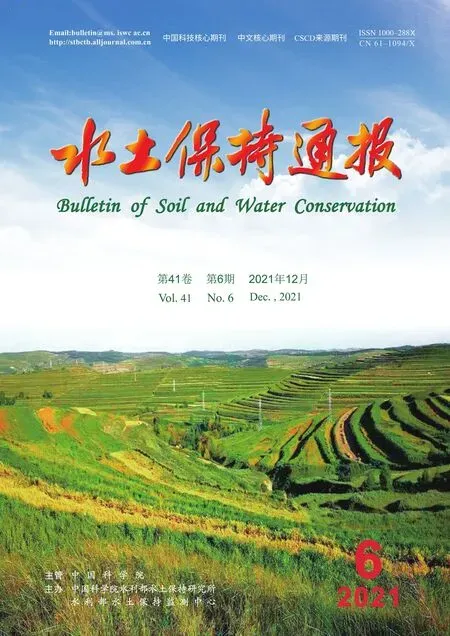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效益綜合評價模型研究
王海燕, 叢佩娟, 袁普金, 李斌斌, 王愛娟, 李 琦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監測中心, 北京 100055)
1983年,中國第一個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八片國家水土流失重點治理工程啟動實施。之后國家先后啟動實施了黃河中游、長江上游、黃土高原淤地壩、京津風沙源、東北黑土區和巖溶地區石漠化治理等一大批水土保持重點工程。對加快水土流失治理進度,改善生態環境,建設美麗中國,維護國家和區域生態安全,以及推動中國早日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 2018 年底,全國累計治理水土流失面積1.31×106km2,水土保持措施年均可保持土壤 1.60×109t,項目區生產生活條件顯著提升,糧食產量增加,農民增收顯著,鄉村面貌煥然一新[1]。但是,從國家水土保持工程實踐來看,與水土保持規劃、科研、設計、施工建設以及工程項目管理等工作相比,水土保持工程實施效果后評價工作相對滯后。盡管一些專家學者和工程技術人員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在一些地方開展了小流域綜合治理效益評價,但并未形成一套受到相關各方廣泛認可的、權威的水土保持工程重點實施效果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
目前,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績效評價等工作也僅停留在設計任務落實、項目管理和資金管理合規性等方面的考量,水土保持工程實施后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和改善作用并未在評價指標中得到充分重視,因而對水土保持工程績效評價和下一階段項目安排布局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另外,現行技術標準中提出了有關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和方法。例如,《水土保持綜合治理效益計算方法(GB/T15774-2008)》給出了一套水土保持工程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評價指標體系,但其在實際應用中存在較多問題,主要包括: ①指標太多,實際應用比較復雜,有些指標采集難度較大,影響評價結果準確性; ②缺少對每個指標權重賦值,僅對給定區域單一水土保持工程可以進行評價,評價結果不足以支撐不同區域、不同工程之間的比較,也不支撐工程實施對生態環境總體改善的定量評價; ③對水土保持基礎效果和衍生效果沒有進行區分,指標之間關聯性較強。例如,增加地表徑流入滲與減少洪水流量,提高地面林草覆蓋度與增加植物固碳量等存在較強關聯性,是基礎效果和衍生效果的關系。隨著國家生態工程建設管理要求和項目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定量開展生態建設工程投資實施效果評估工作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績效評價、后評估等各類水土保持工程實施效果后評價工作也逐步推進,因而,亟需建立一套全面、系統、科學、操作簡便的水土保持工程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支撐相關實踐工作。本文采用頻度分析法和層次分析法研究水土保持工程效益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模型與評價標準,旨在為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績效評價、實施效果后評價等工作提供技術支撐。
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原則
水土保持工程效益評價指標體系是由反映水土流失綜合治理效果各方面特性及其相互聯系的多個指標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構建指標體系遵循以下原則。
(1) 科學性原則。指標體系構建要從改善區域生態環境,促進區域人與自然和諧,實現可持續發展出發,遵循生態學的基本規律,較為準確地反映水土流失治理效果的客觀實際和固有特性以及各指標之間的真實關系。
(2) 系統性原則。評價指標之間要有一定的邏輯關系,從不同角度反映生態技術實施效果的不同特征,綜合所有指標即能刻畫出生態技術實施效果的主要特征和狀態。各指標之間相互獨立,又彼此聯系,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同時,指標體系層次清晰,自上而下,從宏觀到具體,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3) 典型性原則。評價指標應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盡可能準確地反映特定區域的環境、經濟、社會變化的綜合特征,即使在減少指標數量的情況下,也要便于數據計算和提高結果的可靠性。另外,評價指標體系的設置、權重在各指標間的分配及評價標準的劃分都應該與水土流失治理效果特性相對應。
(4) 簡明性原則。評價指標設置應本著簡明性原則,在滿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盡量選擇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指標,避免指標過多過細和相互重疊。各指標盡量簡單明了,數據容易獲取,計算方法簡單易行。
2 評價指標體系篩選
水土保持工程效益是指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實施后促進生態系統的改善以及由此帶來經濟收益和社會收益,也就是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總稱。本質上,水土保持工程效益主要包括最基礎的固持土壤、涵養水源、改善生態,以及糧食等農林牧產品收益的增加和水旱風沙災害的減少。
2.1 篩選方法
本研究擬采用較為常用的文獻頻度分析法[2-3],結合定性分析篩選出水土保持工程實施效益評價指標。基于國內1999—2021年的文獻樣本,以及《美麗中國建設評估指標體系》《水土保持綜合治理效益計算方法(GB/T15774-2008)》等資料,對符合的樣本進行篩選分析,統計指標頻次,初步確定評價指標因子。通過定性分析,判斷指標之間關聯性較低,具有相對獨立性。在此基礎上,采用層次分析法,依據相關領域專家和示范點工程技術人員評價結果,確定各個指標的優先關系及其權重,建立二級評價指標體系。
2.2 指標篩選
從文獻初步統計出水土流失治理效益評價指標45個[4-8],其中土壤固持與保護類16個,水源涵養類8個,生態改善類9個,收益增加類6個,防災減災類5個(表1)。

表1 文獻樣本中水土保持工程效益評價指標統計
2.2.1 土壤固持與保護類 主要包括土壤肥力[9]、土壤理化性狀、土壤孔隙率、土壤密度、水土流失面積比、土壤侵蝕模數、土壤退化、崩塌土石方量、產沙量、洪水泥沙含量、土壤保持量、耕地防護比、耕作層厚度、水土流失治理度、攔蓄泥沙量、水土保持率共16個指標。
統計結果發現頻度最高的指標是土壤侵蝕模數(26%),最小為水土保持率(1%)。水土保持率是2019年水利部部長鄂竟平同志在江河流域水資源管理現場會上首次提出的。2020年該指標納入了美麗中國建設評估指標體系,相關研究文獻較少。其次,土壤理化性狀、土壤肥力、土壤保持量、水土流失治理度、水土流失面積比分別為11%,9%,10%,7%和6%,其他均小于5%。這些指標中,土壤理化性狀與土壤肥力、土壤孔隙率、土壤密度為同類指標可以合并,以降低指標離散度;同理,對水土流失面積比、水土流失治理度、水土保持率也進行合并,優化后水土保持率頻度為18%,土壤理化性狀頻度為22%(圖1)。

圖1 土壤固持和保護類指標
參照國內學者采用頻度分析法研究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方法,選擇頻度高于20%的作為初步選定指標。在此基礎上,分析各類指標間的相互關系,將符合指標體系構建原則的指標作為篩選最終結果。其中,水土保持率為新出現概念,作為美麗中國建設22個評估指標其中一個,是當前評價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較為常用的一個重要指標,應當作為本研究選定的一個指標;土壤理化性狀指標對生態系統修復和改善具有重要意義,進行優化處理后超過了20%,也應保留。因此,土壤固持和保護類指標選定土壤侵蝕模數、土壤理化性狀、水土保持率。
2.2.2 水源涵養類 主要包括徑流模比、減水模數、土壤保水能力、削減洪水量、水源涵養量、提升流域濕度、流域年徑流量、地表水水質優良共8個指標。經頻度分析,徑流模比和水源涵養量分別為37%和23%,減水模數、削減洪水量均為13%,其余均小于5%(圖2)。由于地表水水質優良是美麗中國建設評估指標體系的一個指標,對評價生態環境質量具有重要作用,同時鑒于美麗中國評估指標體系是在大量研究和調研的基礎上形成,且得到相關各方認可,因此,水源涵養類指標選定徑流模比、水源涵養量、地表水水質3個指標。

圖2 水源涵養類指標
2.2.3 生態改善類 主要包括生物量、單位產值生態擾動系數、生態環境容納度、水土保持服務價值[10]、植被覆蓋度[11]、生物多樣性、釋氧量、固碳量、水土保持服務能值共9個指標。經頻度初步分析,植被覆蓋度出現頻度為43%,水土保持服務價值和水土保持服務能值分別為15%和13%,生物多樣性為11%,其余均為2%。其中,水土保持服務能值是水保持服務價值的一種計量方法,二者應歸為同類指標。水土保持服務價值包含了釋氧量、固碳量、生物多樣性以及“保土、保肥、保水”等指標,是一個綜合評價指標,這個指標應作為評價水土流失治理效益的綜合指標,是等同于水土流失治理效益層次的一個評價指標,不應包含在生態改善類指標中,應加以剔除。釋氧量和固碳量應為同類指標進行整合而成釋氧固碳量。優化后進行頻度分析,植被覆蓋度的頻度為59%,釋氧固碳量為18%,生物多樣性為16%(圖3)。中國于2020年9月向世界宣布了新的碳達峰和碳中和愿景,因此,未來生態建設中碳匯將是一個重要目標,釋氧固碳應納入評價指標體系。同時生物多樣性也是評價生態系統發展演化程度和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應納入。因此,生態改善類指標選定植被覆蓋度、生物多樣性和釋氧固碳量3個指標。

圖3 生態改善類指標
2.2.4 收益增加類 主要包括糧食產量、林業產量、畜牧業產量、載畜量、土地生產效率、土地利用變化6個指標[12]。經頻度分析,土地利用變化的頻度為42%,糧食產量和土地生產效率的頻度均為17%,林業產量、畜牧業產量、載畜量均為8%。其中,林業產量、畜牧業產量和載畜量可折算成生態工程實施區農牧民人均年農林牧收入;土地生產效率與土地利用變化整合,優化后指標如圖4所示。收益增加類選定土地利用變化、農牧民人均年農林牧收入、糧食產量3個指標。

圖4 收益增加類指標
2.2.5 防災減災類 主要包括減少洪災、減少旱災、減少沙塵暴、減少泥石流、減少滑坡等指標。經頻度分析,減少沙塵暴的頻度為67%,減少洪災和減少旱災的頻度均為11%,減少泥石流、減少滑坡的頻度均為6%(圖5)。盡管目前相關文獻對水土流失治理減少洪災和旱災關注較少,但因中國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許多生態退化區往往洪澇災害與生態退化密切相關,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實施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減少洪災和旱災,這兩個指標應納入評價指標體系。防災減災類選定減少沙塵暴、減少洪災、減少旱災3個指標。

圖5 防災減災類指標
2.3 水土保持工程效益評價指標體系
綜上分析,本研究最終選定5類、15個指標構成水土保持工程效益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體系為二級指標結構,一級指標包括土壤固持與保護、水源涵養、生態改善、收益增加、防災減災5個,二級指標有15個(表2)。

表2 水土保持重點工程效益評價指標體系
3 評價模型確定
3.1 一級指標參數確定
3.1.1 建立判斷矩陣 對照層次分析法中的指標標度(表3)標準,收集有關專家、示范點工程技術人員以及研究組成員評價意見,對一級、二級指標分別進行對比評價[13]。

表3 指標標度及其含義
對土壤固持與保護(C1)、水源涵養(C2)、生態改善(C3)、收益增加(C4)、防災減災(C5)5個一級指標進行分析評價。依據評價結果構建判斷矩陣P如下:
(1)
3.1.2 計算指標權重 根據矩陣P,求出最大特征值對應的特征向量,特征向量就是評價因子重要性次序,即權重分配。本研究采用和積法求特征向量:
(1) 對判斷矩陣每一列進行歸一化處理,處理方法如下:
(2)
式中:uij是第i單元中第y個因子的值。
得出正規化的判斷矩陣P為:

(3)
(2) 對正規化處理后的判斷矩陣P按行相加,得:
(4)
(5)
計算得,W1=0.404,W2=0.238,W3=0.120,W4=0.047,W5=0.191,求得特征向量W=(0.404,0.223,0.120,0.047,0.191)T
(4) 計算判斷矩陣最大特征值。
(6)

3.1.3 一致性檢驗 根據公式(7)計算層次總排序一致性比例CR,當CR<0.1時,可以認為層次總排序的計算結果具有滿意的一致性。
CR=CI/RI
(7)
式中:CI為層次總排序一致性指標,依據公式(8)計算
(8)
RI為平均一致性指標,僅與矩陣階數有關。對于1—8階矩陣平均一致性指標RI,其取值詳見表4。

表4 平均一致性指標RI值
按照公式(9)計算CR
CR=CI/RI
(9)

計算得出判斷矩陣具有滿意的一致性,說明權重分配是合理可信的。
得出水土流失治理效益評價模型為:
(10)
式中:C1為土壤固持與保護;C2為水源涵養;C3為生態改善;C4為收益增加;C5為防災減災。
3.2 二級指標參數確定
土壤固持與保護(C1)、水源涵養(C2)、生態改善(C3)、收益增加(C4)和防災減災(C5)判斷矩陣詳見表5—9。

表5 土壤固持與保護二級指標判斷矩陣(C1)

表6 水源涵養二級指標判斷矩陣(C2)

表7 生態改善二級指標判斷矩陣(C3)

表8 收益增加二級指標判斷矩陣(C4)

表9 防災減災二級指標判斷矩陣(C5)
對土壤固持與保護判斷矩陣(C1)、水源涵養判斷矩陣(C2)、生態改善判斷矩陣(C3)、收益增加判斷矩陣(C4)、防災減災判斷矩陣(C5)一致性檢驗結果詳見表10。CR值均小于0.1,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因此,基于層次分析法得到二級評價指標權重是合理可信的。

表10 二級指標判斷矩陣一致性檢驗結果
依據上述分析,構建水土保持工程實施效益評價指標體系詳見表11。

表11 水土工程實施效益評價指標體系
3.3 評價模型
確定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效益評價模型為:
(11)
式中:E為國家水土保持工程治理效果評價結果;k為指標權重;A為標準化指標值。標準化處理可以采用總和標準化、最大值標準化等方法。
3.4 評價指標數據監測與獲取
篩選確定的評價指標,均為常用指標,可以通過常用方法測算獲取或者現場調查獲得。
3.4.1 固持土壤與保護類指標 土壤侵蝕模數采用國際上通行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測得。
A=R·K·L·S·C·P
(12)
式中:A為年均土壤流失量〔t/(km2·a)〕;R為降雨侵蝕力因子〔MJ·mm/(hm2·h·a)〕;K為土壤可蝕性因子〔t·hm2·h/(hm2·MJ·mm)〕;L為坡長因子;S為坡度因子;C為植被覆蓋與管理因子;P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土壤理化性狀主要包括土壤養分狀況、化學條件等。一般而言,主要考慮土壤容重和重量直徑,有機質、全氮、全磷、全鉀、pH值等,通常采用常規方法測定土樣獲得相關數據。其中,土壤平均重量直徑是一定粒級團聚體的重量百分比Wi乘以這一粒級的平均直徑Xi,所有所測粒級的上述乘積之和,即為平均重量直徑(MWD)。
(13)
水土保持率(SWC)是指區域內水土保持狀況良好的面積(非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是反映水土保持總體狀況的宏觀管理指標[14]。計算公式如下為:
(14)
式中:Sn指治理區內土壤侵蝕強度輕度以下的現狀國土面積;S是指區域國土面積。
3.4.2 水源涵養類指標 水源涵養量采用水量平衡法計算,計算公式為:
采用Excel 2007和SPSS17.0對數據進行處理與統計分析,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比較處理間的差異性。
Ew=(P-ET)×A
(15)
式中:Ew為治理區水源涵養量(m3);P為治理區年降水量(mm); ET為治理區年蒸散量(mm);A為治理區面積。
3.4.3 生態改善類指標 植被覆蓋指數(NDVI)計算公式為:
NDVI=(NIR-R)/(NIR+R)
(16)
式中:R表示紅外波段的灰度值,NIR表示近紅外波段的灰度值。NDVI取值范圍是-1~1,負值表示地面覆蓋度為云、水、雪等; 0表示巖石或裸地; 正值表示植被覆蓋,其數值越接近1,說明區域植被覆蓋度越高、植被生長狀況越好。
生物多樣性指數計算公式為:
(17)
式中:H為多樣性指數;s為樣地中的物種總數;Pi為第i種物種的個體數占所有種個體總數的比例。
固定CO2的物質量的計算公式為:
ECO2=NPP×1.63×A
(18)
式中:ECO2為固定CO2的物質量(t); NPP為年凈初級生產力(t/km2);A為治理區域面積。
釋放O2物質量的計算公式為:
EO2=NPP×1.19×A
(19)
中:EO2為釋放O2的物質量(t)。
3.4.4 收益增加類指標 一定時期內區域內土地利用變化狀況一般用土地利用變化動態度表示。土地利用變化動態度通常包括單一土地利用變化動態度和綜合土地利用變化動態度。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表示在一定時期內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速度和幅度。計算公式如下:
(20)
式中:K為治理區域某一時段內某一土地利用類型變化速率(%);Si,Sj為水土流失治理前和治理后土地利用類型面積(km2);T為研究時段。
綜合土地利用變化動態度用來定量治理區域某一時期的土地利用變化速率,是預測未來土地變化趨勢的指標。計算公式為:
(21)
式中:Lc為治理區域內某時段內土地利用變化速率(%); ΔSi-j為治理期內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的土地轉化為j類型土地面積總和(km2);T為研究時段。
農民年均收入、糧食產量等指標可以通過查閱統計部門數據或現場調查獲取。
3.4.5 防災減災類指標 減少水旱風沙災害可以通過查閱水文、氣象以及統計部門數據獲取,也可通過現場調查獲取。
減少洪水災害采用洪水頻率變化度表示,計算公式為:
(22)
式中:F為項目區治理前后洪水頻率變化度(%);Fi,Fj為治理前與治理后項目區洪水頻率(次/a)。
減少旱災采用旱災發生頻率變化度表示,計算公式為:
(23)
式中:D為項目區治理前后旱災發生頻率變化度(%);Di,Dj治理前與治理后項目區旱災發生頻率(次/a)。
減少沙塵暴采用沙塵暴發生頻率變化度表示,計算公式如下:
(24)
式中:W為項目區治理前后沙塵暴發生頻率變化度(%);Wi,Wj治理前與治理后項目區沙塵暴發生頻率(次/a)。
3.5 水土保持工程實施效益評價
上述評價指標單位各不相同,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都存在(指標值越大對生態環境改善越有利的為正向指標,指標值越大對生態環境改善越不利的為負向指標)。因此,在獲取原始數據后需要進行標準化處理。按照上述評價模型測算得出的評價結果是在0~100范圍內的分值。根據水土流失治理效果評價分值,結合定性指標要求,確定水土保持工程實施效果評價結論,可分為優秀、良好、緩慢改善、惡化、極度惡化5個級別[15]。限于實際樣本數限制,本研究僅從每類指標中抽取1個指標,分別在西北黃土高原、西南巖溶區選取1個小流域進行試算,初步提出了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效益評價標準(表12)。

表12 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效益評價標準
4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在大量查閱文獻的基礎上,提出了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效益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指標體系基本涵蓋了通常水土流失治理效益評價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包括土壤固持與保護類、水源涵養類、生態改善類、收益增加類和防災減災類5大類,以及土壤侵蝕模數、土壤理化性狀、水土保持率、水源涵養量、地表水水質優良、徑流模比、植被覆蓋度、生物多樣性、固碳釋氧量、土地利用變化、農牧民人均年農林牧收入、糧食產量、減少沙塵暴、減少洪災、減少旱災15個指標。其中,土壤固持與保護類指標中,土壤侵蝕模數主要表征土壤侵蝕嚴重程度,水土保持率實質反映的是水土流失空間分布情況,土壤理化性狀主要表征土壤生產力大小,這3個指標分別側重于水土流失嚴重程度、空間分布范圍、土地生產力,因而是相對獨立的。
本研究提出的評價模型需要在后續研究中跟蹤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實踐,收集相關基礎資料,不斷驗證和完善。同時,限于樣本數及數據不足,本研究初步提出了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效益評價分級標準,需要通過增加樣本數和大量數據進行驗證和完善,才能作為實踐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