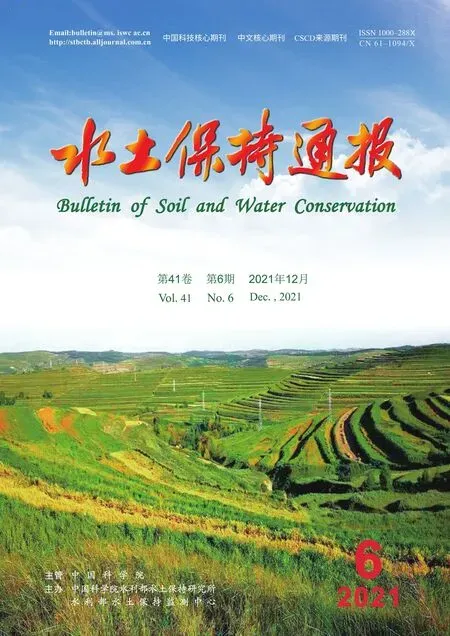基于SRP模型的川藏線2010-2020年生態脆弱性時空分異與驅動機制研究
孫宇晴, 楊 鑫, 郝利娜
(1.成都理工大學 地球勘探與信息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四川 成都 610059; 2.成都理工大學 地球科學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59)
生態脆弱性是指生態系統在特定時空尺度下對外界擾動所具有的敏感性和恢復能力,是在遭受侵擾后表現出來的使系統朝著逆方向發展并難以恢復原狀的自然屬性[1]。20世紀60—80年代,脆弱性研究已被很多國際學術計劃與機構(IBP,MAB,IGBP等)提及并放于戰略研究位置[2-4]。現今國內外對于生態脆弱區的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衍生出多種評價模型與方法,計算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5]、層次分析法[6-7]、模糊綜合評價法[8]、灰色關聯法[9]、熵權法[10]、專家咨詢法等[11]。在評價模型方面,目前比較權威的評價模型包括PSR即“壓力—狀態—響應”概念模型、“暴露—敏感—適應”(VSD)評價整合模型、SRP即“生態敏感性—生態恢復力—生態壓力度”評價概念模型等。其中SRP模型主要以生態系統穩定性的內涵為依據構建而成,其結構系統地涵蓋了生態脆弱性的構成指標,已在生態脆弱性評價中得到廣泛應用[12]。生態脆弱性研究系統現今已發展的較為完善,但在研究區域選擇上還存在不全面性。在以往研究中通常以行政區劃、河流流域、山地高原、特定景觀地帶如國家自然保護區等為研究單位,針對國家重點道路沿線生態脆弱性的研究較少。而對于國家重點道路本身,鐵路基礎設施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道路能否安全運行至關重要[13]。國家重點道路不屬于通常的單一研究區域,其沿線地理空間特征是反映周邊各地區自然與社會差異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川藏鐵路開工建設作出重要批示時強調,川藏鐵路沿線地形地質和氣候條件復雜,生態環境脆弱,修建難度非常之大。此外,沿線施工,會破壞原有的生態平衡,導致生態環境進一步受到威脅。以往關于川藏鐵路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選線的地質環境條件[14-15]和沿線的地質災害易發性等[16]問題上,而對于沿線生態脆弱性的研究極少。為此,本文以川藏線(雅安—新都橋段)為例,基于研究區實地特征選取與生態脆弱性密切相關的15個因子構建生態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考慮到各個指標之間可能存在著相關性,通過空間主成分分析方法予以剔除,并根據選取的各個主成分的特征根得到其權重,建立最終的SRP評價模型[17]。本研究基于地理學、數學、統計科學等多學科,綜合運用空間主成分分析、空間自相關、熱點分析、地理探測器等研究方法,探究研究區2010—2020年生態脆弱性時空分布特征,厘清生態脆弱格局規律以及空間相關性,以期為沿線生態環境保護以及建后可持續發展工作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
1 研究區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川藏鐵路地質環境極為復雜,為了使研究更具代表性和多樣性,選取川藏鐵路海拔地形相差較大、人類活動有明顯差異的地域,比較各種特征因素對生態脆弱性的影響。為此,本次研究線路選取位于川西高原與四川盆地過渡地帶的雅安至康定(新都橋)段,該段始于成雅鐵路雅安站,向西經天全,越二郎山,跨大渡河,經瀘定、康定,越折多山至新都橋站,路段長約248 km[18]。研究區(29°48′—30°14′N,101°25′—103°2′E)面積約6 800 km2。研究區地勢西高東低,位于青藏高原東南緣川滇、巴顏喀拉、華南地塊交匯處,屬于印度板塊俯沖并與歐亞板塊碰撞的碰撞帶東北側,新構造運動劇烈,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頻發[19],主要行政區域為康定、瀘定、雅安(寶興、蘆山、天全、滎經和雨城)的部分地區。2013年雅安市蘆山縣發生過7.0級地震,并且研究區內涉及多處環境敏感區[18]。本文選取2010年(2013年4·20雅安地震與2014年11·22康定地震震前時間節點),2015年(震后時間節點),2020年(震后基本修復后時間節點)為3個時間段,這期間顯著的地質構造變化、環境保護建設以及經濟格局的快速發展為區域內生態脆弱演變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條件。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所需數據包括地形數據、氣象數據、人文數據和其他植被、地災等數據。地形數據包括高程、坡度和地形起伏度,由從中科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下載的分辨率為12.5 m的DEM數據提取獲得,另外地震點基礎數據也從該網站下載獲取;氣象數據包括年均氣溫、年均降水和干燥指數,來源于中國氣象數據網(http:∥data.cma.cn),并借助于ANUSPLIN工具以經緯度與高程作為協變量插值獲取[20]。人文數據主要是人口密度、人均GDP,均從全球變化科學研究數據出版系統(http:∥www.geodoi.ac.cn/)獲取,并通過在91衛圖中進行人工目視解譯以及與研究區所在區縣的統計年鑒進行比對,對原數據進行改善使其精度更高更符合研究區實地情況;植被覆蓋度與土地利用類型數據通過USGS下載的Landsat影像分別進行NDVI計算和人機交互解譯獲取;土壤侵蝕強度和植被凈初級生產力(NPP)分別采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21]和CASA模型[22]計算,此處不再贅述;生物豐度是反映區域內生物多樣性、生物物種數量多少的指數,由土地利用分類數據計算得出[23-24]。最后基于雙線性內插法將所有基礎數據統一重采樣為30 m空間分辨率數據,以便進行后續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評價模型構建
SRP模型即“生態敏感性—生態恢復力—生態壓力度”概念模型,是一項專門用于評價某一特定區域生態脆弱性的綜合評價模型。其中生態敏感性是指研究區生態環境對各種干擾的敏感程度,反映其抵御干擾的能力;生態恢復力是指在外部力量的干擾消除后,生態環境從退化狀態恢復到原狀的能力;生態壓力度是指研究區內人類社會活動對生態環境帶來的壓力強度[25]。針對研究區的實地特征,利用該模型選取與研究區域內生態脆弱性密切相關的指標,設置各不同指標的權重值,將所有權重值與指數的相乘結果再相加的方式,最終得出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指標[23]。根據該模型以及研究區自然與人文環境特征,選取15個指標,構建研究區生態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26](表1)。
由于不同指標量綱不同,要進行指標之間的比較分析,就要制定一個統一的規則,因此要進行標準化處理[23]。本文指標整體分為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定量指標采用極差法,根據各個評價指標對研究區生態環境的消極或積極影響,將其分為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表1)。

表1 川藏線(雅安-新都橋段)生態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
定量指標標準化公式為:
(1) 正向指標:
(1)
(2) 負向指標:
(2)
式中:Yi表示第i個初始指標的標準化值,范圍為1—10;Xi表示第i個指標的數據值;Xmax,Xmin分別表示i指標的最大和最小數據值。
對于定性指標,根據專家打分法和相關研究成果[27-28],結合研究區實際特征采用分級賦值法對指標因子進行標準化處理(表2),范圍設為0~10。

表2 定性指標分等級賦值標準
2.2 空間主成分分析
這里為了避免各指標之間相關性過大導致其對生態脆弱性評價結果重復影響或者指標與生態脆弱性相關性太小的問題,需要采用空間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累計貢獻率大于85%的前幾個主成分作為替代指標進行分析。替代指標計算公式為:
(3)
式中:Wj為第j個替代指標(主成分);Yi為第i個初始指標的標準化值;Zij為第i個初始指標在第j個主成分所對應的特征向量;n為初始指標個數[29]。
2.3 生態脆弱性指數
通過由空間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的6個主成分計算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指數(EVI)。
(4)
式中:EVI為該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指數;Wj為第j個主成分;Qj為第j個主成分的貢獻率;m為累計貢獻率大于85%的前6個主成分個數。生態脆弱性指數越大,表明該地區生態環境越脆弱;反之,該地區生態環境越好。
為了更直觀地對研究區的生態脆弱性進行比較,將EVI進行標準化處理,計算公式為:
(5)
式中:SEVI為生態脆弱性指數標準化值,取值范圍為0~10; EVI為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指數; EVImax為研究區范圍內生態脆弱性指數的最大值; EVImin為最小值[30]。參考專家知識與本研究區特征將生態脆弱性進行分級(表3)。

表3 川藏線(雅安-新都橋)生態脆弱性分級標準
2.4 空間自相關
為了進一步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分布特點進行統計,此處引入全局自相關Global Moran’sI工具,計算公式為:
(6)
式中:n為空間單元數量;Wij為空間權重矩陣;Xi,Xj分別為屬性特征X在空間單元i和j上的觀測值(i≠j);I系數取值范圍為[-1,1]。當I<0且p<0.05,代表空間負相關,說明相鄰空間單元的生態脆弱性不具備空間聚集性;當I=0或約等于0,表示相鄰空間單元的生態脆弱性不存在空間自相關性,呈隨機分布;當I>0且p<0.05,代表空間正相關,說明相鄰空間單元的生態脆弱性具有空間聚集性[31]。
2.5 熱點分析

(7)
(8)

2.6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一組用于探測空間變化并揭示其背后驅動機制的統計方法。包括分異及因子探測、交互作用探測、風險區探測和生態探測[34]。本次研究選取分異及因子探測器和交互作用探測器來探究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分布的影響因素[35]。分異及因子探測器公式為:
(9)
式中:n為區域的個數;L是指標因子分類數;nh,σh分別為h層樣本量與生態脆弱性的方差;PD,H為驅動因子D對生態脆弱性H的因子解釋力,取值范圍為[0,1],其值越大表示驅動因子D對該區域生態脆弱性的因子解釋力越強[5]。
交互探測器主要用于識別不同因子交互作用,即評價因子X1與X2相互作用后是否會增強或減弱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的影響,兩因子之間的關系可分為以下5種(表4)。

表4 交互作用探測器探測結果類型
3 結果與分析
3.1 生態脆弱性時空分布特征
利用ArcGIS與SPSS軟件實現研究區空間主成分分析,既減少了數據量又能保留原始指標足夠的有效信息。根據表2分級賦值標準將生態脆弱性分為 5 級,生成2010,2015和2020年的研究區生態脆弱性等級分布(圖1)。

圖1 川藏線(雅安-新都橋)2010-2020年生態脆弱性等級空間分布
從空間分布上來看,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整體分布特征呈從西向東先遞增后遞減趨勢。研究區西部比東部整體偏脆弱。重度和極度脆弱區主要分布在研究區內康定東部以及和天全縣、瀘定縣的交界處,此處海拔偏高,常年積雪,凍融侵蝕最為嚴重。研究區內康定西部生態脆弱程度主要由輕度脆弱與中度脆弱組成,并大致通過溝谷河流將其分隔,有溝谷河流處脆弱性相對偏低,反之較高。研究區東部雅安各縣區脆弱性以微度脆弱與輕度脆弱為主,其中天全縣西部、滎經縣西部與雨城區市區摻雜少許中度脆弱區。而研究區由西向東主要依次經過研究區內康定西部中度脆弱與輕度脆弱交叉區、康定與瀘定交界處重度脆弱邊緣區、瀘定與天全西部輕度脆弱區,以及天全東部與雨城區微度脆弱區。其中,在線路經過康定與瀘定交界處重度脆弱區附近時應注意環境保護。從時間分布上來看,整體屬于向好趨勢。中度脆弱區逐期減少,尤其是2010—2015年研究區內康定西北部與西南部和2015—2020年天全縣北部減少較為明顯。研究區東部微度脆弱區范圍逐期擴大,整體環境狀況較好。研究區內重度脆弱與極度脆弱區在2015—2020年康定與瀘定交界處重度范圍有輕微增大,但整體來說從2010—2020年范圍減小。
3.2 冷熱點統計分析


圖2 研究區2010-2020年生態脆弱性冷熱點空間分布
從整體來看,研究區西部為熱點聚集,東部為冷點聚集,西北與西南邊緣以及中部地區聚集不顯著。研究區自西向東大約依次經過無明顯聚集特征區、高值聚集區、無明顯聚集特征區和低值聚集區。結合圖2生態脆弱性分布不顯著區主要以中度脆弱與輕度脆弱的交叉地域為主,尤其研究區中部的不顯著區受復雜的地形地貌影響較大,導致同一地域脆弱性過于參差,呈隨機分布。2010與2020年冷熱點分布相對比較相似,2015年脆弱性較高地區范圍明顯較小,但整體趨勢沒有太大差異。
3.3 生態脆弱性驅動機制分析
前文中提取的6個主成分,雖不能完全代表所有初始因子,但大致包括了能對EVI構成影響的因素。因此,本次研究選取7個主要貢獻因子作為自變量,生態脆弱性綜合指數作為因變量導入地理探測器中進行分析,因子探測分析結果和交互作用探測結果分別如表5—6所示。由表5可知,雖然3個時間段內各因子對EVI的解釋能力均有差異,但總體上高程、年均氣溫和NPP對生態脆弱的影響較大,年降水量、降雨侵蝕力和生物豐度解釋力強度一般,地形起伏度對EVI的影響較低。2015年年降水量和降雨侵蝕力的影響力明顯相比其他兩年偏低,主要因為其年整體降雨偏少。研究區地處四川盆地西緣山地和川西高原的過渡地帶,地勢差異大,西部較高,處于高寒地帶,尤其研究區內康定市與天全縣、瀘定縣交界處凍融侵蝕較為嚴重,而東部較低,導致地域溫差較大,進而對生態脆弱性的影響也較大。另外,研究區按地理位置屬于亞熱帶氣候,適宜植被生長,再加上地形多變,人類活動程度較小,所以植被覆蓋較高,植被凈初級生產力對整體生態脆弱性的影響也較高。交互探測器分析結果顯示三年中地形起伏度和年降水量,地形起伏度與NPP以及降雨侵蝕力和地形起伏度,再加上2020年地形起伏度與生物豐度屬于非線性增強,除此之外全為雙線性增強關系(表6)。而且單因子影響力較強的高程、年均氣溫和NPP在與其他因子交互后影響力依舊較強,更進一步得出其是研究區生態脆弱性主要驅動因子。

表5 研究區2010-2020年各因子對生態脆弱性的解釋力強度

表6 研究區2010-2020年交互探測器分析結果
4 討 論
(1) 研究區生態脆弱性空間分布整體呈由西向東遞減趨勢,時間上生態環境狀況整體向好,符合一直以來國家政策對于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的支持。研究顯示研究區存在嚴重生態脆弱區,與劉軍會等[36]劃定的我國18個重點生態脆弱區之一,西南橫斷山生態脆弱區地理位置相符。其中康定東部以及與天全縣和瀘定縣交界處脆弱性最為嚴重,此處海拔最高,地形起伏度大,氣溫較低,凍融侵蝕嚴重,印證了前人得出的高寒地帶容易形成生態脆弱區的結論。
(2) 研究區域內地形復雜,板塊運動強,地質災害因子可能相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分布較為重要。考慮到本研究地災因子其中一項地質災害分布融入進了土地利用數據,可能致使整體的地災因子及其他因子在主成分分析后貢獻率發生變化,這里將地質災害分布從土地利用數據中提取出并設為新的獨立因子,再次利用主成分分析對所有因子重新賦予權重并最后計算出生態脆弱性分布(圖3),觀察其變化。

圖3 研究區突出地質災害因子的生態脆弱性空間分布
由圖3可知,整體來看,將地質災害分布數據獨立為一個因子后,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分布特征未發生明顯變化,脆弱性程度整體輕微增強,中度脆弱區面積增大。從時間分布來看,2010—2020年,脆弱性呈遞減趨勢,與原生態脆弱性變化趨勢相同。另外,研究區西部變化較東部更大,東部主要是極少部分微度脆弱轉變為輕度脆弱,可能與東部雅安地區地災點雖密集但險情相對偏小有關,再加上雅安地區生態狀況整體較好,使因子的輕微變化并不能發揮明顯的作用。
(3) 關于生態脆弱性評價方法的選擇,除了前文中提到的應用較廣泛的幾種研究方法外,在現今多學科交叉的研究環境下,基于深度學習與神經網絡的生態脆弱性研究也已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之后可進一步改進研究方法使研究效果更準確、更符合實際。
5 結 論
(1) 空間上,研究區整體脆弱分布為由西向東呈逐步遞減趨勢;時間上,由2010—2020年生態狀況整體向好。重度與極度脆弱區范圍較小,占總面積的3.95%,主要分布在研究區中部偏西康定市與天全縣、瀘定縣的交界處,此處為高寒地帶,凍融侵蝕較為嚴重。研究區由西向東依次經過研究區內康定西部中度脆弱與輕度脆弱交叉區、康定與瀘定交界處重度脆弱邊緣區、瀘定與天全西部輕度脆弱區,以及天全東部與雨城區微度脆弱區。在線路施工經過康定與瀘定交界處重度脆弱區附近時應注意環境保護。由冷熱點分析結果可知,EVI分布有較強聚類特征,研究區東部雅安地區低值集聚較為明顯,中部偏西為高值集聚區,而西部邊緣與中部康定雅安過渡區生態脆弱呈隨機分布。
(2) 影響研究區生態脆弱的主要驅動因子為高程、年均氣溫以及植被凈初級生產力,研究區地處四川盆地西緣山地和川西高原的過渡地帶,地勢差異大,導致地域溫差較大,進而加劇了對生態脆弱的影響。另外研究區地形多變,開發率較低,又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植被凈初級生產力對生態脆弱的影響也較高。
綜上所述,川藏線(雅安—新都橋段)施工建設在雅安區受降水影響較大,在康定區受地形以及溫差影響較大,在康定東部地形起伏度較高地區要注意地質災害防控。川藏鐵路建設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保護與生態維持也是今后當地社會建設的工作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