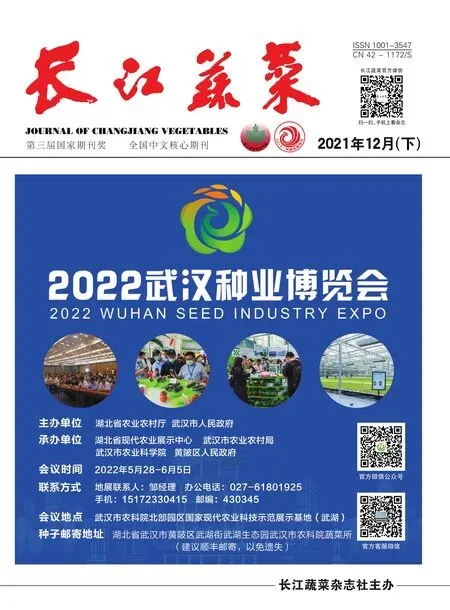『菜籃子』產品保供穩價的路在何方
——以武漢市蔬菜為例
張凱 張麗琴 張耀 劉吟
“菜籃子”產品是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品,一旦出現短缺就會影響生產生活和社會安定。在菜籃子產品中,蔬菜是一個勞動、技術密集型產業,相比畜牧、水產及糧食產業,其機械化程度較低,產銷風險更高。為建立菜籃子穩價保供的長效機制,各級政府有關部門、社會各界學者紛紛諫言獻策,見諸雜志、報端的研究林林總總,但真正從產業鏈、供應鏈深挖和剖析蔬菜產銷的難點、痛點問題不多,其保供穩價的舉措難以長效。筆者經過基層的調查研究,以案例分析形式,提出不同的見解,供決策者參考。
1 城市蔬菜產銷發展現狀
武漢是一個擁有1 418.65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按照《中國居民膳食指南》確定的蔬菜食品日攝取量300~500 g標準,全市蔬菜日保供量應為425萬~710萬kg,年供應量155萬~259萬t。至2020年底,武漢建設有百萬畝蔬菜基地,其中設施蔬菜35萬畝(2.33萬hm2),露地蔬菜45萬畝(3萬hm2),一季園15萬畝(1萬hm2),平均復種指數2.5次;全市擁有龍頭企業303家(其中涉菜龍頭145家),農業專業合作社5 010家(其中蔬菜專業合作社1766家),蔬菜種植大戶500家(其中核心科技示范戶160戶);建設蔬菜大型中心批發交易市場4家、集貿市場5 000余家(其中標準化菜市場318家),大型涉菜超市100余家。
1.1 產銷季節性短缺與過剩
全市蔬菜產銷的季節性、結構性短缺與過剩,帶來菜價不穩定。武漢市近3年來蔬菜播種面積保有量在240萬~260萬畝(16.00萬~17.33萬hm2),年產量580萬t左右。理論計算武漢自給有余,但結構性供給分配不均。從短缺期看,上半年地產菜集中在元旦、春節和4月下旬5月上旬,下半年集中在7月下旬8月上旬。短缺期間日供應量僅有120萬kg左右,不足日需量的40%~50%,50%~60%需要外埠調劑;從過剩期看,地產菜集中在5月中旬至7月中旬,日供應量在1 000萬kg以上,60%以上蔬菜需銷往外地市場。
1.2 突發性風險難以預料
全市菜地規模、市場布局應對一般風險沒有多大問題,但突發性風險卻難以預料。如2021年前期連續低溫、陰雨、寡照,主產地發生暗漬、澇災,導致產量縮減、上市延遲。同時,由于石油價格上行,運輸成本增高,終端價格普漲。自7月下旬以來以菠菜為代表的葉菜價格暴漲,甚至在同一個超市,出現了買1 kg菠菜的錢可以買2 kg豬肉或3 kg雞肉的情況。
2 蔬菜穩價保供難點問題及成因分析
2.1 基地排灌設施工程不可持續
武漢市農業地理環境中“旱包子”“水袋子”的基地接近耕地面積的30%。自20世紀90年以來,市政府投入巨額資金開展流域治理和“高標準農田”建設,如東西湖的高灌渠工程,新洲橡膠壩蓄水工程,江夏南八鄉的百塘堰蓄水工程,黃陂和蔡甸西南部、漢南東部的排水渠工程等,僅解決了一段時期大水排灌問題,但水到田頭的最后一公里一直未妥善解決。深層次問題是投資建設的排灌渠道大多是明渠,容易氧化腐蝕而損毀,加上無專人監管與檢修,年限一長就失去工程效益,導致棄耕現象時有發生。而發達國家的小農水都是管道到田頭。我國云南大理市的小農水也做得很好,當地政府利用高原雪山的水資源興建大型蓄水庫,地下管道網到田頭,村村都有供水加壓站,鄉鎮有專職水管員,農戶只需發一條信息或打一個電話,就能打開水閥,解決了灌溉用水問題,實現了農田灌溉的可持續。


2.2 土地流轉缺乏生機和活力
目前武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施土地流轉的土地40%左右未經過平整,難以實施機械化操作。即使企業實施農田改造獲得政府財政支持,其自身也要承擔50%~70%建設費,使新型農民不堪重負。如武漢香飛農園在東西湖柏泉街先后流轉土地300畝(20 hm2),僅其中80畝(5.33 hm2)土地的平整、灌溉設施配套就自掏30萬元資金。而在江浙一帶,凡列入土地流轉的地方,政府不僅在流轉前進行土地平整,還會在流轉后對從事生產的新型經營主體給予各種政策補貼,以刺激生產的積極性。土地流轉的優惠政策也未落到實處。如國家發改委曾出臺實施土地流轉優惠政策,凡符合流轉的土地,可享受5%的農業附屬設施建設用地。然而,各地在執行上就大不一樣了。在湖北這一政策基本未落地,真正享受政策落地的業主不到5%。大棚房整治讓企業苦不堪言,筆者在“壟上[蔬菜圈]產業官方群”看到,湖北某市一業主發出了“辛辛苦苦十幾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哀嘆!可見這一問題不單是武漢有,其他地市州也存在,是否為湖北的一大“特色”筆者不敢茍同。而東北就不一樣了,2019年6月全國農業產業園區會議期間,筆者參觀了遼寧沈陽、盤錦2個城市的創意農業園和休閑農莊,所到之處,看到的稻田棧橋走廊、木質結構觀景臺、園區生態餐廳均保持完好,體現出濃郁的生產、生態、生活的“三生”氣息。因為這里被占用的農田,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及時調規了。湖北的土地流轉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用足用活政策,也缺乏法律法規保障。
2.3 鄉鎮農技推廣體系網破線斷人散
在全球生態環境平衡被打破的狀態下,近些年來自然災害和重大農作物病蟲害呈頻發多發態勢,由于技術支撐單薄,政府對地產菜保供的底氣不足。根本原因是湖北基層農技站所的事業編制被取消,推廣體系早已網破線斷人散。雖然在改革中推行以錢養事的手段來彌補,但承擔這些以錢養事的農技人員都是失去事業編制的人員。農忙或病蟲害發生的時候,他們忙于自己的農資經營,難以對當地農業生產及時指導到位。同時還存在基層技術服務后繼無人的問題。
2.4 能源價格上行拉升蔬菜成本
石油方面以柴油為例,2020年10月均價為4 960.1元/t,2021年10月為7 440.2元/t,上漲幅度達50%。據一位農業經營者分析,僅油價上漲拉升蔬菜成本0.6元/kg(其中汽油拉升成本0.16元/kg)。汽柴油價格上漲促使運輸費用跟漲,拉動菜價上漲。
農資方面以肥料為例,2020年尿素價格1 800~2 100元/t,2021年曾一度上漲到3 200元/t,近期價格雖回落到2 400元/t,但仍然高出2020年同期20%~40%;磷、鉀肥價格也比2020年上漲40%~60%,如磷酸二氫鉀2020年7 000元/t,2021年上漲到12 000元/t。僅肥料一項投入就增加成本30~50元/667 m2。種子、農藥、肥料投入的成本每667 m2年達到500~600元,高出常年200元左右。農資價格的攀升推高了菜價上漲。
2.5 勞動力用工成本高企
前些年農業勞動力用工費每人80~120元/d,近年來農村青壯年勞力大量外出務工,農業用工荒日益凸顯。據東西湖一家合作社老板介紹,現在勞動力難找,即使找17歲左右的短工,日付勞酬也在150元;70歲左右的勞力,日付勞酬200元。農業用工難、用工貴成為阻礙企業發展的痛點問題。據調查統計分析,現在從事農業的新型經營主體,除了種植大戶、家庭農場尚有微利外,農業企業85%虧本經營、10%保本經營、5%盈利。可見不解決土地平整和農機化作業的問題,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步履維艱。
2.6 營銷體系不健康
一是蔬菜從產地到市場,存在層層盤剝和價格打壓的現象。在產地,蔡甸區張灣街五一村的一群農民反映,菜販子到產地收購的蔬菜要比批發市場價格低出0.8~1.2元/kg;在市場,一位多年從事蔬菜生產與經營的業主介紹:自己的菜進市場交易,不是行幫壟斷蔬菜收購價,就是菜販子合伙砍價。即使國有商超也有難以直言的痛楚,如蔬菜進某大型超市,一般1個月以上才結算,而且給出的價格比批發市場的交易價格還低。
二是產地市場拆易建難,賣菜難問題得不到根除。隨著城市建設的擴充,原近郊的產地市場先后被拆除,而新開發的菜地又沒有興建。據東西湖柏泉農場東湖大隊一位年近六旬的菜農反映,過去自己的地產菜可踩三輪車直接到交易市場出售,現在交管部門不讓三輪車進城,自己因年齡較大沒有考取駕照,再也不能進城賣菜了,加上沒有產地批發市場,只好讓菜販子賺差價。
武漢某新城區一新型經營主體負責人向筆者算了一筆賬:種植667 m2爆汁番茄,土地租金1 500元/年(設施大棚),肥料費用400元,農藥150元,架材費用1 000元(以吊繩代替架材500元),農膜1 500元,噴滴灌200元,勞動用工成本1 500元,生產的直接費、間接費投入需要0.6萬元以上,如果年收入達不到1萬元/667 m2,菜農就無利可圖。
日本的蔬菜經營就很規范,日本每個村都有農協組織,每個農場主都是農協的會員。一方面農協承接政府的轉移職能。如農協辦的村鎮銀行給農民發放各種補貼。另一方面,農協也承擔經營管理職能。產前各種生產資料由農協統一購買,菜農產后的蔬菜由農協組織到市場競價批售,其銷售收入直接返還菜農。既節省了菜農的用工成本和價格成本,而且年終還可參加農協的二次分紅。我國也有農業專業合作社組織,但沒有承擔政府服務外包職能,其組織服務能力就難以言表了。
2.7 政策性扶持的陽光未照到現實生產者
在用地政策方面,工業用地政府給予“三通一平”“七通一平”的支持,農業用地連“兩通一平”都無保障。其根本原因就是農業沒有稅收,政府無支持的積極性。土地不平就難以實施農業機械化操作,必然會增加農業的勞動用工成本。
在經營性設施方面,2013年武漢市為提高快生菜的保供能力,出臺了7萬畝設施大棚建設實施方案,對200畝(13.33 hm2)以上連片建設的大棚,政府給予1萬元/667 m2的補貼。其投資補貼政策吸引了一批建筑老板進入,但他們對農業外行,形成了“一年紅紅火火,二年蕭蕭條條,三年人不見了”的慘淡結局。而一批農業技術能手由于受投資門檻和資金限制被拒之門外。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一設施大棚建設政策補貼的陽光,沒有真正照到懂技術、善管理、會經營的能手身上。
3 蔬菜保供穩價對策建議
3.1 建立和完善土地經營體系
對于空心村或土地撂荒嚴重的村,以村級為單位,村集體經濟組織牽頭,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鼓勵農民以土地入股形式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變農民為股民。土地股份合作社代理農民管理耕地,并向當地政府申請土地平整項目,項目建成后實施土地流轉,代表農民將耕地對外招標,向有實力的農業企業發包。土地股份合作社既承接政府服務職能轉移、組織各項補貼和財政轉移資金的發放,也負責對承接土地流轉的農業企業實施財務監督,確保農戶參與分紅的既得利益。
對于非空心村或土地撂荒不嚴重的村,由村委會推薦懂經營、善管理的能人牽頭,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鼓勵家庭農場、種植大戶加入專業合作社。合作社參照日本農協的模式,既承接政府的轉移職能,也履行經營管理職能。家庭農場、種植大戶根據各自技術優勢,選擇1~2個特色品種生產,形成以“一場一品”“一戶一品”為主的錯位種植特色。對于冬季撂荒的土地,鼓勵合作社直接采取季節性流轉種植越冬菜,以豐富蔬菜市場花色品種。秋冬菜采收后將農田返還農民,變冬閑田為冬儲田。
3.2 建立韌性農業政策體系
伴隨全球通脹預期的到來和生態環境平衡的打破,經濟風險的疊加倍增,韌性經濟、韌性農業成為發展的主旋律。引入韌性所特有的靈活調整政策,建立以不變應萬變的決策體系,防止“菜比肉貴”的風險硬著陸。
一是土地流轉的政策要落地,給農業新型經營主體一個支點。建議凡規模達到200畝(13.33 hm2)以上的農業業主,準許按5%用地搭建農機具、農產品分揀、倉儲冷鏈等附屬設施用房。對于需占用基本農田的用房,當地政府及其土地部門要盡可能地實施土地規劃調整。沒有就地建設調整空間的,也可按照流轉規模所享有的用地政策,批準異地建設。
二是菜地基礎設施要配套,給農業生產創造多種便利條件。建議要科學規劃設計農田排灌設施,建設的政策性補貼要有連續性,給新農人一份獲得感。
三是農機化作業要全程,給農業減輕勞動強度以出路。目前機耕、機耙、機整、開溝等農機作業比較配套,但蔬菜的機收還存在盲區。需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農機設施設備,實施技術再創新。
四是水管隊伍要建立,給農田排灌以保障。建議在街鄉鎮事業編制上作適當調整,在街鄉鎮配備一名以上水管員,行政村配備一名以錢養事的水管員,以便及時做好水務調度服務。
3.3 建立和完善農技推廣支撐體系
解決農業科技服務的最后一公里,需要有一支常走在田頭地角的基層農技推廣隊伍。當務之急是解決網破線斷人散的問題,建議在街鄉鎮中調整人員編制,大型街鄉鎮配備3名以上農技人員,小型街鄉鎮配備2名以上農技人員。以便及時有效地為農業生產者做好田間技術指導服務。市、區農技推廣部門是農業“四新技術”推廣的主力軍,每年要開辦1~2個生產示范區。科研院所和涉農高校要根據技術人員結構或設置的涉農專業,每個科研所或農業學院要在對口幫扶村辦一個示范點。
3.4 建立和完善市場營銷體系
一是規范蔬菜批發交易市場的秩序。出臺相關規范性文件,禁止市場經營者強買強賣,徹底根除欺行霸市行為。
二是降低蔬菜進超市門檻。建議大中型超市讓利于民,凡進入的蔬菜要縮短貨架回款期。
三是持續開展農產品產地批發市場建設。建議對蔬菜連片種植面積達到1萬畝(667 hm2)的產區,準許建設一個產地批發市場,以方便產地菜農就地就近銷售。
四是賦予綠色通道車輛以更多實惠。建議政府可在每年的財政預算惠農資金中切一塊,用于綠通車輛的油料補貼。其石油補貼發放方式,可采取票券形式,也可采取以車牌標識等其他形式。
3.5 建立和完善蔬菜產銷保障體系
一是建立和健全土地流轉的法規體系。建議制定《關于農村土地流轉若干問題的管理辦法》的規范性文件,將土地流轉期間建設的經營設施作為企業貸款抵押資產、土地流轉到期后經營者有優先再流轉的權利等納入文本中,讓新型經營主體放得心、留得住。
二是建立和健全物價監督體系。切實加強物價監督,建議制定《關于鮮活農產品銷售若干問題監管暫行辦法》,對高出產地菜價4倍以上的鮮活農產品實施價格監督與調控,以減輕消費者承受壓力。
3.6 建立和完善蔬菜保供穩價應急預案機制
一是建立和完善災害風險預警應急機制。建立由氣象、水務、栽培、植保、市場營銷專家組成應急專家團隊,運用“互聯網+農業”實施風險在線監測,年度、季度綜合會診分析,提出針對性應急預案,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
二是建立和完善突發事件處置機制。建立由農業、商務、市場、物價等部門組成的領導小組和工作專班,對突發性蔬菜等鮮活農產品短缺、價格暴漲實施監控,并拿出調劑余缺的政策性戰時應對措施。
三是建立和完善農產品市場流通運行機制。在完善批發市場、標準化菜市場規范經營的前提下,鼓勵蔬菜直銷配送到社區,以減少中間盤剝。建議制定蔬菜直通車進城管理辦法,準許蔬菜房式直通車在居民聚集小區周邊限時占道賣菜(西歐、美國有范例)。完善農產品電子商務進小區,方便上班族居民網購和就地取貨。確保“菜籃子”產品調得進、供得上、不斷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