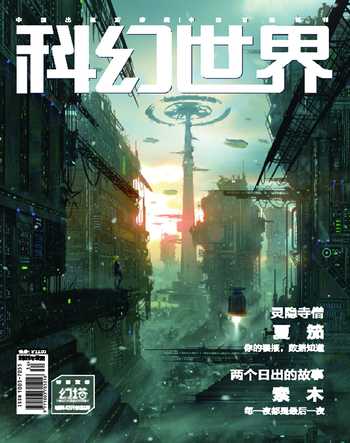菌之球
主持人說:
這兩個月最熱門的科幻話題莫過于《沙丘》電影版的上映,相信不少讀者已經通過大銀幕感受這部科幻巨制的魅力。但也能聽到一些觀眾對電影呈現的科幻感表達了質疑,畢竟整個電影只拍攝了第一本書前一半,單看劇情就像一個傳統的“哈姆雷特”故事。弗蘭克·赫伯特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作了這部作品,真正的科幻核心當然不是簡單中世紀權謀故事,而是沙丘本身——厄拉科斯星球的生態系統。這可是和當下最受關注的生態環境話題緊密相關,極具前瞻性。沙鱒—水—沙漠—沙蟲—香料構成了十分完整的生態閉環,使得厄拉科斯從一個有著濕潤氣候的星球變成了“沙丘”。
腦洞時間:
如果可以利用其它生物反向侵蝕沙漠,又會造成怎樣的一番景象?
嘉賓介紹:
王諾諾,女,青年科幻作家,榮獲第二十九屆銀河獎“最佳新人獎”。
每年的三到四月是種菌子的時節。整個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到處都能看見飛揚的塵土、成堆的木枝和蹲伏著的種菌人。
全世界范圍內沙漠種菌的工程已經啟動了五年。
在五個忙碌的春天過后,這里的主色調還是對比度極低的灰黃。開車三個小時,偶爾遇到幾叢毛茸茸的檉柳,一陣風卷過,就被流沙埋入滾燙的地平線下。
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里,人們日復一日種下一種特殊的菌子,名叫綠環菌。它們的“祖先”赫赫有名:地球上單體最大的生命,蜜環菌。人們曾在美國密歇根州原生森林的地下,發現達到9.6平方千米的蜜環菌菌絲。那一簇蕈菇用了二到四千年的時間,長成了兩千個美式足球場大小。
但在古爾班通古特沙漠,綠環菌面臨的不是泰加森林宜人的氣候。夏季是40攝氏度以上的極端酷熱,冬天是零下40攝氏度以下的極端嚴寒,干熱和干冷輪伺,直至漫漫黃沙被蒸干最后一滴水分。
種菌人將沙土用草方格畫為一米見方的井字,每個草方格內,被固住的那一平沙的正中央都被掏挖出一個淺坑,放入油脂含量極低的椴木段,摞成一個松散的枯木架,再在木枝上鑿一些小坑,嵌入幾塊綠環菌菌種和幾枚天麻種子。
井字格綿延數平方千米,曾經無序的沙脊被劃成密密麻麻的正方塊,沙土下的菌絲和天麻種子就是沙漠成為綠洲的希望。
十年前,科學家用crispr技術對蜜環菌的DNA進行基因編輯,得到的綠環菌擁有更強的保水、輸水能力,和更快的生長速度,可以良好適應干旱環境。同時,它的菌絲分泌出酸性物質,有效分解巖石和砂礫,能幫助沙漠形成富含有機物的健康土壤。它將是改造地球上所有沙漠的關鍵生物。
種菌的季節過去,為了避免陽光直曬,所有草方格里的菌種都被沙土掩埋,沙漠又恢復了它千萬年來的樣子。
種菌人的車隊開走,掀起一片揚塵,這里就像從來不曾有人來過。
沙漠種菌工程的第四十五個年頭。
除了守著祖輩基業的那幾戶人家外,職業的種菌人已經少之又少了。
所謂的基業,就是那些被風沙侵蝕得不成樣子的幾千平方千米的草方格。
風沙不僅在枯草、腐木上留下了痕跡,也在種菌人臉上劃出一道道皺紋。他們的工作在旁人看來是千篇一律的,秋天從南方草原收集牛羊不吃、發黃老掉的枯草,扎成一捆捆的草垛。到了陰冷的冬天,在自家地窖砌起矮墻,培育劍麻和綠環菌菌種。第二年開春,就像切葉蟻一般,把囤了一冬的稻草、腐木,養了許久的菌種、天麻拉到荒漠和戈壁上,均勻鋪灑開來。
春夏秋冬周而復始,只是為了驗證五十年前科學家的一個理論——在吃飽了腐木提供的營養之后,綠環菌的菌絲會在荒漠的地底深處生長、蔓延,尋找地底和周遭的水源,再把水順著菌絲帶回沙漠中,養活寄生的天麻,構成沙漠中最早的拓荒生態。
附近的幾百畝地的種菌人只剩下一個了,外孫女仰頭望著他發黑皴裂的臉:
“外公,我們種的蘑菇什么時候能冒出來呀?”
“你說的蘑菇叫作‘子實體’,只是綠環菌身上很小的一部分。”
“很小的一部分?”
“嗯,蘑菇只是菌子露出地上的那一部分,而菌子的本體在地下。在自然演化過程中,它選擇了一種特殊的生長形態——細長的菌絲。盤根錯節的細長條就在砂礫之間生長,擊碎巖石和礦物,尋找水源和有機物。可能啊,它們在地下已經長得好大了,但就是不愿意把頭探出地面來,長出子實體傳播孢子。所以,外公和妞妞都沒辦法看到漫山遍野的蘑菇。”
“它們真的在地下長大?但是為什么他們說外公這么多年的蘑菇白種了,菌子都沒活下來。”
種菌人看著孫女,一時語塞。沒人知道腳下的綠環菌是否真的存活,地面黃沙一片,跟數十年前、數千年前別無二致,他只憑不能回頭的那一股倔勁兒接過父親的衣缽,堅持到今。至于外孫女,她是否還要重蹈自己的命運?
種菌人也沒有答案。他蹲下身子,輕輕拍拍外孫女的背:
“妞妞還記得爺爺教你的兒歌嗎?”
女孩兒點點頭:
“三月菌子六月天麻,天麻不長根,菌子不開花……”
兒歌的聲音隨著車輪鳴響漸漸遠去。在他們身后,誰都沒有注意到,一叢淡綠色的嬌弱菌傘正掀起頭頂的流沙,從地平線下冒出來。
這邊是世界上第一顆旱地蕈菇——綠環菌的子實體。
這一年,綠環菌的菌絲已經遍布北半球。
菌絲向前生長時,堅硬的頂部可以擊碎巖塊和碎石,將砂礫研磨成適合植物根莖成長的細顆粒土壤。綠環菌如同消化能力極強的一顆胃,哪怕再干涸而貧瘠,荒漠中的有機物和礦物質都可以被綠環菌釋放的酶分解,轉化成可以吸收的養分。
至于那些跟綠環菌共同種下的天麻,它們無法制造有機物,塊根直接吸收了綠環菌菌絲,植物細胞與菌絲生長嵌合在一起,成為了巨大有機生命體的一部分。
就這樣,荒漠上盛放出一片片蕈菇和一簇簇天麻。而這些開拓者完成生命周期后,尸體又變為腐殖質,和細顆粒的沙土混一起,那是植物成長的最好土壤。
“我小的時候,這里還是一片沙漠,現在已經綠化了。喬木和灌木從綠環菌開拓出的肥沃土壤里冒出來,野生動物也開始在這兒定居。”老師在課堂上對著孩子們說道。
“但是老師,我還是弄不懂一個問題,就算土壤富有肥力,植物生長所需的水從哪里來呢?”
“你的腳多大?”
少年愣了一下,說:“36碼。”
“36碼的腳,那就是23.5厘米長,粗略地算,你腳下的面積是0.02平方米。如果你將這一小塊土地下面的綠環菌菌絲首尾相連,那便是500千米。正常人的走路速度是五千米,五百千米要走一百小時。開車的話,以時速一百千米算,五百千米要開五小時。”
“菌絲竟然有那么長!竟然有那么多!”
“是的,這些密密麻麻的細長菌絲構成了一條水汽輸送網,將沙漠地底深處的水抽上來、遠處綠洲的水運過來,一滴也不放過,都輸進了天麻的塊莖里。”
說到這里,老師咳嗽了幾聲。最近他總是覺得胸悶發熱,但學期末了不能耽誤孩子們的課程,便一直忍下來。
“老師,您沒事吧?”
“沒事,同學們還是要注意身體。不要因為生病耽誤了功課。據說這次的感冒連抗生素都不太管用,平時大家還是要注意鍛煉身體。”
講臺下,另一只手舉了起來:“那么老師,未來我們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也會成為一片大綠洲嗎?”
“會的,再過二十年,地下的菌子再大些、廣些,到處充滿了樹和動物,形成了可以對抗惡劣環境的生態系統,那時這里就能成為一片生機勃勃的綠色森林!”
現在這里是一片綠色。
沒人能抵擋得住這致命的綠色,周遭的校舍和居民樓已經荒廢,好不容易墾出的農田長滿了稗草。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這綠色由兩部分組成:幽深沉靜的墨綠,是樹冠和草本植物的顏色;嬌艷欲滴的翠綠,則來自綠環菌的菌傘,細細密密地鋪滿地表和樹干,發著詭異的熒光。
一輛改裝過的越野吉普闖入寧靜的綠色。
“趕緊回來!這是命令!掉轉車頭原路返回,現在還來得及!”對講機里傳出的聲音幾近歇斯底里。
但開車的人卻不以為然,他的面部戴著厚重的生化面具,防護服將每一寸皮膚都包裹在純白之下:“頭兒,那么緊張干嗎?雖說穿這身確實不太好開車……但我會注意不出交通事故的!”
說罷,他一個急轉彎,避開了迎面倒下的腐木,這一動靜讓車尾差點兒甩出路面。
“你瘋了!獨自一人開車去綠環菌密集的森林!別忘了當初是誰救你下來的!你想讓她白死嗎?!”
“那天我去看她的埋骨之地,現在已經是一片綠色的沼澤。如果你不想全世界都變成綠色,那么今天就讓我去吧!”
開車的人掐斷了無線電,周遭除了引擎聲,只剩下一片樹葉簌簌發響——這是死亡臨近的聲音。
沙漠種菌工程已經啟動了八十年。這項初衷為改造荒漠的綠色工程,有過輝煌的過去和短暫的成效,但它最終卻釀成了令人類陷入滅絕深淵的災禍。
相比曾在歷史上成為人類頭號殺手的細菌與病毒,真菌作為病原體通常不那么引人注目。大多數真菌適合在陰冷潮濕的環境生長,而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哺乳動物找到了對抗致病真菌的不二法門:溫血。鮮少有真菌能夠在37攝氏度的恒定體溫中存活、繁衍,自然也就對人體環境束手無策。
但綠環菌不同。作為基因定向改造的物種,它不懼酷暑,更何況人體溫度。然而在納米比亞西部富含鈾礦的納米布沙漠地區中,這種原本無害的蕈菇發生了基因突變,并通過地下網絡“感染”了遍布整個北半球的地下菌絲網絡,變成了可以寄生人體的病原體——它的孢子可以如同繞開土壤中的阿米巴原蟲攻擊一般,欺騙人體的巨噬細胞,對免疫系統“隱身”。
綠環菌孢子主要經呼吸道侵入機體,引起肺部感染,發熱、頭疼、肺水腫、呼吸功能停滯,最終導致人體的多器官衰竭。若進入血液,侵襲中樞神經系統,導致真菌性腦膜炎,大腦會像奶酪一般被綠環菌孢子“蛀”出乒乓球大小的窟窿。
更加糟糕的是,不同于細菌引發的呼吸道炎癥,真菌型疾病是完全不怕抗生素的。人類一旦感染了變異后的綠環菌,沒有特效藥醫治,只能任由病情一步步加重,眼睜睜看著自己器官衰敗,失去活力和健康,成為一灘巨大的培養基。
“誰想做培養基啊?!”開車的男人打開車載音響,吉他的旋律伴隨著甜美的女聲流淌出來。災難爆發以來,地球人口驟減80%,科技、工業倒退至百年前,這盤老舊的磁盤因為被多次播放已經出現失真。
他們是“溯源志愿者”組織,負責在全世界尋找最早的一批變異基因菌株。但由于菌絲為了適應不同的環境迭代極快,加之生長在地下,始終沒能成功。
男人深入曾經的沙漠。現在,這里長滿綠環菌主導的真菌次生林。地下是無處不在的由綠環菌菌絲和喬木根系組成的菌根,菌根所蔓延之處,原有的生態系統就會土崩瓦解,從土壤里先鉆出綠環菌和天麻,空氣中散播致命孢子,絞殺一切哺乳動物,它們的尸體與天麻一道,又成為喬木和真菌最好的養料。
幸存的未感染人類只有躲藏到寒冷的北半球島嶼,那里由于海洋的阻隔,尚未被無情的殖民菌種侵染。但誰又知道呢?或許某天哪只飛鳥和哪陣季風又會把微米級的孢子顆粒帶過來,然后,地球上就真的再無一片凈土。
男人看了看此時的坐標,帶著鐵鍬下了車。
他躬下身,將鐵鍬狠狠捅入大地深處,挖出一抔土,用幾層密封袋裝好。這里面含有的菌根數量,足以完成實驗室對初代變異綠環菌的基因分析。運氣好的話,甚至可以幫助人類找到0號變異菌株。
“如果找到0號變異菌株……說不定就可以……”男人自言自語道,他感到呼吸困難,多天深入菌株密集區的旅途讓他大量暴露在感染風險中,防護服在這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說不定,就可以……”他忍住了咳嗽,帶著密封袋上了車,按照現在的身體狀態,堅持到1600千米外最近的菌群觀測點,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只要到了那里,就能見到人類,把樣本交出去,他的心愿就算完成了。
“只要找到0號變異菌株……說不定就可以再見到你的時候,沒那么多遺憾了。”他瞥了一眼掛在后視鏡上方的吊墜,那里鑲嵌著一個女人殘舊的照片。
他踩下油門,照片里眼睛很漂亮的女人隨著車子啟動輕晃了一下。

從高軌道看地球,是玲瓏剔透的。
這里的“玲瓏剔透”就是字面意思。地球作為一個實體的“球”已經消失了,它被一顆巨大的菌體吸收,菌絲在原本是地殼的地方,盤踞成球的形狀,這代表著地球原來的形狀。
在長達數億年的進化過程中,每個生命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有的耐旱,選擇了沙漠;
有的愛水,選擇了海洋;
有的志向遠大,選擇進化出能力卓越的大腦,用它來制造工具,改造世界;
而真菌,卻選擇了最簡單的生命形狀——細長的絲狀,那也是最堅韌、最強大的形狀。它打通一切巖礫,鉆入所有縫隙,成為地殼中無處不在的一個部分,分解、吸收物質之后,從土壤中冒出蕈菇,利用空氣散播孢子,把自己播散在更遠的地方。慢慢地,一切有機和無機體都成為了它的營養,你已經分不清菌絲和培養基的界限,地球本身……成了一顆巨大的蘑菇!
“我們的祖先,人類,曾經輸給過一種叫綠環菌的真菌。”一個意識說道。
“后來怎么又贏了呢?”另一個意識問道。
“因為人類發現必須拋棄自己作為動物的形態,才能進入生命的下一個階段。在經歷了艱苦卓絕的探索之后,人類把文明上傳到了由菌絲團構成的云腦之中,菌絲的化學信號儲存著我們所有人類時代的記憶。而我們的祖先用這種方式將人類文明以真菌的方式繼續延續。”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任務?吸收營養、生長菌絲、繁殖、再將孢子散播到更遠的地方?”
“是的,承載有人類記憶的超級真菌就這樣戰勝了綠環菌。而我們現在已經進化出了可以在真空中傳播的孢子,要將人類文明送到更遠的星球上。”
“孢子在星系中飛,那要多久?”
“無數的孢子朝向無數的方向飛,真空中沒有阻力,但充滿射線,也會遇到星際塵埃,但總有孢子會飛到新的星球上,無論那里是沙漠還是海洋,是否存在著類似地球的空氣,孢子都會生長出菌絲,改造那里的環境,并把存儲在化學信號中的人類文明散播出去。”
“小小一顆孢子,能攜帶多少文明的信息?”
“我們把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信息留下了。”
“那是什么?”
“只有一句話——活下去。如果說,細長的絲狀是生命的終極形態,而活下去則是每一個生命的最終渴望。”
菌絲構成的云腦中的意識不再“說話”,它們寂靜下來,將更多的能量投入到繁殖和生產孢子的過程中。終有一天,屬于曾經的藍色星球的秘密,會隨著它們擴散到所有的時間和空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