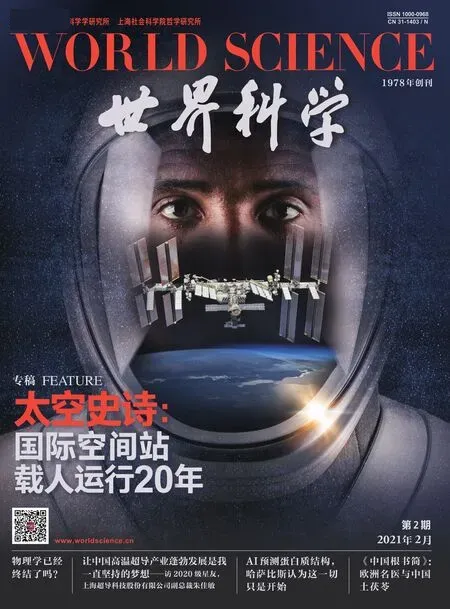劍橋三一語絲
英國劍橋大學大約創建于1209年,是一個由31個自治學院組成的聯邦大學,她的治理權力和功能被劃分在大學的行政中心和各學院之間。劍橋的聲望是建立在牛頓、培根、丁尼生、麥克斯韋、哈代、霍金等名人之上的,正如劍橋大學的校訓“啟蒙之所,智知之源(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
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是由英國國王亨利八世于1546年創立,由原來的兩個學院(創建于1317年的國王學堂和創建于1324年的麥可學院)合并而成,堪稱科學家的王國、詩人的殿堂。三一學院的校訓是“美德乃真正的高貴(Virtus Vera Nobilitas)”。
三一學院16世紀的著名本科生包括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1661年,艾薩克·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進入三一學院成為本科生,一直到1696年,他的最重要的數學和物理學工作在此間完成。19世紀早期的本科生包括拜倫勛爵(Lord Byron)、丁尼生勛爵(Lord Tennyson)等。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本科生包括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約瑟夫·約翰·湯姆森(Joseph John Thomson)、歐內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路德維格·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從1904年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瑞利勛爵(Lord Rayleigh)至2019年諾貝爾獎得主迪迪埃·奎洛茲(Didier Queloz),三一學院共有34位諾貝爾獎得主。
在我的心目中,英國劍橋是一個可望不可及之地,能夠來劍橋真是一個奇跡。每次來到劍橋,都令我超乎想象地興奮:歷史悠久且保護完好的宏偉建筑、青翠欲滴的方庭草地花園,還有步履閑適而又優雅的學者……都給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
牛頓的蘋果樹
三一學院正門的右側原是牛頓的花園、實驗室所在地。后來,三一學院從牛頓家鄉移植了一顆蘋果樹至此(圖1)。這顆似乎永遠長不大、長不高的“牛頓的蘋果樹”陪伴著、激勵著一代代三一莘莘學子生活、學習。

圖1 三一學院原牛頓實驗室遺址上移植自牛頓家鄉的蘋果樹,亦正好位于牛頓當年宿舍的窗外下面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2016年暑期,我訪問三一學院時邂逅了一位英人長者。攀談后,得知他曾經是三一學子,今年返校參加年級聚會,充滿懷舊情懷。他向我講述,那時他還是個少年,知曉牛頓也曾同在此學習后,很受鼓勵。
三一學院榮譽院士、數學家、海洋學家克理斯·加雷特(Chris Garret)20世紀60年代在三一學院念本科,每當回憶起自己當年的宿舍就在牛頓宿舍頂上的小閣樓里時,依舊激動不已。三一學院的本科生到了高年級時,學院會安排研究生指導他們學習。加雷特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年作為研究生的約翰·鮑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輔導他時說:“我并不是最聰明的,但是,我離最聰明的足夠近,理解真正聰明的人在做什么。”
禮拜堂
三一學院又是一個宗教場所,自牛頓起,那里的教師和學生似乎明白:“宗教的目的不是教我們如何去死,而是教我們如何去活。”這句話引自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的小說《阿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
幾年前,我購買了《劍橋:大學與小鎮800年》一書(201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翻閱時,意外讀到有關當年牛頓申請研究經費的軼事:匿名同行專家根本不支持牛頓的研究,他們認為牛頓的研究毫無用處。當讀到這些時,我震驚了。一般人都知道牛頓對數學和物理學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牛頓也曾經申請研究經費失敗過,竟然也有得不到他同時代同行支持的經歷。不過,即便沒有研究經費支持,牛頓仍繼續從事他的研究,不曾中斷過。
2019年10月26日,我幸運地在三一學院教堂里的牛頓塑像前與菲爾茲獎獲得者威廉·蒂莫西·高爾斯爵士(Sir William Timothy Gowers)合影留念。在一位杰出的純數學家面前,我感到很慚愧,在滿足虛榮心的同時,我想以他為榜樣,學習好數學、講授好數學相關課程。
維嘎尼室
來自意大利維羅納的約翰·弗朗西斯 ·維 嘎 尼(John Francis Vigani)是劍橋大學的第一位化學教授,牛頓給他安排了一個化學實驗室,如今,它用作院士的房間,取名為維嘎尼室(Vigani Room)。此室現為流體力學家凱斯·莫法特(H. Keith Moffatt)院士所用,那天,莫法特在此房間熱情接待了我,還允許我拍照(圖2)。

圖2 維嘎尼室
偉大方庭與奇異恩典
“假如我今生無緣遇到你,就讓我永遠感到恨不相逢……”泰戈爾的詩句正是我在三一學院認識了諾貝爾獎得主后心境的寫照。
布萊恩·戴維·約瑟夫森(Brian David Josephson)是197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當年,他只有33歲。2019年10月10日,在劍橋三一學院的高桌晚宴(High Table)上第一次見到他時,我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位是諾貝爾獎得主。午餐后,在休息室喝咖啡時,莫法特介紹我認識了約瑟夫森。回到實驗室我即刻用郵件聯系他是否可以與他合影留念。他謹慎又友善地回復說:“三一學院有很多諾貝爾獎得主,無論怎樣,我們可以找個時間,莫法特作為中間人,我與你合個影。”就這樣,于2019年10月18日,我們就有了一張合影。上天似乎讀懂了我的心思,在劍橋深秋天氣多變的日子特意安排一段晴朗的時間,天空蔚藍如洗,讓我與約瑟夫森留下此美好的時光記憶。
2019年10月2日,基督學院外,偶遇三一學院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格雷哥瑞·保羅·溫特爵士(Sir Gregory Paul Winter),欣喜與他合影留念,內心夾雜著虛榮、鼓舞的喜悅之情。我是幸運的,會好好珍惜生命中的奇異恩典。
高桌晚宴
在劍橋大學訪研期間,我深深地享受著各個學院(共計31個學院)收藏、展示的肖像油畫之美。例如,三一學院餐廳正面墻上就掛有創始人亨利八世的巨幅肖像油畫(圖3),左邊墻上掛有歷任、現任院長的肖像油畫,右邊墻上掛著該學院培養的著名學者的油畫,包括牛頓在內的科學家、文學家等巨匠。三一學院的廚房里也有一幅牛頓肖像。
劍橋三一學院的高桌晚宴只允許該學院的院士或院士的客人用餐。莫法特是數學物理學家、流體力學家、劍橋大學應用數學與理論物理系原系主任、牛頓數學研究所原所長,作為莫法特的客人,2019年10月10日,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進入三一學院的高桌就餐。莫法特在兩張古舊的長方形餐桌中選了其中更舊的那張,我們坐下后,他對我說:“John(我的英文名),這個餐桌比牛頓還老。”接著他又對我說:“John,你可能坐在牛頓坐過的位置……”對我而言,他的鼓勵是受益余生、終身的,如此幸運的我,還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學習、研究、教學?那日,與我們同桌、正對著的分別是菲爾茲獎獲得者高爾斯爵士、三一學院副院長、流體力學家格瑞·沃斯特(Grae Worster),另一桌右上角正對著的是約瑟夫森。
劍橋三一學院的草坪只允許院士和院士的客人行走。2019年12月2日那天中午,湍流學家朱利安·查爾斯·羅蘭·亨特勛爵(Lord Julian Charles Roland Hunt)請我在三一學院高桌就餐。去餐廳的路上,他誠邀我行走在草坪上,他說我是他的客人,我謝絕了并解釋說:“我愛護草坪,也在中國教育同胞向英國人學習愛護草坪。”他理解了。飯后,他和我一道繞開草坪走回他的辦公室。
2019年12月12日,承蒙流體力學家約翰·利斯特(John Lister)教授夫婦的盛情邀請,我第一次有機會參加三一學院的正式晚餐。晚餐由化學家尼爾·肯尼斯 ·哈默(Neil Kenneth Hamer)主持,參加晚餐的還有歷史學家博伊德·希爾頓(Boyd Hilton)。晚餐開始前的禱詞為“愿神圣的主保佑我們”,晚餐結束前的禱詞為“愿神圣的主被頌揚”。
為什么英國皇家、政府、教育部能夠如此重視大學學院的餐廳?為什么英國普通民眾能夠理解大學生、教師本該享受此高檔餐廳?他們似乎都理解這樣一個神諭:我們富裕時,你從驕傲中拯救我們。我們貧困時,你從絕望中拯救我們。那么,你們無論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為榮耀他而做。

圖3 劍橋三一學院的餐廳,正對著的遠方墻面上掛的是創始人國王亨利八世的站立肖像,靠近國王肖像的即是兩排高桌。餐廳里,牛頓坐過的高桌還在
院長官邸
劍橋大學每個學院都有院長官邸(Master Lodge)。經三一學院院長薩利·戴維斯(Sally Davies)的外子威廉·歐維漢(Willem H. Ouwehand)的許可,我拍下該院的院長官邸的內景一角(圖4),其中以牛頓的肖像油畫最多,還有牛頓的小型全裸塑像。三一學院院長官邸里至少有三幅大的牛頓肖像。

圖4 三一學院院長官邸內一景
尼維爾庭與回廊
為了紀念第八任院長托馬斯·尼維爾(Thomas Nevile)對三一學院建設的功勛,三一學院將雷恩圖書館(The Wren Library)前的方庭命名為尼維爾庭(Nevile’s Court)。三一學院的回廊亦是特有的文化,很多人文、科學思想在這里誕生。第一次見到馬丁·約翰·里斯勛爵(Lord Martin John Rees),是于2019年10月25日在牛頓數學研究所參加紀念邁克爾·阿迪亞(Michael Atiyah)的學術會議時。見到這位英國皇家天文學家,我內心充滿了喜悅興奮,亦充滿了一絲苦楚,感慨在三一學院,上帝似乎未死,他深深愛著、眷顧著里斯勛爵:榮膺27個榮譽博士學位;曾任英國皇家學會主席;曾任三一學院院長;榮膺包括英國皇家學會等23個院士稱號。在三一學院的尼維爾庭見到他時,與他合了影。每每想起里斯勛爵、看著這張合影,我感動地就想流淚……這也是生命中的另一個奇異恩典。
新冠疫情期間,里斯勛爵撰文呼吁“大學必須調整適應學生的變化需求”。他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過博士后,亦常去美國各大學,故而,文章有比較、有見解。近日,他又撰文“關于科學與科學家的真理”。按他自己的話說,他仍然努力地試著在老年階段做些科學。
雷恩圖書館
建于1695年的三一學院雷恩圖書館珍藏有牛頓的手稿,也存有一尊高大的詩人拜倫勛爵(Lord Byron)的雕像。鑒于拜倫勛爵道德的殘缺,由丹麥雕刻家托瓦爾森(Thorvaldsen)雕刻的拜倫勛爵雕像(圖 5)被倫敦西敏寺拒絕接受,唯有其母校三一學院能寬容,放置在雷恩圖書館的南側,這是對拜倫的奇異恩典。他的詩句的美麗似乎遠遠蓋過了他道德的殘缺:
我看過你哭——一滴明亮的淚
涌上了你藍色的眼珠;
那時候,我心想,這豈不就是
一朵紫羅蘭上垂著露;
我看過你笑——藍寶石的火焰
在你前面也不再發閃,
呵,寶石的閃爍怎能比得上
你那一瞥的靈活的光線。
仿佛是烏云從遠方的太陽
得到濃厚而柔和的色彩,
就是冉冉的黃昏的暗影
也不能將它從天空逐開;
你那微笑給我陰沉的腦中
也灌注了純潔的歡樂;
你的容光留下了光明一閃,
直似太陽在我心里放射。
結語

圖5 雷恩圖書館里的拜倫雕塑像
英國人是世界上最愛自己歷史的民族之一,這種品質在劍橋大學亦足以體現。三一學院將16、17、18世紀的建筑藝術薈萃于一身。他們為什么能如此珍愛自己的歷史?從劍橋大學可見一斑,珍愛歷史的傳統應該與她的以神為本的文化、牛頓時代就初步建立的立憲君主制相關的,世世代代從君主到平民,培養了愛護和恪守優秀傳統、呵護歷史生命的品質。據霍金在《黑洞和小宇宙及其他論文》(Black Holes and Baby Universes and Other Essays)的第一章回憶童年中敘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德國空軍曾簽署了一項協議:英國不轟炸德國的哥廷根、海德堡大學,德國不轟炸牛津、劍橋大學。正因為此,即使經歷過瘋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劍橋大學也能夠完好地保存下來。經歷過歷史的洗禮,如今的三一學院宛如是一位睿智的賢哲,亦洋溢著孩童般的熱情。
為什么英國劍橋大學能夠從中古走到現代?答案只能是:800余年來,她既恪守已有的優秀傳統,又堅定不移地與時俱進。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給予我們的啟示:所謂大學者,既謂有大樓之謂也,亦有大師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