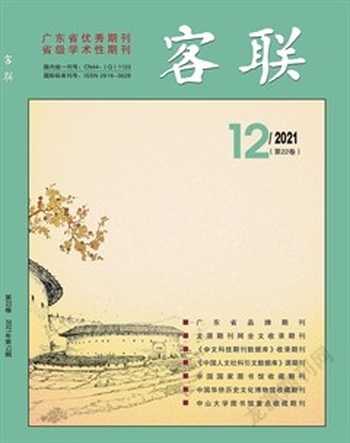簡論商事留置權的構成要件
黃曉麗
摘 要:民法典第448條規定了商事留置權,然其對商事留置權的規定較為簡略,故試對商事留置權的構成要件進行簡要論述。主要從主體的范圍,留置物的范圍及權屬關系以及牽連性是否為必須三個角度進行論述。并且商事留置權適用善意取得有其合理性所在。
關鍵詞:商事留置權;企業;留置物;牽連性問題
對于民事留置權的構成要件,通常認為,有以下幾個要素。其一,須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動產;其二,須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有牽連關系,通常認為,該牽連性體現為在同一法律關系中;其三,須債權已屆清償期。不難得出,主體為債權人與債務人,且應當是為自然人。從民事留置權的起源不難看出,其最初就是債務人對債權人不履行到期債務之時,可抗辯自己不為履行之抗辯權,而不是如商事留置權的債權人直接留置債務人之所有之物或有價證券之物權;其次從基礎不同來看,民事留置權其基礎為公平原則,若超出同一法律關系甚至是牽連關系,對于債權人的優待過厚,違背來維護公平原則之初衷。其客體為動產,并且要求該動產與該法律關系有牽連性,其與公平原則可相聯系。
而對于商事留置權的構成要件,也從主體、客體以及牽連性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商事留置權的主體
根據《民法典》第448條之規定,我國民法將商事留置權的主體限定在了企業之間。企業是一個經濟學上的名詞概念,一般是指以盈利為目的,運用各種生產要素,向市場提供商品或服務,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會經濟組織。企業的特點在于其具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并且其為連續性的進行生產,進行商業經營活動。而在比較法上,將商事留置權的主體規定為商人者較為多見。在《德國商法典》第369條關于商事留置權的規定中,對商事留置權的主體定義規定為:一個商人因自己對另外一個商人由二者之間所訂立的雙方商行為所享有的屆期債權。在《瑞士民法典》第895條第2款中,其對商事留置權的定義為,商人間因營業關系而占有的動產,與其因營業關系而產生的債權,具有欠款所規定的牽連關系。同樣在《臺灣民法典》第929條中也將商事留置權的主體限定為了商人。就此,疑問在于,商事留置權主體為企業還是商人更能使得商事留置權之功能發揮到最大的制度功能?若將商事留置權的主體認定為商人更為妥適,那么如何進行法律解釋呢?
在對商事留置權的主體內容爭議中,即采商人還是企業之定義。但是實質上,其主要在于對從村承包經營戶與個人工商戶是否應當進入到企業的射程范圍內。事實上,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持肯定意見并無太多爭議。有學者認為,商事留置權的范圍應當擴及一切的商人,包括個體工商戶、達到一定規模或經登記的農村承包經營戶。其通過“舉重以明輕”的當然解釋方法,其認為民法上可認“農村承包經營戶”為浮動抵押權人,其對債權的保障是基于未來的動產,而留置權是以現有的動產而為設定,顯然留置權對債權實現的保障更有利。商事留置權自應包括農村承包經營戶。而對個人工商戶也享有浮動抵押權,自也應當承認其商事留置權,以此對立法進行平衡。有學者也認同將個體工商戶以及農村承包經營戶進入到商事留置權的主體范圍內,但其對于通過當然解釋將二者擴張解釋到企業的范圍之中,不贊同。其認為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無法滿足企業的組織形式,故而當然解釋的路徑并不可取。其認為應當對商事留置權進行目的性擴張,進而將兩者進入到商事留置權的主體范圍內。
從商事留置權的萌芽以及發展成熟,商事留置權就是從商人之間脫胎而來。其本就是以商人的誠實信用為原則。故而無論是個體商人、農村承包經營戶抑或是企業,當其以商主體的身份進入到了商事活動中,并且以連續的商行為方式進行利潤的謀取,其應當有成為商事留置權的資格。連續的商行為,其自然需要誠信為其原則,故而一方打破該原則時,承擔商事留置權的法效果無可厚非。這與商事留置權的沿革也無不合之處。其與民事留置權的以公平原則有不同,商主體是因其自身打破了誠信,故而即使是非同一法律關系也應當承擔該法律后果。
二、商事留置權的客體范圍
根據《民法典》第447條之規定,民事留置權和商事留置權的客體并沒有做區分,兩者均為:債權人已經合法占有的債務人的動產。德國商法典對商事留置權的客體規定為動產和有價證券。瑞士民法典第895條之規定,民事留置權的客體為動產和有價證券,而在該條的第2款中對商事留置權的客體規定為動產,對有價證券在第2款中并未如第1款一樣列明。而臺灣民法對商事留置權的客體規定為動產。
從上述不難看出,對于商事留置權的客體爭議主要有兩點:其一,商事留置權的客體是否包括有價證券,或者說法條中所稱之動產是否包含了有價證券;其二,對于法條中所規定之債務人的動產,是否要求為債務人所有的動產,如果要求為債務人所有之動產,那么接下來的疑問是:債權人對留置物有無善意取得可能。
通說認為,商事留置權的客體包括動產和有價證券。從對物的分類來看,可以將物分為動產和不動產,在該分類下,如果對有價證券屬于動產存疑。反之論證,有價證券顯然不屬于不動產,且不能否認有價證券屬于民法上的物。故而有價證券屬于商事留置權動產范疇,是為當然。但是,對于有價證券的內部,即是否所有的有價證券均屬于商事留置權客體的范疇有較大爭議。之所以存有較大爭議,在于留置權其作為擔保物權的一種,其目的是債權人為了保障債權的受償及優先受償。而有價證券本身的分類中,有記名證券、無記名證券和指示證券。無疑問的是無記名和指示證券顯然可以達到留置權的目的。而記名證券,不存在優先受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債務人有威懾作用,因為根據記名證券的流通規定,其流轉需要背書,故而學界有此爭議。有學者認為,記名證券不能作為商事留置權的客體,其理由是,記名證券的實質是一張毫無價值的紙片,因此其作為留置物時很難行事優先受償權。即使債權人將記名證券進行了留置,債務人可能已經通過其他方式行使了該證券上的權利,顯然不利于達成商事留置權的目的。而持肯定說的學者認為,記名證券能夠達到商事留置權的主要目的,即通過留置債務人的物而迫使債務人清償債務;通過留置物本身來實現受償或者優先受償是其次作用;并且其認為通過其他方式行使記名證券上的權利是理論上的想象。同樣持肯定說的學者認為,記名證券按照《票據法》的規定需要連續的背書才能轉讓,但是現在市場交易中非背書的轉讓現象非常常見,故即使不具有連續背書,也不影響記名證券的效力,僅僅是對證明效力會弱。
從商事留置權的起源來看,其是對商主體違背誠信原則之后,通過留置對方的不動產或者是有價證券,從而來保障自己的債權。商事留置權作為一種擔保物權,相當于給予守約方以實現其債權多了一道保障。退一步來說,如果否定記名證券作為留置物,對守約方實現債權并無利處;相反如果其可以作為留置物予以留置,雖然其法效果沒有不記名證券和指示債權對實現債權來得強有力,但是不能否認其作為擔保物權的標的物對守約方債權的實現有一定程度的作用,那么基于從該制度本身出發,顯然將其作為留置物顯然對守約方即債權人更有利。
對于商事留置權的動產應為債務人所有抑或債務人占有,尚有爭議。從我國《民法典》第447條之規定,其要求為債務人的動產,按照文義理解,應當是債務人所有的動產。但是基于商事的外觀主義,以及商事交易的特殊性,其更注重交易的快捷高效。故而應當許可債務人占有的物也可作為留置物。但是如果只要是債務人占有的動產或有價證券,就可以作為留置物,那么對該留置物的所有權人的利益損害極大。故而此時對善意取得制度是否應當適用于商事留置權是有爭議的。有學者認為,商事留置權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其理由在于商事留置權不需要通過善意取得制度來平衡商人之間的整體利益關系,這是與民事留置權適用善意取得的規范目的上的不同。也有學者認為,留置權可以在局部類推適用善意取得之法理,而不是全盤以及直接地適用善意取得。其理由在于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既是依照政正常交易進行,則其行為自是“有權處分”,無善意取得介入之必要。但是在商事留置權中,留置物并非必然為同一法律關系之下的標的物,則此時是否為“有權處分”,有待商榷。也有學者持肯定說,認為商事留置權可以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其理由為。要求債權人事先核實債務人是否擁有處分權或所有權,會增加交易成本且有悖常理。而在實務判決中,對商事留置權的善意取得的態度也有分歧。在“上海知權物流有限公司訴杭州蕭山物流有限公司等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中,法院否認了善意取得以及商事留置權的成立。而在“中國外運長江有限公司太倉分公司與蘇州匯暢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陳亮貨運代理合同糾紛案”中,法院以留置的貨物無須為債務人所有,只要是債務人合法占有即可為由,認可了商事留置的效力。
商事留置權適用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合理性。首先,商事交易其本身更關注的是效率,其取效率優先為原則。在交易發達且迅速的當今社會,如果要求商事主體對每一件留置物或者說每一件交易物品均進行物權歸屬情形審查,未免過于苛刻。其顯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該成本顯然不適宜當今社會的快節奏交易。再者,商事交易其本就采交易外觀主義原則,其通過給予交易外觀以效力來保障交易的安全性。而如果債務人不即使履行其債務或者提供擔保,將留置物從債權人處取回,其對該無處分權的留置物,因其被留置而導致其對留置物本身的處分權人造成來損害。故而,其為了避免承擔該責任,會對債權人的返還有一個心理壓迫效果。
綜上所述,留置物應當是動產包括有價證券的所有類別,并且留置物非為債務人所有為必要。
三、商事留置權之牽連性
商事留置權與民事留置權相比,其最大的區別在于商事留置權對牽連關系的要求沒有那么高。通常在民事留置權中,要求是在同一法律關系中。這與民事留置權以公平原則為基礎有莫大的關系,因為要衡平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故而要求留置權擔保的債務的雙方當事人要一一對映。故而,牽連性是民事留置權成立的不可或缺的要件。而在商事留置權中,牽連性是可以被舍棄或者被擬制的。被舍棄,主要是指法律并未明文要求牽連關系作為權利成立的要件或者通過法律規定明文排除牽連關系適用的情形。而牽連的關系的擬制,主要是通過法律的規定,在所規定情形成就時,視為法律關系存在。
《德國商法典》第369條第1款規定,對以債務人的意思依商行為已經為自己所占有的債務人的動產和有價證券。對于商事留置權的規定并沒有牽連性的規定,是故為德國對商事留置權的牽連性要件是予以舍棄的。《瑞士民法典》第895條第1款規定,與其因營業關系而產生的債權,具有前款所規定的牽連關系。瑞士民法典對商事留置權的牽連性要件,比民事留置權要求更低,其之要求因營業關系發生即可,而不需要債權與留置的標的物有關。《臺灣民法典》第929條,商人間因營業關系而占有之動產,與其因營業關系而所生之債權,視為有前條所定之牽連關系。該條是典型的法律擬制的牽連性,其要求牽連性作為商事留置權的構成要件,但是該牽連性比民事留置權要求更低,其射程范圍更廣,其只要是因營業關系即可。從上述可以看出,無論是采取舍棄還是法律擬制的方式,在商事留置權的構成要件中,牽連性要求已經被淡化。
我國《民法典》第488條之規定,顯然排除了商事留置權要求基于同一法律關系而生的要求,但是對商事留置權的牽連性關系并無其他說明。其可否認為我國在商事留置權中,對牽連性要求也是舍棄的呢?有學者認為,在解釋上,應認為在雙方均為商人的情況下,只要占有和債權均為經營關系而生,就可認定債權與標的物之間存牽連關系。有學者認為商事留置權對“牽連性”的要求有豁免,即不要牽連關系。其理由在于商人之間的留置權所協調的利益關系具有“集合性”,這與民事留置權通常發生只有一次性不同。連續的經營能力與主體資格的存續能力是商人的特點,也是商事留置權不需要牽連性的重要原因。也就是“債權”與“留置物”兩者擁有論交互適用效力。也有學者認為,由法律明確規定商行為的概念以及具體類型,據此認定商事留置權中留置物和被擔保物的牽連性,是最理想的方案。
由上文可知,商事留置權中的牽連性要求越來越淡,甚至可以沒有牽連性。牽連性與否并非最核心,商事留置權的核心在于債權人的留置物與債務人的關系。也就是上文中對于留置物是否必須為債務人所有。債務人所有自然可以為留置,而在債務人為占有的時候,引入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即可。故而,商事留置權中,應當側重考慮留置物與債務人之間的關系,債務人與債權人均為商主體,應當認可該商事留置權。
四、小結
綜上所述,商事留置權的構成要件中,主體應解釋為商人,客體為動產和有價證券以及對于牽連性,有或無均可。在對留置物的處理上,應當適用善意取得規則。商事留置權的法律規定仍有過于簡陋之嫌,并且對于商事留置權的認識與規定并不全面,故而使得在實際應用中也存在較大分歧,故而該制度仍顯“商法化不足”,故而在之后的商事留置權規定有待進一步商法化。
參考文獻:
一、專著類
[1]謝在權:《民法物權論》(下冊)(修訂第五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杜景林、盧諶:《德國商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版。
[3]戴永盛:《瑞士民法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版。
[4]王澤鑒:《民法物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版。
[5]崔建遠:《物權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版。
[6]陳華彬:《民法物權論》,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版。
[7] [日]我妻榮《新編擔保物權法》,申政武、封濤、鄭芙蓉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版。
二、論文類
[1]劉凱湘:《比較法視角下的商事留置權制度》,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99期。
[2]李賽敏:《論商事留置權—兼評物權法第231條》,載商事法論集第14卷。
[3]熊丙萬:《論商事留置權》,載《法學家》2011年第4期。
[4]曾大鵬:《商事留置權的法律構造》,載《法學》2010年第2期。
[5]劉燦:《民法典時代的商事留置權完善路徑》,載《河北法學》2020年第8期。
[6]曾大鵬:《商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研究—比較法的啟示與中國法的完善》,載《時代法學》2011年第5期。
[7]崔令之:《論留置權的善意取得》,載《河北法學》2006年第12期。
[8]孫鵬:《完善我國留置權制度的建議》,載《現代法學》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