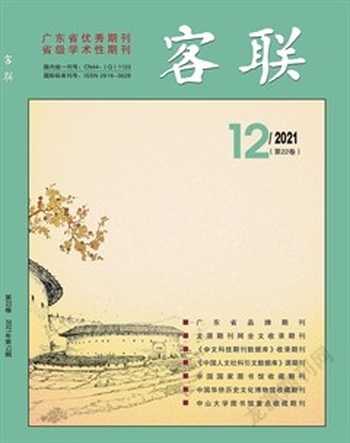智慧司法定位困局新探
張鑫虎
摘 要:伴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智慧司法的發展儼然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但是在將人工智能技術引入到司法領域加以運用的過程中,必須對智慧司法作出準確的定位。無論將智慧司法定位為獨立審判者還是輔助審判者,都無法避免“司法機械化困境”“法律權威危機”“錯案歸責困局”。因此,在現階段,智慧司法系統應該嚴格處于法官的控制之下,被動地參與到司法審判中,將智慧司法定位為純粹工具顯然更為恰當。
關鍵詞:人工智能;智能司法;司法權;司法權威
一、智慧司法發展現狀概述
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技術,人工智能系統在替代人類從事簡單性、重復性以及危險性工作方面存在廣泛的應用價值,目前在金融、安防、客服等行業領域已實現應用,并且在精確度和效率上確實已經遠超人工。i而人工智能在其他領域的高準確性、高效率的表現也引起了司法界的注目,司法界開始構想將人工智能技術有機地引入司法實踐中,以此來提高判案準確度,提升辦案效率,試圖將其作為破解當下“案多人少、難案增多”司法困局的一劑良藥。ii這一智能司法的構想很快即被付諸實踐,智慧法院應運而生。
在智能司法體系的如火如荼的建設過程中,人工智能在司法領域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貴州、海南等地智慧司法系統所取得的實際成績無疑證明智慧司法系統對于我國司法體系的巨大價值,iii但需要注意的是,與此同時,這也對現代司法體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唯有基于對智慧司法的準確定位,方可保證智慧司法的發展程度與方向能夠同現行司法體系相契合,避免智慧司法的發展陷入過猶不及的尷尬境地。
二、對于學界智慧司法定位學說的分析
現今學界對于智慧司法的定位,大致可分為兩種觀點,即獨立審判說和輔助審判說,但是兩種定位都無法回應現階段存在的諸多問題,也因此導致了如今的智能司法定位困局。
(一)獨立審判說之紕漏
獨立審判說認為如果未來的法律機器人因其功能強大而大行其道,法官的存在甚至會變得沒有必要。iv學界對于這一定位的支持者并不多,該定位學說多以輔助審判說的假想敵形式呈現出來,因此,部分學者認為以現在人工智能處理司法問題的技術水平來看,討論人工智能是否有取代法官裁判的可能性,沒有根據也沒有必要。v筆者認為,盡管從技術的視角來看,獨立審判說實質上更近乎于一種明日之說,但是,在關于智能司法定位問題的討論中,從司法的視角來審視獨立審判說則是必要的,該探討有利于認識智慧司法所面臨的司法層面的現實問題,對于之后關于輔助審判說的分析也大有裨益。因此,筆者試圖撇開獨立審判說在現階段技術層面上存在的不足,主要探討獨立審判說在司法層面上存在的邏輯悖論。
1.司法機械化困境
獨立審判說支持者主張借助信息技術、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以及人工智能構建法律數據庫,以法律數據庫作為基礎,以三段論作為推演模式,通過機器代碼來定義和計算人們需要遵守的規則和違反規則的結果,從而獨立于法官作出審判。顯而易見,獨立審判論者認為在技術支持的情況下,以法律規則與三段論演繹作為核心立足點構建的智能司法系統即可以完全地替代法官作出獨立判決,這一構想無疑身陷法律形式主義的泥潭之中。
首先,在法律規則方面。法和法的規則不是永恒的、固定的,而是持續發展的。vi因此一個即使在某一固定時間最為健全完整的法律數據庫,也不能夠保證滿足未來審判的全部需要。人所制訂的法律不可能對所有的事物都規定得很清楚, 也不可能對所有的事物都作出明確無誤的調整, 而在客觀上不得不留有一些自由裁量的空間。vii獨立審判論者若以“法律數據庫能夠不斷自動更新全新的法律”作為回應亦是無濟于事的。德沃金用于詰難哈特的疑難案件同樣可以用于此處,當上述的獨立審判系統面對沒有法律規則加以規制,沒有先例作為參考的全新疑難案件時,顯然難以基于其固定的法律數據庫作出合適的解答。
其次,在三段論方面。霍姆斯說過:“對時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論,對公共政策的直覺,不管你承認與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見對人們決定是否遵守規則所起的作用都遠遠大于三段論。” viii顯而易見,獨立審判論者對于法官司法裁量的認知顯然是片面的,毋庸置疑,三段論在司法推理過程中確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將此視為全部則無疑是以偏概全的。在司法實踐過程中,由于案件事實、人際關系的復雜,單純的邏輯推理時常難以得到準確的結果,必須根據法理、常識作出判斷,此時便不得不訴諸適格法官的自由心證和睿智。ix
2.司法權威危機
獨立司法說在司法層面上所面臨的另一大障礙,即是智慧司法獨立審判系統的構建必然導致司法權威的動搖,主要體現于兩個方面,即為其自身固有缺陷和對于傳統制度權威的徹底顛覆。
首先,智慧司法系統因其自身特點而致使其將必然面臨算法黑箱難題。獨立審判系統倚仗數字驅動,而數字驅動必然導致數據加工和信息處理復雜化,獨立審判系統無法對輸入與輸出之間的法律計算進行細致展示和論證,智能司法的邏輯判斷存在隱秘化、黑箱化,難以徹底取信于民。x相較而言,獨立審判系統試圖替代的法官,則可以通過其學歷、履歷等體現其在法學領域的較高素養,而這也被認為是現代司法權威保障機制中不可或缺的內在因素。xi
其次,以獨立審判系統替代法官來進行裁判,必將導致對于司法制度權威的動搖。伯爾曼強調法律儀式對于樹立司法權威的重要意義,其認為法官職責的標記——法官袍服,法庭布置,尊敬的辭令,對法官心理的影響是令人吃驚的,使用這些標記,不僅使得法官本人、同時也使得所有其他參與審判過程的人、乃至全社會的人,都在靈魂深處體會到,肩負審判重任者必得摒除任何個人癖好、個人偏見、任何先入為主的判斷。xii如果沒有這種嚴肅的儀式, 也就無所謂正義。xiii獨立審判系統的運用會將這些具有權威價值的儀式全盤摒棄。這將嚴重動搖司法公信力,這樣的顛覆對于人民來說顯然是難以接受的。
前文提及的兩點問題即可徹底地否定這一定位,即使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工智能能夠滿足該構想提出的所有技術要求,意欲實現對法官的完全替代也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司法層面上司法機械化及司法權威動搖這兩大鴻溝始終難以跨越。
(二)輔助審判說之悖論
輔助審判說是現今關于智慧司法定位的主流觀點,也是官方對于智慧司法所做的定位。該觀點認為智能輔助辦案系統不是要取代線下訴訟活動,也不是要替代司法人員獨立判斷,而是發揮人工智能在數據方面的優勢,幫助司法人員依法、全面、規范收集和審查證據,統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xiv該論述將輔助審判說與獨立審判說明確區分開來,但是輔助的含義還是較為模糊,需要作進一步的界定。在此處,為了闡明該學說所主張的輔助含義,需要引入工具概念同其進行對比,以明確輔助審判說中所主張的輔助的真實含義。區別于工具的絕對被動性,此處的輔助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動性,而非絕對地被動參與。其具體含義即是在審判過程中,智慧司法系統自動參與到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通過數據采集、整理、分析、綜合,協助法官審理案件,同時一定程度上肩負著監督司法的責任。由于該系統自身所具備的輔助者與監督者的雙重屬性,其對于具體案件的參與便無須經過該案法官的允許或同意。因此,在該模式中,智能司法對于案件的參與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主動性,而非作為工具,純粹被動地參與到案件審理之中,本質上,即是一種更接近于人機共治的模式。
同獨立審判說相比較,首先,由于在輔助審判模式中案件審理的主導權仍然把握在法官手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該模式能夠避免同獨立審判模式一樣陷入法律形式主義的泥潭之中;其次,輔助審判模式對于現有司法體制的沖擊相對于獨立審判模式要緩和許多,相較而言,更易獲得民眾內心的接受;再次,從人工智能技術視角來看,在現階段,相較于獨立審判說,將智能司法定義為輔助審判者也更切合實際。因此,在智慧司法的定位問題上,輔助審判說顯著優于獨立審判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現階段輔助審判定位就是準確的,輔助審判說也面臨著諸多難以解決的現實困境。
1.司法公信力危機
盡管與獨立審判模式相比,輔助審判模式對于現有司法體制權威、司法儀式權威的沖擊要緩和許多,但是還是無法避免其算法黑箱性質所導致的司法公信力的降低。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智能司法的邏輯判斷存在隱秘化、黑箱化特征,難以徹底取信于民。盡管在輔助審判模式中,智能司法系統只是起到輔助審判作用,但是事實上,即使是輔助行為也會對于法官的最終判決造成巨大影響。人工智能輔助裁判雖言輔助、其推論意見雖言參考,但從實質上來講,這樣的輔助或參考卻難免對法官產生相應的錨定效應,因而存在著被智能技術操控的風險。xv由于無法忽略智能司法系統對于最終裁判結果的間接影響,因此,即使是輔助審判定位也無法避免司法公信力危機的出現。
2.錯案歸責困局
在司法領域,錯案責任追究的制度構建是無法回避的重要話題,但是現今智慧司法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尚未確立。而參考我國對于人工智能工作失誤責任承擔的認定,學界和實務界至今仍未有定論。學界認為人工智能工作失誤責任承擔不明的原因在于其獨立法律人格地位的不明確,基于該共識,學界對于人工智能責任承擔問題的解答主要包括三種觀點。否定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論者認為,人工智能的所有行為均是為人類所控制,其作出的行為與引起的后果最終必須由被代理的主體承擔。xvi肯定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論者則認為,將人工智能定義為具有智慧工具性質又可作出獨立意思表示的特殊主體較妥,因此應由人工智能承擔相應責任。xvii第三種觀點則認為應當依據人工智能的不同種類來區分責任承擔的主體。如果違反人工智能屬于不具有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弱人工智能,其違法責任由人類承擔。如果人工智能可以有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具備承擔違法責任的可能。xviii在錯案責任追究問題上,無論采用上述的何種觀點,責任的承擔者必然限于法官、智慧司法系統以及系統的開發者范圍內。然而,基于具體分析來看,無論其中何者作為責任的承擔者均顯失公允。
首先,部分學者認為失誤責任的承擔,應當適用過錯推定原則,由法者優先承擔。xix若如此規定,那么在接近于人機共治的輔助審判模式下,智慧司法系統不但不會提高法官的辦案效率,反而會成為法官辦案的累贅。即使智慧司法系統事先提取了大量案件材料數據,但是由于錯案歸責制度帶來的壓力,法官必然不敢信任該系統所做的工作,最終必然導致智慧司法系統所創造的效率收益付諸東流。
其次,如果由智慧司法系統承擔錯案責任,則會產生兩大不利影響。其一,在這種歸責制度下,法官可以減少自己的獨立裁決,而過度依賴智慧司法系統,且可以將過錯完全地推卸給智慧司法系統,容易導致法官審判態度的松懈。其二,歸責制度規定由智慧司法系統對其錯誤承擔責任,將責任完全歸于人工智能,無疑會讓民眾對司法公正產生懷疑,這勢必會導致司法公信力受損。
最后,如果將錯案責任歸于智慧司法系統的開發者,亦是不盡合理的。不同于自動駕駛汽車的開發商單純出于商業目的,智能司法系統的開發者是由國家組織,接受國家委托進行智慧司法系統的研發,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也正基于此,智慧司法系統才具備其司法公信力。如果嚴格將錯案責任歸于受國家委托的系統開發者,那么一方面作為委托者的國家是否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勢必會嚴重打擊系統開發者在智慧司法研發領域的服務積極性。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得出結論,就現階段而言,盡管輔助審判說優于獨立審判說,但該定位同樣存在諸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按照該學說將智慧司法系統定位為司法審判的輔助者亦是不夠準確的。
三、對于智慧司法正確定位的再探尋
通過對于兩種關于智慧司法的定位學說所存在問題的分析,前文已經闡明,無論是獨立審判說還是輔助審判說,對于智能司法系統的定位都有所偏差,這便意味著應當推翻對于智慧司法的固有定位。在探尋智慧司法正確定位之前,有必要對獨立審判說、輔助審判說這兩種學說失敗的根本原因進行深層次地剖析。
本質上,獨立審判說主張一種人工智能替代法官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模式,而相對緩和的輔助審判說則是主張一種人機共治的模式,雖然二者所主張的模式存在諸多差別,但是兩種模式存在不容忽視的共性,即是兩種模式都不同程度上地弱化了法官對于司法權的掌控,如果法官選擇向人工智能讓渡其部分或全部司法權,那么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現今司法制度宏觀構架以及社會對于司法認知體系的整體崩壞,即是動搖了司法權理論的根基。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具有徹底顛覆性的對于法官的徹底替代,還是相對緩和的審判主體雙重結構,都無疑構成了對于現今司法體系的根本性威脅。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對于智能司法的獨立審判定位和輔助審判定位都已經觸及現今司法體系所能容忍的底線,若對智能司法作出如是定位,即是以毫無節制的“人工智能+”方式改造審判空間,那么法官定位勢必發生極大的動搖,甚至造成審判系統乃至司法權的全面解構。xx這也就揭示了兩種定位所面臨的“機械化困局”“信任危機”“歸責困境”產生的深層次原因。與此同時,司法公正與司法的權威性、司法活動被社會倫理的認同程度、司法制度的宏觀構架,以及司法程序的合理性密切相關。xxi而在司法權威性、司法制度宏觀構架都面臨顛覆性挑戰時,作為司法最高價值的司法公正又從何談起?
上述兩種定位主張都侵犯了法官對于司法的主導權,因而,關于智慧司法的正確定位必須要保證法官司法權的完整性,保證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地位,因此,智慧司法應該嚴格處于法官的控制之下,被動地參與到司法審判中。本質上,即是作為提高司法效率與準確度的一種純粹工具。在具體司法實踐中,法官應該享有對智慧司法的使用選擇權,由法官通過衡量在具體案件中智慧司法的作用價值,最終決定使用與否以及使用程度。這種模式保證了法官在審判過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智慧司法僅僅是作為工具被動性地參與其中,更接近于電腦在現今庭審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官對于智慧司法系統的享有絕對控制權,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審判主體僅是法官,不同于由單獨的人工智能作為審判主體或者人工智能和法官一同作為審判主體的情形,顯然更易于取信于民,不致于引發司法權威危機。與此同時,由于法官對于智慧司法系統的使用具有最終的決斷性,因此對于運用智慧司法系統的可能誤差,法官必將經過充分的權衡利弊,在這種情況下,再規定由法官承擔相應責任顯得更為合理。因此,在將智慧司法定位為純粹工具后,先前獨立審判說、輔助審判說所面臨的諸多難以回應的問題即迎刃而解,顯然,在現階段,對于智慧司法純粹工具的定位顯著優于將其定位為獨立審判者或輔助審判者的兩種學說,也更能契合社會實際,滿足現代司法體系的要求。
四、結語
基于提高司法效率及判決準確度的考量,國家將人工智能技術引入到司法領域,給司法領域帶來了深層次的變革。但在這場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中,必須給予智慧司法以準確定位,而在定位上則必須要保證法官司法權的完整性,保證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地位,警惕人工智能獨立司法及人機共治誤區,應當更切合實際地將智慧司法定位為司法領域之純粹輔助工具。
注釋:
i 參見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標準化白皮書(2018版)》,第1頁。
ii 參見張文顯:《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之間的中國司法———訴訟社會的中國法院》,載《現代法學》2014年第1期。
iii 以貴陽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在部分地區5個月的試運行為例,辦理同類案件的時間同比縮短了30%,因證據不足退回補充偵查率同比下降 25.7%;因證據不足不批準逮捕率同比下降 28.8%,服判率同比上升8.6%,因證據不足作出無罪判決的案件“零發生”。
iv 參見高奇琦、張鵬:《論人工智能對未來法律的多方位挑戰》,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v 參見吳習彧:《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實踐需求及其中國式任務》,載《東方法學》2018年第2期。
vi See Karl N. Llewellyn,The Common Law Tradition:Deciding Appeals.William Twining,1960.
vii 參見江必新:《論司法自由裁量權》,載《法律適用》2006年第11期。
viii Oliver Wendell Holmes,Jr.,The Common Law.1881.
ix 參見季衛東:《人工智能時代的司法權之變》,載《東方法學》2018年第1期。
x 參見李飛:《人工智能與司法的裁判及解釋》,載《法律科學》2018年第5期。
xi 參見汪建成、孫遠:《論司法的權威與權威的司法》,載《法學評論》2001年第4期。
xii 參見[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梁治平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47頁。
xiii 參見陳金釗:《法律程序中的儀式及意義——伯爾曼<法律與宗教>評析》,載《法律科學》1994年第5期。
xiv 參見孟建柱:主動擁抱新一輪科技革命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努力創造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司法文明,載最高人民法院網站,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50472.html ,2018年1月5日。
xv “錨定效應”,是指個體在不確定情境下的決策會受到初始無關錨影響致使其隨后的數值估計偏向該錨的一種判斷偏差現象。參見朱體正:《人工智能輔助刑事裁判的不確定性風險及其防范——美國威斯康星州訴盧米斯案的啟示》,載《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xvi 參見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審視》,載《東方法學》2017年第5期。
xvii 參見姚萬勤:《人工智能影響現行法律制度前瞻》,載《人民法院報》2017年11月25日,第2版。
xviii 參見劉憲權:《人工智能時代的“內憂”“外患”與刑事責任》,載《東方法學》2018年第1期。
xix 參見程凡卿:《我國司法人工智能建設的問題與應對》,載《東方法學》2018年第3期。
xx 參見季衛東:《人工智能時代的司法權之變》,載《東方法學》2018年第1期。
xxi 參見姚莉:《司法公正要素分析》,載《法學研究》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