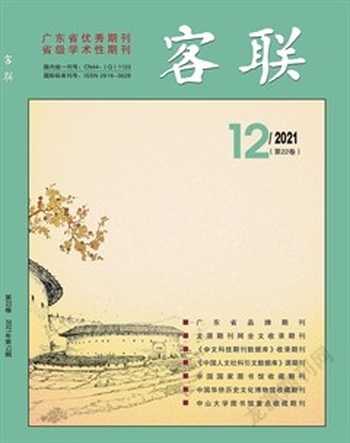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行為濫用的法律規制策略
程健
摘 要:大數據時代,隨著數據搜集能力和成本的進一步降低,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行為屢有發生,這不但涉及到反壟斷問題,還與消費者保護、經濟學、計算機等其他法律領域息息相關。通過對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的概念進行界定,厘清價格歧視的實現路徑,才能更好的制定法律規制策略,在不遏制數字經濟創新的框架下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關鍵詞:定價算法;價格歧視;法律規制
一、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的概念界定
目前,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尚未形成統一的概念界定。大數據時代,數據收集和分類愈加便捷,通過對消費者購買習慣進行數據分析和建模,可向其提供高度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這在消費者知情的情況下本無可厚非,但是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對經濟活動的深度介入除了存在競爭風險以外,也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通過參考歐盟競爭法中關于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定義,可將其概括為在線數字零售商通過算法挖掘消費者的數字足跡,從而對消費者特定項目下的最大消費意愿進行預測,并據此設定針對性的價格。
在反壟斷視域下,只有價格歧視使交易對象處于“競爭劣勢”時,才能認定其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故針對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濫用行為的規制需要認定其實施的市場效果。此外,鑒于各國反壟斷法對“消費者福利”的制度定位不同,對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實施效果的認定也會有所不同,但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是反壟斷法實施的應有之義。 二、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的實現路徑
首先對消費者的個人特征和消費行為數據進行分析,形成不同消費者的購買意愿模型。基于信息平臺和大數據技術,消費者雖然可以享受更加便捷的服務,但是由于數字技術的數據搜集能力和成本進一步降低,電商平臺和在線零售商可能會對消費者的瀏覽記錄、購買意愿進行追蹤,通過分析消費者平時支付行為對其支付意愿做出精準的預估,同樣的商品可能會制定不同的價格,從而形成價格歧視。隨著消費者的行為數據的不斷增加、可用性不斷增強,消費者購買意愿模型也越發清晰,企業就能更好地鎖定目標市場進行針對性的個性化營銷。
其次利用算法預估消費者的支付意愿并進行個性化推送。消費者在線購物必然會留下數字足跡,電商平臺和在線零售商通過分析消費者的數字足跡進行分析并預測消費者的支付意愿,實施定向營銷。經營者利用算法和大數據識別這兩個因素以實施消費者價格歧視,以求達到消費者的最高支付意愿。從認知心理學角度來看,由于各種認知啟發和決策缺陷,人們往往會做出非理性的決定。利用消費者慣性心理以及認知缺失、平臺信賴等因素對特定消費群體收取高價,是價格歧視的主要表現。
第三是為每一個消費者制定個性化價格,實施消費者價格歧視。大數據時代,平臺、商家和消費者三方加劇了信息不對成,平臺及商家可能會利用搜集到的消費者模型相關數據對消費者進行分組,從而對不同組實施不同的價格,消費者往往無法以同樣詳細的程度檢查經營者的定價行為,從而面臨被剝削的風險,由此導致在線消費者只能看到商家為自己“定制”的個性化數字店面,無法察覺到算法價格歧視的發生。
三、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行為濫用的法律規制策略
(一)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的法律規則及理念的完善
如果依據行為特征進行分析,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應歸納為傳統價格歧視的一種,只不過是在數字經濟中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如果單純的以《反壟斷法》將競爭的公平性作為核心認定標準,則可能會延伸出其他問題,應當將行為是否排除、限制競爭作為分析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問題的核心,即充分考量競爭的自由問題。通過反壟斷規則降低企業定價方面的能力,不會就此扼殺企業創新的能力和動機,且消費者仍有可能從技術中獲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對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行為必須予以禁止。
(二)算法權力治理工具的實施
首先要對算法所采集和依據的數據范圍進行明確。算法歧視推動了消費者價格歧視的實施,對于當前傳統的算法規制應從道德層面上升至法律層面,通過立法對算法所采集和依據的數據范圍進行明確,對于明顯超出平臺及商家需求以外的數據應予以考量禁止采集,對于模糊的數據采集范圍應告知消費者采集依據和用途,并讓消費者自由選擇。
其次應確保算法的中立性。可從數據質量以及設計者倫理規范兩方面進行規范,在數據層面應確保其來源、內容、處理可查,明確數據操作過程;在算法設計上應從根本上提高設計者的算法素養,必要時可上升至法律予以規范。同時也可以推動監管機關制定統一的定價算法并要求在線平臺和商家強制實施,從而增強監管的便利性及算法的中立性。
第三應對定價算法進行識別和法律定性。算法披露可能會損害企業的知識產權和創新競爭能力,算法黑箱又容易引起社會公眾情緒的恐慌和焦慮,如何有針對性的進行算法公開,同時不損害企業的知識產權,又可以穩定社會公眾的焦慮情緒尤為重要。可借鑒歐洲監管中心的方案,即針對在線平臺附加新的合乎比例的透明度義務,要求企業向特定消費者提供其購買產品可獲得收益的個性化信息,使消費者通過這些信息分離出基于錯誤感知的成分,避免為產品或服務提供過高的價格。在實施上可以讓具有相應技術和知識的監管人員來對定價算法進行識別和法律定性,這涉及到法律、經濟、計算機領域的融合。
(三)進一步強化消費者數據權益屬性
數字經濟使消費者需求由大眾化轉向精細化和定制化,消費者對商品的選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企業對商品的精準投放,這也就是說,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交易結果,使消費者在交易中處于劣勢。此外,算法的不透明性以及用戶鎖定效應限制了消費者轉向其他更優質的企業,限制、排除了競爭,惡化了消費者自由選擇的環境。為緩解數字經濟對消費者公平交易權以及自由選擇權帶來的沖擊,就需要適當拓寬消費者安全權的內涵。消費者為商品或服務提供對價后,經營者就應當對消費者人身、財產安全承擔相應的義務。特別是隨著非價格維度的考量在互聯網雙邊市場以及多邊市場上不斷提升,消費者數據權益屬性的強化是必然的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施春風. 定價算法在網絡交易中的反壟斷法律規制[J]. 河北法學, 2018, 36(11):9.
[2]周圍. 人工智能時代個性化定價算法的反壟斷法規制[J]. 社會科學文摘, 2021(2):3.
[3]谷月. 基于算法的消費者價格歧視的反壟斷規制探究[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