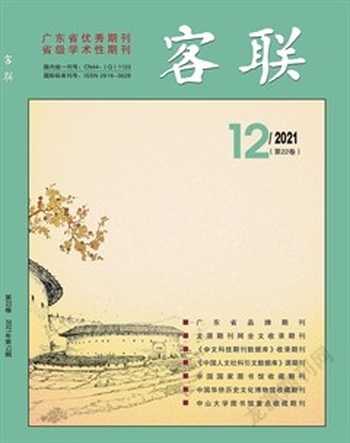淺論海子的抒情短詩的精神世界
常思揚
摘 要:海子詩學博大、獨特、自成體系,是基于海子對人類精神藝術這一大空間綜合考察的結晶,它不僅吸取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汲養,更因其對存在與生存的深切關注而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通由海子詩學,不僅可以切近海子其詩其思,也可透視當代中國詩歌甚至世界范圍內的一些重大詩學問題。本文將就海子的抒情短詩,從形而下和形而上兩個層面全面展開論述,展現海子在詩歌中構筑了一個豐富而自足的精神世界,以及死亡意識。
關鍵詞:海子;詩歌;死亡;意識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關至龍家營之間的鐵道上臥軌身亡,隨身帶著梭羅的《瓦爾登湖》、海雅達爾的《孤筏重洋》、《新舊約全書》和《康拉德小說選》等四本書,這一事件被第三代詩人視為一次神圣的獻祭。陳曉明說,“海子死了”——這是那個時期任何一次關于詩歌的、乃至關于文學的討論會的開場白。足見海子之死在當代詩壇所造成的影響。自那以來,“海子的死亡”一度成為評論界爭論不休的話題,爭議的焦點在于海子之死有無“形而上”的意義。一種觀點認為海子的死亡是以身體和詩歌為犧牲對繆斯女神的獻祭。
一、宿命論的悲劇意識
從浪漫型詩歌的特點來看海子的詩歌,它將生命的意義隱喻到一種叫“遠方”的空間、介質或烏托邦之中,它所要做的,“并不是把事物表現得很明確,一目了然,而是把疏遠現象進行隱喻式的運用看成本身就是一個目的。情感成了中心,巡視自己的豐富多彩的周圍,就把它吸引到這個中心里來,很技巧地把它轉化為自己的裝飾,灌注生氣給它,而自己就在這種翻來覆去中,這種體物入微,物我同一的境界中得到樂趣”。海子希望把語言從道統束縛中解放出來,修復詩歌與神性意旨剝離之傷,生成語言的詩意,還原其思想載體的本質,從而達到“藻雪精神”的審美效果。海子為神性復原、人性復蘇和藝術復興的理想傾盡心力,孤注一擲,他對這一努力的悲劇性也有所認識,像希臘悲劇和意大利文藝復興一樣,它們“是兩個典型的創造亞當的過程。帶有鮮明的三點精神:主體明朗、奴隸色彩(命運)和掙扎的悲劇性姿態”。在這種宿命論的悲劇意識中,海子認為自己已經“走到人類的盡頭”。
愛情的經歷帶給海子心理上的灼傷,他將思想的鋒芒指向自己的內心,形成郁積和創傷,并將其轉嫁給他所處的時代。他通過情欲的道路進入哲學思考的大門,在幻覺中洞見了真理。對他來說,一切似乎不曾存在,卻又像所羅門的鞭子一樣抽打在他的“啞脊背”上。他希望“活在珍貴的人間”,生活的現實卻是在傳統的夾縫中求生存。他所追求的生活模式和創作方式一方面表現出對傳統的潛在認同,但另一方面,他革新的銳氣極為剛猛以至渴望脫離既有的傳統模式,自己也從中被割裂。海子對其所處的時代的感受是:“該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秋》)。
二、以死亡來宣告過去的結束和未來的開啟
海子多次在詩歌中提到“最后一夜的抒情”,表明他作為“詩歌皇帝”的野心——以死亡來宣告過去的結束和未來的開啟。這樣以來他既享有像撒旦那樣進行破壞的末世快感,又享有上帝最初創造世界的那種榮光,這樣的死亡也就無可畏懼。
在書寫《太陽七部書》的過程中,海子對“太陽”的信仰和追逐已經達到“迷狂”狀態,一種類似肉體的興奮,這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縱欲狂歡的時刻,理性簡化為單純的情感。時間“通過輪回進入元素”,世界回到一個共時性的原點。聯想其他在思想和藝術領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人物,尼采在幻覺中肯定自己就是火焰,是太陽,他說:“走向太陽是你最終的行動;對知識的歡呼是你最終的吶喊”。
三、成為太陽的一生——“心的青春是獻給太陽的祭禮”
在海子看來,“死亡比誕生更為簡單”(《土地篇》)。事實上,海子一直糾纏在矛盾的狀態里,不加區分地對待藝術和現實生活。他渴望像凡·高給弟弟提奧寫信時所表示的那樣,兼做畫商與圣徒。既被他人閱知又不犧牲藝術的神圣和純粹性;既期待《舊約》中的嚴苛與復仇,又向往《新約》宣示的寬容與救贖。他一成不變地對美加以追求,幾乎達到自戀的程度,除了對藝術本身的關注以外,他表現出對一切的漠視。海子在談到《太陽·斷頭篇》時說:“詩中的事跡大多屬于詩人自己,而不是濕婆的。只是他的毀滅的天性賜予詩人以靈感和激情”(《太陽·斷頭篇》)。然而面對沒落的世界,他又試圖拯救出“應該救出的部分”;詩人應該“關心糧食和蔬菜”,關注生命存在本身。他像溫克爾曼那樣沉迷在古希臘世界的理想里,但相對于那個古老的文明,他只是一個“遲到者”,因而為此唏噓不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大都具有這樣的特點,他們“解析了生活中的煩惱,并將對它的感覺直接傳達到我們心中,它不是一種巨大的悲傷或激情,而僅僅是對時光流逝的感覺,是必須置身于凡間瑣事的夢幻者的厭倦,是生活于真實與理想之間的矛盾,是一種對休息的渴望,一種懷舊病,一種思病,那是一種非常孩子氣但又富有寓意的悲傷,它與全體人類對于熟悉的地球和有限的天空的最終的悔恨具有相同的意義。
黑夜使人向往太陽的初生、光芒、朝霞以及那個居于夜空之上的神秘實體,黑夜使人得到還原。如歌德所說,“混合一切形態為一的黃昏和黑夜很容易生出崇高之感,而使一切事物區別和隔離開來的白晝卻把它驅除”。顧城的短詩《一代人》打動人的地方在于它說出了那個時代的心聲:“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對比海子在《太陽·詩劇》中的詩句:“兩只烏鴉飛進我的眼睛。/無邊的黑夜騎著黑夜般的烏鴉飛進我的眼睛。”如果說顧城對時間和光明還抱有期望的話,海子則對黑夜的呼喚和追求更加徹底,對白晝的反叛更加決絕,像他在1986年8月的《日記》中所說的,“黎明并不是一種開始,她應當是最后到來的,收拾黑夜尸體的人”。黑夜在海子筆下成為時間的象征,“黑夜是什么?黑夜之前是什么?黑夜之后緊跟著誰”(《桃樹林》)?這些疑問其實是對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謎”的重復。他說,所謂的黑夜就是“讓自己的尸體遮住了太陽,上帝的淚水和死亡流在了一起”(《太陽·彌賽亞》)。黑夜和黎明,在80年代的文化記憶中,成為對一種遙遠的文化理想的祭奠或呼喚。在詩人的思維中,它們成為神的意志的體現:上帝既是破壞者又是創造者。
參考文獻:
[1]西川.海子詩全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773頁
[2]西川.海子詩全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9頁
[3]劉小楓.詩化哲學[M].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7頁
[4]尼采.查拉斯圖拉如是說[M].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