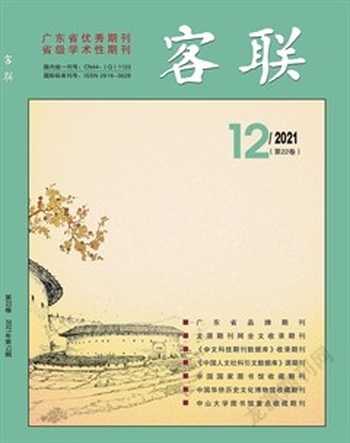淺談外嫁女回娘家活動的成因與問題
李偉梁
摘 要:本文以實地調查廣東省茂名市M、C、X等村為例,探討華南地區鄉村日益興起的外嫁女集體回娘家聯誼的現象的生成原因,同時也發現外嫁女回娘家活動存在可持續性發展的問題,為此提出針對性建議,以引導回娘家活動良性可持續發展,為農村社區發展貢獻力量。
關鍵詞:外嫁女;回娘家活動;農村
一、前言
近年來農村興起了外嫁女回娘家團聚活動,外嫁女性以集體回娘家的形式重新回到當地村民的大眾視野中,喚起了村民的鄉土情懷以及共建鄉村社區的熱情。“外嫁女”一詞具有典型的嶺南地方特色并且外延非常廣泛,廣義上的“外嫁女”是指所有出嫁的女性。據時政、網絡資料顯示,外嫁女集體返鄉團聚活動最先發生在廣東省的粵西地區,后續擴散到廣西、海南等地。因此,選擇茂名市的1區2市(茂南區、高州市和信宜市)作為調研地點,并通過前期的電話和網絡交流,確定成功舉辦外嫁女活動的M、C、X三村作為實地走訪村落,通過對外嫁女和當地村民的訪談獲得一手資料。
外嫁女回娘家活動這種鄉村內生、自下而上為主、以外嫁女性為參與主體的活動在弘揚熱愛家鄉、尊老愛幼等傳統美德發揮著積極的影響。在如今女性地位日益提高,女性力量日漸得到重視的社會背景下,外嫁女在未來或成為農村社區發展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二、興起原因
(一)社會因素
“外嫁女”的“外”字的涵義是傳統社會的外婚制和從夫居等社會制度將嫁女的身份規定為娘家的外人而來的,俗語“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也是這樣的意思。雖然傳統的社會制度規定外嫁女婚后是娘家的“外人”,但外嫁女依然能夠與娘家保持著一定的聯系,其方式是借由日常的“回娘家”習俗。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人口城市化和農民大規模流動,出現“男工女耕”和男女雙方外出務工的性別分工模式,婦女當家成為全國農村的普遍現象。婦女當家也代表著女性地位的提升,沖擊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社會制度,相應地“回娘家”也產生了變化。過去的外嫁女回娘家行為只是單向地接受娘家的情感支持和經濟,但現在女性在核心家庭中也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具有一定的資源,出嫁的女性可以一直保持著作為父母女兒的身份,可以對娘家提供情感、經濟、人力上的幫助。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女性回娘家已經突破了時間場合的限制。
(二)經濟因素
外嫁女回娘家活動的開展是以經濟條件作為基礎,像游街、聚餐、煙花表演、慰問長者等節目是離不開資金的支撐。回娘家活動的經費主要來源于外嫁女群體和村民自愿性捐贈,捐贈的金額不做硬性規定,每個人根據自身經濟條件而定。外嫁女和村民能夠自發性地捐錢背后的深層原因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的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如今,外嫁女們的家庭告別了溫飽時代,步入了小康之家,滿足自身家庭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她們有富余的資金可以自由支配,這是外嫁女活動舉辦的必要前提。甚至有部分外嫁女通過人口遷移以獲取更廣闊的經濟發展平臺,上升到更高的社會階層,這使得她們擁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去反哺家鄉。
(三)科技因素
現代日益發達的網絡與交通技術是外嫁女集體回娘家活動舉行的促進因素。古代地理區域的阻隔以及落后的交通方式,使得外嫁女每次回娘家都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如今發達的交通網讓外嫁女往返自家與娘家更加方便,能夠及時地回到家鄉參與外嫁女活動。
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加便捷。古代信息傳遞方式以人力或畜力為載體,傳遞速度慢,效果不盡人意,使得外嫁女與娘家、外嫁女群體內部無法保持及時的信息溝通,以致一些遠嫁女與其他外嫁女失去了聯系。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國進入“互聯網”時代,智能手機開始普及化,網絡通訊軟件如QQ、微信、微博等被廣大人民所使用。這些網絡通訊軟件不僅可以“一對一”的私聊,還可以以建立群方式進行低成本的、跨時間段的“多對多”的群聊。外嫁女活動的前期聯系都是借助了網絡的便捷性得以順利開展,活動的發起者和籌劃者利用微信組群方式聯系全國各地不同年齡背景的外嫁女,然后在群內的外嫁女又會把自己認識的外嫁女姐妹拉進微信群,經過不斷地“滾雪球”,最后微信群內聚集了上百名外嫁女,為舉辦回娘家活動奠定人員的基礎。
三、活動持續發展的困難
通過獨特的回娘家活動形式與內涵,外嫁女用她們的力量參與到娘家社區的發展,在為農村社區帶來正面效益的同時也間接地提高了舉辦村莊在當地的名氣。但由于外嫁女回娘家活動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群體性自發行為,自發意味會存在不穩定和不確定的因素,因為活動內外部的變動而出現中斷現象,不具備可持續舉辦的特征。目前,外嫁女回娘家活動的可持續舉辦面臨著兩大挑戰:一是來自群體內部的“攀比奢侈”風悄悄蔓延;二是來自外部正式權力對活動的負面反饋。
(一)“攀比奢侈”風
外嫁女回娘家活動的最初舉辦的動機是反哺家鄉、回饋父母、弘揚孝道等樸素的愿景,但隨著外嫁女回娘家活動的傳播與擴散,某些后續的模仿村落的舉辦開始摻雜了競爭與超越前者,不甘落后他者等其他動機。長期以來,村民深受鄉村社會中的“攀比”“講排面”等不良氛圍的影響,尤其在節假日和聚會的時候,炫耀攀比、鋪張浪費的現象更為突出,而舉辦外嫁女活動能彰顯村莊的文化軟實力和經濟硬實力,活動形式越為隆重則似乎代表著村民和外嫁女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因此,部分村落的男性村民開始產生了舉辦外嫁女回娘家活動以彰顯村莊財力和凝聚力的想法,更為積極主動地投入到活動的籌備中。在與S村訪談中,被訪者表示本村的活動預期總經費是20萬元左右,是C村的活動經費的3倍,以求比其他村落辦得更為隆重。
隨著回娘家活動的“攀比”、“講排場”風潮愈演愈烈,村民們將捐贈金額與孝順程度進行等價掛鉤,即“捐得越多越有孝心”,進而對外嫁女們形成了一種道德綁架,并將活動中的鋪張浪費行為進行合理化處理。若是回娘家活動的舉辦動機摻雜了攀比的因素,活動的籌資和預算也相應地變高,活動預算的增長速度一旦超過了外嫁女家庭的經濟收入的增長速度,則外嫁女更可能選擇退出回娘家活動,畢竟選擇超出自身經濟承受范圍去捐贈的外嫁女屬于少部分群體。如此下去,活動預算不斷增長最直接的影響是打擊了外嫁女的參與熱情,并把部分經濟能力有限或較為困難的外嫁女拒之于活動之外,這樣持續下去的后果是參與外嫁女回娘家活動的外嫁女數量逐漸變少,回娘家活動持續性受到嚴重的挑戰,外嫁女回娘家活動或成為曇花一現的時代產物。
(二)活動的行政合法性問題
行政合法性屬于形式合法性,是以官僚體制為存在基礎,獲得政府的默許和認可,對于外嫁女回娘家活動而言,是否擁有行政合法性將會是影響可持續性的關鍵要素,決定著活動能否繼續舉辦。外嫁女回娘家活動最初是自下而上的自發性活動,因其顯著的正面社會影響力被正式權力所注意到,又因其在華南地區的傳播過程中摻雜了“攀比”、“講排場”等因素被某些地方的正式權力所禁止。如2018年8月,海南省澄邁縣加樂鎮的外嫁女們身著鮮艷旗袍站在豪車上聲勢浩大地緩緩行駛的視頻在網絡上被多次轉發,引起網友們的議論紛紛,對此,澄邁縣紀委縣監委方面嚴厲地批評了此次回娘家活動,并指出活動形式過于奢華對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又如湛江市吳川市委辦公室發布《關于狠剎大操大辦“年例”、“外嫁女聚會”等不正之風倡導移風易俗的通知》,導致吳川部分村莊因此取消外嫁女回娘家活動。以上都是政府正式權力對外嫁女回娘家活動中存在的不正之風做出的強烈回應,若使外嫁女回娘家活動成為一種可持續的現象,以慣習的形式嵌入農村社區,則需要獲取正式權力的允許或默許;而獲取正式權力的允許或默許,外嫁女回娘家活動在舉辦過程中必須要去除“攀比”、“講排場”等不正之風,保持那顆“反哺家鄉、回饋父母”的初心。
四、活動優化對策
為了使外嫁女回娘家活動更好地發展,確保外嫁女的主體參與地位的同時引入其他主體參與其中,通過多元協作來實現回娘家活動的良性可持續發展。
首先,政府在看到外嫁女活動雖然在擴散的過程中出現的村與村之間的惡性競爭將活動推向形式化和奢靡化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活動的舉辦向社會傳遞男女平等、孝敬長者、飲水思源等觀念,所以,政府對外嫁女回娘家活動應該是“宜引不宜禁”的。政府需要充當引導者的角色,引導活動宗旨及目的符合當今社會的政治規范,將活動跟鄉風文明建設結合起來,促進鄉風民風建設,促使回娘家回歸“初心”。各級政府應認真落實好全省社會文明大行動動員大會上關于移風易俗的工作要求,印發相關通知,明令禁止外嫁女回娘家活動中的不正之風,不應“一刀切”地禁止整個外嫁女活動,摸索出一條既保留地方文化特色,又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節儉舉辦外嫁女回娘家活動的可持續之路。
其次,村委會的監督管理要貫穿回娘家活動的整個過程。這種監督管理是一種多元主體參與的體現,村莊內部可建立村規民約來確定村委會的監督制度,對外嫁女活動的規范作用。村委會對外嫁女活動的監督應該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對內容形式的監督,堅決抵制華麗花哨的注重表面但毫無意義的活動創新,村委會也可以建議回娘家活動嵌入“給長者送溫暖”、“關愛留守兒童”、“關愛農村殘障人士”等為主題的正能量鄉風建設活動,以充實回娘家活動的內容,賦予其新的意義;二是對財務的監督,村委會代表可以在活動籌劃之前與外嫁女取得聯系,了解外嫁女活動的進展情況和財務預算,并明確村委會方面對回娘家活動的要求和期待,將活動經費預算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使外嫁女回娘家活動成為一種優良的慣習,而不是一場周年性的“夸富宴”。對于回娘家活動的“精華”成分,需要進行保留,倡導外嫁女策劃節儉合理、充滿正能量的回娘家活動以此感恩父母和家鄉。
最后,培養外嫁女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能力。可根據各地的回娘家活動具體情況,積極選拔和培養活動積極分子,并以她們為中心,成立自發的外嫁女組織,若已存在外嫁女組織或類組織,則需要進行鞏固。以外嫁女自組織或類組織為平臺,調動外嫁女的參與積極性,重新喚回外嫁女對自身的知識和能力的自信,讓她們相信“自己的才能是社區的力量”的理念,從而敢于發表各自的觀點,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參與到回娘家活動當中。此外,外嫁女自組織發揮管理的功能,及時注意到回娘家活動舉辦過程中的問題,如外嫁女群體中的部分人員有可能參與不到活動當中,外嫁女自組織關注那些“非自愿”不參與者是活動籌辦過程中的重點,她們有的可能是家庭貧困被“高昂”的活動捐資而被拒之活動外,則外嫁女自組織應該給予關懷,免除她們參與活動的費用。
參考文獻:
[1]蔣志宏.農村“外嫁女”權益糾紛問題法律探索[J].南方農村,2004(04):35-38.
[2]孫海龍、龔德家、李斌,城市化背景下農村“外嫁女”權益糾紛及其解決機制的思考[J],法律適用,2004 年第3期.
[3]何陽.外嫁女反哺:鄉風文明建設路徑創新與引申[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9,18(04):561-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