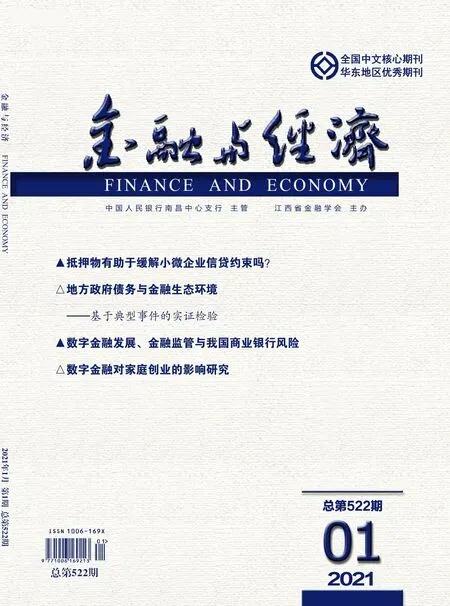后代特征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研究
■潘文東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資產配置視角下的家庭金融研究,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Campbell(2006)認為家庭通過對股票、基金、債券等金融資產進行合理的配置實現家庭財富的跨期優化,從而達到平滑消費并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目的。然而,現實中的家庭金融市場投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例如Bogan(2008)使用美國歷史數據研究發現,美國持有股票的家庭還不到1/3。而根據2015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CHFS)顯示,我國家庭金融市場參與概率為17.9%,股票市場參與概率僅為12.2%,而股票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重僅為2.8%。由此可見,家庭金融市場“有限參與”現象是國內外普遍存在的問題,但我國更為嚴重。該現象的存在會影響家庭資產的合理配置,阻礙在生命周期內的福利最大化。同時,會降低家庭總收入,影響家庭消費與各方面的支出,不利于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等目標的實現。此外,持續低迷的金融市場參與率也會影響我國資本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因此,需要解釋“有限參與”現象的背后成因,挖掘其中的影響機制并采取措施緩解這一現象。后代自古以來都是家庭人口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之“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傳統家庭思想觀念,后代的未來代表著整個家庭的希望。在后代撫養教育方面,家庭會不遺余力地投入時間、金錢等各種資源,來為后代提供良好的成長環境,為其發展保駕護航。因此,從后代特征角度探究其對家庭風險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有助于解釋和應對“有限參與之謎”。
圍繞該選題的研究,既有文獻主要集中在兩方面:第一,后代特征及其經濟效應研究。后代作為家庭人口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會影響到家庭的收入、消費支出和資源分配等行為決策。伴隨家庭后代數量的提高或新生兒的出生,由于母親的利他主義動機,會導致其勞動供給減少(張川川,2011)、收入下降(楊天池和周穎,2019),同時改變家庭的消費結構,提高消費支出,進而增加家庭的財務壓力,提高撫養負擔,在一定程度上擠出家庭金融資產投資(王子城,2016)。此外,后代性別也具有重要影響,我國存在的重男輕女思想仍未完全消除,加之我國男性在婚姻方面的競爭壓力、父母對后代的遺贈動機差異等情況,后代性別的差異可能會導致不同的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結果(藍嘉俊等,2018)。因此,后代特征可能是影響家庭風險資產配置的重要因素,其數量和性別上的差異會導致不同的風險投資決策,進而影響家庭的總財富水平,決定家庭的社會地位,而后代性別與數量差異又會影響到家庭在后代間教育、財富和遺產等資源上的分配。
第二,后代特征對家庭風險資產的影響研究。總體而言,鮮有文獻直接探究后代特征對家庭風險資產的影響。吳衛星和李雅君(2015)從家庭結構這一獨特視角入手,將樣本細分為獨代居住、與父輩同住、與子女同住等4個類型,又將有子女的家庭按子女的婚姻、性別區分為6個類型,研究發現有未婚后代的家庭以提高家庭財富為目的,更傾向于投資風險資產。王子城(2016)和藍嘉俊等(2018)分別從家庭人口撫養負擔和人口結構視角出發,雖然均以后代數量占家庭總人口比重作為核心解釋變量,但得到的結果存在差異,前者認為由于后代數量增加帶來撫養負擔的加重,會降低家庭風險資產特別是股票資產的配置。而后者發現家庭少兒占比的增加會提高風險偏好,從而使家庭更傾向于從事風險資產投資。王翌秋和王昊宇(2018)直接以后代數量為切入點,發現處于滿巢期階段的城鄉家庭會因子女數量的增加而調整家庭資產組合選擇策略,增加房產的持有,同時減少金融資產的持有。有關后代性別的研究更加匱乏,Bogan(2013)將后代性別與家庭的婚姻狀況結合起來,研究發現僅有女孩會提高已婚家庭的風險資產配置,而僅有男孩會提高單身母親的風險資產配置。Lundberg & Rose(2002)認為男性后代對父母工作的激勵效應大于女性后代,而且由于男性承載的社會意義大于女孩,所以更能激發父母進行風險資產投資。譚燕芝和李維揚(2018)使用農村地區樣本數據發現,農村家庭金融行為表現出“重男輕女”特質,有男孩的家庭對未來金融投資表現活躍。而對影響機制的分析,藍嘉俊等(2018)使用中介效應檢驗法實證檢驗發現少兒占比的增加會提高戶主的風險偏好程度,從而促進家庭投資于金融市場。但在對是否有兒子的異質性分析中,雖然指出兒子可能通過風險偏好和由于結婚導致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兩個渠道影響家庭風險資產配置,但并未實證檢驗這兩個影響渠道的存在。Bogan(2013)的研究指出后代可能會通過改變父母特定偏好類型和遺贈動機兩個渠道影響父母的資產配置,但未進行實證檢驗。Wei&Zhang(2011)研究發現有男孩會導致家庭的儲蓄上升,但并未進一步分析這一行為是否會影響家庭風險資產配置。
縱觀已有文獻,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將后代特征與家庭資產配置相結合的文獻較少,缺乏對后代特征影響的直觀和系統研究。第二,缺乏對后代影響機制的實證檢驗。雖然Bogan(2013)和藍嘉俊等(2018)在理論上指出性別偏好、婚姻壓力等機制存在的可能,但并未找出合理的代理變量驗證影響機制的存在。第三,忽略了樣本選擇偏差問題,并且對后代特征影響的異質性缺乏深入探討。據此,本文采用逐層分析的方法,首先探究后代對家庭資產配置的總影響,然后分析不同子女數量影響的差異性,最后基于獨生子女和無子女家庭樣本,在控制內生性問題的同時剔除出后代數量的干擾后得到了后代性別影響的凈效應。實證結果可以更加清晰系統地呈現后代特征對家庭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效果,豐富我國家庭微觀金融需求的相關研究。
二、數據和變量說明
(一)數據來源
數據來自西南財經大學2015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項目,該項目樣本覆蓋全國29 個省份,351 個縣(區、縣級市),1396 個村(居)委會,樣本規模為37289戶。采集了家庭人口特征、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消費、保險與保障等方面的微觀信息,全面反映了我國家庭金融的基本情況。
(二)變量選擇及說明
首先,根據尹志超等(2015)的研究,將風險資產定義為包括:股票、基金、金融債券、企業債券、金融衍生品、外幣資產、黃金;金融資產包括:風險資產、現金、股票賬戶現金、政府債券、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股票市場參與表示家庭是否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如果持有股票取1,否則取0;股票資產占比表示家庭內股票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重。風險市場參與表示家庭是否持有風險資產,如果持有風險資產取1,否則取0;風險資產占比表示家庭持有的風險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重。
其次,核心解釋變量是后代特征變量,包括家庭中后代的數量和性別。其中,后代啞變量表示家庭中是否有年齡小于24 歲的后代,如果有取1,否則取0;后代數量啞變量用于表示家庭中后代個數,分為一個孩子、兩個孩子和三個及三個以上孩子;后代性別啞變量用于在獨生子女家庭子樣本下研究性別對家庭資產配置的影響,分為男孩和女孩。
除了核心解釋變量外,控制了表示戶主特征、家庭收入資產情況和省份的特征變量。戶主特征變量包括:戶主的性別(男性為1,女性為0);戶主的年齡及其平方項;戶主的婚姻狀況(已婚為1,其他取0);戶主的健康狀況(問卷回答非常好、好、一般時取1,其他取0);受教育年限(沒上過學0年,小學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為12 年,中專/職高為13 年,大專/高職為15 年,本科為16年,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為19年);戶口類型(城鎮戶口取1,其他取0);風險偏好(由高到低依次取值1—5)。家庭收入資產特征變量包括:家庭凈資產(用總資產減去總負債得到);家庭總收入;家庭是否從事工商業經營(是取1,否則取0);家庭是否擁有自有住房(是取1,否則取0)。由于家庭總收入和家庭凈資產等變量可能存在異方差和非線性,因此對其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另外,為控制不同省份無法觀測因素的影響,采取省份固定效應加以控制。數據處理中,剔除了家庭凈資產小于0和家庭總收入小于0的樣本。表1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描述性統計
從表1可以看出,樣本家庭中參與股票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家庭占比分別為12.2%和17.9%,這表明中國家庭的股票市場參與率和金融市場參與率均較低,存在“有限參與”現象。進一步看股票和風險資產占比情況,分別為2.8%和7.3%,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樣本中擁有孩子的家庭占比54.3%,其中擁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占36%,兩個孩子的家庭占15.3%,三個及三個以上孩子的家庭占2.9%,在獨生子女家庭中,男孩占比25.9%,而女孩只有18.1%,男孩比女孩多8%左右,反映出我國存在性別比例失衡問題。此外,戶主年齡的均值為52.4 歲;樣本中75.1%的戶主為男性;87.4%為已婚家庭;受教育水平的均值為9.8,即處于初中水平,表明戶主文化水平較低;85%的家庭擁有自有住房。
三、實證分析
(一)估計模型
1.資產參與概率模型
在研究后代特征對家庭股票市場參與和金融市場參與的影響時,因為參與與否用0—1 二元變量表征,持有資產定義為1,否則為零,所以使用Pr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相應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家庭是否有股票市場和風險市場參與,Childi為后代特征變量,包括后代數量和性別,Xi是一系列控制變量,ui是不可觀測的省份固定效應;此外,使用權重數據在省份層面對樣本加權,從而使分析結果更具代表性,同時本文將標準誤聚類到省級層面。
2.資產參與深度模型
在研究后代特征對家庭股票市場和金融市場參與深度的影響時,由于參與深度的比重介于0和1之間且是截斷的,因此使用T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相應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家庭持有股票資產和風險資產占家庭金融資產的比重,y*表示占比大于0的部分。
(二)估計結果
1.養育后代對家庭資產配置行為的總體影響
根據模型(1)和(2),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檢驗后代是否會對家庭資產選擇行為產生影響。表2中(1)、(2)列報告了養育后代對家庭股票和風險資產參與概率的影響,后兩列報告了對兩類資產參與深度的影響,表中Probit模型和Tobit 模型回歸結果報告了邊際效應,表示解釋變量變化1 單位所引起的家庭持有風險資產概率和比例的變化程度。回歸結果表明養育后代對家庭股票和風險資產配置行為均有影響,養育后代會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降低家庭股票和風險資產的參與概率和參與深度。說明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有孩子相比于沒有孩子的家庭在股票和風險資產的參與概率上要分別低1.4%和3.2%,兩項資產的持有比例要分別低0.4%和1.4%。

表2 后代對股票和風險資產參與的影響
其他控制變量的系數大部分都是顯著的,并且與已有的研究結論較為一致。股票和風險資產的參與概率和深度與戶主年齡的關系呈“駝峰”狀(李麗芳等,2015),說明生命周期效應的存在。戶主的身體狀況越健康,金融市場參與概率和持有比例越大(Rosen & Wu,2004)。此外,戶主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參與風險投資的概率越大,且估計結果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住房的邊際效應顯著為負,說明住房對家庭風險資產投資存在擠出效應(吳衛星等,2014)。非農業戶口的家庭投資風險市場的概率更高。家庭收入與家庭凈資產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收入與凈資產高的家庭財務狀況良好,會提高家庭的股票和風險資產參與概率及持有比重。
2.后代數量對家庭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
回歸結果表明,養育后代會顯著降低家庭股票和風險資產的參與概率和持有比重。那么,后代數量對家庭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存在差異嗎?基于此,表3給出了后代數量對家庭風險資產參與概率與深度的影響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有兩個及兩個以上孩子會降低家庭股票和風險資產的參與概率和持有比重,均在1%水平下顯著。而且,隨著后代數量的增多,后代數量對家庭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程度更大。以風險資產參與為例,有一個孩子會使家庭投資于風險資產的概率降低2%,有兩個孩子會降低7.7%,三個及三個以上孩子會降低9.2%,這說明隨著子女數量的增加,家庭的撫養負擔更重,從而對家庭風險資產投資的擠出效果更明顯。在股票資產投資中,一個孩子的影響不再顯著,原因可能是家庭中股票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例很小,僅2.8%,由于單一的股票資產只占家庭總財富的小部分,加之一個孩子所帶來的撫養壓力低于有一個以上孩子的家庭,所以當家庭中僅有一個孩子時并不會對股票資產配置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或影響很微弱。

表3 后代數量對股票和風險資產參與的影響
3.后代性別對家庭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
一個孩子會顯著降低家庭風險資產參與概率和持有比重,這一影響是否與后代的性別差異有關?不同性別的后代對家庭的資產配置行為是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接下來進一步細分后代性別,分析性別影響的差異性。由于生孩子的決策行為并非完全外生,比如孩子多的家庭可能本來就比較富有,傾向于持有風險資產。因此,根據Bogan(2013)的方法,剔除后代數量大于一的家庭,進一步將樣本控制在獨生后代家庭和無后代家庭的子樣本下,控制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進一步研究后代性別與家庭資產選擇之間的關系。根據表4給出的結果,獨生子女導致家庭風險資產參與概率和持有深度降低的原因均是由男孩引起的,男孩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降低了家庭風險資產參與概率,在同樣的顯著性水平下降低了風險資產持有比重,而女孩并不會對風險資產配置產生影響。由于股票資產的配置行為不會因獨生子女因素受到影響,因此在回歸結果中,男孩和女孩均不會對股票資產的配置產生顯著影響,但是符號仍然是負的。

表4 后代性別對股票和風險資產參與的影響
四、影響機制分析
(一)購房壓力
Wei&Zhang(2011)研究發現有男孩的家庭在子女婚禮和彩禮上的花費更多,父母為提高兒子在婚姻市場上的吸引力會進行“競爭性儲蓄”,更多的儲蓄是為了兒子結婚買房,而房產對風險資產選擇有擠出效應(吳衛星等,2014),進而降低了家庭風險資產的配置。但是由于該調查數據并未詢問有關后代婚姻準備情況的信息,故而本文使用家庭擁有幾套房產(numb_house)作為代理變量來初步探索,檢驗是否是由于男性后代因買房而帶來的競爭壓力影響了家庭資產配置行為。
使用Baron & Kenny 逐步檢驗法檢驗購房壓力在后代性別對家庭風險資產選擇影響中的中介作用。中介效應檢驗的基本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中介效應檢驗示意圖
在圖1中,解釋變量后代性別通過中介變量家庭擁有房產數影響被解釋變量風險資產參與概率和持有比例,圖1(a)中c是后代性別對家庭風險資產參與和持有比例影響的總效用。圖1(b)中a 為后代性別對家庭擁有房子數的影響,由于家庭所擁有的房屋套數為分類變量,因此本文使用有序多分類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對其進行估計。c′為在控制了中介變量后,后代性別對家庭資產配置的直接效應。效應之間的關系為c=ab+c′。


表5 中介效應檢驗
表5 是后代性別對家庭風險資產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其中,(1)是有序多分類Pr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2)和(3)中的B 列是對上述方程(4)的估計結果,分別使用的是Probit 模型和Tobit 模型,A 列是沒有加入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從表5給出的結果可以看出,男孩對家庭擁有房子數量變量的影響估計系數a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擁有房產數量變量對家庭風險資產參與概率和參與深度的影響系數b均在1%水平下顯著。在控制了家庭擁有的房產數量后,男孩對家庭風險資產參與概率的直接影響c′的顯著性水平雖然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其邊際效應的絕對值變小了,而對風險資產持有比例的直接影響c′不僅邊際效應的絕對值減小,顯著性水平也下降了。此結果說明擁有房產數量在男孩與家庭風險資產配置中的中介作用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有男孩的家庭由于結婚而產生的購房壓力,會提高家庭生活和財務負擔,擠出家庭風險資產投資。雖然對于中介效應的檢驗多使用乘積分步法、Bootstrap 法等方法,但是溫忠鱗和葉寶娟(2014)發現,當Baron&Kenny 逐步法得到了顯著的a、b 估計時其結果要優于Sobel檢驗、Bootstrap 法等方法,因此本文中介作用檢驗的結論可靠。參照息晨(2019)的方法,由于本文使用了Oprobit 和Tobit 模型對中介效應檢驗方程進行估計,因此使用間接計算中介效用占總效用的比例。經計算,在家庭風險資產參與概率中,來自購房壓力的中介效用占總效用的比例約為25%;在風險資產持有比例中,中介效用占總效用的比例為26.55%。雖然家庭擁有房產數不能完全衡量由于婚姻市場的競爭壓力所產生的影響,但是以上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男孩之所以會導致家庭風險資產參與概率和持有比重下降,其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是男孩結婚購房所導致的財務壓力。
(二)風險態度

表6 后代數量與風險偏好
藍嘉俊等(2018)研究發現家庭中少兒人數占比對家庭風險偏好程度有顯著影響,家庭中少兒占比的上升會提高家庭的風險偏好水平,從而提高家庭金融市場參與和風險資產配置比重。為了檢驗家庭風險態度與后代特征之間的關系,此處將家庭風險態度變量(risklike)納入回歸模型中。表6 是將風險態度變量與后代數量啞變量同時納入回歸模型,對比表3 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引入風險態度變量后,后代數量啞變量依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各變量對家庭資產配置行為影響的邊際效應只是略微大于表3 中的回歸結果。此外,運用中介效應檢驗法,發現后代數量與家庭風險態度之間并沒有顯著性關系。同樣,表7 是將后代性別與家庭風險態度變量同時納入回歸模型的結果。結果表明,在引入風險態度變量后,男孩依然會顯著降低家庭風險資產的參與概率與持有比重,顯著性水平并未發生變化。運用中介效應檢驗法后,同樣并未觀察到后代性別會影響家庭的風險態度。以上結果說明,后代特征并不會通過風險偏好程度影響家庭資產配置行為。此外,在引入風險態度變量后主要結果并未發生顯著變化,說明前文結果是穩健的。

表7 后代性別與風險偏好
五、異質性分析
(一)城市與農村影響差異
表8 和表9 分別為在城市和農村子樣本下,后代數量與性別對家庭風險資產選擇的異質性影響結果。從表8 中可以看出,在城鎮地區,后代數量的提高仍會顯著降低家庭風險資產的參與概率和持有比重。這一結果在農村地區不再明顯,雖然有三個及三個以上后代變量仍顯著為負,但二孩變量均不再顯著。表9是后代性別的回歸結果,男孩對風險資產配置行為的負向影響僅在城市子樣本下顯著。這可能是由于農村地區的金融可獲得性較低且金融素養不高,居民很少將資金投資于金融市場,導致后代特征的影響在該地區難以捕捉。

表8 后代數量與家庭資產選擇(城鄉差異性)

表9 后代性別與家庭資產選擇(城鄉差異性)
(二)東、中西部地區影響差異
按家庭所在區域位置進一步將樣本劃分為東部和中西部兩個子樣本,分別回歸得到后代特征在不同區域位置影響上的差異。從表10結果看,后代數量的影響并無明顯地區差異性,無論是在東部還是中西部地區,子女數量的增加均會降低家庭的風險資產參與概率和持有比,但是后代性別的影響有所不同。根據表11給出的結果,在東部地區,男孩不僅會影響風險資產的配置行為,而且會導致家庭投資于股票的概率下降,同時也會減少股票的持有比重,這一結果與總樣本的回歸結果略有不同。而在中西部地區,男孩雖然仍會影響風險資產配置行為,但影響效果僅在10%水平下顯著,影響效果很微弱。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相比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更高,金融體系更加健全,金融可獲得性更高,因此在東部地區,后代性別甚至會影響到股票這一單一資產的配置比重,而相對發展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后代性別的影響效果就變得很微弱。

表10 后代數量與家庭資產選擇(地區差異性)

表11 后代性別與家庭資產選擇(地區差異性)
(三)不同收入水平的影響差異
進一步按家庭的收入水平,將樣本劃分為高、中、低收入水平三組。表12 與表13 結果表明,后代數量對家庭風險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不存在收入水平上的差異性,但后代性別對家庭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收入水平組,在中低等收入水平的家庭影響效果很微弱。按收入水平的劃分可以看出,由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財富有限,在滿足基本生活條件下很難再有多余的錢用于投資,加上該類家庭的受教育水平可能很低,金融知識匱乏,基本很難再進入金融市場;而高收入家庭的財務狀況良好,在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后仍有剩余,而且該類家庭的金融知識水平通常較高,投資失敗的概率相比其他家庭較低,因此該類家庭進入金融市場的概率更大,所以后代性別對高收入水平家庭影響更明顯。

表12 后代數量與家庭資產選擇(收入差異性)

表13 后代性別與家庭資產選擇(收入差異性)
六、穩健性檢驗①因篇幅所限,結果留存備索。
本文從以下5 個方面進一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第一,考慮到家庭是否生孩子的決策同樣并非完全外生的,家庭中某些因素可能同時影響生孩子的決策行為以及家庭風險資產配置行為。為控制該內生性問題,在回歸分析時本文進一步剔除樣本中的無子女家庭,即在探究后代數量的影響時僅保留有后代的家庭,在研究后代性別的影響時僅保留獨生子女家庭。第二,使用Heckman 兩步法模型控制樣本的自選擇問題,結果中逆米爾斯比率的系數并不顯著,說明樣本不存在嚴重的自選擇問題。第三,使用CHFS目前已完成的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7 年四次調查結果,組成四期混合面板數據,運用面板Probit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檢驗結果的穩健性。第四,參照其他研究家庭人口結構對風險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文獻(藍嘉俊等,2018;余靜文和姚翔晨,2019;樊剛治和王宏揚,2015),使用后代數量占家庭總人口的比重(后代占比)作為后代數量的替代變量。第五,修改家庭后代的定義,將后代范圍縮小到家庭中14歲以下的人口,進一步檢驗后代特征影響的穩健性。以上穩健性結果均證實后代特征對家庭資產配置的影響是穩健的。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實證分析后代特征對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影響,發現因后代數量增加而導致家庭撫養負擔加重的家庭,會擠出家庭在金融資產上的投資,這一影響無顯著差異性。而后代性別不同,后代中男性后代的存在會顯著降低家庭在風險資產上的參與概率和配置比重,而女性后代并不會產生影響。在進一步的機制分析中,本文驗證了由于男性后代結婚買房而帶來的生活或財務負擔的加重,對家庭資產配置產生擠出效應這一影響機制的存在。此外,從城鄉和區域差異看,后代性別的影響在東部和城鎮地區更加顯著;將樣本劃分為高中低三個收入群體后,發現這一影響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在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很微弱。
基于上述結論,為緩解“有限參與之謎”現象并從政府擴大內需視角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第一,從政策層面緩解居民撫養負擔,引導家庭從事風險資產投資并優化家庭消費結構,促進我國消費內循環。面對生育政策改革所引致的撫養負擔加重問題,政府應配套完善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和育兒體系,實現“社會+家庭”二合一的后代撫養體系,緩解家庭撫養負擔,釋放家庭撫養資金,進而促進家庭風險資產合理配置和消費結構升級。第二,緩解居民住房壓力,釋放家庭財務資金。政府應發揮其宏觀調控職能,通過適當調控土地供應,控制房地產投資規模,調整房地產市場供應結構等方式,緩解房地產市場過熱現象,降低家庭住房壓力,從而防止家庭因過度儲蓄和住房資產占家庭資產比重過高而導致的家庭消費和資產投資結構扭曲等問題,實現家庭消費和資產配置結構合理化。而且應更加關注二孩政策時期房地產市場的供需問題,避免未來社會人口年輕化導致房價再次升溫。第三,合理完善我國不同地區金融市場建設,發揮金融資產的實際收入效應,促進消費增長。政府在資本市場建設過程中,可以通過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方式,發揮其資本集聚與輻射功能,以點帶面促進整個區域的金融經濟發展,緩解金融排斥現象,提高我國金融體系的廣度與深度,實現財產性投資渠道的健康發展。要確保各地區家庭有同等機會進入金融市場,實現多渠道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從而使家庭金融資產的財富效應得到有效發揮,有利于家庭降低預防性儲蓄、提高消費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