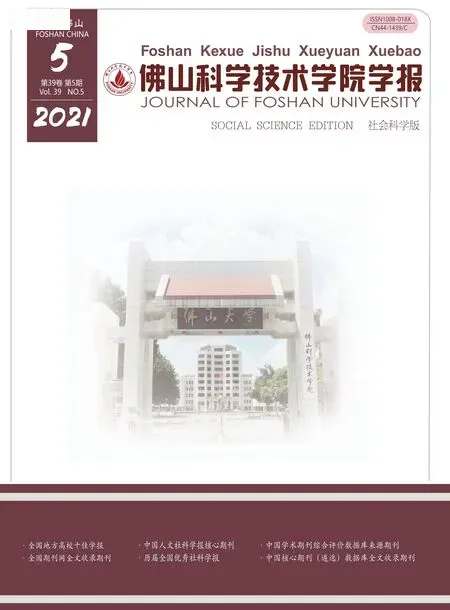林大欽隱逸詩與陶詩風格差異辨析
林玉潔
(廣州南方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廣東 廣州 510970)
林大欽(1511-1545),字敬夫,號東莆子,潮州海陽縣東莆都(今廣東省潮安區)人。嘉靖十一年(1532)舉進士,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兩年半后,乞歸終養老母,“戊辰,翰林院修撰林大欽疏請給假送母還鄉,許之。”[1]辭官后的林大欽,隱居東莆山中長達十三年之久,其間“懷古問經,畜雞種黍,親學老圃,以供朝飧,聊追丈人之蹤矣。逸興時生,率爾成詠”[2]217,日日與山水田園為伴,借詩吟詠性情,抒歸隱之志向。其去世前親自編訂并命名的詩集《詠懷集》,收錄的詩歌,絕大部分是隱逸之作。
鐘嶸曾將陶淵明譽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隱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通過詩歌的創作而呈現。林大欽的隱逸詩歌與陶詩有諸多相似之處,后人評價林大欽的詩歌,亦多將其詩歌與陶詩相比較,如言“其詩沖澹閑適,有類陶、韋”[2]381,“五言古詩,絕有陶彭澤風味,余體亦蕭然自放,骨帶煙霞”[2]372,“蘊藉和平,幽閑淡雅,宛然陶阮風范,令人躁累盡釋”[2]374。從中可以看出,前人認為林大欽詩歌有陶詩沖澹閑適之風,特別是五言古詩。但若細致分析林大欽隱逸詩所表達的內容及情感,會發現其與陶詩的關系頗為復雜,本文將以《詠懷集》為考察對象試論之。
一、林氏隱逸詩對陶詩的繼承
林大欽的隱逸詩有明顯對陶詩模仿的痕跡,詩歌有的直接以陶淵明本人為抒情對象,有的則化用陶詩的詩句來抒寫己志。
(一)隱逸詩中的陶淵明形象
詩集中有對陶淵明本人的直接吟詠,通過分析可以看出陶淵明在林大欽詩中是以何種形象出現,進而考察林氏對陶的承繼處于何種層面。林大欽的五言古詩《懷古三首·其三》:
陶公在園田,而無人世喧。時賴好事者,載酒相與還。有時發清興,高歌黃唐言。身名渺不營,好爵何足論。世事亂如麻,結綬生煩冤。逍遙觀所尚,庶令古道存。[2]225
首句言陶淵明歸隱田園,得免于世俗喧囂紛擾。“而無人世喧”使人不禁聯想到陶詩《飲酒·其五》的開篇“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3]234,高節的隱士形象呼之欲出。“時賴好事者,載酒相與還”借王弘與陶淵明相交的故事入詩,江州刺史王弘想結識陶淵明,以酒相邀,陶氏則欣然前往。“有時發清興,高歌黃唐言”,黃唐指黃帝和唐堯,陶淵明《時運》“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3]8,素琴一張,濁酒半壺。卻終不及黃唐盛世,深深地慨嘆自己的孤獨。后三句言身與名均非本心所追求,高官厚祿更是如此。世事紛繁如亂麻,出仕做官徒生煩惱憤懣。不若任逍遙以觀物,存古道以自適。《懷古》全詩都在寫陶淵明,為我們勾勒了遠離世俗,不好名利,以酒交友,瀟灑自適的隱士形象。詩人贊頌陶淵明以隱居求志的現實選擇,懷古的同時亦是表明己志。
另一首七言絕句《遣興十二首·其三》也是吟詠陶淵明。“陶潛曾作歸來人,臥穩柴桑太古春。卻遺秀句存青史,未絕風流漉酒巾。”[2]296詩中言陶潛曾作《歸去來兮辭》表達自己歸隱的志向,隱居不仕以追慕遠古遺風,留下秀美的詩句和以頭巾漉酒的風流率真。如果說“臥穩柴桑太古春”的陶潛是隱士,“卻遺秀句存青史”的陶潛則是詩人,“未絕風流漉酒巾”的陶潛更是多了幾分魏晉風流,這是林大欽眼中陶潛的形象剪影,是隱士、詩人、逸士幾種身份兼具的自己想要仿效的陶淵明。
此外,再如林大欽的五言律詩《臥起即事三首·其三》“杜甫慚真隱,陶潛已掛冠。他時論出處,江海意漫漫”[2]264中再次寫到陶潛面對出處的抉擇,毅然掛冠歸隱,給后人留下無窮無盡的神往。另一首五言律詩《九日》寫重陽節登高賞菊,“地與陶潛迥,思同謝朓清。長歌待松月,曲盡亦何營”[2]283。雖然自己賞菊的地點與陶淵明不同,但有一份長歌待松月的逸致和清思,為何還要去強求其他無關緊要的東西呢?春日午睡起床后的即興吟詠也好,九月九日重陽節賞菊也罷,詩中的陶潛反復被提及的是他出處的選擇、隱士的身份,而林大欽自身的仕途選擇——棄官歸隱,以隱求志與之何其相似!借陶淵明的隱者形象來抒發己志,是林大欽隱逸詩中多次出現陶潛形象的共同特征。林氏對陶潛的承繼更多地體現在出處態度、人格精神的層面。
(二)詩中對“陶詩”成句的化用
林大欽的隱逸詩除了對陶淵明形象的直接吟詠,更多的是對陶詩成句的化用。如五言古詩《田園雜詠八首·其二》:
人事多舛錯,百年會多憂。知止乃不辱,安命故無愁。投冠旋舊廬,學圃度清秋。忘我千年思,慶此孤生幽。衣食聊自須,沌然無外謀。長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2]219
“人事多舛錯,百年會多憂。知止乃不辱,安命故無愁”,人生難免經歷錯舛,人事百年常懷憂思。只有懂得適可而止,才能安命沒有憂愁。“投冠旋舊廬,學圃度清秋”借用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中的詩句“投冠旋舊廬,不為好爵縈”[3]180,陶詩原句是說自己決心辭官返回故里,不為高官厚祿所動情。林大欽在出處選擇上與陶氏相同,故借“投冠旋舊廬”句言辭官歸隱之志,之后是“學圃度清秋”,通過學做農事、學種蔬菜來度過歲秋。“忘我千年思,慶此孤生幽。衣食聊自須,沌然無外謀”,(隱居山林使我)忘記了人世的種種煩憂,慶幸此生可以遵從自己的內心。衣食姑且可以滿足生存的需要,不用再費盡心機向外百般謀求。“長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一句,化用陶淵明《詠貧士·其四》“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3]336,能與心中追求的仁義之道共生,即便晚上就死去,也沒有什么可遺憾的。詩中有兩句借用了陶詩的成句,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改寫,融入自己歸隱后的真實生活狀態,借以表明自己同陶淵明一樣的人生志趣。
另《田園雜詠八首·其四》也是借陶詩成句和《論語·微子》中荷蓧丈人的典故,坦言做官干祿不是自己的追求。
丈人有素業,乃在南山陲。尺籍觀元化,荒田解歲饑。良辰入奇懷,杖策攜親知。開酌話唐虞,緬然起深思。去運不復還,尼父空棲棲。商歌非吾事,行云聊在斯。舉觴酬巢由,千載何嶷嶷。[2]220
作為隱士的丈人,隱居在南山之下。以子史為伴,觀自然運化,雖然田地荒蕪,但也聊以為生計。觀美景入懷,攜杖策訪友。執杯把酒,追慕堯舜盛世,悠遠邈杳,引我無限深思。逝去的時光不再回來,孔子的內心急遽不安。干謁求祿非我真實意愿,保有己志姑且在山水行云之間。舉起酒杯,敬傳說中的隱士巢父和許由,高節之志,千年后仍令人感佩。“良辰入奇懷,杖策攜親知”,化用自陶淵明《和劉柴桑》“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一句,原詩即景抒懷,良辰美景之中,持杖返回西廬,寫隱者曠達的胸襟和怡然自樂之趣。“商歌非吾事,行云聊在斯”化用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句,“商歌”典出《淮南子》,春秋時寧戚聽聞齊桓公欲興霸業,在其路過的地方以商歌感之,為齊桓公所知,舉為相。陶詩和林詩均反其意而用之,坦言商歌求官不是我的志向,像沮溺那樣并力躬耕的生活才是我的心中向往。
五言絕句《六月觀獲》亦是借陶詩成句表歸隱之志。“暑獲豈不勞?稱心固自好。何如青云人,冰炭滿懷抱。”[2]314炎炎烈日下的收獲豈會不辛勞?但因合乎己志而心滿意足。“何如青云人,冰炭滿懷抱”,“青云人”指得志而居高位者,此兩句詩襲用陶淵明《雜詩·其四》“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3]313,用《淮南子·齊俗訓》中的典故,言得志而居高位的人貪利與求名的兩種心思,常常交戰于胸中,如冰與炭不能相容一般,令人苦痛。“何如”則有慶幸之意,意指不用受冰炭縈懷的名利紛擾,獨享歸隱之樂。
從林大欽詩歌中涉及的陶淵明形象和化用的陶詩成句來看,林大欽對陶淵明的追慕和模仿更多來自陶氏的志節,隱居山林而全其志的出處選擇。
二、“沖澹閑適”之外的繼承與變革
昔日論者往往多關注林大欽詩歌對陶淵明“沖澹閑適”詩風的繼承,較少論及二人詩風其他方面的聯系,本段從“沖澹閑適”詩風之外,進一步探尋二人詩歌之異同。
(一)縱橫何足道,意氣郁嵯峨——對陶詩豪逸之氣的繼承
黃徹《鞏溪詩話》言“世人論淵明,皆以其專事肥遁,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嘗求其集,若曰:‘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其自樂田畝,乃卷懷不得已耳。士之出處,未易為世俗言也。”[3]567陶淵明詩歌平淡自然之下,猶有“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3]559的豪逸之氣,易被忽視。而林大欽的詩歌,在抒寫隱逸志趣、寄情山水之時,也每每有豪逸之氣流露,與陶詩一脈相承。以他的三首《嘯歌》為例:
山中白云歌,天上彩云緩。時乘明玕車,笑接淵明盞。我生欲何為?軒裳空依依。時增陵谷思,羲皇胡不歸?青陽動芳草,白日嗟淪老。卓犖觀前進,曠然清懷抱。[2]251
山高不可登,河深豈可厲!平原九萬里,翱翔足游弋。白龍在深淵,海水揚其波,誤落湘江蹊,泥沙奈爾何?白玉一杯酒,青云在軒牖。笑拉洪涯肩,軒榮復何有。[2]251
青山誰與語,白云空婆娑。壯心徒激烈,歲暮將若何?三杯起高詠,一嘯凈秋波。縱橫何足道,意氣郁嵯峨。[2]285
第一首詩,“山中白云歌,天上彩云緩”以山中自然之景開篇,借李白送友人歸隱時高唱白云歌的典故,暗示自己高臥白云之志,又與詩題“嘯歌”遙相呼應。“時乘明玕車,笑接淵明盞”,瑯玕既指石美而似玉者,也指綠竹。陶淵明《讀山海經》以“亭亭明玕照,洛洛清瑤流”,明玕形容昆侖山的瑰麗。林詩中以乘瑯玕竹車,接淵明酒盞來表示自己對陶淵明歸隱之志的繼承,聯系此詩的后半部分,也未嘗沒有繼承陶詩的不平之氣。下句直言自己的人生志趣:人生之志在何?非在功名利祿,“時增陵谷思,羲皇胡不歸”,“陵谷”引《詩經·小雅·十月之交》“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句,毛傳釋其“言易位也”。世道變易,小人處上,被委以重用;君子居下,反遭到貶謫。這兩句詩流露出林大欽對當時朝政的不滿。流連在春陽、芳草間的詩人,只能不斷地感嘆時光的流逝,“卓犖觀前進,曠然清懷抱”,效仿先賢,以超然之姿在山水間蕩滌心胸。第二首詩歌大意:青山和白云都缺少知音,一如我的壯士之心,徒勞激蕩又奈何,歲暮將至,年華老去,飲酒長嘯,以蕩除心中的憂愁。世間的紛擾何足掛齒,在內心保持著浩然的意氣,自可與高山比肩。而第三首詩大意:山高不能攀登,水深不能渡河,好比世道的險惡。萬里的平原,廣闊的天空,好比隱逸生活的自由逍遙。江海之中的白龍,誤落狹淺的小溪水。借飲酒揮灑心中逸氣,與傳說中的仙人洪崖為友,世俗的高官美譽不再掛懷。此三首詩,都不約而同地言及世俗的險惡,自己的志向不能實現,卻又不愿與世俗同流,故而隱蔽在自然山水之中,借酒抒發胸中的浩然逸氣。此與淵明《歸去來兮辭》中暢言“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的情志何其相似!
再如其五言古詩《田園雜詠八首·其八》,首句“傲然遂獨往,長嘯開云扉”[2]222,高傲不屈的詩人獨自一人徜徉山林,高聲長嘯蕩開云扉。“傲然”“長嘯”兩詞,似破空而來,讀者直接感受到了詩人胸中涌起的一股豪邁、激蕩之氣。而朱熹在評陶淵明詩歌時,也注意到陶詩寓于平淡之中的豪邁,“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3]567陶淵明詩集中不唯《詠荊軻》一篇,其他如《擬古九首》《雜詩十二首》《詠三良》等篇均可印證。薛侃曾形容林大欽的文章有蘇軾的風采,“屈注奔騰,神氣宛肖”[2]283,實則其詩中亦有體現。林大欽詩歌對陶詩豪逸之氣的繼承,昔日論其詩風者往往不及言之。
(二)殘暉與幽色,披豁共吾真——與陶詩風格的差異
林大欽喜用“幽”“孤”“獨”等字摹物狀情,詩中常常流露一種清幽、孤寂之情,此與陶詩風格迥然不同。以“幽”字為例,《詠懷集》中共收錄詩歌356 首,其中有近100 首詩歌使用“幽”字。如用“幽”來描寫自己居住的環境,“不愛芳草根,而從幽竹卜”[2]238,“青山容我放,水竹靜幽居”[2]255,“如今花色濃,吾屋自幽僻”[2]312,比起芳草的紛繁艷麗,詩人更偏愛臨水的幽竹,以此作為自己的居所,保有一番幽靜的天地。
再如用“幽”描繪日常所見的風景。“幽徑少行跡,列樹儼成行”[2]242,“寒流明野際,落日半幽山”[2]277,“清溪吟落日,芳草惜幽扉”[2]259,“芝蘭值幽谷,而無媚世姿”[2]239,“晚色足幽光,蕩揚千古思”[2]224,“悠悠大地幽,神德終不虧”[2]241。興致所致,寄情山水,無論是初春還是晚秋,是清晨還是日暮,正如其詩中所言“殘暉與幽色,披豁共吾真”[2]260,林大欽眼中的“幽景”,落在筆端便化為一縷“幽情”,景是情的外化。
有時“幽”會在一首詩中反復出現,如《五月樓中雨后夕望》中“幽徑少行跡,列樹儼成行。游云向何處,飛鳥度前塘。晚色足幽思,水花搖素光”[2]242,這幅五月雨后的晚景圖中,行人稀少的幽徑,樹列成行的幽色,游云和飛鳥引發的幽思,“幽”徑好像通往詩人的內心,引人去探索景中的孤寂、深遠之境。又如《園居遣懷·其二》中“短景難幽臥,秋風差自強。村幽宜杖履,歲暮識行藏”[2]281,短促的白天難以幽然獨臥,此句化用杜甫《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其二》“短景難高臥”句,但將杜詩的“高”改換成自己鐘愛的“幽”字。幽靜的鄉村適宜拄杖漫步,一歲將終識得萬物行藏。幽臥與幽村,僻靜的居所,引發詩人對生活的追憶和慨嘆。
再如《田園雜詠·其八》“眷然媚幽獨,行歌冥是非”[2]222,坦言自己對“幽獨”的留戀不已。何為“幽獨”?為何能引起詩人的留戀?《田園雜詠·其七》也許給出了答案,“眾芳委時化,幽獨媚孤清”[2]221,群芳隨著季節而凋零,只有一樹幽花和這孤寂清冷之境。“眾芳”是比喻用世之士,而“幽獨”是詩人自比。并非詩人孤芳自賞,而是面對濁世和眾芳的一份傲然獨立和清醒自持。《春日遣興·其四》中“百花叢里結幽亭,萬草青青照獨惺”[2]302亦有相似的表述,“惺”通“醒”,獨醒,用《楚辭·漁父》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典故,此處借百花、萬草的意象抒情,獨醒是詩人自指,喻己卓爾不群,異乎流俗的志向和品格。這里的景色是清冷的、寂靜的,但詩人表達的情感卻是強烈的、激蕩的,難掩的幽思與激蕩的情感在詩中自然地融為一體,遺世獨立的風姿和與世抗爭的風骨,在林大欽的隱逸詩中并存。
三、平生饒幽意,于此慰窮通——林氏詩中的幽意
林大欽喜用“幽”字,“幽”在詩中除了表現景色的幽靜、內心的幽寂之外,還與其對“道”的體悟密切相關。如“風光驚節換,幽興與誰言”[2]261,時光在不知不覺中驚換,幽微的旨趣可以向誰訴說呢?“餐霞吾不忝,真此慰幽惺”[2]257,餐服朝霞而無愧色,唯此慰藉內心的幽明。“平生用幽意,非愛百年名”[2]286,“平生饒幽意,于此慰窮通”[2]265,一輩子喜愛幽深之意,想以此來慰藉一生的困厄與顯達!詩句中的“幽興”“幽惺”“幽意”蘊含著林大欽獨特的人生體驗。
林大欽在《華嚴講旨》一文中言:“諸賢進學,先須理會此心……宋象山氏所謂‘惺惺’,吾朝白沙氏所謂‘至神’,陽明氏所謂‘良知’,圣賢百言,異世同符。是皆形容此心妙義。”林大欽受陽明心學影響,尤其是在歸隱之后,與朋友往來的書信中,不斷探討如何通過“此心”的修持,去追求生命的大“道”。“心”是一切存在的本體,在林大欽看來,宋代的陸九淵、本朝的陳獻章,乃至王陽明提出的“良知”之學,都是對“心”之妙義的體悟。而“幽興”“幽惺”“幽意”等詞均含有一種體道的意味。究竟是何種“道”?我們不妨從其隱逸詩中探尋答案。如《感興十七首·其十五》:
知為傷陵遲,一德可終生。逍遙隨大化,順應故無情。達觀齊萬物,撫己何獨清。冥然絕所慮,斯理日明明。知德形乃實,虛通道之平。鼎鼎百年內,持此慰吾誠。[2]236
“知為傷陵遲,一德可終生”,知識和行為都會損傷人的形神使之衰落,唯有“一德”值得終生追求。順應自然萬物的變換,摒棄世間紛繁的思緒,通過修德以體“道”。“鼎鼎百年內,持此慰吾誠”,為名利忙碌的一生,秉持此“道”以慰藉自己的內心。此詩的最后兩句化用陶淵明《飲酒·其三》的詩句,但卻反陶詩之意,陶氏原詩: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3]230
詩歌一開始便感嘆“道”近千年的衰微,人人自私吝其情。有酒竟然不肯暢飲,只在意世俗的虛名。珍視自我之身,難道不是因為人生只此一回?一生又能有多久,快似閃電令人心驚。為名利忙碌的一生,如此怎能真有所成!陶詩對道喪千載的回應是忘虛名、貴自身,在詩酒山水中度過今生。結句“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此”字指前句詩中的“世間名”,是對放不下世間功利之人的諄諄告誡。而林大欽詩的末句“鼎鼎百年內,持此慰吾誠”,“此”字指代前句中的“一德”,即內心追求的道。
陶淵明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三》中也表明過自己對“道”的看法,“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3]191先師孔子留下的遺訓:君子應該憂道不憂貧。仰慕高論卻難以企及,不如轉而致力于田間耕耘。與落日結伴而歸,以酒漿慰勞四鄰。姑且掩柴門而吟詩,親耕以做農民。詩中認為像孔子那樣“憂道不憂貧”,常人難以企及。自己選擇效法長沮、桀溺等隱士,守節躬耕,隱居南畝,詩中暗含了對孔子“憂道”的否定。與此對比,林大欽詩中反復追尋的“德”,并期望以“德”見“道”就更有儒家的色彩。雖然詩中也時而借用“逍遙”“齊物”“達觀”等道家的概念,但最終落腳點在“知德”“體道”。追尋內心的道以“立命”,這是林大欽隱逸詩的思想核心。
四、余論
潮汕學者蔡起賢在《林大欽集·序》中指出林大欽與陶淵明在思想上的不同之處,“陶潛的思想,還局限于儒道之間。而林大欽于儒道之外,有他自己的習學修養。心學原多有禪意,大欽心學往往與佛家的諸相皆空、唯心不滅之說相合。”[2]5林大欽確實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并有所突破,其文集中多有與浙中學派王畿、錢德洪,泰州學派林春、趙貞吉等人的書信往來,思想更接近龍溪、泰州一脈。林大欽在《與戚南山黃門》中言“道以無為為妙……誠者自誠,道者自道,非人力為之”[2]186,此“道”為心學之道,但又與王陽明的“致良知”之教有別,并沒有是非善惡的人為判斷標準,而是任由自在之心“自照自施,無牽無系”[2]182,又言“善惡同于幻化,思慮等于冥蒙,清凈均于大道,滅絕齊于生發”[2]182,與上文所引《感興十七首·其十五》“冥然絕所慮,斯理日明明。知德形乃實,虛通道之平”表意相同。
進而引出“道心”的修習方式,“人心之真,萬古不磨,原自廓然,非由圣傳而有”[2]190此處提到“人心之真”,對含有人的生命欲望的真心的追求是其體道的方式。而陶淵明詩歌“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4]48的天然文字與本色性情,正好契合了林大欽心中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