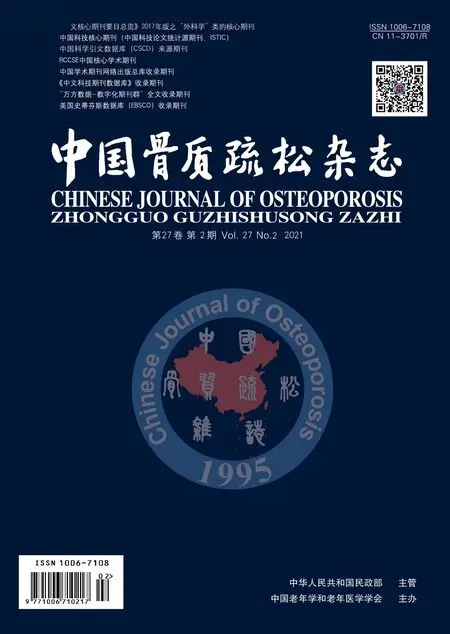絕經后骨質疏松癥女性血清IL-31和腰椎、股骨頸骨密度相關性研究
張曉越 王小紅 王長平
1.甘肅省慶陽市人民醫院,甘肅 慶陽 745000 2.甘肅省慶陽市第二人民醫院,甘肅 慶陽 745000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免疫系統與骨骼之間存在關聯[1]。免疫系統與骨組織細胞之間存在相互影響,這是由共享受體、可溶性分子和信號傳導途徑介導的[1]。T細胞是公認能夠誘發破骨細胞和成骨細胞失衡的關鍵調節劑[2]。白細胞介素31(IL-31)是近十年發現的一種細胞因子,屬于gp130/IL-6細胞因子家族[3],并傾向Th2表型的活化記憶CD45RO+T淋巴細胞表達[4]。IL-31能刺激促炎性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基質金屬蛋白酶的分泌[5]。此外,已經有研究觀察到IL-31可以在無巨噬細胞的系統中對Th1和Th17的分化產生正向和負向影響[5]。這些數據表明IL-31通過調節抗原呈遞細胞或更直接地調節T細胞自身來調節免疫應答的潛在功能。IL-31涉及皮膚病理[6]、炎癥性腸病[7]、變態反應[5]、呼吸道炎癥[8]和某些類型的腫瘤[9],但尚未研究其在絕經后骨質疏松癥中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探索IL-31和絕經后骨質疏松癥關系。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方案
本研究納入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甘肅省慶陽市人民醫院就診(年齡為50~75歲)的健康絕經后女性參加本研究。對于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患者,納入標準為:(1)絕經超過5年;(2)OP患者的平均BMD至少比正常成年人低2.5個標準差。排除標準:使用過或正在使用骨代謝的藥物或保健品,例如激素、骨質疏松癥藥物或鈣和維生素D補充劑;服用可能影響維生素K代謝的肝素或華法林;患有內分泌或其他內科疾病如甲狀腺疾病、甲狀旁腺疾病、鈣和骨代謝異常、自身免疫疾病、腎、心血管、腦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本研究得到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所有參與者均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1.2 一般臨床資料的收集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和病歷記錄收集參與者的相關信息。受試者脫掉衣服和鞋子,換上檢查服,通過使用標準的身高和體重檢測儀器測量其高度,精確到0.1 cm,并且其重量精確到0.1 kg。體質量指數(BMI)通過將體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獲得。使用XR-600 雙能X線骨密度儀對患者的腰椎(L1~4)和左側股骨頸BMD進行檢測。
在受試者禁食12 h后收集血樣。通過使用自動化學分析儀(AU-5400;Olympus Optical Co,Tokyo,Japan)測量鈣和磷。骨堿性磷酸酶(BAP)、骨鈣素(BGP)和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RACP-5b)的水平通過酶聯免疫吸附測定(ELISA,R&D,USA)進行測定。批內CV分別為3.5%~4.2%、3.6%~4.7%、3.1%~4.7%和3.0%~5.4%,批間CV<6.6%。使用自動Roche電化學發光系統測量I型膠原交聯N-末端肽(NTX-1)和25-羥基維生素D[25(OH)D]。批內CV分別為3.6%~4.7%、3.1%~4.3%、4.1%~5.2%和3.3%~5.5%,批間CV<5.6%。根據制造商的說明使用標準夾心ELISA試盒IL-31試劑盒(USCN LIFE SCIENCE,Houston,TX,USA)檢測IL-31濃度。批內和批間變異系數(CV)分別為<1.9%和<2.7%。
1.3 統計學分析
根據變量的特征使用均數±標準差或比例(%)表示。對于非正態分布的變量,以四分位數范圍(25%~75%)表示。對Kolmogorov-Smirnov檢驗后確定為非正態分布的變量進行對數轉換。根據變量的特征使用獨立t檢驗,χ2檢驗或Mann-WhitneyU檢驗來比較骨質疏松組和正常骨密度組之間的差異。使用Pearson相關系數研究血清IL-31水平與其他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使用IL-31作為因變量,其他參數是自變量,進行逐步多元回歸分析尋找血清IL-31濃度與其他變量之間的獨立關系。所有數據均使用SPSS 19.0進行分析,P<0.05表示比較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研究人群的人口學和臨床特征如表1所示。絕經后骨質疏松癥(PMOP)患者的絕經年齡、體重、身高和體重指數與健康對照組(NBMD)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絕經后骨質疏松癥組年齡、血清IL-31、TRACP-5b和NTX水平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均<0.05)。絕經后骨質疏松癥組血清BAP和BGP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P均<0.05)。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患者血清25(OH)D水平明顯低于對照組 (P<0.05)。

表1 研究人群的特征和生化檢測結果Table 1 Characteristic and biochemical data
絕經后骨質疏松組女性血清IL-31水平與年齡、BMI、BAP、BGP、TRACP-5b、NTX和25(OH)D呈正相關;而對照組女性血清IL-31水平與年齡、BMI、BGP和NTX呈正相關,與其他指標未發現相關性;偏相關分析校正年齡和BMI后,絕經后骨質疏松組女性血清IL-31水平與BAP、BGP、TRACP-5b、NTX和25(OH)D仍然呈正相關;而對照組女性血清IL-31水平僅僅與BGP和NTX呈正相關。見表2。

表2 血清IL-31水平與人體測量學和實驗室變量之間的雙變量相關分析Table 2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es between serum IL-31 levels and anthropometric and laboratory variables
在絕經后骨質疏松患者中,股骨骨密度(FBMD)與年齡、IL-31、BAP、TRACP-5b和NTX呈負相關。同樣,腰椎骨密度(LBMD)與年齡、IL-31、BAP、TRACP-5b和NTX呈負相關;而對照組FBMD與年齡、IL-31呈負相關。同樣,LBMD與年齡、IL-31呈負相關(表3)。在偏相關分析中調整年齡和BMI后,對照組IL-31與FBMD呈負相關;對照組IL-31與LBMD(R=-0.339,P<0.01)同樣呈負相關。然而,在絕經后骨質疏松組患者中,FBMD及LBMD均與IL-31、BAP、TRACP-5b和NTX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性。

表3 骨密度與血清IL-31水平和人體測量學和實驗室變量之間的雙變量相關分析Table 3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es between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serum IL-31 levels and anthropometric and laboratory variables
3 討論
本研究表明,與正常骨密度組成的對照組相比,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患者的血清IL-31水平顯著升高;同時發現這類患者血清BAP和BGP水平明顯升高,同時血清TRACP-5b和NTX水平顯著升高。進一步研究發現血清IL-31水平與年齡、BMI、BAP、BGP、TRACP-5b、NTX和25(OH)D呈正相關,股骨和腰椎骨密度與IL-31呈負相關。
年齡和雌激素缺乏可能是發生骨質疏松癥的兩個最重要的危險因素,盡管骨密度降低可能與不同的病理條件有關[10],而且在這些因素中,最基本的決定因素的影響比其他因素更普遍。據報道,某些細胞因子的水平與骨質疏松癥的發生可能存在相關性[11]。重要的例子是絕經期骨質疏松癥雌激素缺乏導致干擾素-γ、白細胞介素-6和白細胞介素-17的產生[12]或腫瘤壞死因子-α在類風濕性關節炎繼發性骨質疏松癥中的作用[13]。本研究證明了絕經后骨質疏松癥婦女中IL-31血清水平升高,發現這種細胞因子似乎與絕經后骨質疏松癥有關。正如研究中發現血清IL-31水平與年齡呈正相關,再次證實年齡是IL-31的獨立預測因子。
本研究結果證實了IL-31水平與年齡之間的關系,這反映在老年患者中這種細胞因子的水平較高。這些發現為更好地了解IL-31在衰老以及與年齡有關的疾病中的多種功能打開了一扇門,并為衰老過程中骨吸收與IL-31之間的聯系提供了證據,表明IL-31在老年骨質疏松癥的獨特作用。IL-31及其受體參與造血祖細胞穩態的調節,特別是與髓系祖細胞的穩態有關[3],它們也是破骨細胞(專門用于骨吸收的細胞)的常見前體[14]。另外,這種細胞因子能夠誘導單核細胞活化[3]。據報道,IL-31增加了促炎基因的轉錄,并在活化的人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中誘導了促炎作用[5]。
據報道,多種細胞因子和轉錄因子與骨質疏松癥的發生有關,其中一些受到IL-31的調節[5,15]。幾項研究表明,IL-31刺激破骨細胞生成因子、趨化因子和基質金屬蛋白酶的分泌[5,15],所有這些都與破骨細胞的分化、募集和功能有關,因此其是破骨細胞在骨重塑過程中的關鍵調控因子。特別指出的是IL-31可以促進促炎性因子IL-1β、IL-6和趨化因子CXCL1、CXCL8、CCL2和CCL18的釋放[3]。這些數據表明,IL-31可能充當促炎細胞因子,參與破骨細胞前體的募集和免疫介導的骨吸收。IL-31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可與IL-17 A媲美:這兩種細胞因子在刺激具有骨骼吸收能力的促炎癥因子和趨化因子的分泌方面顯示出累加作用[16]。而且,促炎細胞因子反過來增加了IL-31及其受體復合物的表達。在用IFNγ、IL-1β和TNF-α刺激后,已顯示出IL31、IL31Rα和OSMR基因表達的最強上調[16]。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的活性氧也能刺激T細胞,單核細胞和單核細胞衍生的樹突狀細胞中IL-31的表達,誘導炎癥反應,從而增強與年齡有關的骨吸收[17]。正如本研究中發現代表破骨細胞活性標志物TRACP-5b和NTX水平、IL-31呈正相關。
總的來說,本研究揭示了IL-31水平升高與絕經后骨質疏松發生有關。但是由于研究樣本量和納入人群的特異性,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大樣本量和選取不同性別年齡的人群加以研究確認本研究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