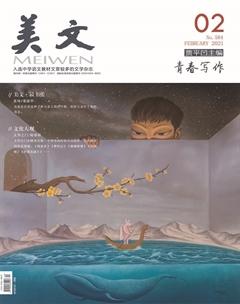聽鐘
周宇亮
我一向是喜愛聽鐘的。
幼時,我曾同父母游覽池州九華,留宿于山間民居。白日里,我們隨團觀覽山中廟宇古剎、突巘危峰、古藤老蘚。每至暮色四合,我們便踩著山寺晚課的鐘聲返回住宿地。彼時我素性淘氣,面對溪徑曲折,疊石參差,并不能有“松間明月,石上清泉”之詠,亦不能解“萬里歸來卜筑居”之嘆。在那時的我看來,聽導游口若懸河地談“這塊石頭有什么傳奇典故”,還不如去追逐一只松鼠或是蹲在路邊看每一級臺階上不同的蓮云紋刻來得有意趣。可我卻格外喜歡聽廟里的晚鐘。鐘聲響起時,即是飛鳥還林時。而我們投宿的主人家也會在堂屋口點上幾個大紅燈籠。每當我蹦蹦跳跳地躍上延伸而上的青石階,就能看見人們在庭院中張羅晚飯的身影,相歡語笑,伴著悠遠的晚鐘,在暮云千里中氤氳融融暖意。隱于山林中的杳杳鐘聲并不講究排場,卻于綠玉青瑤之館安禪自得,在澹泊寧靜中悄然自重,暈染“蒸藜炊黍餉東菑”般的恬淡畫卷。
下山后,我對九華山上最高峰究竟峰高幾許并沒有留下深刻印象,卻常常回憶起那片鐘聲,總是在青山收斂余暉時翩然而至,同行者遙遙致意。
依舊是假日里,我同母親前去新落成的省博物館,在館內的游客體驗區看到了成排的編鐘,母親便鼓勵我敲一支曲子。我依照標牌上的說明,先用丁字形的木槌順次試了一遍高音音階,再用長形棒試出低音,零零碎碎地敲了一段《小城故事》。雖然極為業余,但我卻樂在其中,久久流連。我敲編鐘,自然奏不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漢唐氣象,也展現不出“洋洋兮若江河”的磅礴氣韻,可我卻仿佛在鳴響的編鐘聲中瞥見了波光云影般的古韻。編鐘之音恍若淮水東畔的舊時月色,靜謐而莊重,悄然流淌著苒苒年光。雖早已不見玉人,卻可依稀窺見闌外疏花,清芳散逸,淡入小窗橫幅。
今年“十一”,我在細雨中前往大雁塔。可能是由于天氣原因,早晨慈恩寺的游客不多。我沿著東側小徑走過松竹蒙茸的石板路,穿過老槐樹蔭,最終來到大雁塔下。但大雁塔給我的第一感受并不是“孤高聳天宮”“蹬道盤虛空”的氣勢雄渾,而是每層塔四角上的風鐸自在而舞的靈動。雨聲中,風鐸應風而歌,清脆細碎的樂聲與古樸的雁塔、幽雅的禪院相映成趣,平添幾分活潑靈韻。
不多時,云消雨霽,陽烏光動。游客也漸漸多了,人聲漸沸。此時我立于檐下,卻再難聽清風鐸的歌聲了。
“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這首從孩提時就耳熟能詳的《楓橋夜泊》,于悠遠而沉郁的鐘聲中寄予客心百念。鐘聲,并不拘于響遏行云之偉勢,亦可喚游子近鄉之情怯,曳杖扶籬行過流水人家。一如《漢書·食貨志》中言:“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雖是樵野音律,卻皆懷自然質樸之實,浸潤過日色月光,漫步在寒暑冬夏,散于草履葛衣中伴鐘聲吟誦淺唱,綻放出扣人心弦的滟瀲風華。
《 傾城之戀》的演繹,總有一把胡琴,咿咿呀呀,拉過來又拉過去,《牽風記》的敘述,也常伴七弦古琴,于聲淡中俯仰古今。有時流浪于吟游詩人的足跡,亦驚喜能有曼陀林相倚。而今我再聽記憶中的鐘聲陣陣,仿佛于眼前徐徐展開回憶的大觀園百景圖譜,一切塵封于過往;“少顏色”的舊時光,都在或綿長或清亮的鐘聲里重開了生面,搖曳生姿。
我一向是喜愛聽鐘的,但愿我的漫漫人生路上,常有那一片杳杳鐘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