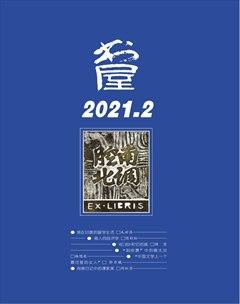晚清湘紳領袖、學界泰斗王先謙
夏劍欽
長沙王氏是以文章官宦起家的。自始遷祖王霑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中進士,通判湖南岳州府,后定居長沙城北以來,就是湖南的望族。至十二世出現晚清學界泰斗王先謙,可說是淵源有自,長盛不衰。
王先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一日出生在長沙市營盤街。六歲學為詩文,父親命其名為先謙,字益吾。十八歲補廩膳生。咸豐十一年(1861)二月其父棄世,年二十的王先謙因“糊口無資”,不得已而投筆從戎,入長江水師向導營任書記。后又兩次投軍為幕僚,終于同治三年(1864)九月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治八年充國史館協修,十一年補國史館纂修。光緒二年(1876)補國史館總纂。五年,升補翰林院侍講,充日起居注官,開始編撰乾隆朝《東華續錄》一百二十卷。光緒六年充會試同考官,升補國子監祭酒。光緒八年編纂《續古文辭類纂》。光緒十年完成《天命以來十朝東華錄》,共四百一十九卷。光緒十一年上疏罷三海工程,以紓民困,矛頭直指慈禧太后,結果外放江蘇學政,結束了他在京為朝廷史官的生涯。
勤于政事續編經解
光緒十一年八月,王先謙以國子監祭酒出任江蘇學政。十月抵江陰,駐學署。隨后即發放“觀風題”,并撰《勸學瑣言》,開設南菁書局,匯刻先哲箋注經史遺書,并“捐千金為倡”。
王先謙為學政期間,勤于政事,辦事效率極高。他每年的春、夏、秋三季,都要到所屬的府、州、縣出棚舉行歲試、科試。如光緒十二年二月,到蘇、松、鎮、太四府州舉行考試,六月回署后又試常州府屬。光緒十三年,二月出棚試徐、海兩屬,歲、科并行,五月回署后又到常州舉行科試;六月奏報歲試完竣,又并科試徐州、海州、常州,八月又出棚科試鎮、蘇、太、松四屬,十一月還出棚科試淮安。光緒十四年,正月科試揚州,二月科試通州,六月科試江寧。而且每次考試的試卷,全都由他親自過目。有資料說,王先謙閱覽文件和起稿均極敏捷。監考時,他端坐暖閣,收到試卷當即批閱,等到終場,已將全部試卷過目一遍,入選的試卷再帶回略加復檢,即交書房上粉牌提復,所以每場均無積壓。
王先謙很看重考生的好文章,曾將他視學江蘇“按試歲、科兩試所得佳文,刊為《清嘉集》初、二、三編,復選嘉慶以來名人時義刊為《江左制義輯存》”,以作為士子學習的范文。
他在江蘇學政任上還做了一件在清代學術史上頗有影響的大事。那就是他在創建僅三年的南菁書院內設立書局,奏準刊刻皇皇巨著《皇清經解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如此巨大工程,首尾歷時三載方告竣,由當時江陰的一流書坊“寶文堂”雇工百余人精心刻印。為刻印此書,單黃楊木片就用掉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塊。此書仿照道光九年著名學者阮元在兩廣總督任內刊刻的《皇清經解》體例,繼續收集清人經學著作匯刊。由王先謙負責編輯,葉繼幹、王賓監刻。所收著作除顧炎武、王夫之、毛奇齡、萬斯大、閻若璩、胡渭、江永、惠棟、程廷祚等數十人的之外,又增加洪亮吉、梁展繩、嚴可均、馬瑞辰、嚴元照、沈欽韓、陳奐、俞正燮、龔自珍、劉寶楠、俞樾等數十家,共一百一十一家,二百零九種。其中很多是清代學者考訂、訓釋經學的成果,從中可見清代經學之演度,并供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和語言文字之參考,于保存文獻、發展學術,功莫大焉。清代文獻學家劉錦藻評價說:“維持文獻之功,阮氏之后為推先謙矣。”此書自光緒十四年刊行后,年年均重印頒行全國,流傳海內外,蓋合正、續兩編,則集清代經學著作之大成矣。
王先謙任江蘇學政時,還重修了學署后于咸豐十年被太平軍毀壞的后花園——寄園。他搜集存雪亭詩碑重建碑廊,名曰“墨華榭”,“綴以梅塢竹徑,間以菊圃菜畦。奇石列秀,嘉樹環植”。又建“永慕廬”三間,供奉王先謙父母遺像,堂曰“虛受”,為朝夕讀書游憩之所,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十三有《重建寄園記》一文記其事。至今,江陰市中山公園內的學政節署舊址及后花園、墨華榭碑猶在,中有王先謙《和駱公曾存雪亭元韻》詩碑一方。江蘇學政衙署遺址有王先謙《燈下閱卷》青銅雕塑一組,展現其燈下批閱考卷的場景。
光緒十四年,王先謙還曾上疏彈劾太監李蓮英招搖,請旨懲戒。對此,朝廷雖未能采納,但王先謙獲“直聲”甚著。十月任滿交卸后,即請假兩月回籍修墓,次年二月假期已滿,他又以“病體未痊”,呈請湖南巡撫代奏開缺。三月獲準辭官后,便在長沙城東北隅的古荷花池前建筑新宅,名曰“葵園”,隨后便開始了他在葵園著述自娛,并主講于思賢講舍、城南書院與岳麓書院的中晚年生活。
主講岳麓書院改章
光緒十六年(1890),回長沙定居后的王先謙應郭嵩燾之聘主講思賢講舍。這是郭氏于同治、光緒年間在長沙小吳門正街的船山祠內創辦的一所小書院。講舍取名思賢,意思是思念王船山、曾國藩等先賢。講舍建成之后,郭嵩燾親自任主講,不教舉業,專講經史。不久,因赴京辦理洋務,他又出使英、法,講學被迫停止。待郭氏重返講舍時,已人到暮年,知道王先謙回鄉了,便“固以相讓”,請先謙繼任主講。王先謙接任后,又與鹺務公所商定,“歲醵六百金”,在思賢講舍內設局刻書,“是為湘省思賢書局之始”。書局當年就輯刊了孫鼎臣、周壽昌、王闿運等人的《六家詞鈔》和毛國翰的《青垣詩鈔》。
光緒十七年,因城南書院山長王楷病故,地方大吏再三聘請,王先謙辭思賢而移主城南書院。是年刊《荀子集解》、《世說新語》、《鹽鐵論》。十八、十九年仍主城南,刻郭嵩燾《養知書屋遺集》、《合校水經注》和吳敏樹《柈湖文集》。
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海戰中,中國海艦全軍覆沒,湘軍又敗于遼東半島的日軍槍炮之下,湘人虛驕之氣為之頓挫,中國面臨著滅種亡國的危機。湘中士紳一改往日保守,而趨于維新,成為戊戌運動的先驅和大本營。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五十三歲的王先謙受湖南巡撫吳大澂之聘,由城南書院山長轉任岳麓書院山長,帶領稱名最古的岳麓書院,開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近代化征程。
教育改革是湖南新政的先導,岳麓書院的改革更是推行湖南新政的排頭兵。可以說,岳麓書院的改革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開始,二十三年達到高潮,二十四年因陷入與時務學堂的爭斗而停滯,而其首倡并力行者,當然是山長王先謙。
岳麓書院的改革,首先是王先謙于光緒二十二年十月發布手諭,訂購《時務報》令諸生閱讀,以“開廣見聞,啟發志意”,備國家棟梁之用。這份手諭首先闡明了訂購《時務報》的理由:“竊惟士子讀書,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守帖括,罕能留意時務,為太平無事時之臣猶之可也。今則強鄰逼處,列國紛乘,脧我脂膏,環顧幾無所憑恃……為士子者,若不爭自振奮,多讀有用之書,相與講明切磋,儲為國器,出則疏庸貽笑,無以勵相國家,處則迂腐不堪,無以教告子弟。枉生人世,孤負圣明,恥孰甚焉?”認為士子們面對民族危機,必須爭自振奮,多讀有用之書,而上海《時務報》“議論精審,體裁雅飭,并隨時恭錄諭旨暨奏疏、西報,尤切要者,洵足開廣見聞,啟發志意,為目前不可不看之書”。為此,他特意讓書院訂購了六份《時務報》,“每二齋共閱一份”,“隨時派人分送”,讓學生“或翻閱抄謄,或略觀大意”,由此可見王山長啟發學生“期于致用”、“留心時務”的苦心。
其次,為了學以致用,王山長主張對書院課程進行改革。他認為:“中國風氣未開,才能未顯,故外人聲光電化之學,皆宜加意講求。”因此,他在光緒二十二年的《諭諸生》中重申原奏內定課程一條,分類為六: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輿地之學,曰算學,曰譯學。又《重師道》一條內稱,算學、譯學目前或非山長所能兼,則舉諸生中之通曉者各一人,立為齋長分課之。并強調:“方今時事多艱,培才為急,將欲講求實用,不能專恃制藝試帖以為造就之資。”(《岳麓書院志·岳麓書院記事錄存》)對此,《湘報》41號也曾報道,說岳麓書院“以經義、治事分門,提倡新學”,“添設算學、譯學”。這些都為古老的千年書院注入了新鮮空氣,也為以后書院改為學堂奠定了基礎。
始與維新終于守舊
甲午戰后的維新運動在全國興起,湖南一些士紳開始興辦近代工業。王先謙不甘落后,投資銀一萬兩,與黃自元、陳文瑋等集股,并撥借官款,于光緒二十二年創設寶善成機器制造公司,始終經理其事。但公司開辦數年,折損頗多,不久交給官辦,終因經營不善而停辦。
與此同時,王先謙還參與了“幡然改圖,廣開學校,悉師西法”的湖南時務學堂的創辦。就在王先謙與蔣德鈞、熊希齡、張祖同等申請公款創辦寶善成機器制造公司的光緒二十二年冬,蔣“嫌其跡近課利”,乃有創設時務學堂之議,獲得眾人贊同。于是,公推王先謙領銜,向湖南巡撫陳寶箴呈送設立時務學堂的報告,很快就批準立案。隨后,王先謙以紳董身份,與熊希齡、蔣德鈞、李維漢、譚嗣同、黃自元、張祖同、陳海鵬、鄒代鈞一起,組成時務學堂九人董事會,參與學堂決策。王先謙還積極促成《時務報》主筆梁啟超、翻譯李維格分任時務學堂中、西文總教習,并高規格接待,為梁總教習等人洗塵。應當說,時務學堂創辦之初與岳麓書院是同屬一條戰線的戰友,王先謙與梁啟超也是互為欣賞的,時務、新學甚至西學是其共同點,而矛盾、斗爭都是后來的事情。
王先謙畢竟是覃受皇恩的國子監祭酒,其政治思想不能突破維新派倡為平等、民權的底線,因此徘徊在革新與守舊之間,使岳麓書院與時務學堂和平共處、并行發展了一段時間之后,必然暴露其守舊的一面。新、舊矛盾的焦點在講學的內容上,用王先謙的話講,時務學堂所講已非新學、西學,而是“謬托西教”,“專以無父無君之邪說教人”。梁啟超自己也說:“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嘩,群起掎之……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飲冰室合集》卷三十七)
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隨著梁啟超離開湖南到上海治病,以時務學堂與岳麓書院為代表的新、舊兩派的分裂才開始公開化。據唐才常《致歐陽中鵠書》:“外間攻學堂事,三月即有所聞,或謂中丞已厭卓如,或謂日內將使祭酒公代秉三,葉奐彬為總教習。”可見梁啟超離湘后,舊派就傳出陳寶箴巡撫“已厭”梁教習的話,說不幾天就將由王祭酒代替熊希齡為總理,由葉德輝代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至閏三月初二月,《湘報》第41號即刊出南學會新派人物周啟明要求整頓岳麓書院的四點理由,新、舊矛盾已公開,且日趨激烈。
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在全國開展維新運動,維新派更占上風,而使湖南新、舊矛盾激化。五月十二日,岳麓書院齋長賓鳳陽、楊宣霖、彭祖年等聯名上書山長王先謙,以維護綱常名教、忠孝節義為名,學理上攻擊康有為、梁啟超的民權、平等主張,稱梁啟超在時務學堂“是借講求時務,行其邪說”,“其所以立說者,非西學,實康學耳”。而“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權耳,平等耳,試問權既下移,國誰予治?民可自主,君亦何為?是率天下而亂也”(蘇輿《翼教叢編》五編)。組織上攻擊時務學堂總理熊希齡及教習譚嗣同、唐才常等,稱其邀梁講學,“邪說浸淫”,使得湘省民心“頓為之一變”,“必欲傾覆我邦家也”。因而,請王山長致書陳巡撫,“從嚴整頓,辭退梁啟超等”。
陳寶箴解除熊希齡時務學堂總理之職、令黃遵憲接替后,王先謙又糾集張祖同、葉德輝等十人向陳寶箴上《湘紳公呈》,將矛頭直指在北京主持維新運動的康有為、梁啟超,說“中學教習廣東梁啟超,承其師康有為之學,倡為平等、民權之說”,“自命西學通人,實皆康門謬種,而譚嗣同、唐才常、樊錐、易鼎輩,為之乘風揚波,肆其簧鼓”,為害甚大,應該“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之人”(《虛受堂書札》卷一)。
與此同時,熊希齡也以被解職之身發起反擊,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湘報》111號上發表其聯名《公懇撫院整頓通省書院稟稿》,針鋒相對地把矛頭直指王先謙和岳麓書院,稱全省書院“積弊太深”,“山長多半守舊不通時務之人”,不能“聽其坐擁皋比”,必須改聘。次日,熊希齡又在《湘報》再登《上陳中丞書》,回應駁辯王先謙等人對他和時務學堂的攻擊,文中乃至有“不能以口舌與爭,唯有以性命從事,殺身成仁”之類“仇深莫解”而愿以性命相拼的話。
對此,逞強好勝的湘紳領袖王先謙更挺身而出,致書陳巡撫,提出停刊《湘報》,又串通湘紳,鼓動岳麓、城南、求忠三書院部分學生,齊集省城學宮,商定所謂《湘省學約》,用以約束士人言行,對抗新思想傳播。及至戊戌變法失敗后,其門人蘇輿編輯《翼教叢編》一書,集中攻擊和污蔑變法維新,并頌揚王先謙能事先“洞燭其奸,摘發備至”,便使一場始于教育改革的維新運動,最終讓位于政治斗爭。政治斗爭的結果是,平等、民權淪為惑世亂心的異學,王山長成了衛道救世的英雄,而實質上是由衛道而成了保守派的領袖。
光緒二十九年(1903),學堂漸興,王先謙仍主講岳麓書院,兼任湖南師范館館長。此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蓬勃興起,王先謙以“人心不靖”,“邪說朋興,排滿革命之談充塞庠序”而不復至館。同年,岳麓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
光緒三十四年,王先謙所著書《尚書孔傳參正》等,經巡撫岑春蓂呈送清廷,受到嘉獎,賞內閣學士銜。宣統二年(1910)湖南災荒,因葉德輝囤谷萬石,不肯平價出售,激起長沙搶米風潮,釀成慘案。王先謙以“梗議義糶”,被湖廣總督瑞澂奏劾,奉旨“降五級調用”。武昌起義后,他改名遯,避居平江,閉門著書,并羅致文人從事古籍和歷史文獻的整理刊印。三年后還長沙,至1917年病逝。
王先謙一生博覽古今圖譜,研究各朝典章制度,治學重考據、校勘,尤喜著述。李肖聃《湘學略·葵園學略》說他“上箋群經,下征國史,旁論文章,用逮諸子”,并譽之為“長沙閣學,季清巨儒,著書滿門,門庭廣大”,“尤有功于楚學”。其所著述,除前述校刻《皇清經解續編》、《續古文辭類纂》、《十朝東華錄》之外,還有《尚書孔傳參正》、《詩三家義集疏》、《釋名疏證補》、《漢書補注》、《后漢書集解》、《荀子集解》、《合校水經注》及《虛受堂詩文集》等,共計五十余種,三千二百多卷。因而被稱為“清末全面研治經史子集的一代宗師”,與王夫之、王文清、王闿運合稱為“湖南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