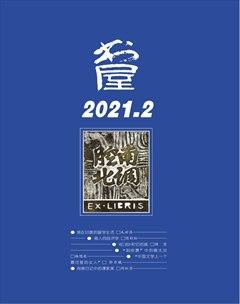日暮鄉關何處是
徐志頻
一
道光十七年(1837),魏光燾出生在邵陽隆回金潭鄉。這年,二十五歲的左宗棠在株洲淥江書院擔任山長。兩人都不會想到,二十年后,時勢、機緣將彼此促到一起。
在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這些湘軍元老面前,魏光燾屬后生晚輩。因曾、左擔當軍事時均已過不惑之年,青年魏光燾有幸趕上第一代湘軍的發展壯大期,肩任大梁。
湘軍最早的源頭,出現在寶慶府。道光二十四年(1844),湖南邵陽新寧籍舉人江忠源在家鄉辦成楚軍,以靖地方動亂。他其時沒有想到,日后縱橫中國十八個行省,長達半個多世紀以拯難救危自任的湘軍,已經從這里開始了。第二位籌備團練以靖地方的人物是胡林翼。道光二十九年(1849),胡林翼在貴州黎平知府任上組建民兵以鎮壓地方匪患,賦閑鄉居的左宗棠為他撰寫練兵、打仗技術資料,兩人知行配合,相得益彰,拉練出了日后走出貴州來支援湖南、湖北軍事的貴勇。待曾國藩將羅澤南在老家組織的湘鄉勇劃歸旗下,以湘勇之名配合湖南巡撫駱秉章以肅清湖南地方匪患,時間已到咸豐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
江忠源率先在寶慶府舉起楚軍大旗,在他的表率作用之下,新寧勇中相繼走出兩名大將,劉長佑、劉坤一叔侄。因楚軍最早,戰斗力也最強,江忠源發跡最速。到咸豐四年(1854),他憑軍功已升任湖北巡撫。其時,欽差大臣曾國藩以兵部侍郎虛銜、湖南幫辦團練大臣實職,率湘勇在籌備寧鄉靖港作戰。曾國藩被授予湖北巡撫實職,已在江忠源戰死之后。但一星期后,朝廷又緊急收回成命。
江忠源死后,寶慶勇從湘軍主力逐漸淪落為偏師。主力湘軍其時分作三股:以駱秉章、左宗棠代表的湖南綠營加地方團練兵;由曾國藩為統帥的湘勇;以胡林翼為主帥的貴勇。
左宗棠其時在湖南巡撫衙門,名義上是幕僚、事實上為軍政一把手。這位以“今亮”自命的大能人,長于計算且善于結人,他依靠湖南巡撫旗下的湖南綠營加地方團練起步,經過八年的精心布局謀篇,到咸豐十年(1860)年終于破繭脫殼,獨立組建楚軍,歸于曾國藩名下。左宗棠的楚軍能夠最終成型且發展久遠,得益于他幕僚時期結識的兩位十分重要的朋友:新寧江忠源,湘鄉王珍。左氏楚軍的旗號,源于朋友江忠源。在湖南巡撫衙門期間,江、左過從甚密。左宗棠欽慕江忠源其才、其品,對其軍隊尤其擊節。待自己獨立建軍,左氏其軍事思想、戰術規劃,也悉數從江忠源的實戰手冊中照搬或借鑒。上述史實,左宗棠在跟郭嵩燾合寫的《江忠源行狀》中均客觀記錄下來。
左氏楚軍班底的首批將士,則有近半來自于王珍創建的老湘營。王珍是羅澤南學生,其人聲強氣壯,平昔顧盼自雄,因跟曾國藩性格、觀念嚴重沖突,彼此水火不容。但王珍卻獨對左宗棠言聽計從、死心塌地。左宗棠搭建楚軍班底時,王珍去世已三年多。左氏不但將王珍老湘營二千余兵全歸于旗下,親自節制指揮,還將他的兩位兄長王開琳、王開化一并邀請加盟,總辦營務。左宗棠如此看重王珍,因為老湘營論作戰能力,在湘軍五大勢力中居首。事實為例,咸豐六年,王珍親率一千余老湘營征戰江西,一年半內,消滅太平軍四萬余人。因戰果空前,時人嘆為奇跡。太平軍從此皆畏稱之“王老虎”,望老湘營旗號便作鳥獸星散。
因為有江忠源、王珍二人,左宗棠八年幕僚,一天也沒有耽誤。他跟江、王早年的這些交往人情,跟魏光燾日后加盟楚軍備加重用,冥冥之中確定下了某些關聯。
二
魏光燾參加湘軍的初心,為了改變生存困境。
他出生所在地邵陽隆回縣金潭鄉,地理上屬于“衡邵干旱走廊”。因為五嶺阻隔云氣,隆回少有降雨,這里十年九旱,勤勞也不能致富,跟徽州環境相似。魏光燾有兄弟六人。因賴以生存的土地貧瘠,加之少年喪父,家境更加貧寒,早年他要靠上山砍柴、下河淘金才能自養。也因此,正史中找不到他私塾求學的記載。
咸豐六年(1856),曾國藩在江西前線的一個偶然想法,改寫了魏光燾的人生軌跡。為打下江西吉安,曾國藩去信九弟曾國荃籌建吉字營。恰好,魏光燾有一堂兄魏瀛,在江西吉安府天華山曾國荃幕府內參贊軍務。十九歲的魏光燾奉母命棄工從戎,徒步跋涉一千余里,風塵仆仆趕赴曾國荃軍營。
背井離鄉參軍之前,魏光燾曾做過一段時間的廚工,每天買菜、洗菜,端菜、分菜,后來還掌過一段時間的勺。廚工不學菜譜改學兵法,頗有點效漢初陳平故事味道。這本是一個特殊工種,三代時期的宰相,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分菜。能夠分均,皆大歡喜,便能德服群倫。
曾國荃吉字營其時新立,急需募才。見魏光燾徒步千里投效,既佩服他的勇毅跟膽識,亦不乏感動之情。因魏光燾有過廚工簡歷,加之人品質樸,老九當即委派他管理錢糧、軍裝事務。三年后,曾國荃攻破江西吉安府城,魏光燾因后勤保障之功,一并得到保舉,以從九品選用。
也就在此時,魏光燾告別了湘勇吉字營,改投奔劉長佑所在的廣西蔣益澧部。
改換門庭的原因,不見于史。推想之下,曾國藩所部湘勇,原本全由湘鄉一地的宗親故舊組成,來自寶慶府的魏光燾既無血緣、宗族紐帶,又存在地緣差異,在宗族化管理的軍事團隊里,身心難以完全融入。劉長佑畢竟跟他是寶慶府同鄉。晚清湖南人內部畛域陳見仍深,一般細化到以縣域為界。此外,以文化學歷、天賦性格來分群別類者也經常可見。如湘鄉人蔣益澧跟同鄉楊昌浚、寧鄉人劉典,因學歷過低,性格過于偏激,同屬于曾國藩舍棄的人才。
曾國藩用人首重學歷,次重地域,再重拙誠,最后還要看忠誠度。左宗棠則反其道而行,不但起用大批學歷偏低者為將,而且打破府、縣地域人才界限,搞“五湖四海”;左氏選拔將士也勿須拙誠,而格外看重樸強;對部將管束不以理學忠誠為旨,而以法家部勒,不重對統帥個人的效忠跟服從。
魏光燾投奔的蔣益澧,其人如漢初韓信,才干超拔,卻游俠風格,任俠使氣。曾國藩顧忌而不敢用,蔣益澧只好作為湘軍機動部隊,在各大勢力中間充當填漏補缺的游擊隊,數年內帶兵游蕩,隨意依附。左宗棠建楚軍后,蔣益澧被一眼看中。咸豐十一年(1861),左宗棠趁楚軍在江西節節勝利的情勢之下,以出兵攻打浙江軍士不足為由,向朝廷申請將蔣益澧部八千游蕩在廣西的偏師歸于楚軍,獲得批準。其時,魏光燾正在蔣益澧部湘勇營中管理營中軍裝支應。三年來,職務、地位并無多少長進。這是一段吳下阿蒙抓緊補學文化的階段。魏光燾聰明好學,文墨日見長進,文牘溝通漸次順暢無礙。因其人質樸,好學善謀,嫻于調配,蔣益澧遇有軍事方面的困惑,開始征詢魏光燾意見。其后,蔣益澧正式委任魏光燾辦理全軍營務,兼管督兵和太平軍作戰。
這些為魏光燾其后得到左宗棠的器重,打實了基礎。
三
同治六年(1867),是左宗棠從征戰東南到轉戰大西北的轉折之年,也是魏光燾個人職務、地位開始升遷加速的拐點之年。
左宗棠重用魏光燾的標志,是將他從蔣益澧所部調離,轉入楚軍王牌部隊老湘營。
果然,隨蔣益澧部加盟楚軍后,魏光燾不負眾望。以同治四年(1865)十月二十八日一戰為例,其時,左宗棠奉命入閩督戰,魏光燾由寧波乘輪船赴福州,與將領高連陞配合攻打太平軍。因太平軍兵力眾多,魏光燾被層層圍困。情急之下,他“沖馬突圍而出,敵軍跟追至山埠,相隔丈許,前山阻,巖高數十丈,馬忽騰空躍下,敵驚愕不敢窮億,合隊而返”。
之后,魏光燾約會楚、皖軍合力圍攻,切斷太平軍餉道,一舉殲滅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收復了長泰縣城和漳州府城。左宗棠聞訊,倍感欣慰,當即向朝廷保奏,魏光燾以道員留閩浙,遇缺即補。
其后,魏光燾跟隨左宗棠,軍事才干與后勤才能盡情展現出來。這從左宗棠三次成功保舉的時間間隔可以看出來:
同治十年(1871)三月,三十四歲的魏光燾出任甘肅平慶涇固道;光緒六年(1880)九月,四十三歲魏光燾接署甘肅按察使一職;一年后,補授甘肅布政使之職。
光緒十年(1884),新疆改設行省。經左宗棠鼎力保舉,老湘營統領劉錦棠出任首任巡撫,魏光燾擔任首任新疆布政使。四十七歲的魏光燾,成為有清以來首位非科舉選拔而做上從二品高官者。
因為文化基礎先天欠缺,在清朝崇文抑武的時代觀念里,魏光燾對文才之士頗為敬重。光緒元年(1875)六月十九日,左宗棠出兵新疆不到兩月,魏光燾便作為魏源家族的代表,邀請左宗棠為再版《海國圖志》作序。在序文中,左宗棠自道邀約經過與出版緣由:“邵陽魏子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成于道光二十二年,續增四十卷成于咸豐二年,通為一百卷。越二十有三年,光緒紀元,其族孫甘肅平慶涇固道光燾懼孤本久而失傳,督匠重寫開雕,乞余敘之。”
左宗棠是一位看重辦事能力的實干家,魏光燾出身底層,知民間疾苦,辦理實事分毫不讓于人。在新疆布政使任內,魏光燾修城建衙,設郡縣,建官制,舉軍政,定餉章;整頓郵政,興辦學校;開礦、屯田、畜牧、堪國界,開辟羅布淖爾千余里地方,成績卓然。是年十二月十日,朝廷因他治疆之功,賞加頭品頂戴。
光緒十四年(1888)十二月,劉錦棠回湘鄉丁憂,魏光燾奉旨護理新疆巡撫。這是他晉升封疆大吏的開端。
四
左宗棠身后,魏光燾作為楚軍元老,先后擔任過陜甘總督、云貴總督、兩江總督等職。光緒十八年(1892),他回到邵陽原籍丁母憂。兩年后,朝廷突然下旨,令他接手一件軍事。
光緒二十年秋,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年過六十歲的湘軍統帥、時任兩江總督劉坤一被朝廷下旨授為欽差大臣,節制山海關內外防堵各軍,督師作戰。作為左宗棠舊部的魏光燾、曾國荃舊部的陳湜、湘勇悍將李續賓之子李光久均奉命援助遼東。朝廷特旨召魏光燾出關助戰。
中、日海戰結束,日軍搶先登陸,陸戰迅速展開。
其時,魏光燾與湘軍各部陸續抵遼河下游的田莊臺,籌劃第三次反攻海城之戰,而牛莊是清軍后方要地。
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初七日,日軍集中二萬精銳,分兩路進擊牛莊。
魏光燾親率武威軍在街口搶筑一尺厚的土墻等掩體,安排左、右、中三營防守西北面;前、后兩營防守東北面;自率大營炮隊、馬隊及衛隊防守中路。此時,日軍步騎炮工兵兵力達一萬二千人,火炮五十九門。魏光燾加上后來增援的李光久部,才共計十二營五千余人,火炮不足十門。
魏光燾率大營炮隊、衛隊御北路日軍。戰斗打響,初戰斃傷日軍百余人。很快,戰斗進入白熱化狀態。左營總兵余福章陣亡,右營提督沈寶堂兩臂被打折,幫帶參將陳勝友戰死。魏光燾親率衛隊同日寇血戰,大營總兵肖有元中炮傷重,衛隊傷亡過半。下午,李光久率部趕來支援,局勢稍緩。到晚十時,魏光燾、李光久子彈俱盡,魏光燾往來督戰,三易坐騎。直至深夜,始由西面突圍,向田臺莊突圍而出。
據目擊者稱,日軍占領牛莊后,“執劍挨戶搜查,殺人無算”,“路旁伏尸相枕”,許多民房門前,“尸積成山,尸山之間流出幾條渾濁的血河”,“走進門里院內也堆滿了尸體”。
湘軍牛莊戰敗傳到國內,譚嗣同刺激最深。他甚至發出“甲午的戰敗,實是我們湖南人害國家的”這種偏激憤慨之言。譚嗣同預感到日軍將對中國人實行大屠殺,為了保全中國人的“黃種之苗”,譚嗣同發起成立“南學會”。
牛莊戰役壯烈慘敗,也是出于朝廷的預設。因為中、日海戰失敗后,還沒等陸戰結果,慈禧太后已經下旨派李鴻章前往日本和談。
回望左宗棠于光緒六年(1880)統帥楚軍駐軍哈密,在鳳凰臺部署二萬部隊控制伊犁,令俄羅斯不戰而屈;在光緒十年(1884)督辦臺灣軍務時,左氏不但將占領臺灣的二千多法軍全部打敗趕跑,而且部將馮子材率恪靖定邊軍在中越邊境取得涼山、鎮南關大捷。楚軍之前在外戰中還沒有過失敗的紀錄,孰料在左宗棠去世后九年破例了。
客觀地看,劉坤一統帥軍隊戰略固然不及左宗棠,魏光燾指揮軍事戰術也不及劉錦棠,但這些都不是湘軍慘敗的主因。在慈禧昏聵當國、李鴻章退讓迎合已經導致海戰一敗涂地的大前提下,中、日牛莊陸戰不過應景,換誰也無力改變大局。
戰事結束后,清廷表彰魏光燾“孤軍苦戰,不計勝敗”,命他接統關外軍務。
至此總結湘軍歷史,從道光二十四年(1844)江忠源辦楚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胡林翼肇湘軍之始,到曾國藩于咸豐二年(1852)集湘軍勢力之大成,歷十二年歲月而平定太平天國,為第一波高峰;到左宗棠統帥湘軍各部精銳組成西征軍成功收復新疆,首次將湘軍事業推上了史無前例的巔峰高度;及光緒二十年(1894)湘軍元老劉坤一統帥湘軍余部對日陸戰,楚軍舊將魏光燾遭遇牛莊慘敗,五十年時間,湘軍經歷從朝霞噴薄墮入落陽殘輝。
五十年湘軍史,由邵陽人負責開篇序言,亦題下落筆尾聲。從這里走出過三位總督(劉長佑、劉坤一、魏光燾),一位巡撫(江忠源),可以看出,邵陽人貫穿了湘軍全程,起著砥柱中流的作用。
放進湖南甚至全國去看,邵陽人可能稱得上是最具血性、最為忠誠的一地之人。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犯北京,魏光燾因率兵勤王之功,晉升陜甘總督,隨即又調任云貴總督,三年后又移督兩江,權勢一時間達到頂峰。
光緒三十年(1904)九月,魏光燾調補閩浙總督。次年春,自愿卸印回籍,在邵陽城內考棚街筑“亦吾廬”,同時,他在東郊佘湖山下修筑“湖山別墅”,自號“湖山老人”,作為休憩養老之地。
宣統二年(1910)四月,清廷打算向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舉借外債,條件是出賣粵漢、川漢兩條干線路權。消息傳到國內,民眾掀起“拒債商辦”的保路運動。八月初五日,湖南省推代表曾繼暉等持咨議局正、副議長各界人士三十余人函件來到邵陽,請魏光燾“前往代表輿情,以救危險”。魏光燾應邀趕赴長沙,專折上奏:“現在湘路公司興工集款既有成交可稽,是仰遵先朝遺訓,不借外債,實為名正言順”,而借債賣路,“甚非所以保元氣而固民心”。外債輸入,將“使湘省億兆人生命財產均無保存”,“民雖至愚,何能甘心?方今預備立憲,首務聽從民便,君不從其便而又拂之,其未可也”。
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發。朝廷緊急任命魏光燾為湖廣總督前去鎮壓,魏光燾堅辭不任。五年后的1916年3月,魏光燾病逝于湖山別墅,享年七十九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