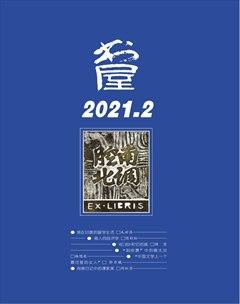中國現代文學的國際版圖
戰玉冰
最早聽說王德威教授關于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后文簡稱“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構想是在2011年底,當時王德威教授來復旦大學做了一連四場的系列講座,其中第一講題為《“重寫”重寫文學史》。講座中王德威教授選取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十個富有象征意味的具體時刻作為他文學史闡發的立足點,以散點透視的方式來展開他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理解和論述。當時只覺得王德威教授氣質儒雅、舌燦蓮花、角度新穎,整個講座既內容豐富又妙趣橫生。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那場講座應該正是如今這本“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萌芽和“雛形”。
縱觀整本“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它將我們傳統意義上所認知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內涵和外延從時間、空間和“文”的概念等方面都進行了大幅度的擴展,比如其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上溯到1635年傳教士來華,又如書中將“文學”的定義泛化,與中國傳統“文”的概念中所包含的“文章、文化、文明”等含義相勾連,將文學的范疇遠遠突破到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四門之外等。而在我看來,全書最富啟發性的一點在于它對傳統文學史寫作中的“中國”概念進行了別開生面的拓寬和延伸。
在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中國”概念的討論上,王德威教授提出了“華語語系文學”的說法,其中既包含了中國大陸以及臺灣地區的文學書寫,也涵蓋了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華人社群,以及旅美、旅歐、旅日等華人寫作者及其作品。在王德威教授的“華語語系文學”中,一方面“漢語”被作為劃定作家作品范疇的最大公分母,另一方面整個概念本身又是開放性的,即它同時也以補充說明的形式包含了中國文學中的非漢語寫作和漢語書寫中的方言口語等現象。
關于“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最早由史書美提出,但王德威教授在借用了這一名詞后已經反復強調自己的“華語語系文學”與史書美的理論并非同一件事。的確,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文學”頗有一種重點圍繞港、澳、臺來談中國文學的傾向;相比而言,王德威教授的“華語語系文學”概念則更有包容性,并且似乎暗含著某種對文化意義上的“大中華”(greater China)的向往和追求。
在中國,雖然現如今將香港地區、臺灣地區以及新、馬等海外的華人作家作品納入中國現代文學考察的范疇之中這一做法似乎并不會引起太多反對(中國主要的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期刊上都曾發表過關于這些地區和國家的作家作品、文學事件、流派、思潮、甚至文學史的論文便是明證),但在具體的文學史寫作與實操層面上,我們可以說,現存絕大多數中國學者所書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還都不能很好地統合不同政治、地理與語言背景下的中國現代文學。
應該沒有人會否認白先勇、朱天文、張大春、劉以鬯、也斯、西西、金庸等港、臺地區作家是中國作家,他們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成就頗高或文學影響頗大的重要作家。但另一方面,在中國一般的文學史著作中,港、臺地區文學依舊處于一種普遍缺位的狀態,即使出現,也只是在講完中國的“主流”文學后再附上一兩個章節,形成“聊勝于無”的存在。一直困擾這些文學史著作的地方在于它們似乎很難對港、臺地區文學做出合理定位。至于黃錦樹、黎紫書、潘雨桐、李永平、商晚筠、張貴興、黃孟文等作家如何被給予充分的研究和肯定并以合理的方式進入主流文學史敘述過程,更是每一位文學史寫作者所必須認真面對和思考的重要問題。
王德威教授提出以語言來約定文學的方法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切入和統攝角度,畢竟文學直接是以語言文字為基礎的。“華語語系文學”的“華”不僅僅是指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而是文化與文明意義層面的“中華”。這樣一來,馬來西亞華人作者、新加坡華人作者,旅日、旅美、旅歐的華語寫作者皆可被納入這一理論范疇之內,王德威教授在全書序言中稱其為“世界中的中國文學”(Worlding Literary China)。
將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華語文學創作一并作為“華語語系文學”的考察范圍不僅僅是擴大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版圖和研究疆域,更為我們觀察和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豐富性和生命力提供了多種可能。有著不同在地經驗、行旅經歷和思想經傳的華語寫作者,將他們各自的生活和思考通過文學書寫匯聚到“華語語系文學”這個大的精神母體之中,從而極大程度地豐富了華語文學書寫的多樣性。這里不僅有蕭紅的呼蘭河、沈從文的湘西、張愛玲的上海、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與陳忠實的白鹿原,也有西西的肥土鎮、簡媜的胭脂盆地、黃錦樹的季風雨和水獺、木心筆下來自林肯中心的鼓聲,甚至于金庸的桃花島與絕情谷,張系國的呼回世界與索倫城……當華語成為這些不同經驗與思考的書寫載體之后,華語書寫本身的面向與寬度也得到極大的拓展和延伸。
與此同時,王德威教授的“華語語系文學”又并非一個封閉性的概念,而是一種維特根斯坦式的開放型的定義,它在肯定了以漢語為書寫語言的大多數中國文學作品的同時,也容納了“非漢語的表述”和用方言口語寫作的作品。這樣,1949年以前一批以日文寫作的臺灣作者——吳濁流、龍瑛宗、呂赫若等,還有從林語堂到湯婷婷、譚恩美、任璧蓮,再到哈金、裘小龍等一批生活在美國、以英語作為其文學創作語言的華人作家及其作品等皆可被納入我們的考察視閾之中。而如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金宇澄的《繁花》、黃碧云的《烈佬傳》等作品,它們對于非方言區的讀者雖然有一定的閱讀難度,但毫無疑問,它們也應當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所必須關注和研究的范疇并閃爍出其無可取代的獨特光芒。
此外,王德威教授“華語語系文學”定義有助于打開的“非漢語的表述”的窗口。在現存大多數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如果細數以漢語為主要書寫語言的中國少數民族作家,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老舍(滿族)、端木蕻良(滿族)、沙葉新(回族)、張承志(回族)、陳村(回族)、霍達(回族)、阿來(藏族)、白先勇(回族)、席慕蓉(蒙古族)……但以少數民族語言作為主要創作語言的作家作品卻成為一個文學史敘述中普遍存在的“盲區”。一般文學史著作中一提到少數民族文學,基本上是圍繞漢譯的藏族《格薩爾王傳》、蒙古族《江格爾》、彝族《阿詩瑪》等一類史詩性質的作品,而對于當代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卻談得少之又少,甚至只字不提。端智嘉、平措扎西、買買提明·吾守爾、阿不都熱依木·吾提庫爾、孟和等作家是否要進入以及他們應該如何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絕不僅僅是一個裨補缺漏的問題,而是涉及研究者更深層次的文學史觀的大問題。再以我所在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本科專業建制為例,“中國語言文學系”下轄“漢語言文學專業”和“漢語言專業”。單獨來說文學部分,“中國語言文學”與“漢語言文學”兩個概念之間顯然不能劃等號,二者的差別很大程度上在于以少數民族語言為創作語言的作家作品是否應該被“看見”,及其最終將何去何從,而這種差別在實際研究與教學過程中卻經常被忽視。 “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也涉及了這一方面的內容,比如當代漢、藏雙語詩創作等。當然,“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真正的意義不在于其如何深切地探討了這一問題,而在于兩相對照之下,我們發現了以往文學史書寫中所存在的漏洞,以及由此帶來的新的關注與延伸性思考。
戴燕教授在《文學史的權力》一書中認為:“作為近代文學、科學和思想的產物,‘文學史的重要基礎,是十九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觀念,如果按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民族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那么,文學史便為這種想象提供了豐富的證據和精彩的內容……文學史是借著科學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對民族精神的一種塑造,目的在于啟發愛國情感和民族主義。”文學史寫作在戴燕教授這里被認為是構建民族文化自我的一種努力,與民族主義的思想動力密切相關,而這也是傳統文學史寫作的重要內在驅動力之一。如果說,戴燕教授所認為的文學史是構成民族國家“想象的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王德威教授的這本“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則是他海內外“大中華”,甚至“中華大同”理念的文化依托。在王德威教授的理論體系里,不同政治、不同地理、不同民族身份、不同生活經驗、不同創作語言的作家作品都可以被安置于“華語語系文學”之中來被討論,他借此構造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國際性版圖,或者回到王德威教授自己所發明的概念中,這便是他所說的“世界中的中國文學”。
在關于“華語語系文學”的具體討論中,王德威教授又格外注重其間的“行旅”與“跨地”經歷或經驗。從明代西方傳教士來華,到乾隆時期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從晚清“福爾摩斯來中國”,到秋瑾東渡日本接受民主政治思潮的熏陶;從一批先后在哈佛大學接受過教育的中國作家或學者(如陳寅恪、林語堂、吳宓、湯用彤、俞大維、洪深等),到京劇大師梅蘭芳赴蘇聯演出;從“上山下鄉”運動,到日本漫畫《黑塔利亞》借助互聯網傳到中國并被中國漫迷戲擬創作出其同人漫畫《為龍》……“行旅”帶來的是文化的交匯和互動,進而帶來文學自身的發展和轉型。而正是這種以各種形式不斷出現的作家與作品的“行旅”,才使得“華語語系文學”內部始終處于一種相互交錯影響的狀態與生機勃勃的生長態勢。
至此,我們可以大致描繪出王德威教授“華語語系文學”的基本面貌:以漢語為最大公約基礎,同時補充進中國作家的非漢語寫作(包括外語寫作和少數民族語言寫作)與方言口語等現象,進而將不同地區、民族、國籍、甚至語言的文學統合在同一視閾之下。而在這一宏大的文學版圖之中,又重點考察其間作家作品在不同時空中的穿梭流動和“行旅”變化,最終呈現出一個內在復雜交匯且極具生命力的“大中華”文學世界。而這個“大中華”文學世界與王德威教授對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溯源、對“文”的概念的延展、在“史”的寫法與編排上借鑒錢鍾書《管錐編》一書,再進一步將其上溯至中國歷史上“三言兩語”的詩評、文話、書信、序跋的傳統一起構成了他這部“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最終宏大的構想和藍圖。
“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書寫與編排手法上所積極踐行的“華語語系文學”理念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具開創性意義的新的觀察視野,但真正的文學史著作又不能僅僅滿足于將所有作家作品都以等量齊觀的章節形式按照編年順序進行簡單并置,這絕對不是最終的處理方案。我們的進一步問題在于,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夠容納這些來自四面八方、世界各地的“華語語系文學”視角之后,我們應該如何統籌和處理這些作家和作品,重估、比較其文學價值,并對其展開一種有效的歷史化敘述。
總而言之,王德威教授的這本“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是一部非常具有啟發性意義的著作,它必定給后來的文學史寫作者們打開更多的討論空間和研究視角。中國現代文學還在不斷地變化發展過程之中,那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也必將不斷繼續發展下去。就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陳思和、王曉明教授主持的“重寫文學史”運動被寫入了這部“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之中,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部“‘重寫重寫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也一定是后繼者書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時所不能繞過的重要文本和事件,而其“中譯本”的即將出版問世,也是一件頗值得學界和讀者期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