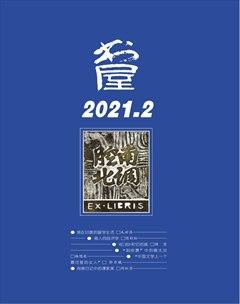九面之城的構思
王旭彬
對于紐約而言,美國人各有所悟。“顛覆,顛覆,顛覆!這就是紐約的箴言。”1845年,當時紐約市長菲利普·霍恩如此形容。美國第一位城市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曾如此盛贊紐約:“令人愉悅的潮汐周而復始,帶著漩渦與浪花盤旋往復!”永不停歇的港口、擁擠繁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紐約是一個“驕傲又充滿激情的城市——勇敢、瘋狂又奢華放縱”。在惠特曼眼里,紐約的故事每一天都在開始,故事的結束永不會發生。
這一切正如喬安妮·雷塔諾(Joanne Reitano)在《九面之城:紐約的沖突與野心》(以下簡稱《九面之城》)中所描述的那樣。她將紐約城的九面分別概括為“漩渦之城”、“吊詭之都”、“驕傲之都”、“帝國之城”、“野心之城”、“逐夢之城”、“世界之城”、“威脅之城”以及“躁動之城”。紐約像是擁有多重人格,每一個時期都有一個人格起著主導作用,從而形成特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局面。在這些突發性事件中,紐約的其他人格被釋放出來,這些事件往往成為一個轉折點,細微而又堅定地改變著紐約行駛的軌跡。我們一直會記得上一站是什么,卻永遠不知道下一站將會停在哪里。
被數屆總統譽為“美國精神之父”的小霍爾肖·阿爾杰(Horatio Alger,JR.1832—1899)在《衣衫襤褸的迪克》(又名《紐約的街頭生活》)中對美國前工業化時期成功模式進行了簡單的理想化描寫,而這本書卻在無情而復雜的十九世紀后期工業化年代廣受歡迎。喬安妮·雷塔諾認為:阿爾杰的意義正在于他展現出來的這種反差。他在小說中寫道:“憑著誠實正直、不屈不撓的樂觀精神和艱苦奮斗的工作,善良的孩子會得到應有報償——盡管這種報償往往憑好運而突然到來。”“爛衫迪克”第一次出現在讀者們的視野中時,是一名奢侈浪費、抽煙賭博、花錢大手大腳的紐約街頭擦鞋童,但他“從不做任何卑鄙或不光彩的事,不偷竊,不欺騙或欺負比他小的男孩,而是為人坦率,光明磊落,有獨立性,有男子漢氣概”。這樣一個善惡交織、有可塑性和發展性的人物形象,給了千千萬萬紐約移民一個心理投射。
喬安妮·雷塔諾在《九面之城》中對此做出了如下分析:“阿爾杰用他的小說減輕了歷史學家塞繆爾·海斯(Samuel P.Hays)所稱的‘變革的震動帶來的沖擊。”我們閱讀小說時往往告訴自己要把現實社會和小說世界截然分開,然而身處現實中時,很多預判都是依據曾經看過的虛構類文本內容展開。在這個邏輯下,虛構類文本的情節設計取自現實,因此形成一個閉環。而《衣衫襤褸的迪克》更多的是暢想,是構思,是從“美國精神”出發的未來描摹與情緒安撫。“它安慰了讀者,告訴他們:在一個日益冷漠無情、道德淪喪的世界,個人努力依然重要,古老美好的價值觀也依然并非無關緊要”。通過對阿爾杰一系列小說的分析,喬安妮·雷塔諾發現:阿爾杰“情節動人但文學價值欠佳”的小說強化了樂觀主義精神以及自由資本主義優越性的信念。他通過小說把紐約的部分形象典型化為一個人物——出身卑微的都市英雄。正如迪克所說的那樣:“我并不是徒勞無功地游蕩在街頭巷尾。”
讀《九面之城》這幾個月的光景,正是紐約疫情泛濫到“無政府”狀態式的急速下墜,掩卷之時,眼看這座人類文明史上的典范之城在“美式失敗”(《時代雜志》語)中狂奔向陸沉末日,令人惋惜。但與此同時,看到紐約市民自治自救的場景,又不免令人欣慰。美國從獨立戰爭時期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再到1964年的哈萊姆騷亂,一系列沖突與亂局不斷出現,它們深植于紐約歷史中的所謂的“失序的傳染”。
但,紐約總能在至暗時刻遇見轉機,在瀕臨崩潰的前夕力挽狂瀾,雖然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這體現的是紐約城的戰斗精神、看似散漫實則一直存在的集體榮譽感以及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2020年7月6日起,紐約市經過漫長的黑暗混亂與自我調整,終于開始了第三階段的“重啟”。在這危機時刻,街頭藝術家卻借此機會在木板上自由創作,形成疫中一景。然而在最為困難的那段時間,街上充滿了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口罩”——一塊隨手拿來的布、人們自制的形狀滑稽顏色鮮艷的口罩、玩具面罩等。這種無所謂的自嘲式娛樂,于人人自危的疫情期間在紐約街頭上演一出黑色幽默。
“大多數人都知道紐約,知道這里的財富、活力與夢想,但大部分人并不了解紐約,不了解這里的變革、混亂與堅韌。”《九面之城》中不惜筆墨地描述了紐約所經歷的一次次混亂與沖突——荷蘭人與英國人的控制權之爭,老移民與新移民的話語權之爭,殖民者與印第安人的資源之爭等。紐約在這些矛盾中被錘煉,變得更強大、更復雜,也更多元、更包容、更加野心勃勃。
電影《海上鋼琴師》里,來自歐洲等地的移民乘“弗尼吉亞”號偷渡來到美國。他們站在擁擠的甲板上眺望著美國的方向,一束束熾熱的目光匯聚成“弗尼吉亞”號永不熄滅的探照燈。當自由女神像沖破紐約港上空的云靄從弧形海面上緩緩升起,甲板上的人們發出此起彼伏的驚喜吶喊:“America!”而第一位看到自由女神像的旅客早已說不出話。這部電影的原名是The Legend of 1900。回溯這個時代,那是美國經濟大蕭條前最為繁榮的一段熠熠閃光的歷史——美國GDP首次超過英國,對移民采取寬容態度。1910年,“美國現代藝術之父”阿爾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用“野心之城”來形容他所拍攝的煙云翻滾的紐約港。喬安妮·雷塔諾在《九面之城》中采用了這一說法并表示贊同:“‘野心之城的比喻生動捕捉到了紐約對于進步發展的激進、樂觀態度。野心彌漫在整個城市,挑戰著傳統,也激發著沖突。”一顆新星從陌生的美洲大陸升起,全世界的人都在注視著她。因此,“理想”、“未來”被具象化并冠以“美國夢”的名號,而夢想的起點就是抵達那個光明而自由的地方。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在1925年說了這樣一段話:“全世界沒有什么能比第一次駛入紐約更令人激動了。紐約不愧為逐夢之城,接近上帝的通天塔之城,希望與愿景之城。”
在喬安妮·雷塔諾心中,紐約是一座九面之城,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存在。因此,她專注于紐約市與紐約州地方歷史的研究,并撰寫了多本關于紐約歷史的作品。然而,紐約不是一座孤獨的城市,除她之外還有很多相似的存在。
流光溢彩的城市是一場橫貫中西的迷夢。紐約如是,巴黎、北京、香港……哪個又不是多面之城?郝景芳筆下的《北京折疊》,若昂·得讓畢生致力關注的“現代城市”巴黎,王家衛鏡頭下魔幻但又寫實的香港……城市是人潮洶涌的地方,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復雜的動物。城市因人而變得復雜,因族群而文化多元,這是城市的魅力,是每一個體用一生都無法探尋完全的所謂千姿百態。然而,城市又是如此地適合被擬人化——不同時節的景色織成色彩繽紛的衣物,基礎設施運轉良好與否,經濟盈虧、活力與彈性,不同時代主流文化大合唱與各路文化交響,政治舞臺上的喧囂與緘默等,都是城市多變的心境與情感表達。
無論紐約、巴黎還是北京,城市們總是呈現出一種欲拒還迎的狀態,城市中的人也總是處于一種“沖進去”和“逃出來”并存的狀態。人們懷著“城市夢”來到這里,經歷一個“夢碎”又“筑夢”的過程。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心中的思維模式已經無形中被置換,和根植于這個城市中的框架結構趨于相似。這一切正如《九面之城》當中所說的那樣:“紐約不會變得被動、墨守成規、枯燥或自滿,而是始終保持激進、創新、令人興奮、充滿爭議。紐約的躁動不安將是紐約最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