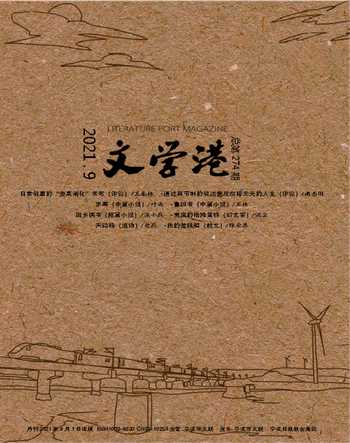通過有節制的敘述呈現灰暗無光的人生
南志剛

《文學港》編輯部雷默兄發來《歲寒》,囑咐我閱讀并談談閱讀感受。他說《歲寒》原文五萬多字,限于篇幅請作者壓縮成現在這樣,作者葉端是杭州人,復旦大學創意寫作碩士,現在社科院攻讀博士。閱讀《歲寒》,讓我對這個1992年出生的年輕作者“刮目相看”,深感“后生可畏”。《歲寒》表現出的敘述定力與耐心,超出了葉端的年齡,她對敘事欲望的節制,對敘述語調和敘述節奏的把控,像一個操弄寫作的“老手”,顯露出老練的一面,讓我對她的寫作充滿期待。
中短篇小說是控制的藝術。如果說,長篇小說還有放任敘述欲望的空間,那么,對于中短篇小說而言,能否控制敘述是小說成功的關鍵。在小說寫作過程中,作家想表達的東西很多,如何把諸多雜念通過敘述呈現出來,需要遵循敘事邏輯。作者既不能過于放縱敘事欲望,把小說寫作視為展示語言才華的試驗場,也不能過度壓抑敘事欲望,一旦敘事“低線運行”就會令讀者閱讀欲望下降。這就需要寫作者有所“節制”,既表達敘事欲望,也能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那種毫無節制的敘述,那種控制過度而失去趣味性的敘述,都會給小說本身和讀者閱讀帶來傷害。葉端的《歲寒》是一篇有“節制”的小說。
《歲寒》的敘述節制,首先表現在對主人公顧慎夕生活片段生活指向性選擇層面。作為夷陵護專的教師,作為一個年輕姑娘,顧慎夕的日常生活,包括戀愛、結婚、生子、與情人江寒幽會,絕不全是灰暗無光的無奈和湊合,應該也有光亮的一面,至少有些許光彩的瞬間。然而,《歲寒》完全屏蔽了顧慎夕日常生活中那些開心的、光亮的、浪漫的空間和時間,把她放置在灰暗無光的時空中,凸顯顧慎夕一系列湊合著、對付著、不開心的日常生活。這對一個年輕作者而言是不容易的,如果沒有經過相對嚴格的寫作訓練,沒有對自我表達欲望的有效節制,是很難做到的。
《歲寒》的敘事姿態和敘事語調是“節制”的。葉端始終保持著“低調”的敘述姿態,保持著羅蘭·巴爾特所說的紀德式的“謙遜” 寫作。敘述者既沒有用諸如人性、理想、存在等理性思考干預顧慎夕的生活,讓顧慎夕——這些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在內心展開對生活本質、人生存在的哲學反思,從而給人物貼上思想的標簽;也沒有用這些理性標簽衡量和評價顧慎夕的日常生活。《歲寒》完全在顧慎夕日常生活狀態的自我呈現、自我闡釋過程中,完成了對“故事”的“復制”,敘述者保持著一種“謙遜”的態度,完全撤出故事、撤出人物,讓顧慎夕的生存狀態以“生活流”的方式呈現出來。
《歲寒》敘述語調和敘述節奏是平穩而節制的。葉端采用了與主人公顧慎夕相對等的敘述語調,一直保持著顧慎夕對城市、工作、丈夫、孩子、親戚等的感覺,沒有溢出顧慎夕的職業身份和生活態度,甚至在歡愉感覺的敘述中,葉端也保持著冷靜、節制語調,沒有人為地給顧慎夕添加激情與浪漫,而是讓顧慎夕沿著“醫學”的線路呈現并不美好的感覺。《歲寒》的故事沒有起伏,沒有設置懸念,沒有在現代小說敘事時間里的扭曲變形,所有的敘述保持著一個基本節奏,平穩地向前推進。小說結尾將顧慎夕徹底框定在“照片”外,消解了主人公孩童游戲里對愛情婚姻浪漫而稚嫩的憧憬。《歲寒》設置的故事氛圍和敘述語調是壓抑的,這壓抑既來自主人公沒有光彩的日常生活,也來自主人公沒有光彩的內心生活。敘事沒有波瀾、沒有突轉、沒有懸念、沒有隱秘,既不像納巴科夫《洛麗塔》的纏繞敘述,也沒有余華《文城》那樣殘酷的單線突進式敘述,一切敘述都是在“確定”的敘述軌道上平穩推進。
通過葉端有“節制”的敘述,我們看到:顧慎夕對生活采取妥協的態度,沒有自主性、應付著過日子,她的日常生活沒有光彩,只是順應“生活本身”的平淡邏輯,也看不到解脫的路徑。《歲寒》一開始就預示著這注定是一個日常生活里的平淡故事,顧慎夕“整理好試管器材,把玻璃器皿里的小白鼠關進籠子里,脫下白大褂,鎖上實驗室門。”普通人的日子常常遭遇小變故,會經受一些麻煩事,“校車開走了”就是顧慎夕現在遭遇的小麻煩,而她對待這麻煩的對策,是習慣性承受、順應,選擇自己坐公交車,并且在站臺上遇到同事江寒。當顧慎夕與江寒一同乘坐公交車時,就開始了自己灰暗無光的人生。初次在慧貞婆婆家見到陸永山,顧慎夕是不滿意的,陸永山“比慧貞丈夫大許多,梳一個中分的漢奸頭,好像還抹了摩絲,油光光的”“起著紅疹的面部”,從“汗津津的手掌”抽回手,表明了顧慎夕的態度。顧慎夕盡管有心理準備,也沒有想到慧貞婆婆給自己介紹這么一個人,兩個人的對話也完全不在同一個頻道上:顧慎夕說“這天真熱”,陸永山回答是“快天黑了吧”。第一次見面,顧慎夕覺得兩個人“同病相憐的一點點出頭的艱難”,竟然成為她和陸永山戀愛的基礎。然而,顧慎夕順從了老書記和慧貞婆婆的意思,試探性地、湊合著和陸永山約會、看電影。他們的戀愛過程沒有絲毫浪漫和甜蜜,有的是瑣碎和對付。陸永山時不時到學校來,“蹭吃蹭水蹭電扇”,顧慎夕覺得很尷尬、甚至有些氣憤。而對于結婚,顧慎夕也沒有少女的憧憬,“總會結婚的”說出了顧慎夕對結婚的全部態度。顧慎夕對婚姻這種湊合的態度,似乎來自家庭“遺傳”,在小說中,顧慎夕的大哥、大姐的婚姻就是湊合著過來的,二姐不愿意湊合婚姻,堅持自己選擇男朋友,卻不被父母認可。《歲寒》中,大家都是湊合著過日子的婚姻,維持著婚姻的“外殼”,顧慎夕是這樣,大哥是這樣,大姐是這樣,江寒也是這樣,二姐不愿意“湊合”,婚姻就維持不下去。這種湊合的態度和對付日子的生活方式,成為小說中人物的普遍選擇,于是,顧慎夕湊合著結了婚,湊合著生了孩子,甚至湊合著找了情人,和江寒對付著情人關系。在生存壓力下,顧慎夕“湊合”著過日子成為一種“習慣”。小說結尾的時候,顧慎夕躲進了研究生的“象牙塔”中,她答應江寒讀完書就與永山離婚,然而,離婚以后怎么辦?如果仍然對付著過日子,顧慎夕的未來也許依然沒有光彩。
讀完《歲寒》,我們不禁要問:是什么把一個重點大學畢業生,一個原本青春洋溢的女大學生,變成了對付著過日子的“顧慎夕”?研究生生活只能是一個臨時的港灣,讓她暫時躲避原有的工作、丈夫和情人,但她能在這個臨時港灣里躲多久?她永遠躲不過生活本身!100年前,魯迅在《藥》的結尾處,給夏瑜的墳頭添加了一圈紅白的花,讓華大媽看到生活的希望,也為夏瑜的死增添了些許光彩。畢竟,生活需要一絲光彩,尤其在灰暗無光的日子里。顧慎夕需要紅白的花,作者需要紅白的花,讀者也需要紅白的花。
30年前,雷達先生將“新寫實主義”寫作稱為“寫生存狀態的文學”,他發現“往昔戳露在外的形形色色的觀念消隱了,代之而來的是生活本身的樸拙、硬度和質感;可以制造戲劇沖突的手法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新鮮而酷烈的生存原色;沉溺在內心幻覺和遠古夢想的情景遁避了,代之而來的是堅實的大地和大地上的風景;傳統的和諧、均衡、嚴謹的美似乎解體了,代之而來的不憚于‘惡、‘丑的嚴酷而粗糙的美……”我從葉端的《歲寒》中看到“生活本身的樸拙”,看到“生存原色”,看到“大地”上的顧慎夕及其周邊“風景”,這不就是“新寫實”嗎?雷達先生說“新寫實小說是一種過渡”,它“冷靜展示壓倒主觀抒發,客觀描繪‘狀態代替對某種值得肯定的價值的肯定”。閱讀《歲寒》,我知道,雷達先生所說的“過渡”還存續著,這是“新寫實”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