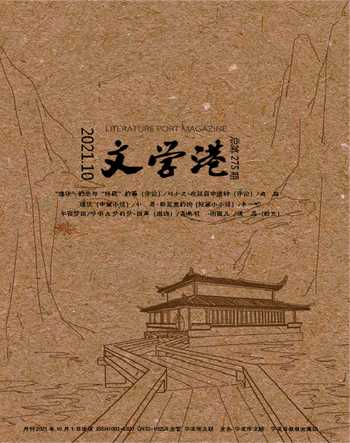在延宕中逆轉
南翰

沿著小昌為我們鋪設好的敘事路徑,我一口氣讀完了這篇小說。盡管在這種類似于“迷宮式”的敘事中有著不乏枝蔓叢生的細節,但好在敘述者“我”始終貫穿于小說文本的字里行間,也就是說,讀者只要緊跟住了“我”的步伐,讀完它并非難事。但讀完之后,至于要明白小昌真正想表達的意思,又確乎是一件十分犯難的事情。除了更多地知道小說中的“我”(一個得罪了頂頭上司被驅逐出大學講堂而成了一名無為的圖書管理員)那幽暗的人性被扒得體無完膚之外,由此所引出的系列灰色人生的點滴倏然間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一種強大的虛無感頓時升騰起來,令人沮喪不堪。
小昌很鐘情于博爾赫斯,所以他才會在小說創作中義無反顧地滲透著博氏的理論。應該說,此篇小說最堪為代表他那“迷宮式”敘事表達的實踐范本。為了更好地豐富這種深藏于文本內里褶皺中的小說意味,小昌在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來推進故事情節發展的過程中,又恰好地借助于各種諸如通電話、發信息、插入回憶片段、他人轉述、夢境展現等形式來推動敘事進程,這便把完整的故事解構成了一個個話語的“迷宮”,呈示出片段化的敘事特征,進而讓讀者穿行于作者為我們構筑的小說日常之中。
小說《埋伏》中,人物之間各種關系顯得微妙又復雜,呈現出一種網狀結構模式。小說通過“我”與表弟萬五父子在“我”家相處的幾天里,緊緊圍繞著萬五出獄后為打聽妻子慧慧的下落,不斷對“我”進行多次問詢的敘寫,情節上安排了“我”與女學生“小鵪鶉”等人在KTV包廂喝酒唱歌,“我”與萬五潛入“我”的仇人家里泄憤砸東西進行報復,“我”帶萬五兒子魁兒一起去餐廳吃飯與“小鵪鶉”不期而遇,以及萬五找到慧慧之后一起來到“我”家領走魁兒這樣四個相對集中的故事內容,同時小說的情節又隨著“我”對慧慧深藏多年的情欲被揭秘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這種在時空的穿梭中出現的眾多交錯與分岔的敘事,充分地挖掘出了各色人等不能直視的“人性”。當“我”與萬五趁一個月黑之夜潛入仇人家里,卻偶然間發現處在大洋彼岸的妻子早已出軌于仇人的一幕,這種看似荒謬的卡夫卡式的藝術處理,更為小說揭開了一層層神秘的面紗。
很好地把控著敘事節奏,以平衡的方式逐漸推進故事情節,應是小昌在此篇小說中力求表現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篇小說相對勻稱的故事結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小說敘事的平衡性,然這種有意為“蓄勢”而制造的平衡,更多地還是體現在情節設置的重復與延宕上。或許這與小昌讀大學時學習動力工程專業有關,長期地接觸機器零件,故而自然形成了一種精密、細致的小說敘事美學風格特征。小說中隨處可見的這種“伏筆千里”的照應安排,讓各要素之間出現了猶如建筑學上的“榫卯”結構,前后緊密呼應、嚴絲合縫,收到了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如處處貫穿的“萬五的眼睛”,時時出現的“枯井”,以及反復呈現的“割耳朵”等,顯得虛幻而不真實,一切預示著人物那不確定命運的迷惘走向。
小說亦隨處閃耀著戲劇化情景處理的藝術光芒,如在包廂里,出現了我模仿豬八戒背媳婦的情節架構,這無疑是小昌不乏奇特想象的精彩之舉:
“我背著小鵪鶉,在飯桌周圍轉了一圈。她的胸脯緊緊貼著我的后背,能感到她小小的乳。我不想放她下來,就想那樣一直背下去。”
你看,短短的兩行文字,小說的趣味由此被激發,這一神助之筆,順利地照應了后面揭秘的“我”在初見慧慧時,萌發的青春激情的愛欲。“青春是什么?一場夢。愛情是什么?那場夢的內容。”(克爾凱郭爾語)是的,那場夢的內容,終將與“我”這一生如影隨行的愛欲表現處處對應,小昌就是由此一筆延宕開去,讓我對“小鵪鶉”(可以說是慧慧的化身)產生著“混亂的想象”,甚而在包廂里對“小鵪鶉”進行性的挑逗,均緣于此,讀來真正耐人尋味;小說中另外又安排了一處看似荒誕實則極具藝術化的處理情節:酒后亢奮的萬五拿著一把菜刀,讓我扮演那個被他搶劫過的收糧人。我想,此刻的萬五肯定像極了福克納筆下那個揮舞鐮刀的沃許,情節上的這種對經典的戲仿讓小昌小說充滿了戲謔的味道,著實增添了不少生動的意蘊。
當小說行進到最后,出現了一幕幕急遽“反轉”的情節。這位曾經的玩伴,小時候一向聽“我”話的表弟萬五認定“我”是“合謀者”之后展開了強勁攻勢,他主動找到“小鵪鶉”:
“先掉下枯井的那個人是我,萬五為了救我,才跳下去的,那個嚇破膽的人是我,不是他,他一直在安慰我。”
這讓“小鵪鶉”認為“我”是個懦夫,說完就轉身走了。緊接著,萬五帶著慧慧來到“我”家,竟然“將她連拉帶拽,扯進另一個房間里”,干起了床笫之事,徹底讓“我”體會到了這“破碎的愛與欲”,小說的情節終于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轉,至此,寫與被寫已經完全成為了一種悖論,最終使“我”不得不以重寫萬五的小說來結束全篇。
如果說小說《埋伏》在敘事情節處理上有著較為出色表現的話,那么小昌同樣以其出彩的人物描寫進一步塑造出了相關人物形象。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心理還是神情表現都顯得較為虛幻,我們根本看不清他們的真實面目。如小說中的“我”思緒始終飄忽不定,行事往往前后矛盾,有時膽大得驚人(如在仇人家實施報復時的極度野蠻);而有時卻又膽小如鼠(連扮演舉刀搶劫都顯得“無所適從”)。又如面對萬五不斷詢問慧慧的下落,開始“我”一口咬定不知道,因為一來伙同慧慧的私奔者德興曾是“我”的救命恩人;二來慧慧為此事曾求助過“我”,這讓“我”為能得到慧慧有著自己的小算盤。然在故事行進的過程中卻逐漸出現了動搖,直到后來萬五領著兒子,并讓魁兒跪在“我”面前逼迫“我”說出慧慧下落的時候,“我”的心理防線又全面崩塌,終于告訴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小說正是讓“我”時時處處感覺生活在周圍的人對“我”的算計、懷疑、嘲笑、奚落、指責、誤解,甚至于羞辱的包圍之中而日漸變得豐盈厚實的。
小說中,出現了一系列如對“手”“胎記”“刀”“監獄”“象棋”“夢境”“門”等含有象征隱喻的意象描寫,這些碎片化的夢幻之物,它們更多的是在探尋現代人的精神迷失與價值思考。同樣,與之相呼應的還有小昌不忘在行文中適當穿插地表現“夕陽”“暗夜”“雪花”等環境,而這些環境更多的是以落寞的、灰色的、冰涼的色彩作基調,象征著隱遁在人性暗河中不斷翻滾的那不可捉摸的灰色人生。正因為如此,小說完成了類似于高更的“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到哪里去?”對生命意義的追問。
小昌的小說語言頗具藝術性,顯得成熟老到、簡而有味,同時亦具有強烈的現代性。而這種現代性是以放大特定意象的想象生發來得以完成的,如那夸張、變形了的“手”,那“梧桐葉”般的“胎記”等。這些自由綿延于小說現實主義溫床上的意象,又力圖以“夢境”的形式,始終閃爍在小說虛擬的縱深處,最終通向了現代主義那充滿著“無限才智與想象力”的“小徑分叉的花園”之中。總之,這種敘述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逆轉,使小昌小說《埋伏》在揭示人性幽暗的同時,也形成了難能可貴的圓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