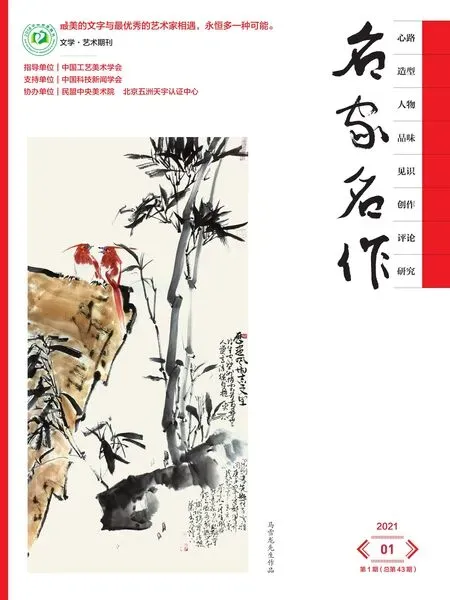董其昌與云居寺“寶藏”
翟杜鵑
一、“寶藏”
1.“寶藏”
董其昌書“寶藏”,質地為青石,長方形,高45 厘米,寬96 厘米,厚11 厘米。刻石鐫刻于明崇禎四年(1631 年),原嵌于石經山第六洞窗上,現存云居寺。碑記如下:
寶藏
董其昌書
司爟氏新安許立禮,同侄中秘志仁,文學謝紹烈、黃玉虬、何如霖、田鐩、李自杰游小西天勒石。大明崇禎四年三月四日。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萬歷十七年(1589 年)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太子太保等職。崇禎九年,卒,賜謚“文敏”。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禪理、精鑒藏、工詩文、擅書畫及理論,是晚明最杰出、影響最大的書畫家。存世作品有《巖居圖》《明董其昌秋興八景圖冊》《晝錦堂圖》《白居易琵琶行》《草書詩冊》《煙江疊嶂圖跋》等。著有《畫禪室隨筆》《容臺文集》《戲鴻堂帖》(刻帖)等。
許立禮,字季履,號蓮岫,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今屬安徽)人。明代官吏。蔭生。歷仕中書舍人、工部主室、員外郎、云南府知府。許立禮的父親許國,是董其昌的老師。
許國(1527—1596),字維楨,明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今安徽歙縣)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考中進士,歷仕嘉靖、隆慶、萬歷三朝,先后出任檢討、國子監祭酒 、太常寺卿、詹事、禮部侍郎、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萬歷十二年,因“平夷云南”有功,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死后,朝廷追加謚號為“文穆”,著有《許文穆公集》。
董其昌為許國作《太傅許文穆公墓詞記》中,“公之諸子季履中舍輩以為是役也,天子給秘器以寵之,命皇華以督之,雖莬裘之卜經,始于達生”,其中季履指的就是許立禮。
除董其昌與許立禮外,題記中游玩的其他人,皆不可考。

天津圖書館藏《許文穆公集》,明萬歷三十九年(1611)許立言、許立禮刻本

房山云居寺石經山董其昌題“寶藏”拓片
2.董其昌“寶藏”與米芾“寶藏”
董其昌題“寶藏”,一方面應該是感慨房山石經刊刻這一浩大工程,以及古人佛教信仰的虔誠深遠;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對他高度關注、推重并引為楷模的米芾的致敬。
米芾(1051—1107),初名黻(fú),后改芾,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岳外史、鹿門居士。祖籍山西太原,遷湖北襄陽,后定居潤州(現江蘇鎮江)。曾任官校書郎、書畫博士、禮部員外郎等職。米芾是北宋著名的書法家、畫家、書畫理論家,能詩文、擅書畫、精鑒別,尤精擅篆、隸、楷、行各書體,與蘇軾、黃庭堅、蔡襄合稱“宋四家”,其傳世書帖、碑帖、書卷散見中外博物館,名重四海。
米芾書“寶藏”碑,歷史記載有過兩次。一次是在北宋崇寧三年(1104),米芾任安徽無為縣軍使知州時為千佛禪寺所書。再一次是在熙寧年間(1068—1077)任廣東英德縣、浛洸縣縣尉時為浛洸司所書。但是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兩通碑刻均遭毀壞,僅有無為縣千佛禪寺復刻“寶藏”木匾一紙拓片傳世。
董其昌書“寶藏”與米芾所書“寶藏”均為行書,雄渾有力,縱橫奇宕,豪逸有氣,以勢為主,天然痛快。
董其昌論書主要是以提拔形式集中于他的《容臺集》《容臺別集》以及《畫禪室隨筆》中,其中關于米芾的題跋就有百條左右,由此可見他對米芾的推崇。
《畫禪室隨筆卷一》中董其昌直接用“宋朝第一”來評價米書:“米元章嘗奉道君詔,作小楷千字,欲如黃庭體。米自跋云:‘少學顏行,至于小楷,了不留意。’蓋宋人書多以平原為宗,如山谷、東坡是也。惟蔡君謨少變耳。吾嘗評米書,以為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山谷直以品勝,然非專門名家也。”同卷另有一條評價:“然自唐以后,未有能過元章書者。”而且,從董其昌對其他書法家的評價中,也能看出其對米氏的重視,《容臺別集卷四》中有:“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獨云林古淡天然,米癡后一人也。”云林即倪瓚(1301—1374),初名倪珽,字泰宇,別字元鎮,號云林子、荊蠻民、幻霞子,江蘇無錫人,元末明初畫家、詩人,“元代四大家”之一。董其昌在“元四家”中獨推倪瓚,稱其書法古淡天然,是米芾后第一人。可見在董其昌這里,宋、元、明三代書家以米芾為魁首。

安徽無為縣千佛禪寺“寶藏”木匾拓片
二、董其昌與房山石經
董其昌不僅參訪房山石經并題字“寶藏”,他還參與了明代房山石經的鐫刻,明代刻經中留有題記“華亭董其昌助”。
明代房山石經大規模刊刻已經停止,明初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名僧道衍(姚廣孝),前往石經山視察。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姚廣孝到達房山石經山,驚嘆于靜琬以來歷代刻造石經事業之宏大,題詩《石經山詩》并序,“鐫于華嚴堂之壁”。之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朝廷曾撥款修理過云居寺和石經山一次。又,據《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三載:“永樂十八年三月,旨刻大藏經板二副,南京一藏,六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十五字。又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向后木的壞了,有石的在。”但明代官刻石藏后來似未實現。所以明初雖然對房山云居寺和石經進行了考察、保護和修理,但并未見續造的石經。
明代房山石經較為特殊的一點是明中期有道士募刻道教經典《玉皇經》貯藏石經山。宣德三年(1428 年),有全真教道士陳風便和正一教道士王至玄等,募刻道教《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髓》《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玉皇本行集經纂》《無上玉皇心印經》四部,共刻石八塊,送至房山石經山貯藏(藏于第七洞)。根據跋文《無上玉皇心印經終傳經始流》所記,這幾部道教刻經的目的在于“刻金石,藏之名山,傳之萬世也”,這與石經山藏經洞開辟者靜琬大師“鐫鑿華嚴經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的心愿非常一致。
成化年間,云居寺的住持以及保定府新城縣信徒張普旺等,對云居寺和石經盡力維護,但是到萬歷高僧達觀真可與憨山德清到云居寺訪問時,云居寺石經山又趨于衰落。
明末佛教復興,萬歷末年至天啟、崇禎年間,時有南方在京做官的居士葛一龍、趙琦美、馮銓、董其昌等以及佛門僧人等,在北京石燈庵續刻佛經《華嚴經》《法寶壇經》《寶云經》等10 余部,送至石經山瘞藏,因當時山上洞窟已滿,便另辟一石洞貯藏,即今石經山第六洞。至此,房山石經較大規模的刻造活動停止。
三、董其昌與佛教
房山石經明末的續刻,一方面是由于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達觀真可禪師在石經山雷音洞發現佛舍利,敬獻慈圣皇太后,云居寺在京城聲名大振;另一個原因是晚明時期,晚明四大高僧接引文人士大夫廣泛學佛參禪,形成了一種居士化浪潮。陳垣在《明季滇黔佛教叢考》中指出:“萬歷而后,禪風寢盛,士大夫無不談禪,僧亦無不欲與士大夫接納。”這種居士佛教的興起,支撐了大規模的佛教刊印活動的展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方冊本《嘉興藏》的雕造。
萬歷七年(1579),達觀真可禪師感嘆佛教經書卷帙重多,因此想要刻造方冊,使佛法流通方便。萬歷十二年(1584),在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達觀真可、憨山德清與陸光祖、馮夢禎、曾同亨等人商議刊刻方冊大藏經,正式開始雕造《嘉興藏》。《嘉興藏》的雕刻,歷經129 年,規模巨大,僅僅依靠僧侶們的力量難以完成,達觀真可門下的居士們,比如陸光祖、焦竑、袁宏道、馮夢禎、湯顯祖等,他們從人力、財力上都對《嘉興藏》的雕刻起到推動作用。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房山石經的續造自然也成為晚明居士捐刻佛經,實現他們虔誠信仰的一種表現。作為捐助人之一的董其昌,在對他的書畫研究之外,他的居士身份和佛教信仰,值得我們探討研究。
1.明代佛教概況
明清以后,中國佛教步入衰微時期。明朝建立初期,明王朝推崇理學,強化專制統治,對佛教采取既充分利用又嚴格控制的政策。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設立善世院,管理全國佛教。其下又設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員,實現對佛教教團的全面有效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又將天下寺院分為禪、講、教三類,要求所有僧眾分別專業。同時為了便于管理,對各類僧侶的服色也做出規定,不允許混淆。同年,又詔令禁止寺田買賣,在經濟上加強對寺院的控制。明初廢除僧侶免丁錢,度牒免費發放,但是對剃度有嚴格限制,度牒發放嚴控,限制良多。到明代中晚期,因為政治腐敗、宦官專權、戰事與自然災害影響,為緩解財政壓力,代宗景泰二年(1451),開始實施賣牒救災,后世沿襲此法,直至明朝末年。這直接導致僧尼人數膨脹。
從佛學思想上來說,理學的興起進一步制約了佛學的發展,理學家一方面批判佛、道,另一方面卻吸收了佛、道的哲學思想和修行方法。在形式上,理學是以儒家為主導,維護宗法禮教制度,而在內容上理學則實現了儒、釋、道三教的融合。面對理學的這種沖擊,佛教努力適應宗法制度需要,不斷推進世俗化。為了滿足一般信徒的現世利益和個人愿望,明代佛教思想與儒、道思想結合得更為緊密,甚至吸收了民間信仰和神話傳說。
在這種情況下,到明中葉時,佛教衰微已極。從宣德(1426—1435)到隆慶(1567—1572)近150 年內,禪宗、凈土二宗均毫無聲息。但是從萬歷(1573—1620)起,因“四大高僧”的積極推動,佛教復呈繁榮返照之象。
2.董其昌的佛教之路
晚明四大高僧中,董其昌與達觀真可、憨山德清和云棲祩宏都有交往。
達觀真可(1543—1603),俗姓沈,吳江(今屬江蘇)人,字達觀,晚號紫柏大師。門人尊他為紫柏尊者,是明末四大師之一。達觀大師一生廣研經教,振興禪宗,“始從楞嚴,歸至歸宗、云居等,重興梵剎一十五所”,倡導刻造《嘉興藏》多部。達觀真可禪師的弟子門人眾多,“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眾”,董其昌就是他的弟子之一。
董其昌與達觀禪師的交往,在他的《容臺集》《畫禪室隨筆》以及達觀真可禪師的《紫柏老人集》中都有記載。《居士傳》提到董其昌尚為諸生時,聽真可禪師講述文章與禪理,后又得真可弟子密藏道開的“激揚”,參禪悟道,漸入佳境:“參紫柏老人,與密藏師激揚大事,雖博觀大乘經,力究竹篦子話”。“竹篦子話”是與禪師大慧宗杲有關的著名公案。達觀禪師逝世后,董其昌為其做贊: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壞。不妄動。身不壞。不弄精魂不捏怪。這回方驗真持戒。要與人天插個標。何妨地獄還些債。咄。債已還。有甚待。端端坐待老憨來。打破從前舊皮袋。一道神光火電飛。風流鐵漢今疏快。
關于二人的交往,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四載:
達觀禪師初至云間。余時為書生,與會于積慶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為思大禪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尉妙于文章,陸宗伯深于禪理。合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于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內典,參究宗乘。復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后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如云水東南,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卯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恩,有以也。
觀師答問,常有不經人道語。余曾問:“菩薩處胎受生之后,還知前生為誰,如所云宿命通否?”師曰:“圣人無我,但受生之后,前生所作,循業發現,宛然如一日,安用自知為張三李四?許多我相。”又,余時方應舉,日用攻舉子業。余問:“此于學道,寧不相妨否?”師曰:“譬如好色人患思憶病,此人二六時中,寧廢著衣吃飯一切酬應否?雖復著衣吃飯一切酬應,其思憶病相續不斷,即作意斷之,其病益深。”李太白詩曰:“抽刀斷水水更流,是也。”有患煩惱塵緣能障道者,若為掃除。師曰:“如一男子,有殺父仇,懷憤欲報,拂拭純鉤,畢生尋覓。初聞張三,二十年后知此真仇本是李四,便舍張三,直覓李四。諸人欲掃除煩惱,正為未知真仇也。”此語與張拙斷除煩惱重增病,更覺透徹。
今《紫柏老人集》,乃不見載,知法語所遺,多矣。
《紫柏老人集》中也收錄了這兩段,并載有真可禪師給董其昌講解佛法的信,不過此信從內容來看似乎并非是董其昌提到的導致二人“不復相聞”的信。
緣起無生之旨,祖佛骨髓,而像季黑白,千萬人中,求一二信者不可得。今足下于此獨能信入。非夙具靈種緣因熏發,那來現行暫露。何快如之?
來書謂:“初頗暢快,茲又不活潑,若將失去,病在何處?”此既現行暫露,熏力稍微,自然隱沒,不必生疑。惟宗門語句,不可草草。若以足下信入者,擬通其關棙,所謂“魯君以己養養鳥”也。昔兜率悅問張無盡:“宗門葛藤,有少疑否?”無盡曰:“惟德山托缽因緣未了。”兜率厲聲曰:“此既有疑,其余安得無疑?!”逕入方丈不顧,無盡由是發憤參究,然后大徹。今足下十有二三不透,則去無盡尚遠,極當發憤,此生決了,不得自留疑情,遺誤來世。
來示又謂:“念念起處,索頭在手。”敢問足下。為念起處本即無生?為了念本空,乃契無生?若念起本即無生,則知無生者,念耶?非念耶?若了念乃契無生,則了者,謂有念了耶?謂無念了耶?有念則早乖無生,無念則無生誰契?于此透脫無疑,席幾草庵借宿,猶非寶所。
第來示所謂“如何踐履?如何保持?待力之充,及涉境試驗”云云,自知時節矣,豈待貧道饒舌?貧道不惜口業如此,總是缽盂添柄。惟足下或宗乘中,或教乘中,大著精神,作個仇讎,務必摟破其窠窟,搗其棲泊,再共商量未晚。
從以上董其昌自述以及達觀禪師的回信來看,對于這位學生的學佛思想和他的虔信程度,達觀禪師似乎有所懷疑,從他的《與黃慎軒書》以及《與馮開之書》中提到董其昌的部分也可見端倪:
近見董思白,拶及此事,渠于不知不覺中,佛法習氣漸覺生疏,橫口褒貶古德機緣,判寂音決非悟道之僧。道人從容謂渠曰:“汝信大慧杲禪師悟道否?”渠曰:“是一定大悟徹的。”又問曰:“寂音乃大慧平生所最仰者,脫寂音果見地不真,大慧難道作人情,仰畏他耶?”思白俯首無語。
唐一所董玄宰輩,得一紗帽蓋頭,惟快情恣識,逞其素所不逞,寧暇及此。趙定老近有信占,宇泰中甫,當委曲時警家之。
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字澄印,號憨山,法號德清,謚號弘覺禪師,安徽全椒人,明朝佛教出家眾,為臨濟宗門下。其復興禪宗,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董其昌與憨山德清的交往見于他自己的散文集《畫禪室隨筆》:萬歷十六年冬(1588),董其昌與唐元征、袁伯修、瞿洞觀、吳觀我、吳本如、蕭玄圃同會于松江龍華寺,聽憨山禪師談“戒慎恐懼”之道。
云棲袾宏(1535—1615),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因久居杭州云棲寺,又稱云棲大師。其提倡禪、凈雙修,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萬歷二十年(1592),董其昌題《金剛經》:“送云棲大師,藏云棲寺庫。”董其昌自述,“每有追薦,大師出余手書,令僧持誦”。萬歷三十二年(1604),五十歲的董其昌應蓮池大師之請,為云棲寺書寫了《重建云棲禪院碑記》。萬歷四十二年(1614),董其昌六十歲。此年,他書《凈土經》紀念蓮池大師八十初度。董其昌稱:“云棲蓮池大師,甲寅正月八日初度,余以師純提凈土,掃彼狂慧,行在《梵綱》,志在《觀經》。”《梵綱》是菩薩戒經,《觀經》就是《觀無量壽經》,是凈土宗的重要經典。
董其昌的佛學之路,一方面來看是因為當時禪風盛行,士人居士受社會風氣影響,另一方面與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關系。從他的仕宦經歷可以看出,他對政治異常敏感,一有風波,他就堅決辭官歸鄉,幾次反復起用,在晚明政壇詭譎無常,成了難得的善始善終的一位士大夫。他在官場上不激不隨甚至適時退隱的態度,可以看出他性格上的圓滑與謹慎,而這種性格也反映到了他的佛學信仰之路上,從他的老師達觀真可禪師給他的回信以及提到他的評價來看,達觀禪師認為這位學生的佛修之路有相當的功利性,以至于將“學道”與應舉做官相比較。
明萬歷年間,達觀真可來到房山云居寺,感慨:“涿州石經山為天下法海。自隋琬祖以來,龍象蹴踏,振揚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為草莽,金碧化為泥涂!”達觀禪師在石經山上發現了佛舍利,并敬獻慈圣皇太后,后又募緣修理了琬公塔。憨山德清撰寫《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記載此事。董其昌在他的晚年支持房山石經的續刻,游玩石經山并留下“寶藏”題字,不僅是對他書法上的“第一”米芾的致敬,還表達了對他老師達觀禪師的敬意。理清這段歷史,對我們研究明代房山石經,對了解明末居士佛教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