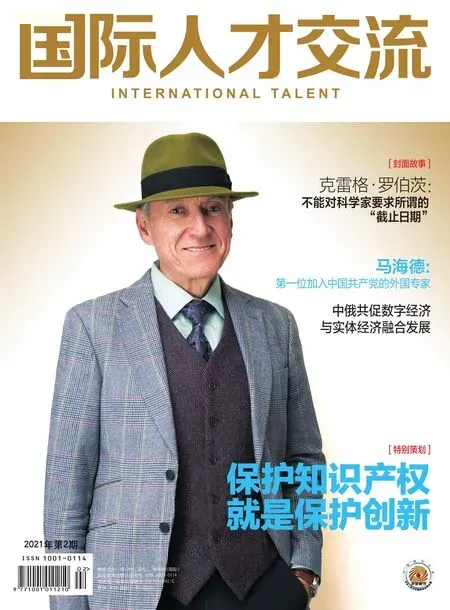深層鏈接行為的著作權法規制
文/毛銘浩
深層鏈接作為鏈接方式的一種,被廣泛應用于互聯網領域,是指設鏈網站所提供的鏈接服務使得用戶在未脫離設鏈網站頁面的情況下,即可獲得被鏈接網站上的內容,此時頁面地址欄里顯示的是設鏈網站的網址,而非被鏈接網站的網址。但該內容并非儲存于設鏈網站,而是儲存于被鏈接網站。深層鏈接被廣泛運用在音樂搜索網站、視頻網站或視頻聚合平臺、內容聚合性 APP 等產業。隨著互聯網絡視頻產業的發展,各種內容聚合APP 的推廣,深層鏈接行為引發的糾紛頻頻登上頭條,如搜狐、騰訊、優酷土豆、樂視網等指責百度“盜鏈盜播”;“今日頭條”受到騰訊、搜狐、新京報等內容提供方的“口誅筆伐”;全國還出現了首例因“深度鏈接”侵犯著作權被判處刑事處罰的案例。
問題的提出
深層鏈接行為涉及的著作權侵權糾紛無論在司法實踐還是理論研究上一直存在爭議。深層鏈接行為的法律困境成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深層鏈接行為的法律定性存在爭議;二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范疇界定存在分歧。
網絡鏈接最初的主要功能是信息定位,幫助用戶在開放的互聯網空間里快速、準確地找到目標信息,屬于信息網絡服務的范疇,不構成提供行為。對于此種鏈接的法律定性,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基本達成共識,并沒有太多爭議。但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網絡鏈接技術也在發生變化,特別是網絡聚合平臺等新型商業模式的快速興起,網絡鏈接技術也進一步得到更加廣泛的應用。網絡鏈接技術的多樣化發展,使得深層鏈接不僅僅具有提供信息定位的功能,而且用戶可在不需要跳轉至被鏈網站的情況下,直接在設鏈網站獲得其他網站的作品。由于我國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司法解釋對此類網絡鏈接并無明確規定,并且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規則條文也比較籠統、抽象,使得此類網絡鏈接模糊了提供服務和提供作品的類型化邊界,受到學界和司法實務界的廣泛討論。
深層鏈接行為法律認定的困境成因
信息網絡傳播權在制定之初,其控制的作品提供行為主要表現為將作品置于向公眾開放的服務器中,鏈接的形式也主要是提供網絡服務的普通鏈接。因此,當新型的鏈接形式比如深層鏈接出現時,應當如何認定其法律性質,以及現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規則是否可以涵蓋此種行為類型,這是新的社會實踐提出的法律難題。
因此,深層鏈接的困境成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相較于普通鏈接,其法律定性是否存在差異并產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現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規則是否可以涵蓋新的行為形態,也即信息網絡傳播權控制下的提供行為應當如何界定。
深層鏈接的法律定性爭議
在深層鏈接法律性質的認定上存在的分歧,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深層鏈接與普通鏈接相比,不僅技術層面存在不同,而且在具體行為形態層面也存在差異;另一方面,相關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對此類新型網絡鏈接并無明確規定。
雖然新《著作權法》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律含義進行了規定和修改,但是條文表述并未對具體的提供行為本身作出限定,其側重于作品價值實現的基本方式,因而并未涉及深層鏈接的法律性質,并且將“提供作品”的“作品”一詞刪掉,是否在立法層面擴大了提供行為的涵蓋范圍,也令人不得不產生疑問。我國頒布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23條是關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搜索或者鏈接服務的法律規定,涉及的網絡鏈接在性質上屬于普通鏈接,并不能直接適用于深層鏈接。2012年出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在第3條第2款具體規定了可被法院認定構成提供行為的情形,包括將作品提供至服務器中,但并不能排除深層鏈接行為構成提供行為的可能性。

2017年8月18日,全國首家互聯網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正式成立,該法院定位于用互聯網方式審理互聯網案件,集中管轄杭州市轄區內基層人民法院有管轄權的涉互聯網案件,當事人通過互聯網,足不出戶就能完成訴訟,實現“網上糾紛網上了”(新華社記者 翁忻旸 攝)
由此可見,對于深層鏈接行為的性質認識不同并進行差別化界定,在實務和學術界產生了根本分歧,而爭議的焦點在于深層鏈接行為應當屬于提供行為還是網絡服務提供行為。
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范疇界定爭議
深層鏈接行為產生的著作權法律問題,之所以對其法律性質的認定存在爭議,深層次原因則是因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律表述抽象籠統,導致權利范疇的界定不明確。因此在認定提供行為時,實務和學術界對其法律內涵存在不同的理解,進而提出不同的侵權認定標準。理論和司法實踐提出的不同標準爭議的背后,本質上是對于著作權規范的理解上存在根本分歧。
信息網絡傳播權是著作權法保護著作權人在網絡環境中傳播利益的一種重要的專有權利。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定直接來源于WCT第8條后半段的規定,也即是向公眾提供權。然而,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對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內涵以及侵權認定一直存在爭議:一方面是對于WCT有關向公眾提供權的規定以及我國《著作權法》的具體規定存在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伴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特別是網絡深層鏈接技術的廣泛應用,也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適用帶來新的問題。
由于我國關于如何界定信息網絡傳播權控制下的作品提供行為存在爭議,特別是在判斷深層鏈接的法律性質方面產生了根本分歧,進而在服務器標準之外,又發展出不同的侵權判斷標準。因此,深層鏈接的法律定性不明確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范疇界定模糊使得深層鏈接的著作權法規制成為一個還未得到合理解決的法律困境。
深層鏈接行為的著作權法調整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深層鏈接行為產生的著作權法問題的關鍵在于深層鏈接行為是否構成向公眾提供權或者信息網絡傳播權,以及如何認定的問題。國內和國外對此均產生爭議,并提出不同的認定標準和思路,但并沒有使得該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
無論是普通鏈接還是深層鏈接,均是具體的社會實踐形態,會隨著技術發展以及商業模式的變化而變化,對于深層鏈接的法律定性,其本質上在于對信息網絡傳播權控制的提供行為進行認定。首先,通過分析深層鏈接與普通鏈接的區別和差異,進而確定其在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法律含義,對其法律性質作出合理認定;其次,在現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規則下,應當以該權利的規范性目標為指引和約束,明確權利本質和邊界,進而對相關規則進行法律解釋,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范疇提供合理的界定方案。
深層鏈接的法律性質認定
之所以對深層鏈接行為的法律定性產生分歧,根本原因在于相較于普通鏈接而言,其技術以及功能上的差異是否會產生不同的著作權法效果?而關于兩者性質是否相同的認識又來源于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第8條、我國新《著作權法》第10條第1款第12項規定以及對相關司法解釋解讀和理解的差異。因此,將對涉及深層鏈接的國際公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進行重新解讀,并將深層鏈接與普通鏈接進行性質分析,進而對其法律性質合理認定。
國際公約以及我國相關規定的再解讀。WCT第8條制定的初衷是為了應對未來可能的技術發展與應用,因此在向公眾提供權的規定上遵循了技術中立原則,即無論現有或者未來采取何種技術手段向公眾提供,都可以涵蓋在該條規定的權利中。從國際公約關于向公眾提供權的規定和解釋來看,初始上傳行為并不屬于對向公眾提供權意義下提供行為的解釋和界定,而且就深層鏈接行為本身而言,符合使作品處于公眾可獲得的狀態這一要求,從而屬于WCT規定的向公眾提供權的涵蓋范圍。
我國新《著作權法》第10條第1款第12項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定義進行了修改,將“提供作品”中的“作品”一詞去掉。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定最初是來源于WCT第8條后半段的規定,也即所謂的向公眾提供權,該條對于向公眾提供權意義下的提供行為可表述為:“通過有線或者無線的方式向公眾提供”。通過對比表述可以發現,信息網絡傳播權在修改后,其關于提供行為的表述才與向公眾提供權意義下的提供行為完全符合。很明顯,根據WCT第8條的規定以及立法修改的結果,完全是可以將使作品處于公眾可獲得狀態的其他提供行為包含在提供行為的范圍之中,也就在立法層面肯定了深層鏈接等行為可構成提供行為的可能性。
深層鏈接的著作權法含義界定。無論是國際條約,還是我國法律規定以及司法解釋,均沒有將深層鏈接行為明確排除在向公眾提供權或者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范圍之外,并且分析深層鏈接本身的法律性質,也可以得出其可構成作品提供行為。根據我國《著作權法》行政法規以及司法解釋關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定,相較于普通鏈接,深層鏈接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其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著作權法效果:
首先,從公眾獲得作品角度來看,在普通鏈接情形下,網絡用戶是被引導至被鏈網站獲得作品,但在深層鏈接下,網絡用戶可以直接在設鏈網站獲得作品;其次,從作品提供角度來看,在普通鏈接情形下,由于網絡用戶被引導至被鏈網站,因此作品提供行為是由被鏈網站實施,設鏈網站對于作品等內容并沒有任何控制力。但是在深層鏈接的情形中,設鏈網站可以將被鏈網站的內容直接變為其組成部分,進而對相關內容可以進行選擇性傳播,使得網絡用戶可以在設鏈網站直接獲得作品,對被鏈網站上的作品等內容具有較強的控制力;最后,從作者的傳播利益角度來看,雖然設鏈網站并未在其服務器上存儲作品等內容,但卻通過深層鏈接等方式可在其網站實現向公眾傳播相關作品的效果,使得網絡用戶可以在其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這種鏈接行為實質上相當于取代了被鏈網站的作品傳播者地位,對作品的許可傳播產生了實質性替代效果,對作者的作品市場產生了消極影響,也就違背了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目標。初始提供行為并不是構成作品提供行為的必要條件,深層鏈接等針對作品已經被提供于互聯網環境下的再提供行為也完全符合國際條約或者我國《著作權法》對于作品提供行為的界定。
深層鏈接侵權認定標準的重構
目前理論和司法實務界提出的認定標準的基礎,即對信息網絡傳播權意義下的提供行為要素的理解和解讀。但是有觀點指出,任何具體標準的論證過程,都應當明確相應的規范性目標,并在該目標的指引下明確權利屬性、合理界定權利邊界,同時可合理辨析不同侵權認定標準的優勢與不足,進而對深層鏈接的侵權認定標準進行重構。
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本質及范疇界定。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對著作權專有權利的規定,是以特定行為作為其權利法定內容,進而來控制對作品使用行為的行使。從具體條文來看,《著作權法》采取列舉加兜底條款的方式,對著作權權利范圍的具體行為作出規定。此種權利規則的構造,并不能對著作權本質有清晰的認識,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對著作權邊界的合理判斷。
然而,著作權的權利本質與著作權制度的立法宗旨密切相關,也即著作權的規范性目標。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1條的規定,著作權保護的目的在于“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創作行為決定了著作權的產生,而傳播行為則是權利行使和實現的表現方式。并且從該法的第10條第1款規定可以得出,著作權是指權利人控制作品以及獲取經濟利益的權利。而作為調整著作權傳播行為的法定權利之一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其最基礎的規范性目標或者立法目的就是保護作品的傳播利益,進而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本質也即是權利人控制作品傳播的權利。眾所周知,信息網絡傳播權作為一項絕對權,排他性效力是該權利的應有之義,也是其權利本質的實現方式,表現為對作品上特定利益的排他性控制,也即對作品傳播利益的排他性專有。根據我國新《著作權法》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定,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排他性只能表現為對提供行為的控制力,以確保權利人或者被許可人獲得特定的經濟利益。
綜上所述,在明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范性目標即保護作品的傳播利益這一前提下,從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定義以及具有的排他性效力出發,只要行為人未經權利人許可,將作品等內容在互聯網空間向公眾提供,使得公眾可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即屬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范疇。
新實質替代標準的提出與適用。關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提供行為與公眾獲得作品可能性兩個要素之間的關系認定,應當以該權利的規范性目標和權利本質為基礎進行分析: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作品的傳播利益,而保護方式體現在對提供行為的排他性控制。具體而言,從立法目的出發,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著作權人等權利人的傳播利益,而直接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認定也是要判斷某些行為對于著作權人等權利人的傳播利益是否造成了消極影響,這種影響的判斷在于是否能夠使公眾獲得作品這一行為效果的認定。
從絕對權的保護方式角度來看,無論是有形的物權還是無形的知識產權,絕對權請求權是在權利的支配效力受到阻礙時,權利人要求侵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的權利。立法上對于絕對權請求權方式的規定,更多是基于侵害行為產生的結果,也即權利的圓滿實現狀態受到破壞或者破壞的危險來判斷。
綜上所述,應當從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效果要件出發,認定相關行為是否使得作品處于公眾可獲得的狀態,進而對是否構成信息網絡傳播權意義下的提供行為進行認定,最終得出是否構成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權判定。
在明確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認定論證思路的基礎上,從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目的以及權利屬性來分析,實質替代標準存在合理性和合法性:首先,實質替代標準是北京海淀區法院在騰訊公司案中采用的關于認定深層鏈接行為是否構成信息網絡傳播權直接侵權的認定標準。從絕對權保護的角度來看,該法院認為被告采取的一系列行為對著作權人傳播利益的損害以及給自身帶來的利益和直接向用戶提供作品的行為并無實質差別,這種認定思路與絕對權保護的救濟方式是一致的;其次,法律解釋應以立法目的為指引回歸法律規定,以法律文本作為法律解釋和適用的基礎。《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第5條完全可以作為實質替代標準的法律依據和基礎。根據該條規定,其表述為“以提供網頁快照、縮略圖等方式實質替代其他網絡服務提供者向公眾提供相關作品”,但其列舉方式為不完全列舉,這也體現出立法并不排除新行為包含其中。也就是說,只要新技術構成實質性替代其他作品傳播者地位向公眾提供作品的行為,在法律解釋上完全符合本條。
然而,該標準僅局限于討論設鏈人獲得利益與直接向用戶提供作品獲得利益并無區別,并沒有對提供行為本身進行法律解釋和論證,存在法律缺陷。本文在實質替代標準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重新解讀,以后續提供標準為補充,提出新實質替代標準。該標準以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目標為基礎,只要相關行為可使得作品處于公眾可獲得狀態,則即可認定構成提供行為。關于公眾獲得可能性的認定,則應以實質替代標準予以判斷,即如果設鏈行為替代了被鏈網站提供作品,擴大了傳播范圍,從中獲得利益與直接向用戶提供作品沒有差別,則認為作品處于公眾可獲得狀態;關于提供行為的認定,以后續提供標準為判斷依據,只要未經許可行使權利或者破壞權利人或者被許可人對專有權的控制,則認定屬于提供行為。在兩者均滿足的情況下,最終認定相關行為構成信息網絡傳播權意義下的提供行為。
綜上所述,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權認定標準應采用新實質替代標準,從行為后果出發,考察相關行為是否使得行為人實質替代其他網絡傳播者的地位,使得作者失去對作品的控制進而對其傳播利益造成消極影響,再考察相關行為是否未經許可行使權利或者破壞權利人或者被許可人對專有權的控制,進而作出對提供行為的最終認定。
結論
網絡鏈接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商業模式的多樣化,使得有關深層鏈接行為的法律定性產生爭議,主要表現在深層鏈接行為是否構成信息網絡傳播權控制的作品提供行為,進而構成直接侵權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本文通過梳理國內外有關深層鏈接行為的司法判決以及理論研究,并分析出深層鏈接行為的法律困境成因:一是深層鏈接行為的法律定性存在爭議,二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范疇界定存在分歧。對網絡深層鏈接的法律定性以及侵權認定標準提出了新的解釋路徑:在法律定性方面,網絡鏈接可分為普通鏈接和深層鏈接,并且在著作權法上具有不同的法律后果:普通鏈接屬于信息網絡服務范疇,而深層鏈接由于可以提供作品等內容,屬于提供行為,進而落入到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控制范圍;在侵權認定方面,新實質替代標準不僅符合著作權法的立法目標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權認定思路,而且也可從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第5條找到法律依據。因此,在將深層鏈接認定為作品提供行為的前提下,應采用新實質替代標準在個案中認定相關鏈接行為是否構成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直接侵權,以便保護互聯網環境下著作權人與其他當事人、社會公眾之間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