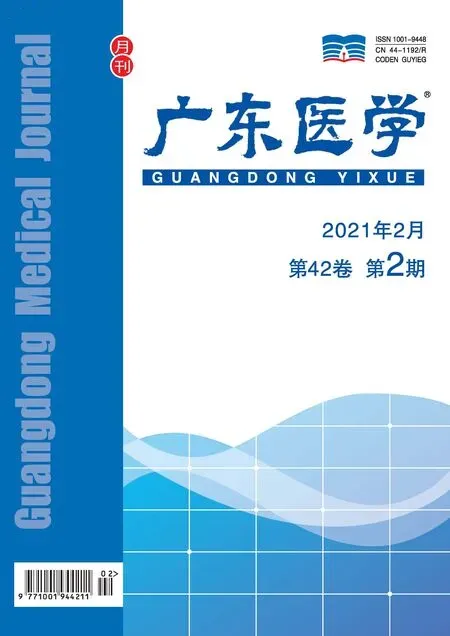小細胞肺癌免疫治療機制的研究進展*
斯伃恬,應昊軒,張健
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腫瘤中心(廣東廣州 510280)
小細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占所有肺癌的13%~15%,是一種神經內分泌腫瘤,以高度侵襲性,生長迅速,伴癌旁內分泌和早期廣泛轉移為特征[1]。在我國,大部分SCLC患者有長期吸煙史,且伴有慢性基礎疾病,因此臨床治療效果往往不理想。目前,化療和放療仍是治療的SCLC的主要手段,臨床上此類治療的初反應性也較高,且放化療常貫穿患者的整個治療過程。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于腫瘤復發較早,患者預后極差,2年生存率<5%[2]。令人遺憾的是,在過去的30年里,SCLC患者的生存率未得到顯著的提高,改善率僅為2.8%~7.2%,因此SCLC被定義為一種難治性的癌癥[3]。目前,關于SCLC的治療研究主要分為五大類:針對腫瘤的生長轉移途徑,DNA損傷修復,細胞周期抑制劑,表觀遺傳學研究和免疫治療[4]。近年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改變了非小細胞肺癌和其他實體瘤的治療模式[5],免疫治療已逐漸成為研究腫瘤治療方法中的熱點,其不但可以提高機體免疫系統的抗腫瘤能力,而且對正常組織的影響十分輕微。目前,越來越多的臨床證據表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可改善SCLC患者的預后,具有改變未來治療的潛在能力。
1 免疫治療協同作用的分子基礎
1.1 zeste同源體2 在近幾年的研究中,Zeste基因增強子同源物2(EZH2)/Schlafen家族成員11(SLFN11)通路的增強子在化療和免疫治療中的重要性得到了證實(圖1)。已知表觀遺傳修飾劑EZH2是由免疫療法誘導的,在黑色素瘤模型中,用免疫調節劑治療可增強EZH2的活性[6]。而且,已經證明免疫治療可以下調與抗原提呈相關的過程,并且EZH2活性是獲得這種免疫抑制表型所必需的[6]。另一方面,在SCLC的人源腫瘤異種移植模型中,SLFN11的作用是使同源修復機制(HRM)沉默,尤其是在化療耐藥模型中[7]。EZH2活性是SLFN11抑制所必需的,因此提示其在化療耐藥中也起作用。在SCLC-PDX模型中的鉑/依托泊苷化療中添加EZH2抑制劑可防止耐藥性的發生[7]。作為HRM的成員,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的活性在SCLC[8]中也發生了失調,并且受到SLFN11[9]的調節。
一個Ⅱ期臨床試驗評估了對復發性SCLC患者使用帕洛昔布(一種PARP1-2抑制劑)聯合替莫唑胺治療的療效,結果表明其對患者的PFS和OS無明顯影響;然而,在接受維利帕利聯合替莫唑胺治療的患者中觀察到明顯更高的客觀緩解率(ORR)。需注意的是,進行聯合治療的SLFN11陽性的腫瘤患者的PFS和OS均得到了改善,而SLFN11陰性的患者沒有發生明顯變化[10]。這些不同的結果表明,需要一種具有預測性的生物標記物,以便更好地在治療中使用這類藥物。
1.2 極光激酶A 極光激酶A(AURKA)是有絲分裂的調節因子,可以抑制G2-M轉換,在MYC擴增的SCLC中有重要的作用[11]:抑制AURKA可誘導細胞周期停滯,并強烈抑制SCLC模型中腫瘤的生長(圖1)[12-13]。此外,AURKA可能通過與肝激酶B1(LKB1)的相互作用,從而在腫瘤細胞生長和轉移中發揮作用。LKB1的磷酸化可阻止其與AMP活化蛋白激酶(AMPK)的相互作用,導致LKB1/AMPK通路的負調控,這通常是導致腫瘤耐藥性的原因[18-19]。因此,LKB1活性在調節腫瘤細胞代謝中是至關重要的,它還可以調節細胞內谷胱甘肽的濃度,從而抑制氧化應激。LKB1的滅活使腫瘤細胞對氧化應激更敏感,從而對化療和放療更加敏感[20]。

注:SCLC細胞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G1-S細胞周期檢查點TP53和RB1缺失[14],因此SCLC細胞依賴于G2-M細胞周期檢查點,其可能會收到Aurora激酶A(AURKA)過表達[11],Myc擴增驅動的突變SCLC亞型[15]和Chk1-WEE1通路[16]的影響。在化學誘導的DNA雙鏈斷裂后,Chk1被ATM/ATR信號通路激活,從而誘導WEE1磷酸化而導致G2-M細胞周期停滯[17]。E2F1為RB1基因的表達產物,zeste同源物2(EZH2)作為E2F1的作用靶點,是免疫治療和化學治療均可誘導的表觀遺傳修飾劑。EZH2活性的抑制對于獲得免疫抑制表型,下調抗原呈遞過程(誘導免疫治療抗性)以及通過抑制Schlafen家族成員11(SLFN11)的負調節劑來增強化療抵抗性是必需的[6]
最近,Skoulidis等[21]證明,攜帶LKB1基因突變的KRAS突變型肺腺癌與較低的無進展生存率(PFS)和應用PD-1治療后較低的OS相關,這提示LKB1在這類藥物的原發性耐藥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時,這些結果表明,需要一種具有預測性的生物標記物,以便更好地在治療中使用這類藥物。
2 腫瘤免疫微環境在SCLC中的作用
近期的大量證據表明,腫瘤免疫微環境在腫瘤發生和發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組織學相同的腫瘤中,腫瘤免疫微環境的組成也會隨著腫瘤的進展而發生變化,它是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腫瘤特征和預后的決定性因素之一[22]。而SCLC與其他類型肺癌不同的是,SCLC具有強大的免疫抑制功能,且腫瘤免疫微環境中存在多種免疫細胞浸潤,如調節性T細胞、CD45+T細胞等,這些細胞種類和數量與患者的預后相關,也在SCLC的生長和轉移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作用[3]。
一項關于SCLC細胞與其腫瘤免疫微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早期研究闡明了SCLC腫瘤細胞抑制活化的CD4+T細胞的機制[23]。這種抑制活性不需要直接的細胞間接觸,而是由腫瘤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IL-15)介導的,它可以誘導淋巴細胞向樹突狀免疫表型(FOXP3+CD4+T細胞)分化。另一項研究分析了SCLC患者活檢組織中FOXP3+的浸潤情況,發現FOXP3+的比例是這些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預測因素[23]。在一項評估CD45+免疫細胞預測預后的價值的研究中,SCLC-腫瘤免疫微環境的組織學評估是重中之重。CD45+浸潤的程度與更長的OS相關,且不受臨床參數的影響[24]。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腫瘤免疫微環境能夠調節PD-1/PD-L1通路,從而幫助癌細胞逃避免疫監視[25]。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早期進行手術治療的ED-SCLC和LD-SCLC患者的CD8+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s)與PD-L1表達量之間存在相關性,而FOXP3+浸潤與PD-L1陽性的腫瘤浸潤T細胞呈正相關[26]。此外,FOXP3+TILs的高度浸潤是早期疾病的特征,與LD-SCLC患者的良好預后相關,這為TILs的T調節亞群在惡性腫瘤中具有爭議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線索[26-28]。
3 SCLC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反應的預測性生物標記物
目前,已經有一些尋找潛在的反應性預測標記的試驗或相關研究。PD-L1在腫瘤細胞中的表達是目前研究最深入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生物標記物。除此之外,腫瘤突變負荷,微衛星不穩定性,腫瘤微環境,外周血和微生物組等也有著巨大的潛力[29]。
近期的Keynote-158 Ⅱ期研究顯示,PD-L1在約40%的SCLC中可以檢測到,且能預測pembrolizumab的治療活性[30]。在Keynote 158的SCLC隊列中進行的探索性分析顯示了PD-L1綜合評分的潛力,即將PD-L1陽性細胞(包括腫瘤細胞、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占腫瘤細胞總數的比率作為評分來預測免疫治療的療效[31]。PD-L1評分能夠確定接受pembrolizumab治療的ED-SCLC患者中,ORR、1年PFS和1年OS較好的患者亞群。
然而,在Checkmate 032中腫瘤PD-L1的表達情況不能預測SCLC患者的免疫治療療效[32]。鑒于這一發現,研究者對樣本進行了進一步分析:進行了全外顯子組測序,并將腫瘤突變負荷定義為非同義體細胞突變的總數[33]。具有更高腫瘤突變負荷(定義為高于研究人群突變分布的上1/3)的患者從治療中獲得了更好的治療效果,尤其是進行聯合用藥治療時。因此,腫瘤突變負荷成為了免疫治療中具有較大潛力的生物標志物之一[34]。然而,由于成本、檢測標準、基因突變和水平差異等問題,腫瘤突變負荷作為預測性生物標志物還存在很多缺陷,其中復雜的機制和關聯也需要研究者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35]。
在之前的研究中,基于組織的腫瘤突變負荷評估的血液替代物已被證明是阿特珠單抗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療效的潛在預測標志物[36]。與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不同的是,使用阿特珠單抗聯合卡鉑和依托泊苷治療的SCLC患者在OS和PFS方面顯示出更好的治療效果,且與血液腫瘤突變負荷無關[31]。
除此之外,一項早期的國內回顧性分析顯示,肺癌細胞中若存在MHC-Ⅰ下調則提示患者的預后不良;且基質中CD8+細胞的數量與患者的預后相關。這些研究可能提示了患者MHC-I分子高表達以及腫瘤免疫微環境中較高含量的CD8+T細胞可作為潛在的患者預后良好的預測性生物標志物[37]。
SCLC的臨床治療是腫瘤科醫生面臨的一大挑戰,而根據SCLC的分子生物學特征,免疫治療展現出巨大的魅力和堅實的生物學基礎。在實際研究中,對于使用PD-L1的表達情況來預測療效,不同的研究團隊提出了不同的評價方法。以SCLC的耐藥性和侵襲性為基礎的分子機制研究有助于進一步了解其免疫耐受機制,有助于制定新的聯合治療策略,提高免疫治療的臨床效果。在未來的研究中,除了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化療和免疫治療相結合外,還需要探索新的治療方法,特別是能干預SCLC生長和化療耐藥的分子途徑的治療方案,以便改善SCLC患者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