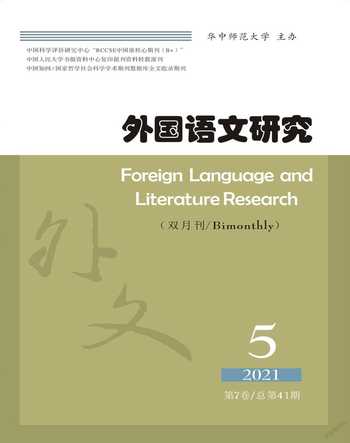“文學空間研究”三人談
方英 劉英 羅伯特?塔利
內容摘要:本文是對美國文學空間研究領軍學者羅伯特·塔利的訪談,也是關于“文學空間研究”的一次對話(2019年11月,寧波大學)。塔利認為,“文學空間研究”概念涵蓋面很廣,可用于指稱任何關于聚焦空間、地方和繪圖的研究,如地理批評、地理詩學、空間人文研究等。但“文學空間研究”不應被泛化,也不應成為一個標簽。文學空間研究首先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其次,(文學)空間性是此類研究的核心。塔利還就地理批評、空間批評、文學地理學、處所意識等概念做了仔細辨析,并贊同應當區(qū)分“空間”與“地理”、“spatial”與“geo-”。關于文學空間研究的新趨勢,塔利認為以下領域值得關注:數(shù)字人文和空間人文的結合,女性主義地理批評,批判性地域主義,類型小說,流動性研究等。
關鍵詞:文學空間研究;空間性;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處所意識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文學空間批評研究”(17BZW057)。
作者簡介:方英,浙江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敘事學研究、文學空間批評研究。劉英,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研究、文學地理研究。羅伯特·塔利,德克薩斯州立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EH)杰出人文教授,主要從事文學空間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研究、文化批評研究。
Title: A Dialogue on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T. Tally Jr.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T. Tally Jr., a leading scholar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also a dialogue about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at Ningbo University in November, 2019). Tally claims that the concept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can broadly encompass almost any approach to the text that focuses attention on space, place, and mapping, such as geocriticism, geopoetics, the spatial humanities, etc. However, this concept should not be over-generalized or deemed as a label. The core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which are first of all a sub-field of literature, is (literary) spatiality. Tally also explains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some similar and relevant concepts, such as geocriticism, spatial criticism, literary geography, and topophrenia, as well as distinguishes “space” from “geography”, “spatial” from “geo-.” With respect to the new trend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Tally observes that the following deserve much attention: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spatial humanities, feminist geography, critical regionalism, genre fiction, mobility study, etc.
Key words: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spatiality; literary geography; geocriticism; topophrenia
Authors: Fang Ying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er area of academic specialty includes narratology and spati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ttbetty@126.com. Liu Y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geography. Robert T. Tally Jr.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Texas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78666, USA). He is also NEH Distinguished Teaching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方英(以下簡稱“方”):塔利教授,您好!感謝您接受這次訪談。很榮幸有機會就“文學空間研究”(spatial literary studies)這個話題與您展開討論。我閱讀了您的許多文章和著作,以及幾篇關于您的訪談,了解到“文學空間研究”這個概念最初是2014年提出的,當年麥克米倫出版社推出了“地理批評與文學空間研究”(Geocriticism and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系列叢書。
羅伯特·塔利(以下簡稱“塔利”):是的。我擔任這個系列的主編。這個系列至今已出版三十多卷,包括專著和論文集。當然,我對這個概念的構思更早,大概是從2013年開始的。由于我翻譯了韋斯特法爾的《地理批評》(Geocriticism: 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2011),并主編了《地理批評探索》(Geocritical Explorations: Space, Place, and Mapping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2011),這兩本書都由麥克米倫出版社出版,因此,出版社希望我牽頭組織一個名為“地理批評”的系列叢書。但我認為“地理批評”這個術語不夠寬泛,不足以涵蓋更多與空間、地方、繪圖、空間性相關的研究,因此我提出將這個系列命名為“地理批評與文學空間研究”。這個名稱顯然更具囊括性,也的確更受作者和讀者的歡迎。但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無論是使用“地理批評”,還是“文學空間研究”,我都沒有將其當作一個學科(或子學科),而是將“geo”當作描述性前綴,將“spatial”當作形容詞使用,以標明怎樣的書可以在這個系列出版。我的出版構想得到了認可,因此2014年出版了這個系列的第一本書(Emily Johansen, Cosmopolitanism and Place)。
方:從這個系列的名稱來看,“地理批評”和“文學空間研究”似乎是相互平行的兩個研究領域。但您在后來的一些文章中似乎主張后者可以涵蓋前者。是這樣嗎?
塔利:是的。嚴格而言,“文學空間研究”涵蓋面更廣,可用于指稱任何關于聚焦空間、地方和繪圖的研究,如地理批評(geocriticism)、地理詩學(geopoetics)、空間人文研究(spatial humanities),或其他類似研究,不管那些研究冠以怎樣的標簽或高舉怎樣的旗幟。我在《勞特里奇文學與空間手冊》(Routledge Handbook of Literature and Space, 2017)的前言(“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literary studies”)中曾簡要論述這個問題。
方:能否更詳細地談一談何為“文學空間研究”?尤其是這種研究與其他類型的文學研究有何區(qū)別?
塔利:我在自己的寫作中使用文學空間研究這個概念,部分原因是我想要一個涵蓋面較廣的術語,可包含處理空間、地方、繪圖和空間關系的各種文學方法。很明顯,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常常會引用地理學著述、政治理論或社會理論家的觀點。我的理論基礎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它本身就是跨學科的,能覆蓋很多領域。因此,我認為“文學空間研究”可包括“文學地理學”(literary geography)等與空間、地方、地理等相關的研究領域。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文學地理學是一個更成熟的領域,或者說某種交叉學科。但文學空間研究是一個更寬泛的術語,它包括景觀和建筑;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包括文本空間。例如,詩人們經(jīng)常談論書頁上文字的空間。文學空間批評家可能會把重點放在那些與地理關系不大、或毫不相關的事情上。但我真沒有想到“文學空間研究”會成為一個像標簽一樣的關鍵術語。我其實只是把“spatial”當作形容詞來搭配“l(fā)iterary studies”。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我非常希望文學空間研究這個詞對不同類型的作品和各種研究進路保持相當開放的態(tài)度,但不希望它成為一個專業(yè)術語。我更傾向于將其定義為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而非嚴格意義上的跨學科工程,盡管有些人會在他們的著作中跨越學科界限或采取跨學科的方法。
方:我贊同您的觀點,即不能過分泛化文學空間研究,也就是說,應當為這個研究領域設定一個大致的邊界。我認為,邊界和劃定邊界的標準都在于“(文學)空間性”。“這是各種相關概念、理論、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共同點,也是文學研究中各種空間、地方、地理、場所、地圖、空間組織、空間關系、空間結構和文學繪圖的共性”(方英,文學空間研究 68)。
塔利:我同意你的觀點。空間性的確是文學空間研究的核心。
方:剛才您提到了文學地理學,我注意到《文學地理學》(Literary Geographies)的編輯希拉·霍姆斯(Sheila Holmes)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學地理學”是地理學(而非文學)的一個子學科。雖然文學地理學也涉及文學作品,但更重要的是具有人文地理學的學科性質,其理論和實踐不僅屬于人文學科,而且屬于社會科學;文學地理學主要以地理學的方法閱讀或處理文學作品,而不是以文學批評為主要目的;因而不應將“文學地理學”歸入“文學空間研究”的旗下。①您如何評價她的觀點?
塔利:我最近發(fā)表了一篇名為“文學空間研究與文學地理學?”(“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VS Literary Geography?”, 2019)的文章,就是對霍姆斯那篇文章的回應,以及對這兩個概念或研究領域(即“文學空間研究”和“文學地理學”)關系的詳細討論。從霍姆斯的文章來看,這兩者似乎存在沖突。實則不然。我想再解釋一下我對文學空間研究的界定。在我看來,文學空間研究盡管具有與生俱來的跨學科特色,但首先應屬于文學研究,應當面向文學。也就是說,文學空間研究的邊界在于“文學研究”本身,焦點是空間、地方、繪圖,或者,你說的(文學)空間性。正如霍姆斯所說,我對文學空間研究這個術語的使用太寬泛了,因為我把文學地理學放在從屬于它的位置。霍姆斯認為文學地理學是真正的交叉學科:一半是文學,一半是地理,或者換一種說法,一半屬于人文,一半屬于科學。她甚至提到,他們通常會將一篇需要同行評議的文章發(fā)送給兩位學者,一位是地理學家,一位是文學學者。因此,如果廣義而言,文學空間研究可以涵蓋文學地理學——正如我在《勞特里奇文學與空間手冊》和《教授空間、地方與文學》的前言中所述——那么嚴格來說,它至少可以包括文學地理學這個子學科中聚焦文學研究的部分。
方:我持相似觀點。我認為“空間”概念比“地理”概念更寬泛。從構詞法來看,“geo-”這個前綴決定了地理學主要是關于“地”的,而“空間”概念顯然可以包含地理空間。空間可大可小(其尺度的變化既可大于地球,又可是微觀的容器),可抽象可具體,可真實可虛幻,可包含也可完全脫離“地”這個范疇。有許多空間都不可能以“地理”替代,如賽博空間,身體空間,心理空間,親密空間等。地理首先是空間性的,而空間未必是地理的。因而,文學空間研究的范圍很廣,可以涉及:建筑,如福柯的全景敞視監(jiān)獄,家宅空間,商場等消費空間等;特定場所,如酒吧、臥室、火車、飛機等;較為抽象的空間類型,如邊界,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神圣空間”,福柯的“異托邦”,科特(Wesley A. Kort)的宇宙空間、社會空間、親密空間(cosmic space, social space, intimate space),德勒茲的光滑空間、條紋空間(smooth space, striated space)等;社會空間結構,如沃勒斯坦的中心與邊緣(the core and the periphery),詹姆遜的后現(xiàn)代空間;太空;乃至空間實踐與經(jīng)驗,如游蕩者的漫步,邊界建構與跨越,空間中的流動,等等。這些空間不是“地理”、“地理批評”或“文學地理學”可以完全涵蓋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文學空間研究的確可以包含文學地理學。
塔利:的確,空間與地理具有一些差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小說的背景與地理位置的關系一般不大,它更多是與小說中的地點類型或空間排列存在關聯(lián)。小說里的空間和地方既可以指人物活動的自然環(huán)境和空間布局,也可以指小說中人物對各空間或地方產生的感覺、思想和看法。也就是說,我們往往討論的是文學中的空間問題,如空間布局、空間元素、空間知覺、空間體驗等;而非純粹的地理問題。文學作品中的空間并不僅限于物質性的或政治性的地理,而是包含更豐富的空間元素,如建筑、室內設計、城市規(guī)劃、空間組織等;而且還應包含人對空間的情感,比如,對“家”的情感反應與對純粹的公寓、房子、住所的地理位置的情感反應頗為不同。②
方:空間與地理的差異讓我想到了文學空間研究的定義和邊界問題。在您關于“文學空間研究”討論的基礎上,我曾先后兩次嘗試著界定這個概念。第一次是在《空間轉向與外國文學教學中地圖的使用》這篇文章中:“此研究借鑒哲學社科領域的各種空間理論、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成果與方法,研究文學世界中與空間、地方、地理等相關的現(xiàn)象;或以空間性概念為切入點,探究在空間視角下的作品主題、人物活動、權力關系、意識形態(tài)等問題;以及文化批評中對空間性問題的研究”(方英,空間轉向 107)。后來我意識到這個界定還不夠完善,因此在《文學空間研究》一文中指出,文學空間研究“可囊括圍繞(文學)空間性開展的各種研究,因而與西方的文學地理學、地理詩學、空間詩學、人文空間研究、制圖學、環(huán)境美學等具有不同程度的重合與交集,也應包括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開拓與貢獻,如文學地理學、空間敘事、空間美學、生態(tài)批評、城市研究等領域的相關探索”(方英,文學空間研究 69)。
塔利:你的定義非常好。但我本人始終盡量避免給這個術語(以及其他術語,比如“地理批評”)下定義,因為我希望這些研究領域或方法能始終向各種不同的方法、文本和思想敞開,能不斷容納并吸收新元素。你剛才特別提到文學空間研究“應包括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開拓與貢獻”,這一點我特別贊同,我也特別希望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有更多了解。你能簡要介紹中國的文學空間研究現(xiàn)狀嗎?
方:非常樂意。我的博士論文《小說空間敘事論》(2014)研究的就是空間敘事問題。從那時起我就對西方的空間理論和文學空間批評特別感興趣,并開始關注國內的空間批評研究,或者說,文學空間研究。就我梳理的資料來看,自從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越來越關注空間問題,文學空間研究呈現(xiàn)上升趨勢,并逐漸成為人文學科的研究熱點之一。從研究的領域來看,中國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關于西方相關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引介、梳理、研究與本土化。比如,與文學研究相關的空間理論,如關于列斐伏爾、索亞、哈維、福柯、詹姆遜、段義孚等人的相關理論的譯介和研究;關于文學與地理的交叉領域,尤其是對文化地理學、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的譯介和研究;借鑒西方相關理論對特定文學現(xiàn)象(如流動性問題)、特定文類(如旅行敘事)、特定作家(如莎士比亞、劉易斯·辛克萊、魯迅等)或作品(如《變形記》)的研究。第二,對中國理論和批評話語的探索與建構。主要涉及以下幾點:文學地理學話語建構與理論重構;關于空間敘事的研究;空間美學研究(包括環(huán)境美學和生態(tài)美學中相關的部分)。第三,中外合作與交流增多,比如中國學者與您、與韋斯特法爾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塔利:感謝你的介紹。我對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研究非常感興趣,希望有機會能有更多了解、交流與合作。而且,我也非常希望將中國學者的研究介紹到美國和整個西方學術界,比如,在麥克米倫出版社出版中國學者的英文著作,可以是英文寫作,也可以是翻譯版。另外,我也想編撰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論文集,如《中國的文學地理研究》或《文學空間研究在中國》。當然,這些想法的實現(xiàn),需要中國學者的參與。
方:非常好的想法。我本人非常期待這些變成現(xiàn)實,也愿意參與到您的工作中。
塔利:非常感謝!
方:我想談一談文學空間研究中的其他幾個概念。中國學術界有不少學者從事“文學地理學研究”,也有一些學者主張“空間批評研究”。近幾年,韋斯特法爾的“地理批評”也受到越來越多關注。請問,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文學研究界會使用“空間批評”這個術語嗎?此外,能否談一談“文學地理學”和“地理批評”之間的異同和關系?
塔利:我從“地理批評”這個術語開始吧。我的靈感來自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的地理哲學(geophilosophy)。德勒茲在與瓜塔利(Félix Guattari, 1930-1992)合著的《何為哲學?》(What is Philosophy?, 1994)中專辟一章討論“地理哲學”這個話題。早在地理哲學問世之初,就有一些學者使用了地理詩學(geopoetics)和地理歷史(geohistory)這兩個詞。所以我不敢說是我想出了一個很酷的新詞。我的意思是,類似的詞在不斷流傳。我相信在我之前(我是在研究生階段開始使用這個詞的)有人用過“地理批評”這個詞。由于多種個人原因,比如博士畢業(yè)后繼續(xù)攻讀法學博士學位,我有7年時間遠離了文學研究,直到2005年重返這個領域。我當時想,是不是還沒有人真正使用地理批評這個詞?然后我發(fā)現(xiàn)了一本更早的書,是韋斯特法爾編的《地理批評用戶指南》(La géocritique mode d'emploi, 2000),我發(fā)現(xiàn)作者在那本書中對“geocritic”(géocritique)這個詞的用法比我具體得多。我的“geocritic”指的是對空間問題感興趣的批評家,所指寬泛得多;他討論的是他以地理為中心(geo-centered)的項目。這個項目從一個特定的地方開始,然后收集關于這個地方的文學、文化方面的參考資料,可以是小說或詩歌,也可以是旅行手冊或城市規(guī)劃文件,可以是任何文學或非文學文本。韋斯特法爾主張,以地理為中心的方法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ego-centered)。也就是說,不要專注于某個特定作家與地方的關系,比如喬伊斯與都柏林,或者福克納和密西西比;而應當將“作家與地方研究”看作各種聚焦或凸顯空間的批評實踐的一種。他所感興趣的遠遠多于某一種批評方法。而對我來說,我的博士論文是關于麥爾維爾和他對世界體系的文學繪圖(literary cartography),所以我仍然樂意以自我為中心或以作者為中心(author-centered)。這是我與韋斯特法爾的區(qū)別之一。
下面談一談空間批評。空間批評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用的短語,而不是一個關鍵詞或術語,其中一個原因是它的涵義更廣,可適用于各種批評實踐。正如我們曾經(jīng)談到的,“空間的”比“地理的”(geo-)更寬泛。“geo-”指的是地球/大地及與之相關的各種聯(lián)想,地理批評主要是關于地理的;而空間批評還可涉及其他類型的空間關系。但我不想將空間批評當作一個關鍵詞,而是將其作為各種類型的聚焦空間的批評實踐中的一種。
廣義的文學地理學往往涉及很多東西。在某些情況下,有字面意義上的“繪制地圖”(mapping),比如拿出一張地圖,然后繪制某些事物的地圖。如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如果我們想看看達洛維夫人為了買花而出門后去了哪些地方,看看邦德街上發(fā)生了哪些事,我們可以拿出一幅倫敦地圖來查看。這當然是一種文學地理學。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和他在斯坦福文學研究所(Stanford Literary Lab)的團隊曾做過類似的研究。他1998年出版的《歐洲小說地圖集,1800-1900》(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就是以那樣的方式使用地圖和文本的。芭芭拉·皮亞蒂(Barbara Piatti)和她的瑞士團隊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制作歐洲文學地圖集。他們試圖用可視化軟件和繪圖軟件,繪制出關于歐洲文學的地圖。那是另一種文學地理學。在我看來,文學地理學的領域比圖表和地圖所顯示的豐富得多,也廣闊得多。許多非地理學背景的文學批評家對這一領域亦做出了不少貢獻。例如,文學地理學研究引用最多的例子之一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的《鄉(xiāng)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但威廉斯沒有引用任何地理學家的著作。在我看來,在地理學的旗幟下,可以開展極其多樣化的工作,而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其中有些研究呈現(xiàn)出不同維度。例如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非但沒有在全球化大潮中消失,反而正在經(jīng)歷一場復興,因為人們在全球化背景下或其他似乎破壞地域身份(regional identity)的事情中變得更加關注地域。如果說這與文學地理學不同,但仍然與這方面的一些工作有關。
方:感謝您對這幾個概念的仔細辨析。關于“地理批評”,您剛才主要談到自己的“geocriticism”,并談及您的概念與韋斯特法爾的“La Géocritique”之間的差異。我知道您非常了解韋斯特法爾的研究,而且發(fā)表了好幾篇關于他著作的書評和論文。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他的地理批評理論與實踐?
塔利:韋斯特法爾的《地理批評》一書提供了分析文學文本中不同空間實踐之間相互影響的理論和方法,強調了文學與現(xiàn)實世界之間的互動方式,并幫助我們通過虛構性理解“真實的”地方,又通過真實性理解虛構的地方。這本書(以及他的相關地理批評研究,如關于地中海的項目)最獨特的貢獻是“聚焦地理的”方法。我在《空間性》一書中解釋了地理批評方法的四條原則:堅持“多重聚焦”(multifocalization),即來自多種文類、文本和多個作家的多種觀察視角;擁抱“多重感知”(polysensoriality),包括視覺、氣味和聲音對空間的感知;擁有“地層學視野”(stratigraphic vision),將地方看作包含多層次意義;將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置于研究的首位。③地理批評方法不僅向讀者呈現(xiàn)了關于某個地方的各種文本,以及各種空間表征方式,而且塑造出相對無偏見的地方形象,這些形象盡管必然會不全面,但是是多元的地方形象。但這種方法也存在明顯的悖論和局限。首先是關于文本庫的問題:誰來決定應當選擇哪些文本作為“閱讀”一個地方的文獻?即便選擇是集體做出的,個體研究者各自的視角仍然隱含在關于這個地方的整體現(xiàn)象學中。實際上,主體這個問題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建立文本庫必定要有所選擇,這就必然存在某種程度的排斥和“審查”,以及不可避免的偏見。其次,空間變成可識別地方的方式受到各種互相沖突的力量和觀點的制約,但地理批評方法沒有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再者,韋斯特法爾雖然提出了“代表性門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就何時何地到達這一門檻達成共識,因而這個門檻并不能真正解決韋斯特法爾方法的困境。當然,韋斯特法爾本人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他在《地理批評》的姊妹篇《擬真世界》(Le Monde plausible: Espace, lieu, carte, 2011)中試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些問題。比如,為了克服此前各項研究中的指示性(referentiality)問題,這本書始終將文學中的和現(xiàn)實世界中的地方同時納入考慮,并堅持一種后結構主義立場,也是一種擁抱空間關系和社會關系之整體性的姿態(tài)。
方:謝謝您的介紹。這幾年中國對韋斯特法爾的譯介呈迅速升溫之勢,但還不夠深入。我相信您對韋斯特法爾的研究一定能為中國學術界提供許多借鑒和啟發(fā)。
劉英(以下簡稱劉):塔利教授,您好!最近幾年,我對文學空間研究、文學地理研究等問題也十分關注,有一些問題想與您交流。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與文化地理學相比,文學地理研究能做出怎樣的獨特貢獻和社會意義?
塔利:謝謝你的問題。首先,文化地理學也有很多需要回答的問題,因為我不確定一個文化地理學家是否能證明他所做的工作是必要的,是更有社會價值的。我并非對地理學家有所微詞。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假設一個領域是實用的,而另一個領域不是,這種假設已經(jīng)帶有偏向性,而且是不真實的。它顯示了對藝術和人文的偏見。實際上,對人文學科的偏見更甚:在美國,藝術還能獲得一些基金的資助,而人文學科很難拿到基金項目,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設立的基金。如果你想做藝術裝置,你可能會得到一筆資助;如果你想寫關于藝術裝置的文章,可能就得不到了。但我堅信,在當今,文學對于教育和增強想象力仍然是必要的。在此,我借用了加拿大文學理論家諾斯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話。他寫的一本書的標題為《教育的想象力》(The Educated Imagination, 1964),這本書最初是20世紀60年代初在CBC(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播出的一個系列節(jié)目。在這本書中,他向加拿大公眾解釋了為什么文學很重要,并在標題中給出了回答:文學能培養(yǎng)想象力。我們很難說文學比其他領域更好;但想象力很特別,其與理性或認知不同,是人類最直接受到文學藝術激發(fā)的思維能力。當然,科學與工程都有很大價值。我可不想讓詩人來設計橋梁,盡管我或許希望工程師在做設計之前先讀一些詩歌。
大多數(shù)文學研究學者不僅從事文學研究,而且還從事教學工作。因此,這關乎訓練學生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發(fā)現(xiàn)我們有一種傾向,認為教學與寫作、研究是完全分開的。我不贊同這個觀點。在我的學校里,我從來沒有教過一門空間批評的課程。我正在教的是一門關于烏托邦的課程。顯然,烏托邦具有空間維度;但同時,烏托邦文學是少有的具有政治使命感的文類。因此,即使我們(文學研究學者)所做的事情不具備明顯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但,這些意義是存在的。我想,這是文學研究學者對社會的一種貢獻吧。
劉:我贊同您的觀點。文學,以及藝術和哲學,具有無用之用,因而是大用。文學能培養(yǎng)人的想象力,尤其是道德想象力。剛才您闡述了文學的一般功能。那么,具體到空間研究,文學研究能做出什么獨特的貢獻呢?
塔利:如今,就連地理學家也將文學文本作為地理研究的對象和材料。因此,我打算回到訓練想象力這個觀點上來。我在幾篇關于奇幻(fantasy)的文章中談到了這一點。在我的第一本書(Melville, Mapping and Globalization: Literary Cartography in the American Baroque Writer, 2009),以及《空間性》的最后一章,我指出奇幻是有價值的,并反對批評家將奇幻歸為非嚴肅文學。奇幻可包括諷刺、烏托邦等,它們都具有某種實驗性。在一部奇幻作品中,我們讀到的不僅是不可能性,而且還把它當作真實來對待。奇幻是很好的思考方式。我認為奇幻思維也適用于文學,甚至現(xiàn)實主義文學。它有助于培養(yǎng)和增強想象力。
比如,當涉及到城市規(guī)劃或城市重建這樣的具體事情,需要想象一下如何規(guī)劃新社區(qū),或者進行某種城市重建項目,以及改造過去的貧民窟或諸如此類的東西。我認為文學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來處理這類事情,如描寫或表征社區(qū)和城市的不斷變化。許多寫過城市衰落的落魄人士都可以提供幫助。我想舉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拍攝的影片《唐人街》(Chinatown, 1974)為例。這部作品是關于土地使用規(guī)劃、特別是水使用規(guī)劃的。杰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飾演的私人偵探試圖解開的謀殺謎團與這種奇怪的調水規(guī)劃有關。盡管偵探小說是一種古典或新古典主義體裁,但特定城市規(guī)劃的概念,包括城市管理者的官僚作風和限量供水計劃,卻成為故事情節(jié)的核心部分。在此,與文學作品和電影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某種類似城市規(guī)劃的東西。
劉:這個例子非常有趣,是研究城市敘事(city narrative)的典型案例,而且揭示了文學作品對城市規(guī)劃、城市發(fā)展等問題的表征,可以說是文學研究和文化地理都感興趣的文本。
塔利:是的。
劉:文學空間研究或文學地理研究在美國有哪些新的研究動態(tài)和趨勢?
塔利:我不想吹噓自己熟悉文學空間研究的所有領域,或者說掌握了所有相關的專業(yè)知識。不過,關于這個領域的新發(fā)展,我想到了科技的飛躍,特別是將地理信息系統(tǒng)(GIS)技術應用于人文或其他領域。因此,數(shù)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和空間人文(spatial humanities)的結合似乎是文學地理學家可探索的新領域和新課題。我還注意到,文學地理學家們正在將空間批評延伸到我們可能正在從事的其他領域。比如,某種女性主義地理批評揭示,現(xiàn)在我們正以一種以前不夠重視的方式認識到,空間的性別化(the gendering of spaces)以及空間中人的分布,是與父權制或性別歧視主義的社會關系相聯(lián)系的。我讀過一本20世紀60年代的小說,里面提到一種位于樓下的秘書空間,書中稱為“女孩池”(“the girl pool”),這是一個獨特的性別化空間,這個空間在高管和工程師(都是男性)工作的區(qū)域之外。我還想到這樣一些領域,其研究本身已具有強勁的發(fā)展勢頭,但現(xiàn)在更專注于空間關系或地圖繪制。此外,批判性地域主義或諸如此類的問題也值得研究。可能會不斷出現(xiàn)關于舊問題的新版本,或者說新解讀。我還想提一下類型小說(genre fiction)。文類本身已成為供讀者或作家探索的一種地圖或一種方式。因此,文類批評和地圖繪制讓我頗感興趣,特別是當我們以更寬泛的意義來看待什么是文學的時候。過去,人們可能會談及文學敘事④與漫畫的對比,或者與科幻小說等文類的不同。現(xiàn)在,不僅漫畫和科幻小說在大多數(shù)文學課堂上受到歡迎,就連我們可能認為是文學作家(literary writer)的人現(xiàn)在也在從事過去被稱為類型小說的創(chuàng)作。因此對類型小說的探索是我感興趣的領域之一。
劉:我最近在研究文學中的“流動性”(mobility)。請問,這方面的研究在西方是否已成為一種研究趨勢?
塔利:在英國和美國已經(jīng)有一些關于流動性的討論。安德魯·薩克(Andrew Thacker)的《穿過現(xiàn)代性:現(xiàn)代主義中的空間和地理》(Moving Through Modernity: Space and Geography in Modernism, 2003)一書不僅主要討論流動性,而且還聚焦于空間和地圖繪制。流動性研究似乎的確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我看來,有一種趨勢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將空間看作是動態(tài)的。人們看似處于固定的位置,或穩(wěn)定的狀態(tài),但其實都處在動態(tài)的流動系統(tǒng)中,比如我們身處諸如全球金融體系的資本流動等各種流動中。顯然,現(xiàn)在你錢包里的錢的價值很可能會受到地球上另一個地方的事物或事件的影響。
劉:談到流動性,我聯(lián)想到文學空間研究以及人文地理研究的一個關鍵概念,地方。段義孚(Yi-Fu Tuan)區(qū)分了空間與地方,將空間看作開放的,自由的,流動的;而將地方看作具體的,穩(wěn)定的,與一定的價值、情感和文化相關。⑤由此,我又想到您出版的新書《處所意識》(Topophren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2019),其標題中的“topophrenia”顯然與“地方”或“處所”相關。這本書,尤其是這個單詞,令不少學者頗為著迷,同時也有些困惑。大家都希望您能詳細解釋這個詞。比如,您是怎么想到要創(chuàng)造這樣一個術語的?為何使用“phrenia”?
塔利:我是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⑥中開始使用這個詞的。討論這個詞,要先提及文化地理學家段義孚的第一本書《戀地情結》(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這是一本關于文化/人文地理學的佳作。“Topophilia”意為“對地方的熱愛”。這本書只要談到“地方”(place),幾乎都是愉快的心情。他以一件軼事開篇:他在沙漠中看著太陽升起,懸掛在仙人掌上空。你可以感受到他對這個地方的喜悅。但我覺得“戀地情結”無法描述我關于地方的某些經(jīng)歷。幾年后,段義孚還寫了一本書,名為《恐懼的風景》(Landscapes of Fear, 1979),他在書中討論了各種程度的“地方恐懼癥”(topophobia),即對某個地方的恐懼。如果我們懂足夠多的拉丁語,并把它們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想出很多有趣的單詞;這正是我創(chuàng)造“topophrenia”的方式。我試圖尋找一個既非積極亦非消極的術語。我只是想表達,我們意識到空間并思考空間時,是怎樣的狀態(tài)。希臘語詞根“phrenia”表示“mindedness”;因此,“topophrenia”(處所意識)意味著“place-mindedness”(地方關切)。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總是處于某種空間意識或空間感中,我們總是意識到某個地方。這不一定是有意識地想到我們意識到自己“在其所”(in place),或“離其所”(displaced),或“不在其所”(out of place)。在我看來,我們的空間意識或我們的“空間關切狀態(tài)”(topophrenic condition)也可以是一種重要的關系。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圍繞在我們周圍,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
中國讀者可能對我的《空間性》更熟悉。這本書從但丁在樹林里迷路說起,并旋即與詹姆遜關于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章展開比較。詹姆遜的文章談到了大家在洛杉磯的博納旺蒂爾酒店(Bonaventure Hotel)迷路的經(jīng)歷,這是美國文學批評家內部的一個笑話。那是1982年,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年會在那家酒店舉行。許多人迷路,以至于無法按時參加小組討論。最后,所有小組討論都被取消了,因為人們要么上錯了電梯,要么因為其他什么原因而不知如何到達會議地點。詹姆遜在一次學術會議的發(fā)言中談到了這段空間經(jīng)驗。如其所言,我們還沒有進化出能夠在這樣的空間中為自我導航的知覺能力,這些建筑已經(jīng)超出了人類應對空間的能力。《空間性》一書的第一句話是“你在這里”(You Are Here.),這是地圖上的一個點。這樣的地圖為我們所在的空間提供了虛構的或圖像的表征,而令人放心的圓點“你在這里”或其他標記則提供了參照點。它提醒我,我是以怎樣的方式置身于這個更抽象、最廣闊的空間里,因為我知道這個點就是我。它提供了一個方向,幫助我們想象空間并在空間中為自己導航。這就是后來我在《處所意識》一書中所命名的人的空間狀況,即topophrenia。
論及處所意識,我的意思是,我們一直都在“繪圖”(mapping),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很明顯,如果我們試圖從此處到別處,我們必須繪制我們周圍環(huán)境的地圖;也就是說,必須確定自己與這里及周圍任何其他東西的位置關系。這顯然包括導航、方向和定向。即使我們在原地不動,試著估量我們所處的位置和其他正在發(fā)生之事的位置之間的關系,這也是一種繪圖。誠然,這里的“繪圖”具有隱喻性,但也是真實的。
劉:非常感謝您的詳細闡述。最后想請您談一談您的新書。我了解到您有一本書剛剛出版,對嗎?
塔利:是的。這本新書于2020年10月出版,書名為《文學空間研究:空間、地理和想象的跨學科方法》(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Space, Geography, and the Imagination)。這是一本論文合集,由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撰寫的19篇論文組成,聚焦于地理批評、文學地理學以及其他相關主題。
劉:非常期待閱讀這本書。
方:非常期待。并再次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注釋【Notes】
① See Sheila Hones, “Literary Geography and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Literary Geographies 4.2 (2018): 1-3.
② See Robert T. Tally Jr., “The Space of the Novel,”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Novel, Ed. Eric Bul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8): 156.
③See Robert T. Tally Jr., Spati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42.
④ 塔利此處沿用了喬納森·艾瑞克(Jonathan Arac)在《美國文學敘事的發(fā)生:1820-1860》(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Literary Narrative: 1820-1860, 2005)中對文學敘事(literary narrative)、國家敘事(national narrative)、地方敘事(local narrative)和個人敘事(personal narrative)的區(qū)分。
⑤See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3-7.
⑥Robert T. Tally Jr., “Topophrenia: The Place of the Subject,” Reconstruction 14.4 (2014). 這是塔利組稿的特刊“Spatial Literary Studies”中的一篇。
引用文獻【W(wǎng)orks Cited】
方英:空間轉向與外國文學教學中地圖的使用。《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3(2018):107-113。
[Fang, Ying. “Spatial Turn and Maps in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40.3 (2018): 107-113.]
——:文學空間研究:地方、繪圖、空間性。《美學與藝術評論》(第19輯)。朱立元主編。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56-72。
[---.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Place, Mapping, and Spatiality.”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Review (Vol. 19). Ed. Liyuan Zhu. Taiyuan: Shan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9. 56-72.]
責任編輯: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