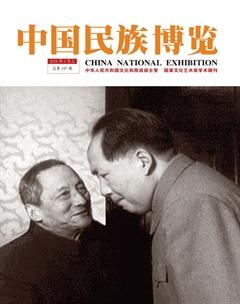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不能先利而后義
陳來

《孟子》的開篇是《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跟孟子說,老先生,你不遠千里而來,給我們帶來什么利益?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它的各級領導人都只是追求怎么對我自己有利,那么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他最后得出一個結論,說“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那就是說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它不能夠先利而后義 ;如果是先利后義,或者是后義而先利,只能導致這個社會的利害爭奪。所以從價值觀來講,必須要提倡、倡導先義而后利,這個國家才能夠有序生存。這個問題的討論,我們以前也叫義利之辨,義利之辨就是要辨別義利、辨明義利,把義和利的關系搞清楚。
今天,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我們看這個問題更清楚了,義利的問題,辨義利的問題,就是價值觀的問題。在古代,應該說我們很早就碰到價值觀建設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是有爭論的。在當時社會比較流行的主張,就是后義而先利。但是孟子跟流俗的主張不同,堅持一定要先義而后利。這個問題應該說涉及到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如何確立的問題。一個社會,每個人當然可以有他自己的價值觀,可是一個社會,特別是從治國理政的角度,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它主流的價值觀和基本的價值觀,必須正確確立。所以每個人可能奉行他自己的價值觀,但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定要確定一個主流的價值觀,而這個主流價值觀的核心就是辨明義利,要對義和利的關系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孟子的思想是很明確的,就是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必須反對唯利是圖,在義和利發生沖突的時候,必須要堅持以義為先,以義為上。孔子已經講了,“義以為上”。“義以為上”就是在一切事情上,如果義和利發生沖突的時候,應該是以義為上。當然孔子沒有把“義”和“利”明確地在價值觀上把它做一個對立,彰顯出處理好義和利的關系對文明社會、對國家的意義。孟子就發展了這一點。
荀子明確講“先義后利者榮”,荀子的這個主張應該說不僅是對孟子這個義利之辨的一種繼承,也是對孟子另一句話的發展,即孟子講過“仁則榮,不仁則辱”。榮辱觀也就是價值觀,我們十幾年前,也進行過榮辱觀的教育。特別是新世紀初我們講八榮八恥,這個八榮八恥也好、榮辱觀也好,都是價值觀的問題。今天我們特別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而且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立,要以中華優秀文化價值觀作為基礎和源泉。從這一點來看,我們說今年重新溫習孟子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孟子書的《告子下》中,孟子在和宋钘的談話里,又一次申明了這個道理。因為當時宋钘想用這個利字,即利益的利字,去勸說這秦、楚之王,來罷三軍之師,來避免戰爭,消弭戰爭。于是孟子當時對宋钘說這么一段話,他說如果你想勸說他們消弭戰爭,罷戰,但是卻用“利”這個字去說服他們,就會導致一種情況,就是“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這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終去仁義”,就是最終沒有仁義了,把它去掉了,于是人與人之間都是“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這個想法,我們看跟剛才講的《梁惠王》這個例子是一致的,但是有點區別。《梁惠王上》講的義利關系,他舉的例子,主要是講各級領導,比如說國王下面是大夫,大夫是士,士下面是庶人,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他舉的例子,我們可以說舉的是關于各級領導的例子,掌握各級權力的這些人的上下級的關系,是舉這樣的例子,來說明不能后義而先利。
但是我們看《告子下》舉的例子,當然也舉了人臣和君主的關系,但是他也舉了父子、兄弟,然后他的結論是“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這個“相接”它超出了政治上的上下級關系,變成更普遍的一種社會交往、社會關系。這樣一來,義和利不僅僅是上下級的政治關系要處理的價值觀,它廣泛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普遍相接,這個相接就是相處、打交道。所以義利關系不僅是政治秩序要處理的問題,也是所有人與人相處、打交道的基本原則。人與人相處、打交道,相接不能夠唯利是圖,只是為自己的利益來出發。而應該怎么樣呢?應該“懷仁義以相接”,這樣一來,從義利來講,他講的仁義也就是義利的義,義再進一步講就是仁義。所以從《告子下》所舉這個例子,我們會看出來,《梁惠王上》更注重從治國理政,從政治關系來強調義利關系正確解決的重要性。但是《告子下》這一段,他把義利問題更加社會化,更加普遍化,成為人與人相處的普遍原則,就是強調要正確處理義利關系,先義后利,不能夠后義先利。因此我們看這一段,就把關于義利價值觀的問題層次擴大了。第一個層次,屬于治國理政的層次。第二個層次,屬于社會文化的層次。第三個層次就是個人層次,孟子講人生在道德選擇的緊要關頭,怎么樣處理義利的問題?我們熟知的孟子講,義利關系也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形式。比如孟子曰 :“魚,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講的這個例子,他所講的就是人生的,是個人人生的道德選擇。
孟子所講的這個義利的價值觀包括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中國古代價值觀體系,它的核心是義利之辨,是辨別義利。中國古代有它完整的價值觀體系,它有一套核心價值。這個價值觀的體系,其核心應該說從孔子時代就開始了,孟子把它確立為義利之辨。而這個義利價值觀,它是講先義而后利。這個義利觀作為價值觀,它是貫通在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次。它的核心很清楚,強調義利問題 ;而這個義利觀作為價值觀,它既是治國理政的價值觀,又是社會關系的價值觀,也是人生道德選擇的價值觀。從這方面來看,中國古代文化對價值觀的處理,它對我們今天來講,還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今天我們講的二十四個字組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優秀文化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泉和基礎,說我們現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很多就是從古代文化提出來的。我覺得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不是從一個實然的角度來講的,不是說我們現在這二十四個字就已經很完善地吸取了古代優秀文化的價值觀體系,就已經把中華文化和我們現在的價值觀體系建設結合得很好。它是在一個比較理想的層面,即應然的層面,是講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該是以我們古代中華優秀文化為源泉、為基礎的。但是不等于說我們現在的二十四個字就已經很完整地把古代文化的優秀價值觀都體現出來了。總書記講的那六句話,即舉例來說明優秀傳統價值觀的講仁愛、重民本等六句話,就是在不同的場合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補充了很多的中國古代優秀價值觀的重要理念。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重看孟子的價值觀的現實意義,就是因為對我們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它提供了有利的啟示。講明了古代中華文化價值觀的核心是義利的問題,而且它能夠貫通到三個層次。這個我們再反思、再完善今天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時候,應該考慮。比方說講仁愛、重民本這六句話,就可以加一條,叫“辨義利”。不僅講仁愛、重民本,還要加一條辨義利。我覺得這個才能使我們現在這個價值觀更多更好地體現出古代文化優秀的價值觀。
我認為,關于義與利,孟子并不是認為二者完全不可得兼,相反,如果二者能夠得兼,就不必片面把那兩者對立起來。我想今天我們講的“一帶一路”,我個人覺得“一帶一路”就是一個二者可以得兼,就是義利雙行的這么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規劃。
我覺得可能有一種不自覺的相混,即把治國理政的價值觀建設和肯定市場經濟法則混而不分了。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回答也不同,不是肯定一個即要否定另一個。事實上,在社會各個不同領域有不同的運行法則,如市場經濟領域是利益法則,政治領域是正義法則,文化領域是創造法則,各有其合法性,不能相互替代。主流價值觀不是要取消或替代各個領域的原則,而是在更高的社會層面維系社會的穩定有序,提供更基本的人與人、人與社群、人與社會關系的普遍法則。一個市場經濟的從業人員必須依照市場經濟的法則活動,否則其經濟活動就會失敗。但利益法則只是適應市場經濟的法則,不能泛化為其他領域的主導法則,唯利是圖不能成為社會整體的法則。而治國理政關注的社會價值觀,它承認各個局部領域自己的法則的適用性,但它是從社會整體的團結有序和文明發展著眼的,這是有根本不同的。從治國理政著眼的社會價值觀建設,不會否認市場經濟有其法則,而是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警惕市場法則侵入家庭、學校、團體、社會,變成人與人關系的普遍法則。也可以說,正是由于市場經濟有一種力量力圖跨界而影響整個社會,所以更需要有一種力量來駕馭它、對沖其泛化的影響,實現對社會進行引導和約束。更不要說,利欲的追求本身要受到各種法律和規則的制約。
如何從治國理政的方面理解孟子的義利之辨,這里補充一個材料。《孟子荀卿列傳》是司馬遷做的簡單的傳記,但是司馬遷不僅為孟子做了傳記,他還在其中講了一段話,對孟子的思想提出了他自己的感想。太史公講 :“愚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嗟乎!利誠亂之始也。”說國家的亂根源在哪?利這個東西就是亂的根源,根源就是大家都求利,以求利為先。
太史公司馬遷對孟子《梁惠王上》的解讀,在思想方面的感想,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主要研究歷史上的治亂,一個歷史學家不僅僅是記述現象,還要總結歷史的規律和經驗。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國家治亂的經驗。他通過讀《孟子》,結合他自己的歷史知識,他得到結論是“利誠亂之始也”,認為孟子講的確實是對的,如果我們講治國理政,不能夠以利字當頭,把利字放在優先的地位。我想以司馬遷這樣一個大歷史學家的身份,以他對歷史的了解,應該來說他對孟子的《梁惠王上》的思想做了一個有力的見證,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值得借鑒與思考的。
孟子所闡明的儒家先義后利的價值觀,就對象而言,主要指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指向官員,而不是針對民眾。尤其是義利之辨所引申的公私之辨,主要針對的是承擔公共事務責任的官員。對于民眾,儒家始終強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 ,肯定民眾利欲需求的合理性。孟子的仁政王政思想正是以此為基礎,來滿足民眾的利欲需求的。所以在孟子思想中強調義利之辨和重視民欲民利是沒有對立的。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